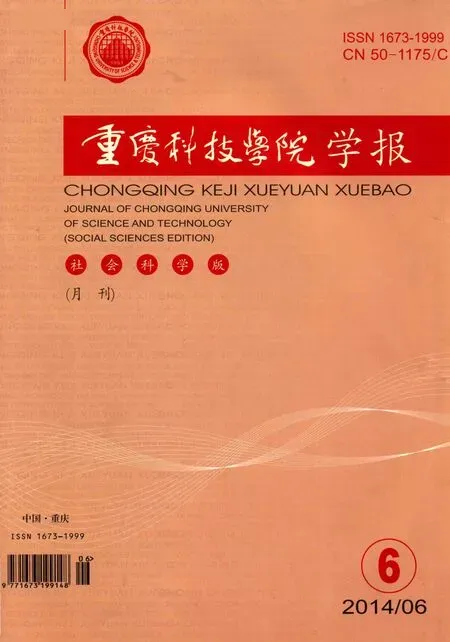奥古斯丁神正论的理路
2014-03-25龚宸
龚 宸
希腊时期,哲学家们专注于世界基质或真理真善的问题,而没有将世界主宰的“一”人格化时,神正论还没有被讨论的必要。而在部分哲学神秘化、宗教化的希腊时代,上帝的存在开始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伊壁鸠鲁十分尖锐地使用了二难推论来直击基督教哲学的神正论底线:上帝或者希望消除所有恶事而不能,或者他能而不愿意;或者,他既不愿意又不能;或者,他既愿意又能。如果上帝愿意而不能的话,他是软弱,这与上帝的品格不符;如果上帝能而不愿意的话,他是恶毒,这同样与自己的品格相冲突;如果上帝既不愿意又不能的话,他就既恶毒又软弱,因此就不是上帝;如果上帝既愿意又能,这唯一符合上帝,那么恶事到底从何而来?或者为什么不消除这些恶事?上帝既然以其全能、全善、全知造人,人的恶又如何而来?上帝又如何容许恶的存在?既然恶产生了,那么给予人以生命、指引着人类的上帝该不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上帝、人类、恶之间的博弈,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成为了维护教义、制定教规的教父们不可回避的。年轻时对恶的特殊体验以及摩门教的挑战,使神正论问题成为了教父哲学集大成者奥古斯丁的主要论辩范畴之一,也使这条理路在前人的积蓄与他本人的聪颖的思辨能力相结合的条件下,形成了理性的逻辑。
一、恶的问题:恶的含义与上帝的至善
神正论的首要任务是使恶与上帝泾渭分明。上帝与善是分不开的,上帝就是至善,因此,归根结底,处理上帝与恶的问题就是处理善与恶的问题。两者关系无非就是以下四种关系中的其中一种:善包含恶,恶包含善,善恶等同,或者善恶无关。而上帝既是全善又是全能的,不可能有超越他创造之手的存在,那么,恶与善等同或者恶包含于善之中。显然恶是不能等同于善的,否则无异于亵渎上帝。因此,在上帝存在并且至善的预设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为神与恶的关系辩解:恶不是非善,而是善的一种表现。这正是奥古斯丁的理论。奥古斯丁在恶的含义的讨论上,明智地将长期以来置于对立面的善与恶放在了单极语境下,通过存在论、等级论、属世与永恒等角度,提出了“缺乏论”一说。“缺乏论”即恶非不善,而是善的缺乏。
首先,从存在论角度看,纯然的恶或者无善的本体是不存在的,恶来自于虚无,因而就这个上帝创造的存在的世界,恶只有依附于善才可以成立。“若你这样问(善的转离——引者补),我只能回答说,我不知道。……凡是虚无,就不能被人知道。”[1]90奥古斯丁坚决地否定了恶从上帝而来的可能,而将其归之于虚无。显然,“我不知道”有因信仰的敬畏而禁言的言下之意。于是,他从量的逼近法,借助“朽坏”的过程趋近,在极限处来排除无善的情况。“若朽坏完全夺取它的善,它所存留的就不能朽坏,因为再没有善存留给朽坏夺取,以致能加以伤害,凡朽坏所不能伤害的,不能变成朽坏。……朽坏使之成为不朽坏。”[1]120“朽坏”可以看作“恶”的动态量变和“恶”不可缺少的属性,“朽坏”将“善”的量减少以换取“恶”的量,而如果“恶”的量可以全数代换“善”的量,那么“恶”就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力“朽坏”,也就失去了“恶”之为“恶”的依据,恶便不存在了。由此,物在奥古斯丁那里,为了存留最后一点善而被诠释为善恶混合成的存在,因存在而不失善,也就否认了恶独立于善之外。所谓恶的个体,实质是善的缺乏。
从存在论的角度去分析“恶”,已经借助了量的概念。在其他言论中,奥古斯丁进一步将量的差异扩大成空间维度的等级,从等级性将恶定义为低等的善。各种的恶成为善的低等,如私善。奥古斯丁没有说明什么是私善,但其中可以窥见,他已经将一些恶归类于善的低等状态中。“若意志弃离那公诸大家的不变的善,而归向一种私善,无论是在它以外或以下,它就犯了罪。……一旦它渴望知道别人的私事,它就是归向在它以外‘一旦它爱好肉体的快乐,它就归向在它以下的。”[1]88“罪”一词是“恶”的趋势的后果,“只是自由意志对其本性的抗拒而膨胀其自愿性,恶才能从存在论进入到生存论的层面上,即恶向罪发生转变。”[2]23“犯”这一动词暗示了恶的存在,是膨胀的自由意志连缀善与恶的触发点,在奥古斯丁那里具体表现为 “弃离”一种善而 “归向”另一种善——恶的产生不但离不开善的范畴,而且是善的降级。
其次,在时间的维度上,奥古斯丁也用类似的方法使恶归于善的统辖。“公诸大家的不变的善”[1]89蕴含了“不变”这一时间的尺度,“永恒之律”是服从善的人们所尊崇的,是一种完全隐秘的、更大的律法;与之相对的是“属世之律”是由人制定的法。“属世之律”都是来源于“永恒之律”,服从前者的人仍不能逃避后者。然而,“属世之律”是不完善的,它纵容着恶,“不惩罚那爱好这些东西的罪,而只惩罚那将这些东西从别人手中非法夺取的罪”;它也有合理性“确是贪着那好东西,所以这种贪念是无可指责的”[1]11。可见,“属世之律”的缺陷在于它着眼于那些已失去的非永在之物,从而产生了恶的可能。换言之,恶之罪不在于爱好本身,而在于爱好了短暂的对象,而善是爱好着“永恒之律”,只爱着上帝。“爱好”将两者置于时间的坐标上,恶是坐标的一个有限区间,善是超越整个坐标的无限时间区间,甚至是在时间之前就自由自在的存在。那么,在时间的维度上,恶即是善的时间上的有限时的变异,“邪恶是在于意志离弃不变的善,而归向可变的善”。
由此,奥古斯丁语境下的恶是善的缺乏,不是一个独立实体而是善的外延内的一种应受上帝惩罚的特殊情况。如此,全善的上帝没有创造恶,上帝施予的只是善,而恶是人类自身受到蒙蔽之时,善的缺失;上帝恩赐了善,而人类在善的范围内,远离了善的圆心——上帝,而屈从了边缘之善,较少地接受了上帝的光照,“恶”便应运而生。上帝则是正义。
二、自由意志的问题
“缺乏论”的推论中,奥古斯丁初步划清了上帝与恶的界限——恶作为善的缺乏而与上帝的至善并存。然而,“善的缺乏”仍缺少一个确切的来源,同样需要与上帝划清界限的来源。即便有了独立的 “缺乏”的来源,上帝为什么不以其全能阻绝缺乏的来源,上帝为什么不以其全知预言缺乏的来源,这些问题仍考验着上帝在责任上的正义性。“自由意志”是奥古斯丁解答这些问题的中心依托。
为了让自由意志为人类的恶的产生负责,奥古斯丁又一次诉诸于严密的理性思维。
(一)自由意志的责任
1.外部因素的排除
奥古斯丁选择从外至内的论证方向,首先阻断恶的生成的外来路径。奥古斯丁将外来之物对于人的选择的触动变通为“学来”这个动词。
“因为知识是借教育传授或激发的,除了由教育以外,没有人能学到什么”[1]4,教育凭借它的功用得到了善的定性,以作为奥古斯丁恶的封闭外部来源的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奥古斯丁的内在理路十分清晰:教育是善的;教育与学得是同一过程中的双向的动作,因而学得的是善的;恶区别于善,学得必是善的,因而恶不可学得。奥古斯丁还提供了反面论证,“假如恶是学到的,我们是要学到避免恶行,而不是学到作恶。因此作恶无非是违反教训。”[1]4正反两面的夹逼似乎使结论成为事实。但实质上,“学到避免恶行”即教育与学得的善的定性,在两面的陈述中,都被当作已证无误的真理性前提来使用,而回溯它由功用而推衍至性质的论证就更显得不那么可靠。
奥古斯丁没有止步不前,而顾及到教育叫人作恶的可能性,又求助于另一个概念“理解力”。理解力是优秀的东西,自然是善的,没有理解力不能学到,凡理解者为善,凡学习者就理解,因而学习者为善,因而恶是不可以学到的。当争论的焦点从教育转移到理解力,奥古斯丁的理性的勇气是十分难得的,但是理解力的“我想它自然是善的”[1]5比“教育是善的”可靠的理由,也许只能因这更贴近人的体验。
2.内在自由
对外在对恶的引导的否定不足以完全等价于对内在的完全自由的肯定,奥古斯丁有着敏锐的逻辑感,又从正面直接否定了一个人的意志能被迫向恶。
“既然那平等者或优越者因其正直而绝不会使一种有驾驭力和美德的心智作情欲的奴隶,而那较逊者又因其软弱而不能如此,那么如我们的论证所证明的,心智除了本身的意志和自由选择以外,再没有什么让它服从贪念了。”[1]26
恶来源于人对于易失去之物的贪恋而远离了上帝这一最高善,心灵是自由地作出了这一选择。心智从造物之中得知了上帝是至善的标准,却抛弃自己的本性,忘却了自己应从之正义的指引,不享受这些美善,而使自己被欲望扭曲到歧路上;它不去感恩它已得之指引与恩赐,反而在追逐上帝的自是永有中丢失了善的能力,背离了上帝。越专注于永远地获得外在的非于自己的事物,自凭己力,自以为是,越是远离真正的永恒、独一无二的至善。贪恋将人带至与贪恋的高处相反的深渊,坠入了恶的泥淖。
人的心灵就其自身,拥有无与伦比的智慧、理性和德行,处在最优越的地位。逼迫心灵臣服于贪欲,必须拥有更多的智慧、理性和德行,所以它们不会催逼着心灵向恶的,并且也没有出于这样地位的人的自身所有物;高位者因其高度而不愿从事,而低位者因其无能而不可从事,他们太虚弱无力了。又一次通过完整的分类全部可能的情况,然后逼近至唯一合理解释,奥古斯丁得出唯一的可能:自由意志完全自由的屈从于恶,没有其他帮凶。
自由意志没有外在来源,又没有内在非己的压迫者,因而自由意志的选择没有理由为自己申辩,自由意志出自于人自己的全然选择。
奥古斯丁未能说明“为何我们的意志趋向于恶”的问题,他将问题交给了信仰,而满足于他的解释的推论:人应该为自由意志犯下的罪负责。
(二)自由意志的意义
自由意志存在着使人远离上帝的可能性。如果说这种可能性不可能是全能全善的上帝的对人的设定上的一种疏忽,那么解释这种可能性在上帝的完美的标准中保留的意义就是比较重要的。在奥古斯丁看来,自由意志不会影响上帝的正义性,反而对人的正直生活意义重大。
自由意志对生的意义十分重大。自由意志的丧失会使上帝的创世失去创造性和丰富性,使人失去生的意义。奥古斯丁多次强调,自由意志对于生命力的重要性,一个会犯错的人好过不会犯错的石头灵魂,绝不会变得比有形之物还低。“所以灵魂总胜过身体,而有罪的灵魂,不管堕落到什么地步,也永不变成身体;它作灵魂的本性,永不完全止息,因此它永不停地胜过身体。”[1]105对于整个上帝所创的世界而言,无生命物、动物、人和天使等各个等级存在都是构成这个世界的和谐要素,不管他们定意犯罪与否,失去任何一个等级,既差异又和谐稳定的世界就不复存在,“若没有灵魂犯罪或不犯罪,以致全体的秩序无所变动,那么创造就缺少一种重要成分”[1]118。一个有差等的等级世界有助于体现上帝的慈爱与生命的丰富性。
自由意志对于正直的生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人缺少自由意志不能过正直的生活,这就是神给人自由意志的充分理由”[1]44。当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时,他是以这样一种意志去指引人类做出正确的选择,过正确的生活,而人滥用了这个恩赐。自由意志的重点在与选择而非意志;自由意志来源于上帝,选择在于人;善的可能来源于上帝,恶的选择出自于人。人的滥用、背离使人应该担负罪的代价。
人的滥用与背离看似与人的正直、上帝的正义相违背,实则并不矛盾。人的滥用源起于偷食禁果,根据奥古斯丁的理解,在那之前人既有犯罪的能力(posse peccary),也有不犯罪的能力(posse not peccary);在那之后人的意志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自由”,而被注定了犯罪的宿命。滥用的必然性不是上帝的设定,也不是上帝的纵容,而是上帝出于原罪的罚的需要。上帝的惩罚是一种匡正,通过罪的苦痛使人自己放弃自由意志的滥用。上帝造人充满了慈爱,不会因为人无知的偶然的失误放弃他们而重造,但出于改造他而将原罪的失误放大为人无可避免的犯罪的世俗的一生,让他们经受罪的苦痛以明白善与恶的界限,最终在末日审判之前通过最严厉的处罚涤除人的无知,使人在经受教育后获得重生。“假若人没有意志的自由选择,那么,怎能有赏善罚恶以维持公正的善产生出来呢? ”[1]44
总之,各种生命在有无自由意志、是否得当的使用自由意志等差异上,共同构成了如此丰富精彩的世界,体现了上帝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自由意志预留的人两个向度的可能性:从善的向度作为人的最终追求的目标而体现着上帝对人的眷恋;滥用的向度使人暴露其弱点,成为上帝在不加言说中昭示人们善恶的标准的依据,充当彰显上帝惩恶扬善的正义性的平台,从而使人在上帝的启示下正当的生活。
三、上帝的预知与上帝的惩罚
在自由意志为犯罪的过程负责时,上帝在过失之前预知的必然性与过失之后惩罚的正当性,仍待奥古斯丁以理性去捍卫。
伊阿丢斯提出了另一个令他困惑的命题,“上帝能预知一切未来之事,我们怎么会有犯罪的必然性。若有人说,某件事可能超乎上帝的预知而发生,他便是企图废掉上帝的预知,而这乃是极其疯狂亵渎的”[1]95。如果上帝的全能不能否认,他的预知力也许就可决定自由意志,而不得不为自由意志犯下的恶行负上责任;如果人的自由意志真的可以自由地喜恶从善,又至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约束力于何地?两者纠缠在一起,让人无所适从。
奥古斯丁却决然否定了两者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上帝预知那些人凭自己的意志要犯罪,他却并不强迫人犯罪。”[1]102“上帝预知他自己的行动,但他不是他预知的一切行动的原因。”[1]102一方面,上帝预知着行动的发生,预知着人们对于意志的能力,自由意志的能力非但不会因此而失去,反而因此而更确实地拥有这能力。预知不是预定,预知也不是逼迫或操纵。另一方面,奥古斯丁肯定自由意志不会被预知抹杀,但强烈反对假设上帝安排是微弱的或不公正的来为自己开罪。奥古斯丁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守两端:为了上帝的正义,给予意志自主的权利;为了上帝的权威,限制意志自主的权威。虽然,权威与自由的权衡在奥古斯丁的努力下可以达到,但这点往往让奥古斯丁诉诸激愤的信仰的宣言,“应当纠正的是你,而不是你所妄加谴责的”。
信仰优先的原则在奥古斯丁论及上帝惩罚的正义性时,几乎成为了唯一理据。首先,罪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是自发的、可责难的,因而惩罚是公正的。“它们自甘处于那种景况中,不热心寻求和学习,也不由谦卑、认罪、祈祷来得到真理和力量,所以上帝要将公义的刑罚降给它们。”[1]135其次,“灵魂为本身的罪恶受惩罚,乃是由于创造主正直、公正、不动摇、不改变的尊严和本体”,信仰者不能说上帝不应当将自由意志给了人,因为它是给了人一切美好的主给的赐予,并且必须甘心受惩戒,努力借着上帝的光照亮虚无的无知,感激上帝没有剥夺向他求告的机会,接受他慷慨而仁慈的医治。奥古斯丁晚年更是否认自由意识能够发动善良意念的能力,上帝给予的力量是行出善的唯一原因。
综上,在奥古斯丁看来,自由意志是上帝预知统摄下的自由而要自己为自己负责,不可归罪于上帝;上帝的惩罚是上帝的恩典,要因上帝的公正而赞美他。
四、结语
在奥古斯丁关于神正论的理论体系中,我们看到,他承袭了部分希腊哲学的思辨思想,用具有逻辑条理的思路,试图从理性上捍卫上帝的正义性。他立足多个维度将恶界定为善的缺乏,从而在性质上保全了上帝至善的形象;将恶的可能性转嫁于人的自由意志的错误选择,从而保证了上帝与恶的来源无关;用上帝的预知的必然性统辖自由意志的随机性,以达成在上帝至高地位的巩固下,两者的统一和谐;视上帝的惩罚为上帝的爱的表现,勉励人们审视自身、进行忏悔而谦卑地信仰上帝。
预定论和神恩论是奥古斯丁展开辩证思考的原则,他的理性被局限在对上帝的信仰恩典范围内,他的论述是在上帝是善的隐形预设下的封闭式论证。然而,正视理性恶作用,尝试用理性去解决信仰危机,在中世纪是较早的勇敢尝试。奥古斯丁的学说也启示着我们,不但理性之于信仰是极好的工具,而且信仰也有着理性所不能替代的治愈和教化的效果,在面临当下理性的偏执带来的危机时,我们也许可以衡量一下:两者到底是必有优劣之分,或者只是对于诸多问题的效果不可一概而论的两种不同解决方案而已。此外,基督教哲学中的一些伦理信条对于当代的道德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
[1]奥古斯丁.恩典与自由[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琚亮.恶与罪的生成辩证:论奥古斯丁恶的观念[D].杭州:浙江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