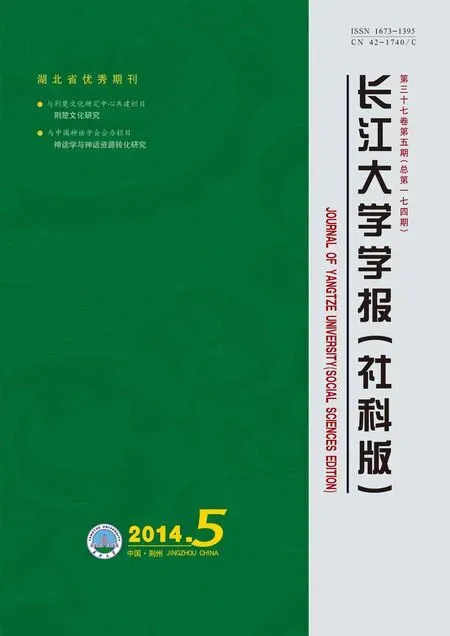社会道德失范成因探源
2014-03-25丰帅冯文全
丰帅 冯文全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2014年央视春晚小品《扶不扶》让观众捧腹大笑,但这个节目带给观众更多的却是发人深省的思考,尤其是那句台词:“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要是倒了就扶不起来了!”字字直击人心。这个小品的创作绝非偶然,扶人被讹事件,前有彭宇案,后有许云鹤案,都是促成这个节目的真实动因。这些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在心里拉起了一道警戒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等,再次成为人们心理的引航员和保护伞。除了扶人被讹事件外,其他有伤道德风化的社会性事件还有很多。可以说,当下社会道德现状已经到了一个不容乐观的境地。
面对当前的情形,许多人经常处在两难选择的状态,并陷入迷茫无措之中。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人正处在道德迷惘的痛苦之中,人们高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似乎谁都做不出肯定的答复。”[1](P151)不良社会风气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这里面既有风俗文化中的隐性流毒在作怪,也有时代发展中的显性疫变在兴风。
一、狭隘的幸福标准和唯物质主义
人是欲望的集合,人类的追求就是不停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荀子说“人生而有欲”(《荀子·礼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荀子·性恶》)。其实人类就是在欲望的支配下不停地发展壮大的,所以欲望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前进动力,是人类一切行动的力量来源。有学者说:“欲望既是一切行为的原动力又是一切行为的目的”[2](P215~216),“趋乐避苦确实是每个人的人生目的,是每个人恒久的、主要的行为目的,但是并不是一切行为的目的。人生目的不同于一切行为的目的,人生目的都是为了行为和快乐,而一切行为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总归来说是满足欲望”[2](P141~142)。所以作为高级个体的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欲望而展开的。而人类欲望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霍尔巴赫认为:“人在本质上就是自己爱自己,愿意保存自己,设法使自己生存、幸福。”[3](P273)洛克说:“追求幸福是人生最伟大的欲望。”[4](P273)康德也说:“一切人对自身幸福的爱好都是最大最深的。”[5]由上可知,人最终的追求就是为了满足幸福的欲望。那到底什么是幸福?
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最高的善,并且把它理解为生活得好或者做得好。”[6](P10)在他看来,“善的事物已被分成三类:一些被称为外在的善(财富、高贵出身、友爱、好运),另外的被称为灵魂的善(节制、勇敢、公正、明智)和身体的善(健康、强壮、健美、敏锐)”[6](P21)。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所有的善,都是我们所欲求的,但是就当下现实来看,“外在的善”和“身体的善”成为了人们最热衷的追求对象,并且这两项的部分事物被人们等同于幸福,而与德性直接相关的“灵魂的善”几乎被人所遗忘。其部分原因是,物质是一切生命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一种初级需求,而满足这种需求,能极大地带给人们强烈的心理刺激和满足感。马斯洛就发现:需要越低级,其心理体验越强烈,需要越高级,其心理体验越淡泊。[7](P113)所以人们更倾向于体验物质带来的快乐,并认为这才是幸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如果从人们所过的生活来判断他们对于善或幸福的意见,那么多数人或者一般人是把快乐等同于善或幸福,所以他们过享乐的生活。”[6](P11)为此,人们忙着追名逐利,忙着吃喝玩乐,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读书和反思,给空虚的精神世界补充一些营养。此外,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唯物质主义,而唯物质主义的盛行又导致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普遍陷落,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愈发促使人们疯狂地攫取物质利益,由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物欲的无限度膨胀,致使物质享乐成了人们首要的追求目的,思想的病变致使幸福标准被扭曲,这一切又造成真正的幸福与现实生活的逐渐远离。在这种集体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人们一切向钱看齐,最终导致其人生价值观的扭曲。
二、社会至上论和价值取向冲突
人是社会动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社会性又决定了人对人的重要性,霍尔巴赫对此有过精辟论述。他说:“人乃是自然界中对人最有益的东西”,“在所有东西中间,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8]尤其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异常紧密,人和社会群体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人的成长发展,所以适者生存法则被越叫越响,而且逐渐有被泛化和滥用的倾向。用辩证的眼光来看人们对适者生存法则的理解,其中虽不乏正确认识,但也含有很多消极因素,如果过分夸大其作用的话,那么就变成了对社会的迎合和屈从,这样就从社会适应论变成了社会至上论。恰恰是这种思想态度的转变,为社会上种种不良风气的滋生,提供了心理温床。当下道德失范事件的频发,就是社会至上论悄无声息间带来的不良后果。这种影响来去缓慢,且危害巨大。尼采说:“他人和社会是自我发生异化的根源。”[9](P166)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他一生都在不停地接受异化,虽然适应社会是必要的,但是在无意识之间,很多人就慢慢地变成了社会不良现象的帮凶。这就是异化后从众、跟风心理造成的恶果。正是对社会至上论和从众、跟风的集体怠惰,才让这个社会看起来如此冷漠混乱。同时,因为社会至上论的效应,社会上的唯现实主义、唯实用主义得以盛行,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人事的评判标准,“只要有所谓的‘知识’,不管你有没有德性;只要你有技能,不管你是否全面发展”[10](P10)。除了对人自身硬件条件的要求外,还有许多潜规则,而有些潜规则迫使人们突破道德底线,如此一来,道德信条就成了人们的牵绊和负累。有的人完全抛弃道德信条,有的人挣扎在道德信条的边缘。迫于生活的压力和现实的残酷,越来越多的人的道德在沦陷。
社会风气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家庭教育的基调,往往以社会风气作为导向,而现在的利己教育则是当下家庭教育的取向。对学校,家长更看重的是其可以帮助学生获得实用的生存技能。家长让孩子入学读书,绝大多数都是以“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目的的。至于学校德育,家庭教育则会对其自动过滤,即有利于自己孩子生存于社会的则留,不利于生存的则去,所以有学者说:“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带有实用主义性质的教育,它带有相当程度的强制性。”[11](P212)由于父母和孩子的特殊关系,学校的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的过滤和围攻下,几乎全军覆灭。在家庭实用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国家经济中心主义还有学校自身生存利益的复杂背景下,学校德育和受教育者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和困惑的境地:德育相关课程在国家规定里是必修课程,但家庭教育的过滤作用和社会教育的染缸效应,几乎让学校德育名存实亡;而受教育者更是迷茫失措,不知道到底哪种取向正确,而这种状况往往会使他们以实用主义作为其行为的判断标准。如果任由这种现象蔓延发展下去,那么就意味着民族危机的开始。
三、功利的智育和理想的德育
人终生的奋斗,几乎都是为自身谋取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P8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经济发展的狂潮中,人们的视线被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牢牢吸引,加之其他原因,致使唯经济主义诞生。“所谓的唯经济主义是指视经济为决定人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将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道德等等精神活动被排除在人们的视域之外。”[1](P142)学校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的教育目的的制定和人才培养方式以及教育内容的设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以及当下对社会主义接班人唯实用的评估标准指导下,学校教育也变得严重功利化。“当今,在我国,唯经济主义盛行,从而催生了严重的功利主义教育。追求大学升学率成了中学教育者的座右铭,面向市场追求就业率,成了大学教育者的指挥棒”,“整个教育在‘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个人在为出人头地、发大财、找好工作而读书,教育的其他功能,被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而剩下的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躯壳。道德教育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遭到了实质性的冷遇和歪曲”。[10](P177)道德教育受到冲击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流于形式,甚至在升学的关键阶段被直接取消。学校德育已经岌岌可危。
除了功利主义教育对德育构成的外部威胁外,道德教育自身也有内在的问题,即过于理想的培养标准。中国的道德教育思想,来自于儒家伦理观和共产主义道德观。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追求的是“内圣外王”,个体发展要树立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共产主义道德观要求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等。有学者指出:“虽然理想的德育目的论往往具有人格上提升的重要作用,但是理想的德育目的如果不与具体、现实的德育目的结合,往往容易导致要求过高而无法在道德教育的实际中落实。”[13](P65)中国与西方的道德文明程度相比,就目前来看,尚有差距,有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培养目的。有学者指出:“古往今来,我国的德育目的始终是趋于理想化的。这种理想化好像宗教一样,德育目的的最终指向也就是趋近于神的理想人格。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一直以圣贤人格的养成为最终的目的。我国现在学校的德育目的也存在着这一问题。在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其教育目的基本都是比较现实的。”[10](P177)
过高的德育目标,让人觉得遥不可及,既得的利益却又让人体验着快乐。此种状况下,趋乐避苦的本性驱使人们选择享乐,以至于过高的道德要求成了摆设,人们对它视而不见,甚至背道而驰`。一旦人在心理上没有底线和敬畏之后,就会为所欲为,做出许多损人利己的事。这正是当下社会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1]鲁洁.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法)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M].管士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英)洛克.人类理智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邓安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程朝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8]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研究室.18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9](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0]何玉海.服务德育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11]陈建华.基础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3]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