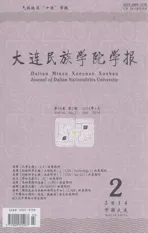蒙古族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研究
2014-03-21王福革王续增
王福革,王续增
(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
蒙古族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研究
王福革,王续增
(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
通过天与人、人与神以及人与英雄等范式的哲学研究,揭示了蒙古族哲学的思维路径,历史地展示了蒙古族在形而上等问题上的哲学智慧以及道德思考的民族性。
蒙古族哲学;思维方式;天人关系;人神关系;英雄
蒙古族哲学以天与人、人与神和人与英雄等范式,在哲学一般性问题上,阐述了蒙古族哲学的特殊性,是一种“蒙古族的哲学”智慧。研究蒙古族哲学,要把握以“诚”为代表的民族道德的主旨,并用民族文化的精神背景衬托蒙古族哲学思维的特殊性。
一、天人关系思维方式
长生天是古代北方民族,诸如突厥、蒙古族等民族关于天的原始描述方式,不同的民族文化赋予了其不同的民族内容。从蒙古族的历史看,长生天在不同的时期与神、英雄、黄金家族等形象相结合,演绎了蒙古族思考天人关系的主题。
在蒙古族思想文化中,长生天首先出现在早期萨满教的祭词、赞歌和神话传说中,如早期的开天说,描绘了远古时代,世界是由气(云雾)、水(脂膏)和土(物团)三种物质组成,它们是创世的基本始料或者说是万物之源,后来逐渐形成了天地。在这些传说中,原古的人们用自己身边的事物说明世界,是人类早期直观的表达方式。开天说代表着蒙古族的直观思维形式,把对天的肯定放在终极的位置,是对世界本身来源的说明。开天说把人与世界相分离,反映了早期人类意识到天地与人之不同,用思维把自己与世界相分离。列宁说过:“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过程区别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范畴是区分过程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1]开天意识是一种初级范畴,加入了人类劳动的作用,以之区别于人之前存在的自然世界。可以说,人们把眼前的世界开始区分为自然与文化的不同,使人从本能的状态走向了社会,并通过对自己劳动的肯定,表达了对自己智慧和价值的认可。
与开天说对天的直观表达不同,在神话故事中,天通过神的影子走向与神性相联系的天性之中。在“冰天大战”和“麦德尔娘娘开天辟地”的传说中,用“魔王吞日”解释日蚀和月蚀;用“冬天和夏天的由来”解释夏热冬冷的原因,用神话回答生活中的问题,神话的认识功能是蒙古族思维从直觉向综合的转变。在神话传说中,天具有了神的生成功能。看似荒诞的神话,体现了人们求真的精神,对客观事物联系的追求,对因果关系的探索。
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开天说与神话传说具有了自然崇拜的性质,表现为在自然神和职能神中形成了长生天——腾格里,形成了以腾格里为主神的众神系统。在腾格里主神的领导下,出现了众多的职能神,如玛纳罕、吉雅其、苏勒德等。腾格里具有两方面的神性,一是创世的神性。二是造人的神性。至此,在蒙古族的天人关系中,天从质料性的物上升为与人性不同的神性,完成了天对人的至上性权力。
创世神话回答了天地的来源问题,并从可感知的具体事物探索了因果联系,试图解决天地的终极性问题,是人类思维至上性的体现,与因果性相结合,构成了人类思维的必然性。
在史诗中,提出了宝木巴的理想社会,“夏日常在,没有冬天,——永远年轻,没有死亡——人丁兴旺,没有孤独——永远安宁,没有战乱。”[2]从宝木巴的内容看,表达了人们对心中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人类精神的寄托,表达了与信仰相关的思维构架,与开天说表达的理性思维相结合。信仰思维的形成说明了蒙古族哲学思维走向了自觉与成熟[3]。信仰思维是一个民族思维构架的完成,信仰在思维中表现,是一个民族哲学自觉成熟的标志。
“统一是全书(《蒙古秘史》)的主题”,从全书的逻辑结构看,以天命观为起始,以感光生子等天人关系中天命的思想论证了成吉思汗汗权的神授性。用天命观论证了世俗政权必然性,神学成为世俗的先导。“就问题来说,天人关系已摆脱宗教形式而直接以抽象的形式表达,并由此引申出价值问题、道德问题和人性问题,使哲学的思考深入到哲学的各领域。就哲学意识看,其自觉性更有成熟的表现,在这一时期,哲学曾三次表现出它的批判精神,一是针对宿命论,提出‘以诚配天’,从听天由命中把人的思路解放出来;二是针对‘祖述不变’,提出‘祖述变通’的思想,要鼎新革故、宣扬弘远,要从武功向文治转变,适应了汗权治天下的历史任务;三是针对黄金家族的汗权论,提出‘政教两道并行’的主张,对汗主有明确的要求,其中有并没有血缘种属条件,这是汗位继承上对黄金家族观的否定,为汗权的巩固和发展打开了新的思路。”[4]
尽管有天命神权的论证和蒙古帝国的强大,以忽必烈汗为代表的蒙古贵族在处理天人关系时,尊重现实,提出了“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治国方针。与早期的天命观不同,他强调先天人合一的关键在于人要以德合天,实惠与至诚同等重要。在他那里,天人合一具有了实惠的内涵,实惠成了联系天人之间的桥梁,这使蒙古族传统思维伦理化倾向具有了世俗的内容,是蒙古族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
在《十善福经白史》中,作者倡导政教两道并行的治国方针,以“道”来论证汗权的合理性,并对“道”作了形而上的说明。与早期的天命观不同,天命逐渐为“道”所排挤,使蒙古族文化从神学走向了哲学。笔者在《蒙古族英雄文化时期哲学思维方式研究》中提到过“约束”。事实上,“道”是先前“约束”一词的理论发展,“约束”主要的内容集中在道德上。到了《十善福经白史》,“约束”演化为“道”,超出了道德的内涵,成为根源性的东西,表明人们更加关注事物内在的根本,这体现了人们从感性直觉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进步。
二、人神思维方式
在天人关系中,交织着人神关系,在人神关系中反映蒙古族文化的天人关系。
原始萨满教以自然物崇拜为特征,包括把日、月、山、水、禽兽、火等作为崇拜物来供奉(这是早期的神祇),以后才逐渐出现了玛纳罕、吉雅其、苏勒德等职能神。从自然物、职能神,再到天神腾格里,人们的思维能力从最初对个体事物的把握逐步走向概念抽象。在自然崇拜阶段,人们的思维停留于个体事物的属性,到了腾格里阶段,人们的思维上升为共性的腾格里,出现人造神,这标志着人们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是思维能力本身的提高。就宗教发展史而言,是自然宗教向人文宗教的过渡。
在最初的自然神和职能神中,不存在相互的隶属关系。只是私有制以后,才出现主从的神统观念。最高的神为霍日穆斯塔(腾格里),下面有55位西方天神等次级神,再往下还有成千上万的翁贡等,这样的神谱体系表明,蒙古族原始平等的思维走向了一种不平等思维。
在英雄文化时期,萨满教统治着蒙古族的信仰世界,到了汗权文化时期,萨满教的地位有所下降,特别在成吉思汗和合撒尔的冲突中,成吉思汗对萨满的处罚,突显了政治高于宗教。在英雄文化时期,人们的信仰是先信仰后理性,但到了汗权文化时期,宗教服务于政治,变成了先政治后信仰。从先信仰后理性,再到先政治后信仰的转变,是蒙古族信仰思维的根本变化。
与英雄文化时期到汗权文化时期相适应,宗教也实现了从神启宗教向道德宗教的转变。所谓神启宗教是指英雄时代的萨满教把世界一切看成是神的启示,人们不过是按照神的启示来生活,人在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附从,其思维方式是由神到人。道德宗教是指汗权时代的人们已经把先前神启的对象演化成一种道德标准,神已经变为一位道德的长生天,由最初的对神崇拜发展到对长生天的崇拜,而对长生天的崇拜演化成对道德境界的崇拜,其思维方式是由人到神。也就是说,在汗权时代的宗教领域中,崇拜的对象已经由神转化到了道德境界,而道德境界的设定不是由神来规定,而是由人来设定,这样一来,在人和神之间,变成了由人来规定神,而不是由神来规定人,人成为了思维的中心和内容。也就是说,人的能动性在神面前得到彰显。这是人们思维的重大转变[5]。
自16世纪喇嘛教成为国教后,喇嘛教主导了蒙古人的信仰,形成了新的人神关系,构筑了民众文化时期的出世思维。
首先,喇嘛教以“空”为自己的信仰开端,主张“缘起性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6]。“有”是事物的假象,“空”为事物表象后的“真有”,是“有”中之空。“空”的主张在理论上,把人存活的基础挖空了。
其次,喇嘛教以“空”为基础,立足于“苦”,使人产生出走的思维冲动。喇嘛教认为一切众生之体出没无常,轮回之中没有永恒,一切存在都难免灭亡。人生是苦难的。喇嘛教把现实的世界看成是痛苦的,符合了人们对生活艰辛的感悟。“苦”的观点在理论上产生了熄灭现世渴望、追求来世的冲动。
第三,现世景象的幻灭,带来了归宿于佛的终极走向。既然人性是空的,活着又是痛苦,人只有“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才能最后解脱,“脱离苦海、慈航普渡”[7]。至于如何能够达到“大空”境界,只能靠自己努力修行,自己悟道。
从喇嘛教的推理看,人要服从“命运”的安排,勤加修行,秉持戒律,才会有“来世”的幸福。这样,出世的选择成为理论上的必然走向[8]。
三、人和英雄人物关系思维方式
英雄是蒙古族文化脱离神性后人性的神化,是世俗文化中俗人的主宰,是民族精神的寄托。
神话是早期蒙古族部落斗争和部落首领与氏族成员之间关系的反映,尽管天命论和有神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但现实的斗争使人们已经在神和英雄之间重新选择新的主人。在《征服黑龙王》《莫日根射日》《阿拜格斯尔》等神话中,最初把英雄和天神对立起来,说英雄罕哈演贵是“为了和天神们战斗而生”、“为了与地神作对而诞生”。在神和人的斗争中,着力颂扬英雄的威力,突出肯定人力的思想。这时,人们已经从最初的崇神开始了疑神,这是一种对自己价值的肯定,人的利益、人的道德、人的力量在史诗中得到张扬,这表明了人对自身有了认识,即人的自我意识已经生成。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用人的意识去批判神权思想,人的自我意识思维开始出现,突显了以人为主体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的发端。
继神话之后,大量的史诗开始出现,据统计有近三百部。史诗文学的形成开辟了蒙古民族的新纪元,使民族文化由神话阶段进入人文文化的新时期。它把人们的理想追求从天上神界拉回到现实生活之中,用歌颂英雄替代崇拜神灵,赞美人的力量能战胜邪恶,坚信勇敢和智慧定能使善战胜恶。总之,人的需求、人的能力、理想的实现都具有了肯定的价值。使得人们思维的对象从神转向了人自身,英雄形象成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载体。
史诗通过英雄的业绩来说明英雄的伟大。《江格尔》在说到江格尔时,问“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谁”?回答说“江格尔是阳光下的万物的主宰”,是“世界的主人,主宰阳光下的生灵”。体现了人对自身认识的觉醒,并从神祇主宰万物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对于宝木巴,过去这些理想被人们依附在神灵的身上,不是用神话的形式表达和实现,就是安在善神身上成了善神的神性。当英雄作为人们的理想的化身被崇拜后,宝木巴又成了英雄的栖身之地,这样安排的在于提高英雄在宇宙中的地位,客观上提高人的理想价值。除了他的功绩外,英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天神有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生长在地上的天神。也就是说人们把天神崇拜变成了人对人的崇拜,这是一种人对人肯定的思维。尽管英雄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已,也是人从自身来思考自身的开始。
与史诗相衔接的《蒙古秘史》,它把成吉思汗为代表的黄金家族作为新英雄的代表,并影响和左右着蒙古族的命运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蒙古秘史》是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英雄神话历史的史学记录,或者说,从成吉思汗的22代世祖到窝阔台,黄金家庭的历史成为蒙古民族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偶像崇拜达到了顶峰,成吉思汗也由人变成了蒙古人间的神,特别是入主中原后,汗权成为蒙古民族的精神寄托,标志着崇拜思维世俗化的开始。
《蒙古秘史》开篇就讲:“成吉思合罕的祖先是承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成吉思汗被传说是苍狼和白鹿的第22代子孙,是蒙古民族图腾崇拜之子,他完成了对蒙古草原的统一,重创金朝,西征欧洲,被呼为“万国皇帝”。蒙古族成为草原的主人,而成吉思汗变成了主人之上的缔造者,并演化为民族的神灵,人们对成吉思汗的崇拜也达到了蒙古民族崇拜史的顶点,众英雄崇拜的思维模式开始向一神崇拜转化。
入主中原后,忽必烈的元帝国不仅奠定中华地域的基本版图,也开创了蒙汉民族融合的新纪元,成为影响中华民族走向的重要历史时期,蒙古族在中原的政治与文化统治也达到了空前的影响。可以说,元朝是蒙古民族的骄傲,忽必烈等可汗人物成为民族骄傲的领跑者,是黄金家族的杰出人物。人们在成吉思汗的影子下思考后辈的蒙古民族。
在北元时期,从脱古思帖上木儿汗到岱总汗,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九位汗主,争斗始终围绕黄金家族的正统与否来进行,直到1479年巴图蒙克达延汗继位,在满都海夫人的帮助下,汗权才又回到了黄金家族的手中。人们正统思想的秉持直接影响着蒙古民族已经形成的汗权崇拜思维模式,并左右着政治王朝的基本走向。
对大汗的崇拜也表现在文化等方面,如《罗·黄金史》中,作者用了五分之三的篇幅讲述成吉思汗的业绩和必力克,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忘其祖先”。罗卜桑丹津在书中始终打着祖先成吉思的旗号,借着成吉思汗的影子说明了蒙古民族要做的事情,这样的写作方式是蒙古汗权崇拜的思维模式在文化方面的表达[9]。
四、以诚为主的道德思维判断
以“诚”为主的道德性是蒙古族文化最显著的地方,在诸种的关系中,“诚”主宰着判断的精神,并逐渐演化为一种思维的判断形式。
在萨满教的诸神神性中,人们把善与恶看成神性的规定性。神被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善神,一类是恶神。在善神与恶神的斗争中,代表光明、正义的善神总是战胜代表丑陋、残暴的恶神。宗教的问题变成了善恶伦理概念的争斗,宗教走向了伦理,或者叫伦理入教,伦理思考问题的方式成为宗教的标准。神灵被道德化,人们由最初的对自然神的自然属性崇拜变成了对神灵道德品性的崇拜。伦理学中的善恶思维方式走进了萨满教。另外,在解决众神关系中的“敬”字等原则中,我们也看到一样的东西,“敬”字本身是一个道德概念,在这里却变成了神学的标准。也就是说,用道德的标准处理宗教的问题。在萨满教中,处处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例子。
在成吉思汗箴言中,忠诚被放到重要地位,看成长生天的属性。成吉思汗对众人讲“汝在背处也,仍如在俺眼,汝去远处也,仍如在俺近边,如此思之,则汝将获上天佑乎。”[10]在人和天的关系中,人做到了忠诚,长生天才会保佑你,忠诚是天与人之间的桥梁,而桥梁的主要构成是道德,用道德做思维判断是当时思维的主要特征之一。成吉思汗把忠诚看成长生天的属性,长生天又是世界的生成的来源,因而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使忠诚在世界生成论中取得了自己的地位。
《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编年史,书中记载了大量的道德故事,形象而又生动,如“五箭训子”,告诉人们只有相互团结,才能战胜困难,形象的比喻成为蒙古民族摆事实讲道理的基本方法。在这些故事中,告诉人们:做人要胸怀博大,对主人要忠诚,上战场要勇敢等,因此,《蒙古秘史》也是一部道德教化史。
《蒙古秘史》宣扬的忠诚、勇敢、广博等道德范畴,在作者看来是上天的属性,是天人合一的核心,如成吉思汗对速别台讲“我们如果忠诚,上天会倍加佑护的。”[11]在这里,道德范畴被客体化。《蒙古秘史》从属性出发来思维,并把道德推演成客体的方法,是一种“道德属性客体化思维。”
事实上,蒙古族文化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可以发现它的道德思维判断,如蒙哥汗“以德治经”的主政思维;忽必烈汗的“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治国方针;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回批》中提出的“我欲做忠臣而成为不忠,欲做义士而成为无义”[12]163的文学批判。特别要指出的是,尹湛纳希提出了智慧和忠诚的关系,认为耿直生忠诚,忠诚出大智。他说“福德势恩如车轮,首尾相关而转动,车轴就是贤明”[12]634。在解决势与恩即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关键是贤明,这就把过去“以诚配天”的思维转向了“以智配天”,智成为连接天人的车轴,使天人关系从道德的领域走向了知识的领域,这是蒙古民族在思维天人关系上的重大变化。
研究蒙古族哲学思维方式,用蒙古族文化阐明蒙古族哲学,不仅解决了蒙古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更重要的是证明了蒙古族哲学的民族性。上述研究仅就一些问题的原则作了说明,意在为研究蒙古族哲学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就视域看,许多问题有待深化。本文抛砖,期待美玉。
[1]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90.
[2]江格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7.
[3]王福革.蒙古族英雄文化时期哲学思维方式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1):21-24.
[4]苏和,陶克套.蒙古族哲学思想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71.
[5]王福革.蒙古族汗权文化时期哲学思维方式研究[J].前沿,2008(8):80-83.
[6]龙树.郭然巴注.中论[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2.
[7]严北溟.中国佛教哲学简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25.
[8]王福革.蒙古族传统思维方式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08(11):112-114.
[9]王福革.蒙古族民众文化时期哲学思维方式研究[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8(4):298-302.
[10]蒙古民间英雄史诗:上册[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46.
[11]额尔登泰.《蒙古秘史》还原注释[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634.
[12]额尔敦·陶克陶.蒙古族作家文论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inking Mode of the Mongolians WANG Fu-ge,WANG Xu-ze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 History,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Tongliao Inner Mongolia 028000,China)
By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man and God,man and hero,the paper reveals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mode of the Mongolians,demonstrates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the Mongolians in metaphysics and their judgment ofmorality.
Mongolia nationality philosophy;thinkingmode;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hero
C95
A
10.13744/j.cnki.cn21-1431/g4.2014.02.002
1009-315X(2014)02-0100-04
2013-07-26;最后
2013-10-2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09BZX071);内蒙古东部经济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资助项目(D07)。
王福革(1968-),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民族文化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