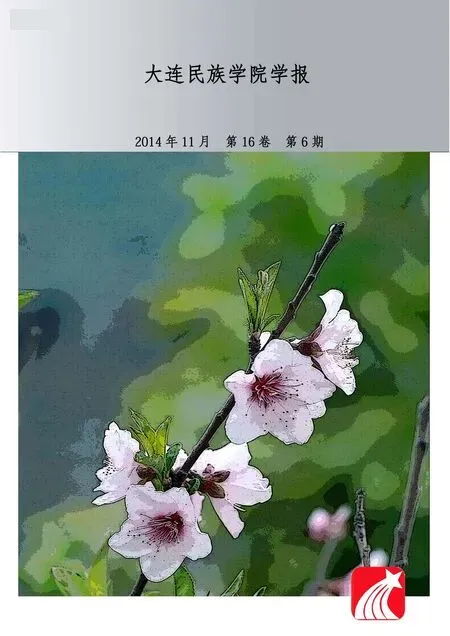韩(朝)《玩月会盟宴》与中国小说之比较
2014-03-21吴世畯
张 迪,吴世畯
(1.大连民族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辽宁大连 116605; 2.韩瑞大学校中文系,韩国忠清南道瑞山)
韩(朝)《玩月会盟宴》与中国小说之比较
张 迪1,吴世畯2
(1.大连民族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辽宁大连 116605; 2.韩瑞大学校中文系,韩国忠清南道瑞山)
认为李氏朝鲜时代的长篇家门小说《玩月会盟宴》明显受到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表现出韩(朝)封建社会对“礼”“孝”的正统认识。其主题思想脱胎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与中国清代思潮几无相涉。作品的本民族特色体现在对家门血缘的极端重视,在艺术上有其独到之处,所蕴涵的封建卫道士思想使作品内涵黯然失色。
韩(朝);玩月会盟宴;中国;小说;比较
一
和明王朝不同,虽然朝鲜王朝以儒家思想为圭桌,人们实际上更关注的是家族血脉。基于这种理念,朝鲜王朝追溯周礼,采取了极端重视“礼”的国策,力图以此来维护王位世袭和社会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之礼也就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之中,成为国民性的根基,使得朝鲜时代家门小说得以出现与发展,其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颇有意味的是,孔子在2000多年以前就哀叹“礼崩乐坏”,中国明代士大夫(甚至帝王)更是缺乏这种对于“礼”的固执,而表现出领会与实践“礼”的游刃有余的态度。明代稗官文人更极其缺乏这种对“礼”的固执,表现了一种把“礼”从形而上拉向形而下的文化心态。就才子(作家)小说而论,瞿佑的《剪灯新话》成书于明朝洪武年间,其作品一部分内容透露了对性理虚伪夹缝中存在的性灵所囊括的人间真情实欲的偏爱。折射了一种不以忸怩遮掩作伪、直视人间情欲的社会心态,表现了一种文学不必只做道统附庸的文化心理。如《联芳楼记》毫无忌讳地描写薛兰英、薛蕙英姊妹隔窗偷窥郑生沐浴,投下一对荔枝传情,并用竹蓝吊郑生上楼与二女幽会。似乎作者给人物命名也颇有其隐语含义。“郑”就是“正”。兰蕙在东方审美观念中就是“正人君子”,因此姊妹“兰”“蕙”之名还是“正”。而“薛”恐怕就是“学”的含义了。那么,为了说明她们的艳情为正非邪,作者借姊妹之口讲了一番幽情私会虽违礼教但合人情的道理。在明朝遗老遗少的哀叹中,哲学家黄宗羲表现了强烈的离经叛道的新思想。各种思潮表现在中国明清文学上,必然就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
和中国明清小说主题与题材呈现的五彩缤纷相比,朝鲜时代主流小说基本显示出主题的单一性,即离不开伦理道德和惩恶扬善主题。虽然朝鲜时代也接触到《唐人小说》类言情小说,但由于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其“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念,在朝鲜则表现为适应朝鲜时代特色的“性理学”思想理论,不能不使这类小说处于非主流地位。因此,简单地从一条主线来说,在朝鲜中、前期,正统士大夫文学小说基本为两大类,一是军谈小说,二是家门小说。也可以说,它们是由一个伦理道德主题为纲,以两个方面来体现和互为补充的,即国家方面和家族方面,其中充满了儒家礼教的意味。朝鲜时代著名的儒学思想家与文学家李退溪看到了主流文学的机械主义公式化与劝善惩恶的简单化,也看到了非主流文学的不合周“礼”的淫词与合性灵的情趣。为此,他在文学观上提倡一种被士大夫称为“醇正文学”的文学。他在古稀之年,居住乡村,慕恋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写过歌颂田园风光的《陶山十二曲》。后人赵润济为避他人认为有脱离正统儒学之嫌而评说李退溪《陶山十二曲》为:“淬然一出于正。”一生致力于弘扬儒家思想的李退溪则有些担心与心虚,惟恐后人误解,便自行解释做诗初因:“吾东方歌曲,大抵多淫哇不足言。如翰林别曲之类,出于文人之口,而矜豪放荡。兼以亵慢戏狎,尤非君子所宜尚。……故写一件藏之箧笥,时取玩以自省,又以待他日贤者之去取云尔。”(退溪言行录)[2]从思想家李退溪尊孔尊礼之一斑可窥朝鲜时代文学理念与状况之全豹。事实上,李退溪是想在思想上与实践中解决表现在文学上的“礼”的束缚与摆脱礼的束缚的这对矛盾。面对强大的历史惯性与社会中这对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想找到一条出路,谈何容易!因此,在朝鲜时代不能不始终存在两种文化,一种是官方的道统的,一种是民间的自由的。然而,在当时社会不可能把这一对矛盾调和之时,历史文明的进步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学潮流也不以道统儒家学派的意愿而停滞,反而以自己的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在朝鲜时代末期出现了抒发人之情性的代表性作品《秋风感别曲》等。此时,尽管当时社会还以儒家思想为正宗,但作为“封建教科书”的《玩月会盟宴》,由于历史的必然选择,被人们抛掷于脑后的发展趋势是在所难免的了。朝鲜时代正统文学之所以呈现单一性,其原因不在于文学家们的才华如何,而在于“礼”对文学发展的制约与束缚,乃至对社会人思想的限制与束缚。
二
从《玩月会盟宴》对《烈女传》《孝经》《女训》《女戒》以及织女、姮娥,道家名位等的直接引用可以认定作品深深受到了汉文化及汉文学的影响。其幽明互通的表述,恐怕就受到汉魏六朝的“世说体”《世说·贤媛》和志怪体小说《拾遗记》《幽明录》《搜神记》的影响,它们在描写慈训有方的老妇,或者在表现时空往来无拘无束的意识时有极其相似的一面。尤其是在方术玄思与史实错综叙事方面,表现出《晋纪总论》所述的共通的“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3]的思想宗旨。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不在于描写幽冥,而是把幽冥审美化,写出民性、人情、道德伦理,或演义伦理教义,灾祥征兆、因果报应,表达一种无论是天界、地界、冥界都有人之信义、情爱等类的人间伦理道德的意愿。在神秘主义艺术演义中,表达出作品对人世的关怀。这种关怀是以现实的生存的危机感作为潜在的思维逻辑起点的。《玩月会盟宴》正是如此,它的著述起点是对士大夫家族能否保持繁盛的忧心忡忡。由于保证血统延续与家门的昌盛,严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玩月会盟宴》特别强调胎教的作用,这又与汉魏六朝杂史小说的表述相吻合。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中谈到《青史子》佚文三则,其中一篇专记胎教之道。在《玩月会盟宴》中出现的人物常常怀孕伴有异香、祥云等征兆。《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就说:“金天氏之末,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女枢幽房之宫,生颛项于若水。”虽然《玩月会盟宴》反映出与中国汉魏六朝志怪小说所呈现的神话的世俗化和鬼话的人情化相同的倾向,然而它所反映的思想的矢量方向却与中国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相反。中国汉魏六朝志怪小说总是把神怪,乃至纲常名理尽力人情化,而《玩月会盟宴》则相反,它总是把纲常名理、乃至人情尽力神怪(圣)化。由于存在这一分歧,客观就反映出如下的效果。中国志怪小说的神秘色彩给中国中古文学带来极大的想象张力,它所呈现的力的作用方向是发散的。而《玩月会盟宴》具有的神秘色彩则给朝鲜时代文学带来有限的想象力的同时,却带来更大的对幻想的约束,它所呈现的力的作用方向是收敛的。这是因为《玩月会盟宴》总是把伦理道德放于“神怪”之上。换句话说,在中国志怪小说中,神怪总是为世俗人情服务,而在《玩月会盟宴》中,“神怪”总是为伦理道德服务。不过,这种用世俗为经,以神秘色彩为纬的艺术形式,在神秘色彩小说中已成定式,所以朝鲜时代作家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需要,演义出一部星宿命定与伦理道德交织的《玩月会盟宴》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综上可见,中韩(朝)两国在文化历史上有着极为密切的因缘关系,沿此线路会找到更多的文学艺术表现的异同点。
客观地说,《玩月会盟宴》既受汉小说的影响,又具有其本民族特色。在家族血统、恩怨、男女主人公的亲情与爱情、妻妾勾心斗角的矛盾等情节展开中,表现了朝鲜时代家族与社会的世情观与家庭教育与闺阁教育的积德行善观。《玩月会盟宴》在作为朝鲜时代民族独特的家门小说及叙述过程及所选用的素材、道具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朝鲜时代的民族特色。无论小说设置怎样的时间、空间背景,小说带有民族历史的烙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三
如果说在中国出现过与朝鲜时代家门小说题材类似的小说,那就是“世情小说”之“家庭小说”。中国家庭小说以《金瓶梅》为祖,后有《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歧路灯》等。《金瓶梅》写欲,《醒世姻缘传》写夫妻之情,《红楼梦》写儿女之情,惟有《歧路灯》写理。前三部书的主题思想均与《玩月会盟宴》主题思想迥异。只有清代作家李绿圆写出了中国小说史上惟一一部充满哀伤与希冀的训诫子弟书——《歧路灯》。李绿圆生于公元1707年,卒于公元1790年。名海观,字孔堂。最有意味的是,李绿圆家境寒微,却自愿为封建家族卫道,以儒家道德伦理来激励自己,并以此来训诫别人。其直接原因在于他具有类似《红与黑》中于连渴望跻身上流社会的心理特征。在他写书过程中,儿子李蘧又金榜题名,中进士,做高官,使得他更加珍视封建家族的前途。和《玩月会盟宴》相同的方面是:(1)两部书都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以人伦教化为本,描写主人公的矛盾冲突与妻妾争斗,可谓两本两国具有异曲同工的修身教科书。(2)从《歧路灯》书中所反映与折射出的思想来分析,再加作者身居中州之地,中州是朱子理学兴盛之地,可见作者也同《玩月会盟宴》作者一样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3)《歧路灯》是一部完整的叙事小说,并且在重视家庭教育与探讨对青少年教育等思想方面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4)两书都于后世受到了几乎同样的冷落的境遇。不同的方面是:(1)《玩月会盟宴》是朝鲜时代家门小说的代表性开山作之一,而《歧路灯》并非中国家庭小说的开山代表作。(2)《歧路灯》不但没有玄怪思想的加入,反而异乎寻常地注重写实。似乎直接写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可以拉近读者与书的距离,以此来表达作者的发自肺腑的拳拳之心,提高信任度或增加恳切感,力图抵消封建伦理道德的冷漠感。(3)《歧路灯》作者从一个下层社会的视角切入主题,必然反映了同情下层人物的一面。(4)《歧路灯》作者经历功名的奔波劳苦,晚年如愿,做过边远地区的知县,使得他有机会了解下层官场,并揭露了一些贪官污吏的丑行,颂扬了一些清官的德行。(5)《歧路灯》多少反映了资本主义在社会中的萌芽状态,写出了王春宇等十数人的工商业者的形象。表现了作者调和封建地主与市民爆发户之间矛盾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特殊形态。(6)由于《歧路灯》作者为圆自己设置的虚幻的梦想,以大团圆的结局结束全篇。由于《歧路灯》成书早于《玩月会盟宴》,由资本主义萌芽的表述,可见朝鲜时代社会发展的进程在当时稍滞后于中国明代社会的进程的事实。这种历史的进程必然带动了人们对新历史条件下的伦理道德的结构与建构的思考。另外,《歧路灯》在正写伦理的同时,穿插了许多反写。虽然《玩月会盟宴》也有所表现,但其严格遵守儒家伦理道德的意味更浓,更强烈,毫无松动的可能性。说明在当时朝鲜时代是不允许对儒家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有丝毫的变更,更不用说有丝毫的怀疑了,表现了实施儒家伦理道德的国粹性。
在中韩(朝)古代文学比较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小说家对于儒家思想的认识比韩(朝)古代小说家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多了一种灵活性。如,对男女授受不亲之礼,孟子就曾在理论上表达了一种灵活性。他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权”是非“常”,即变通之意。推衍开来就有权衡、权且人情之义,也有权利、义务人性之义。既然亚圣为冷漠禁锢的“礼”开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权”的缺口,到了小说家那里就把这种温情演义成了人之情欲,乃至性欲,这不能不为艳情小说家们的创作找到了堂而皇之的宗经的理论根据。朝鲜时代士大夫之所以看重《金瓶梅》,不仅在于它是明代出现的小说,也并非忽略它的形态,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明王室为正宗的大帽子下,对纯粹的对人性冷漠禁锢的理学不堪重负的一种反拨。这种反作用力在士大夫心底与社会底层表现得更为强烈,最终不可避免地形成两种分道扬镳的力量,或为离心力或为虚伪。从儒家旧营垒反叛出来的朝鲜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泽荣就曾剖析过朝鲜王朝的腐朽、理学的虚伪、党人的倾轧。他说:“此李浚庆遗《疏》所谓一言不合,排斥不容,高谈大言,虚伪成风者。呜呼,痛哉!”(金泽荣《韩(朝)史綮》卷5《太上皇》,第11页)而《玩月会盟宴》与《歧路灯》则表现了对“理”的眷恋与对“礼”的不可逾越的认识而产生的企图延续儒家伦理道德的理念本质。就小说而言,《歧路灯》是在正反对比过程中宣扬道德正统,而《玩月会盟宴》则在正反因果报应结果中宣扬道德正统。不管如何,从封建卫道目的而言,两书的比较,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但从小说形态而言,《玩月会盟宴》是反映封建国家中的豪门贵族的家门故事,而《歧路灯》所表现的则是家族中“败子回头”的家庭故事。虽然在卫道方面,前者表现得更纯粹更固执,后者表现得痛心疾首,但二者表现的渊源关系则来自于同一儒家伦理道德的源流,不过分别处于一段河流的前后罢了。
客观而论两书的得与失,必然会得到如下结论。两书的得,在于追溯与塑造“高尚人格”,两书的失,在于眷恋与维护封建道德,表现了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状况。简而言之,其价值不在于他们想说什么,而在于他们说了什么,也就是作品的史料价值。
[1]稣在英.韩国古典小说研究[J].国语国文学,1982 (87):56.
[2]退溪学丛书[M].首尔:退溪研究院,1988:256.
[3]李娟.韩国古代家庭小说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6.
(责任编辑 王莉)
A Com paritive Study of the Korean Novel WanWolHoeMaengYon and Chinese Novels
ZHANG Di1,WU Shi-jun2
(1.International Culture Exchanging Institute,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116605,China;2.Chinese Department,Hanseo University,South Korea)
WanWolHoeMaengYon in Li shi Korea Dynasty wa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novels of the ancient time,and show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rituals"and"filial piety"by the Koreans in the feudal society.Itsmotif is based on Confucianism,especially the neo-Confucianism and bears litt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oughts of Qing dynasty.Its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re demonstrated by the greatemphasis on blood relationship.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novel has exhibited its uniqueness in narrative arts but the thoughts of feudal apologists have overshadowed it.
Korea;WanWolHoeMaengYon;China;novel;comparison
I206
A
1009-315X(2014)06-0628-04
韩国李树凤先生在1992年于《韩国家门小说研究》中认为,“壬丙之乱”(公元1592-1597)、“丙子之乱”(公元1636-1637)前后,韩(朝)家门小说形成背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主要方面[1]。(1)历史:为强调忠孝节烈,赞颂祖先,弘扬遗业,出现了韵文形式的叙事诗和家门小说。(2)文化:个人文集和说话类短文志的增多。当时儒家思想反映在文化上则是以文风刷新为标志的。(3)思想:自有朝鲜以来,虽然取儒家思想整伤社会,但其落脚点还是为士大夫家族繁盛服务的。虽然李先生叙述得比较客观,但这里还应强调客观存在的一个根本东西,也就是贵族男性血统的至高无上性及不可动摇性的不断得以强化。由此而表现出适合韩(朝)封建社会的对“礼”“孝”的认识,这些都脱胎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和中国清代思潮几无相涉。因此可以说,韩(朝)古代思想家或社会意识始终信赖的是所谓正统的“汉儒家传统”。这在对待《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态度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中国人眼中,《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而且是巅峰之作。然而,在朝鲜时代它却没有得到如此殊荣。《红楼梦》讲述的则是一个家族的衰败史,并预言封建家族衰败的不可避免性。这些正与朝鲜时代家门小说主题思想及作者的憧憬相抵牾。这不能归结于朝鲜时代文人的鉴赏能力低下,而是思想、政治使然。
2014-04-11;
2014-04-15
张迪(1950-),男,山东长清人,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