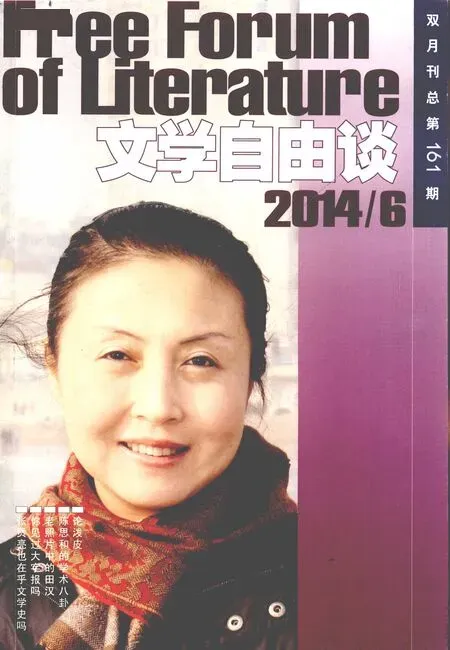文事三疑(外一章)
2014-03-21文/闫纲
●文/闫 纲
文事三疑(外一章)
●文/闫 纲
一
有史以来,文学分为两大类:韵文和散文,韵文之外都是散文。文、史不分家,散文与说史水乳交融。传奇和话本的出现,散文分成虚构与非虚构两大类。现当代,我们把虚构的散文称作小说等,把非虚构的散文称作纪实文学,包括自传体文学与报告文学等。今之散文,其实是非虚构的散文中纪实文学的一部分,或称狭义的散文。
借此,我希望搞清楚直到现在仍被弄得混乱不堪的体裁定位:理应是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而不是报告文学包括纪实文学和散文。报告文学是个筐,非虚构的文体尽量往里装,鼓鼓囊囊,成了体裁圈地,侵犯别人的主权。“鲁迅文学奖”只设报告文学奖助长了报告文学的圈地活动,要么“拉郎配”,要么都往一条道上挤,拥挤不堪。为什么只设“报告文学奖”而不设“纪实文学奖”呢?
二
年度选集何其多!这是好事,人人心里一杆称,但是个人化的、突出艺术风格的选集极缺。大路货的选法年年有,天花乱坠,言行不一。编者骗人说,评委们在上千部的大海里捞针,反复地遴选,如何认真负责。把戏揭穿后,说是书商们干的,天啦,可不能把“选权”交给书商,他们怎么来钱怎么弄。
现在的评奖不只一种,官方民间一齐上,也好。希望在评奖过程中对读者和作者负责,一篇一篇地读,一本一本地选,不要远离文本,不要只委托给极个别评委定生死,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再给出血的人留一个……让人指着鼻子骂街。
三
较之其它门类,受命或受雇于人的报告文学运作起来好像“不差钱”,开个研讨会什么的一张支票即刻敲定。拉不到钱,谁给你开会,谁给你锦上添花写评论,写出评论谁给你发表?言及于此,我很替一般写作者着急,也为好货可能被埋没而心痛。
有的研讨会实在不敢恭维。与会者读就读了,没读就没读,没读完就说没读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不要见钱嘴软,为了眼前的什么而失掉自己宝贵的什么。
跟维熙狱地重游
从维熙的新作《我的黑白人生》由生活书店出版。在作家与读者的见面会上,我百感交集。一个人的遭遇,两代人的死生。时在2014年8月23日晚,会场坐满了,年轻人居多。
从维熙是新中国第一代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也是“大墙文学”的始作俑者,开辟了文学史上的新时段,即“冰河解冻”的时期。从《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细无声》到《走向混沌》,再到现在出版的《我的黑白人生》,从维熙的“大墙文学”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如果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和《雪落黄河细无声》等率先暴露真相、戴着手铐控诉、却胆怯地留下光明的尾巴的话,那么,《走向混沌》便是惊人的真实和亡命的呐喊,“革命的浪漫主义”少了,直面血泪的忧愤多了。读到从维熙夫妇二人上厕所都不准松开手铐时,我想起十二月党人流放时妻子双膝跪倒,用滚烫的嘴唇狂吻冰冷的手铐的情景,我的眼睛湿了。
现在出版的《我的黑白人生》,对于“大墙”里非人苦难的再现,以及对暴力折磨的愤怒,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你能忘记骷髅一般躺在冰冷的破被里,没有叹息、没有眼泪,彬彬有礼的学者吕荧吗?你能忘记好心人帮他捉虱子,虱子耐寒,捉不干净,生活不能自理,大名鼎鼎的美学专家吕荧吗?你能忘记唯一的一个当场为胡风叫屈而后又冻又饿无人为他叫屈被扔到荒野茅草屋里等死的铁骨铮铮的汉子吕荧吗?吕荧活活地死了,埋在荒草丛中,没有任何标志,后来起地引水,改为大芦花荡的养鱼池,草密鱼肥,一切有形的罪恶被抹得干干净净。
关于母亲的追忆,让人肝肠寸断。你能忘记母亲拐着小脚,背着食品,拖着孙儿,赶火车,步行几十里,到渤海湾边上的茶淀劳改农场探监看儿子吗?能忘记母亲脖子上挂着木牌子扫马路的情景吗?也不能忘记夜晚睡觉儿子偷偷将木牌摘下,母亲催他快快回农场,一再叮嘱说:“没被打死,就算阿弥陀佛了,你放心,妈挺得住!”书中写道:“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千千万万伟大的母亲,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承受人生负荷如此沉重的中国母亲!”
书的第三个动人之处,是对三个逃犯姜葆琛、王臻和张志华的追忆。张志华在北大与林昭同时划为右派,从维熙在书中征引了其长诗《还乡》中的八节,其中有这样一节:“阶级斗争的学说/天天说,月月讲/这里坟茔的密度/日日增,年年长。”相信年长一些的读者会与我有同感。
《我的黑白人生》可以看作是《走进混沌》的续集,是从“走向”混沌”到走出“混沌”,三中全会后的畅想取代了浪漫主义的虚妄,从维熙更清醒、更自觉。在《走向混沌》里他理直气壮地回应了“写真实”这一命题的审美立场,然而,在《我的黑白人生》里,他最有条件质疑却未能质疑并回答:如何深化“写真实”这一“真善美”的头号命题,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记忆没有被关进监狱。今年四月,春光明媚,无霾的一天,从维熙邀上邵燕祥、柳萌我们一行,去茶淀北京监狱参观。人性化的管理堪称模范,卫生医疗条件也属上乘,“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正在积极落实。宿舍里一尘不染,被子方方整整,像一块块刀切的豆腐块,学习室的墙报上能发现诗的语言,游艺厅可歌可舞可健身,“入禁区犹如走进兵营……”,怕比喻不当,心里想着,没敢说出口。
我们特意让从维熙“老犯友”领着,直奔大芦花荡,一路坦荡,旧貌换新颜,唯当年的炮楼依稀可见。再到“老残队”旧地寻访吕荧监禁的囚舍,一无所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去墓地吧,冤魂何处?远远望去,空留一泓鱼塘。
归来,监狱管理局的同志手捧《我的黑白人生》,交口称赞,旧事重提,忆苦思甜,庆幸今天过上好日子。席间,一大盘鲤鱼上桌,主人夸赞本鱼塘的大鲤鱼美味之极,觥筹交错的一刹那,我心头一惊,执杯的手有点哆嗦,想起风度翩翩的吕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