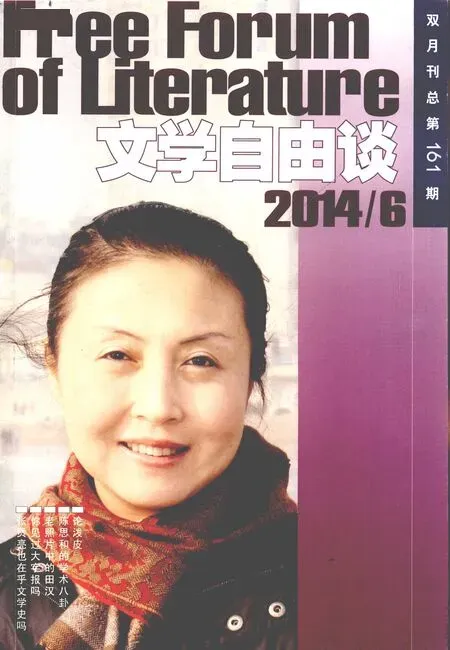对萧红貌似公允的冷酷
2014-03-21郭玉斌
●文 郭玉斌
伴随电影《黄金时代》的公映,萧红再度引起人们的热烈关注,在腾起的灼人气浪中却听到一个锐利的呼哨。寻声望去,原来是章小东,一位美籍华裔女作家。她在新作《尺素集》中说萧红“杀婴”,骂萧红是“妓女”,还要掴萧红耳光。一个人能刻薄至此,真令人无语了。但是,章小东再三发声,这股诽谤萧红的歪风大有越刮越猛之势,作为萧红的“粉丝”, 我不得不“跳”出来说几句话。
“杀婴说”:残忍的补刀
章小东要掴萧红,因为她认为萧红是个 “残酷的母亲”,这主要是指萧红的两个孩子的事。《尺素集》中谈到此事时说:“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自由,竟然两次抛弃亲生的孩子?这实在是一个残酷的母亲。”真是这样的吗?章小东在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的访谈时声称:“我说的都是事实,不能够抹杀掉的。”那好,我们就用事实来说话。
萧红有两次生育,但很不幸,两次生育在萧红的心灵上都留下了巨大的创伤。萧红1932年秋在哈尔滨生下一个女婴,这是她与未婚夫汪恩甲的孩子。萧红怀孕后,汪恩甲一去不复返,旅馆老板向萧红追讨二人欠下的大笔食宿费,甚至要把萧红卖到妓馆抵债。萧红向哈尔滨颇具影响的《国际协报》写信求助,得到萧军等人的救助。那年哈尔滨发大水,萧红意外逃离险境,不久在医院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萧红当时可以说一无所有,她能住院完全靠的是萧军的蛮力。萧红的处境极为艰困,所以孩子降生不久就送人了。孩子送走后,由于身心受到强烈刺激,萧红在医院大病一场。但因为没钱缴纳住院费,医生拒绝治疗,萧军再次用蛮力威胁院方,萧红才得到医治。这次生育仿佛让萧红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在哈尔滨送人的这个孩子一直是萧红的牵挂,她的自传性小说处女作《弃儿》就写到了自己弃儿过程中的那种锥心的痛。好友舒群记叙了萧红1937年在北平时,“每逢走到儿童服装的橱窗,萧红就踌躇不前,望着陈列着的童装,思念她那没有下落的孩子”。萧红在香港病重期间,还曾对骆宾基提起过她在哈尔滨生的这个女孩子:“她怀念的沉思着:‘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的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直到弥留之际,萧红还让端木蕻良答应,将来有条件去哈尔滨一定要把那个孩子找到。
艰难时世卖儿鬻女的事并不少见,章小东不分析造成悲剧的具体情况,而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苛求彼时的萧红,对处于底层的、年轻的弱女子一味地横加指责,这公允吗?在那种情况下,萧红自己的生存都是个问题,又怎么能哺育一个小生命?孩子送人也许是唯一理性的选择。是让孩子与自己一起沉入无底的深渊,还是给孩子一条生路,究竟哪一个更“残酷”呢?萧红无奈地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却招致章女士所谓“自私”的指责。想起一句歌词:“易地换处境,怎说应不应?”
萧红1939年11月在重庆生下一个男婴,这是她与萧军的孩子,但是孩子降生几天后就夭折了。萧红告诉好友白朗说孩子抽风死的,对此白朗有些疑惑,她要找医院理论,被萧红拦住了。章小东并没有采用最初的资料,而是引述了一位萧红传记作者的文字,而这位作者又在原材料上添油加醋了,说萧红“十分平静”地告诉白朗这件事,“医生、护士都很吃惊,说要追查原因,萧红自己反倒非常冷淡,也没有太多的悲伤”。章小东进一步认定:这个长相酷似萧军的男婴是被萧红害死的。当初白朗仅仅是有些疑惑,后人越传越走样,到了章小东这里,终于把这件事“坐实”了。司法上讲“疑罪从无”的原则,但章小东推测“可能”犯罪就“认定”犯罪,若让章女士做法官,不知要造出多少冤狱。然而,绝大多数人不肯花气力回归初始材料,寻求真相,这便是流言广布的原因。
萧红杀婴的说法不成立,还因为萧红的大爱和底线。萧红是有做人底线的:她流浪哈尔滨的时候,决然离开了做皮条生意的老妇人的家,宁愿露宿街头;住在欧罗巴旅馆的时候,尽管挣扎在饥饿中,但她终于抵抗住巨大的诱惑,没有去偷别家房客门上挂的“列巴圈”。萧红的大爱是无处不在的:她在散文《小黑狗》中,对一条小狗的命运流露出无限的怜爱;在散文《同命运的小鱼》中,她连收拾活鱼都不敢,对养了多日而死去的小鱼更是伤心不已;在小说《生死场》中,她对那即将走向屠宰场的老马都怀着悲悯,也终于不忍让二里半的柴刀砍向那老山羊。对弱势群体,萧红更是满怀爱心:她同情东家的婢女小菊、同情乞讨的女人、同情一个老漆匠;她新做的棉袍还没穿一次就要送进当铺,但还是从当得不多的钱中拿出一个铜板给了路遇的老乞丐;她给雇来锯柈子的老头买面包而不要钱,为他们生活的艰难而流泪。说到孩子,萧红其实是满喜欢的:1939年萧红住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上下山要路过保育院,她常去看望那里的孤儿,还专为其中的一个叫林小二的孩子写了一篇散文。萧红的小说作品中也频频出现儿童的形象:《王阿嫂的死》中的小环、《生死场》中的小金枝、《桥》中的小良子,等等,《呼兰河传》更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写到了许多孩子。而且,在作品中一旦出现孩子的身影,字里行间就透出氤氲的母性。就是这样一个满怀悲悯的女性,竟被章女士指认为杀人的凶手,并且是杀婴,并且是杀害自己的孩子!难道萧红的这份大爱单单就不施与自己的亲生骨肉?根本就讲不通嘛。
每每在指责完萧红弃婴、杀婴之后,章女士总是不忘说上一句“我为你的孩子哭泣”之类的话。在把萧红妖魔化后,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善女人,这更见其冷酷,简直冷入骨髓。萧红已经遍体鳞伤了,但人们分明看到了章女士对萧红残忍的补刀。
“妓女说”:欲坠人于深渊
章小东要掴萧红,不仅因为萧红“狠毒”,还因为萧红“狡诈”,是个很有心机的、特别善于依靠男人的女人。她说萧红:“遇到困难的时候,先做出一副弱女子受委屈的模样,寻找强者去靠一靠。”她举的例证是:“那次端木蕻良打架引起公愤,缩回到家里,你不是走出去面对,而是跑到楼上,依靠我的爸爸帮助你解决。”这说的是在重庆的时候,端木打了邻居的保姆,那是一个泼皮的四川女人,她在街上不依不饶地闹了起来。这样的例子得出那样的结论未免太可笑:章小东的父亲靳以(原名章方叙)既是端木复旦大学的同事,两家又是常走动的邻居,有了麻烦找邻居帮个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特别是碰上那么一个泼悍的女人,懦弱的端木关门躲了起来,萧红作为文化人能与那个女人在大街上打吵吗?萧红是把靳以当作朋友才请他帮助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没想到多少年后这位朋友的女儿竟把这当作萧红依赖他人,人格不独立的证据!
章小东透露:“婆婆私底下告诉过我:她(萧红)的相貌平平,功课也一般。”为了贬损萧红,章女士甚至把别人“私底下”告诉她的话都翻出来了,真可谓不遗余力!关键不在于“相貌”和“功课”这等小事,而在于接下来的一句话:“看起来,你要跳出你的呼兰河,必须另谋出路。”这“另谋”的“出路”是什么呢?章小东的结论是“捉住一个男人,就是为了让这个男人帮你跳出你的呼兰河”。萧红真的那么工于心计吗?与萧红共同生活了六年的萧军,都承认萧红“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与萧红朝夕相处了几个月的丁玲也回忆说:“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然而,与萧红不曾谋面、又是萧红晚辈的章女士,却认为萧红为了“跳出”呼兰河,不停地利用男人。她说二十年前曾求教一位“颇有名望的男性评论家”萧红为什么这么“红”?答曰:“因为妓女。”章女士说当时还“吓了一大跳”,但很多年以后,“随着阅历的增厚”她才渐渐认同了这种观点。章小东说:“你为什么自己不能尊重自己?这就让男人不会尊重你。他们看低你,看低你是‘妓女’也就理所当然了。”为什么在章小东眼里萧红是“妓女”呢?章小东说萧红“一开始就跟过好几个男人”,并且说这“实在又是不可掩盖的事实”。我发现了,每次章小东说完谎都强调她说的是“事实”,那么我再次用事实来戳穿她的“事实”。
萧红一生到底有几个男人?如果下面有若干备选答案的话,倒很像一道选择题。好了,别猜了,以我近三十年对萧红的关注,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三个。多一个都没有!这三个分别是:汪恩甲、萧军和端木蕻良。如果超出这三位,都属子虚乌有。
汪恩甲是萧红的未婚夫,萧红上初中时家里给她订的亲事。据萧红的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汪恩甲“也算相貌堂堂”。萧红当时并未表示反对,两人开始关系还不错,后来萧红发现汪恩甲有抽大烟的恶习,几次劝不听,渐渐讨厌他了。初中毕业后,萧红为求学,也为摆脱汪恩甲,出走北平。在父亲的经济制裁下,萧红无奈地回到家里,不久被软禁在家族的大本营阿城福昌号屯。半年后,萧红逃出来,开始了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冬天的风雪阻止了萧红流浪的脚步,她宁可屈就还爱着她的汪恩甲,也不向父亲低头。再后来萧红怀孕,汪恩甲走人,萧军出现。萧军尽管救助了萧红,但他是行伍出身,对萧红时有家暴,尤其让萧红受伤的是他习惯性的出轨,他们的婚姻在维系六年后分手。之后与端木结合,端木是家里的小儿子,平时不会关心人,也让萧红吃了些苦头。两人共同生活了四年,直至萧红病逝。综上,萧红的感情生活还是认真的,她的每一段感情都是全身心地付出,然而最终伤害的是她自己。分明是萧红遇人不淑,章小东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萧红身上。
不仅如此,章小东把萧红出走北平时投奔的表哥陆哲舜当作萧红“一开始就跟过”的男人。但有资料显示,他们在北平时分别住在一处四合院三间北房的东西两头,各居一室,他们并未越雷池一步。萧军不能算作“一开始就跟过”的男人,如此算来,萧红“一开始就跟过”的男人只剩下未婚夫汪恩甲一人了,那么章女士所说的“好几个”是从何而来呢?当然就是无稽之谈了。要说“一开始就跟过好几个”的,倒很像是说萧军,然而章女士对萧军显然是存有极大好感的,唯独对无辜的萧红大加挞伐,是何道理?
章小东还把骆宾基当作萧红的男人了,说骆宾基在战乱中与萧红“厮守了四十四天”。这又是在编瞎话,实际情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骆宾基想回内地,前来向端木、萧红辞行。端木请他留下来帮助照看病重的萧红,骆宾基答应下来。此后的四十四天骆宾基与端木一同护理着萧红,其间端木有短暂的外出筹钱的情形,何来骆宾基与萧红“厮守了”四十四天?骆宾基是萧红弟弟的同学,是崇拜萧红的青年作家,他在萧红生命的最后阶段照顾了萧红。而从萧红这方面讲,她已重病在身。生命都难保了,谈何感情?萧红病逝后骆宾基撰写了 《萧红小传》,这是第一本萧红传记。但因为是第一本,所以还存在材料不足、事实有误的现象,尤其是带着较强的情绪色彩,所以也降低了它的可信度。随着萧红在港材料的发掘和丰富,一些真相浮出水面,然而章小东却依然采用老旧的、不实的材料,不知何故?
萧红真的是个很依赖男人、缺乏女性自主意识的人吗?显然不是。萧红是家里的长女,从小独立意识就很强。她为争取上中学的权利,与父亲苦斗了一年,终于使父亲妥协,她后来说:“当年,我升学了,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初中毕业后为了继续求学(也是为逃婚),她出走北平。后来萧红四处漂泊,也并未依赖男人。萧红曾叹息道:“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萧红要是依赖男人,就不会主动离开萧军,也不会在与端木的生活中成为里里外外一把手。
萧红“利用”男人,结果如何呢?章小东说萧红“这种女人是最简单可以让男人趁机的”,她认为“这在男性的眼睛里,特别是传统男性的眼睛里,就会变得‘低贱’”。她讽刺萧红有“本事”,还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有如此高级的智商,怎么就不会摆脱男人,自己站起来呢?”最后恨恨地说:“你利用别人,别人也利用你,却没有人真正要你。”多么刻薄呀!萧红1932年困居哈尔滨一家旅馆,差点被旅馆老板卖到妓院抵债,萧红投书报馆求助才算躲过了一场劫难。谁也不会想到,八十年后的今天,竟有人骂萧红是“妓女”,这真是不幸的萧红身后的又一大不幸。
“毁人不倦”:戾气的释放
章小东不仅要掴萧红耳光,还要同鲁迅打架。她在《尺素集》中为鲁迅的前妻朱安愤愤不平,她并不认为封建婚姻带给鲁迅很多的不幸,反倒认为鲁迅在上海有老婆有孩子,蛮开心的。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这样的:鲁迅二十六岁奉母命与朱安结婚,却一直没过夫妻生活,他们二十年的婚姻徒有其名。朱安固然可怜,难道鲁迅就幸福吗?再说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10月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当时鲁迅四十五岁;1927年10月8日两人在上海同居,当时鲁迅四十七岁;1929年9月22日海婴出生,当时鲁迅都四十九岁了。鲁迅认识了许广平,许广平嫁给了鲁迅,他们在沪生活十年,并育有一子,这或许是上天对鲁迅的垂怜。难道鲁迅与朱安无子无孙、厮守一生、同归于尽才是道德的吗?然而章女士在受访时说:“这个人 (朱安)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跟鲁迅打起来。”(《半岛都市报》)看来章女士脾气不好,动辄就要打人,有相当程度的暴力倾向。
尽管章小东的丈夫孔海立是《端木蕻良传》的作者,并且孔先生书中的观点比较客观,但章小东的《尺素集》却捡鸡毛凑掸子,把端木贬得啥也不是。她说端木“是制造迷雾的高手”,证据是:端木的《鴜鹭湖的忧郁》把鴜鹭湖写得很美,与端木的出生地辽宁昌图县的鴜鹭湖相去甚远;她说端木“这个人有点阴暗”,证据是:“窗户都是用深色的纸糊得严严实实,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说端木“实在有些机关算尽”,证据是:笔名的前两个字用的是少见的复姓,后两个字用的是“红高粱”的改写;她说端木没有“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证据是:端木拿不出他与萧红的结婚证书,“也没有到报上刊登启事”,甚至没有办过婚宴。难道作家应该像照相一样地展露实际生活吗?难道布置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就是心里“阴暗”吗?难道给自己起一个满意的笔名就是“机关算尽”吗?笑话!至于没有结婚证,萧军与萧红结婚也没领证啊,在战争年代文化人四处漂泊,有多少人结婚领证?当时又有几个人浪漫地刊登结婚启事?还有那次婚宴,早有1981年刘国英的《回忆萧红和端木婚礼前后》一文作证。章女士能够如此无视事实,看来她铁了心地要“毁人不倦”了。
还有更暴力的,章小东曾当面向黄源求证,当年萧军在上海时是否真的和黄太太许粤华“发生了床上的关系”,把八十九岁的老人家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许粤华与萧军出轨并怀孕,周围人都知道,萧军也认账,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够狠!可怕的是,章小东事后并无悔意,心里还有些不平:“萧军和他老婆有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问问又有什么要紧。”简直不可救药了!在说别人“冷血”的时候,也不自家好好照照镜子?
章小东在《尺素集》的自序中貌似公允地宣称:“我只想在我知道的真实磨损之前,无拘无束、肆无忌惮地把这些真实释放出来。”勇气可嘉,看来她要扮演斯诺登式的英雄。然而,斯诺登爆的是实料,章女士“肆无忌惮”地“释放”的不是真相,而是戾气。章女士旅美三十年,深受美式文化的影响,但东方文化的底蕴毕竟有限。中国著史有一原则,叫做“为尊者讳”,然而,章女士致力于揭短,致力于显示“人性恶”,为此可以罔顾事实。以这样的态度来述史,不仅其可信度大打折扣,同时也是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的。
萧红生平的资料是有限的,已经被研究者开发殆尽。但有人为了有所创新,不断地进行挖掘,于是出现了捕风捉影、大胆推理的现象,甚至于胡编乱造、无事生非。“新意”倒是有了,也真个与众不同,但经不住事实的检验。当年萧红研究界所谓的“养女说”,就严重干扰了研究的方向,使一些人热衷于萧红八卦的身世,从而削弱了对萧红文本的关注。章小东今天抛出的所谓“杀婴说”、“妓女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其破坏力较前者有过之无不及。近来电视剧流行的一句台词觉得挺好玩儿,送给章小东:“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收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