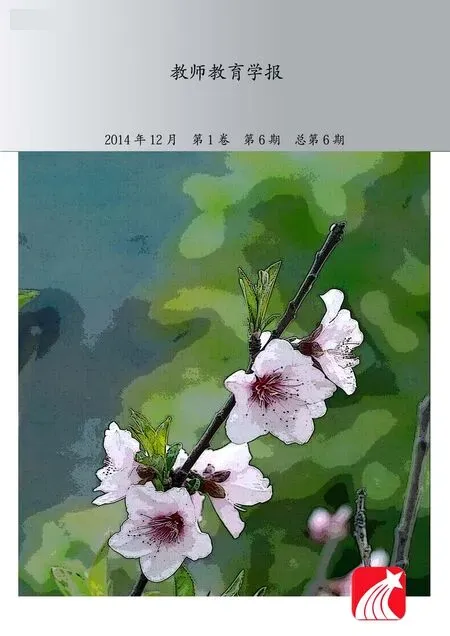清末民初赫尔巴特“五段形式
——以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为考察中心
2014-03-20肖菊梅
肖 菊 梅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一、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导入的背景
美国教育史家鲍尔生认为:“在19世纪前半叶,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的发展,乃是教育领域中另一重要因素……在很长的时期里,人们便把‘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和‘科学教育理论’作为同一词。”[1]直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经过其再传弟子莱茵的发展和推广才逐渐被世人重视并影响世界各国的教学发展,日本就是受影响的国家之一。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大力普及国民教育并借鉴欧美先进国家的教育理论。明治十五年(1882年),日本政府“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宪法,并命他开展从德国招聘教育专家的工作”[2];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文部省“聘德国人爱弥尔·郝斯耐克特(Emil Hausknecht)为帝国大学讲师,郝氏宣讲海尔巴脱(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即综合伦理说与心理说的教育学说”[3]。一时间日本教育思想界为“海派学说所风靡”[3],并受到谷本富、大濑甚太郎、汤原元一等日本学者的狂热追捧。他们通过论著、讲习会或翻译赫尔巴特、林德纳、莱茵、科兰等欧美教育家的著作等形式来广泛宣传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并因此成为“日本赫尔巴特运动的指导者”[4]。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派遣留学生,如波多野贞助、野尻精一、汤本武比古等去德国学习赫尔巴特教育学。随着留德学生相继归国,“日本赫尔巴特学派”的力量得以加强,他们把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贯穿于教育学和教学论教材的编写中,如大獭甚太郎的《教育学》、谷本富的《教育学讲义》、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等。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日本处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全盛时代”[5]。
而此时,正是国内清政府推行“新政”、实行改革之际。“新政”改革涉及教育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的兴办、师范教育的勃兴及留学生的派遣等。学制的颁布意味“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6]515。新式学堂的兴办急需教师及各科指导书。为此,清政府在《钦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为解教师之缺乏,速派人去国外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6]533;中等师范学堂开设“教育学和教授法”科目;对于教授用书,认为“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6]546。这种“急用”下的“急需”,为近代西方教育学和教学论的导入提供了前提条件。此时,留日学生也成为翻译和介绍日本教育理论著作和教育学说的主力军。国内教育杂志的创办,更是为西方教育理论著作及学说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1901年5月,罗振玉和王国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这是我国最早创办的教育专业刊物,也是最早向国人较为系统地传播西方教育理论的“窗口”。《教育世界》的创办主旨,从罗振玉所撰的序列中可窥知:“……一、附译之书,约为六类:各学科规则,曰各学校法令,曰教育学,曰学校管理法,曰学校教授法,曰各种教科书。一、教科书分小学级、中学级二者。一、此杂志中所译各学科教科书,多采自日本……兹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海内外学人若据此编成中国合用之书,则幸甚等。”[7]重视介绍和引进外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始终是《教育世界》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之一。该刊文章以译自日文为主,“从第1号到第18号,全文译载日本各项教育法规、条例达84种之多,以后又陆续译载日本各类教科书、教育学及教育史专著50多种”[8]。1901年11-12月,《教育世界》第12-14号连载了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这是“从国外导入中国的第一本教学论教材”[9]8。通过《教授学》的导入,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被国人知晓,它对近代课堂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教授学》及其“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内容解读
《教授学》系日本学者汤本武比古的重要著作。《教育世界》刊载《教授学》一文时并未署译者名,有学者认为,“这些未署名的文章也系出自王氏(王国维)之手”[9]43,若以此类推,《教授学》也应属于王国维的译作,笔者暂以此说法为参考。汤本武比古,日本长野县人,明治十六年(1883年)毕业于东京师范学校,后留学德国,系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回国后历任文部省编辑局职员、学习院教授、开发社社长、高等教育会议员等。该著共14章,另附5个教案及一个补录。全书篇幅不长,仅四万五千多字。鉴于绪论部分通常更具基础性和引导性,加之文章篇幅有限,本文着重选取《教授学》“绪论”中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和“教案”部分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整理各节所涉及的知识要点(表1)。

表1 汤本武比古《教授学》中“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知识要点一览表
由表1可知:从第九章至第十三章,作者主要论述了赫尔巴特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即预备、授与、联合、结合和应用。从文中可知,此“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与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有差别。赫尔巴特把教学过程划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形式阶段,其弟子齐勒尔将第一阶段“明了”再分为“分析”和“综合”两个阶段,于是就成了“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此后,齐勒尔的学生莱茵又把这“五段形式教学阶段”重新命名为预备、提示、联想、总括和应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也称为“五段形式教学法”)。从上述知识点可知,《教授学》中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所描述的是学习心理阶段过程而并非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中所阐述的五个阶段的不同心理特征。这说明传入中国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经过日本和国内学者的再次转译已失去了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思想的本义。正如学者所言:“客观地讲,阅读清末《教授学》的译文,难以领略赫尔巴特原著的思维方式与叙述逻辑。”[10]这种现象在近代国人和日本学者译介教学论著作的过程中很普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翻译方式便于国人接受了解。日本学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对赫尔巴特著作进行编译,《教授学》就是经过汤本武比古编译的著作。这种著作经由日本传入我国,再经过国人的编译,其思想内容与原著就相差甚远了。尽管如此,这种经过“转译”注重“学习过程”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经首本教学论译著传入我国后还是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近代的教学发展。近代教育家俞子夷回忆,“后来师范生和一般教师只对过程有兴趣,其所自出之五段法则不闻不问……师范附小为实习地,搞过程,确是当务之急”[4]479。
此外,作者在文中最后一章附录了6门学科教案(古谣、算术、语文、自然、科学、物理和历史),主要系莱茵所编(物理教授案系林德遵编)。这些教案形式主要根据莱茵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编写而成。它为我们直观呈现了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教案原型,成为我国教师编写教案的原始范本。而文后附录的孔子五段教授,作者运用孔子的教学思想来解释赫尔巴特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经过作者的解释,赫尔巴特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与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相互联系,“从表层看反映了东方儒学者对孔子思想的顶礼膜拜,而从深层看则反映了文化传播对本土文化的依赖性。”[12]利用孔子的“启发式”解释赫尔巴特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把新的学说置于中国的教育语境中,以利于中国人接受并实践。这种尽量避免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将新思想纳入传统思维方式可接受的范围内,并使其在教育实践中畅行无阻的引进方式,正是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尽管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在清末的引进与实践是浅显的,但是这种经过“转译”而注重“学习过程”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在中国的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的事实却得以证实。
三、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推广
《教授学》的导入,受到国内学者的热烈欢迎。俞子夷回忆:“汤本武比古、小泉又一的著作译本,当时比较流行。”[11]475通过《教授学》的介绍,国人能较为完整和直观地了解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近代教育家俞子夷把“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在1908年前,五段法仅仅在讲义或口头谈话中推行,小学课本里很少出现;第二期夹在单级里传播;第三期在辛亥革命后,推行的方式多,效果算不小,而主要依靠师范学校的大发展”[11]473-475。这是作者以时间分期来划分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法”的发展。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拟从以下三方面来直观地呈现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导入后的发展概况。
(一)以“教材”为载体
通过《教授学》的译介,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传入国内。此后,相关教育学和教授学著作成为传播“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重要载体。从该时期传入的教育学著作看,如波多野贞之助的《教育学讲义》,在“教授论”谈到“教授固不外分解总和二方法,而其阶段要必依儿童发达之秩序以顺授之,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勿稍凌乱,斯谓之真正教授”[9]71。其分段如下:(1)教授材料之分节;(2)教授事项之预告(包括目的、期望等);(3)受领,又分预备和提示;(4)理会,又分比较和统括;(5)应用。其实际教授阶段为(3)(4)(5),即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的《教育学》(《教育世界》第9-11号刊载),该著系传入我国的首本教育学著作,其中有关于“教授之形式”内容。此外,其他教育学译著,如天眼铃木著、张肇熊编译的《教育新论》(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熊谷五郎著、范迪吉译的《教育学》(上海会文学社,1903年);东京富山房编、范迪吉等译的《教育学问答》和《教育学新书》(上海会文学社,1903年);小泉又一著、周焕文等译的《教育学教科书》(北京新华书局出版,1904年);吉田熊次著、蒋维乔译的《新教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等,均十分推崇赫尔巴特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从教授学(法)译著的内容看,除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之外,其他教授学(法)著作,如樋口堪次郎的《统合新教学法》(文明书局,1903年),“纯粹赫尔巴特派,各科教法仅及史地理科等部分,五段法最实用此等科目”[11]475。此外,多田房之助的《教授指南》(东京并木活版印刷,1902年);长谷川乙的《教授原理》(教育丛书第5集),槇山荣次的《新说教授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03年);长谷川乙的《教授学原理》(《教育世界》1905年2-3月,第93、94、95号);神保小虎的《应用教授学》(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5年),等等,均涉及“五段形式教学阶段”。
除上述译著之外,国人编写的教育学和教授学(法)讲义、教材均成为“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重要理论来源。如1901年,湖北省教育部编辑的《师范讲义》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把它作为训练师范生的基本内容。据笔者所查,这是国内最早介绍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书籍。秦毓钧的《教育学》在“教授之阶段”一章中对赫尔巴特四段和五段教学法进行概述,然后说明“各学科之性质不相同,概分五段于教授上之实施,不无窒凝。故后之言教授者,每变化阶段之作用以求其适当”[13]。换言之,作者根据学科性质不同对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进行改编,把“知识类”科目的教学过程分为“预备、教习和应用”三段,把“技能”科目分为“预备、示范和练习”三段。张毓聪在《教育学》中论述“教授之阶段(教段)”内容时,认为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即后世五段教授之滥觞也”[14]。作者把孔子作为教学过程的肇始者,但是在教授学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教学过程始于“海尔巴德氏(赫尔巴特)”四段教授法及其弟子莱茵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认为“莱茵氏承启氏说,重加修订。颇适于教授实际。氏据心理上发达之理法分为三段即直观、概念、应用是也。自三段细分之则为五段,即预备、提示、连接、总括、应用是也”[14]。说明莱茵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源于赫尔巴特“四段形式教学阶段”。最后作者以莱茵“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为基础,依据教材的性质和儿童的心理发育程度对所授教材的教授方法(顺序)进行详细阐述。谬文功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文明书局,1906年)系国人较早自编的教育学教科书,在论述教授章节内容时,有关于“教式”的阐述。此外,其他教育学著作,如张子和的《大教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周维城的《实用教育学讲义》(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王炽昌的《教育学》(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朱兆萃的《教育学》(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等均涉及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介绍。
从国人编写的教授学(法)教材看,如朱孔文的《教授法通论》,“这是我国自编最早的教授法教材”[15]。作者在序言中阐明:“一是我国教授法,而非外国教授法;二是国民教授法,而非个人教授法;三是活用教授法,而非死煞教授法。”[16]4该书“教授之方法”章节论述了“教段”,即“依儿童心理之发达而定自然之顺序谓之教段”[16]5,作者认为,教段有两类,即裴斯泰洛齐的三段法(直观、概念和应用)和莱茵之五段法(预备、提示、比较、概括、应用),并对两类教段进行比较后,选择适合我国各科教学实际情况的教段,即莱茵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此外,其他教授学(法)教材,如湖北留学生编的《教授学》(湖北学务处,1905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的《教授法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蒋维乔的《教授法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钱体纯的《教授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等,均涉及“五段形式教学法”的内容。从国人编写的教育学和教授学(法)教材中关于“教段”的介绍来看,其形式虽然与赫尔巴特学派“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有区别,但正如俞子夷回忆:“日本通行的一套,本质虽不出五段法窠臼,但实施方式却不呆用五段法术语。有些科目,有些教材,很难用五段的框子硬套,似亦有些变通办法,例如有主张四段者,更有主张三段者。”也就是说,“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传入国内,国人对教学过程进行改编,使之适合国内各科教学。但是不管怎样改编,其“基调始终保持不变”[11]479。
总体而言,以教育学及教授学(法)教材为载体,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开始融入到我国教学理论中,为其传播和推广打下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以“课堂教学”为实践场所
清末学制的颁布确立了班级集体教学组织形式,为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导入客观上提供了可以依赖的实践场所。1904年,《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颁布,规定初级师范学堂科目包括“教育史、教授法、教育法令、学校管理法等”。并规定师范生于附属小学进行教学法练习。而“师范各科教员及附属小学堂长与教员,务须会同督率师范生监视其授业,品评其当否,且时自教授之以示模范”[17]。于是,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随着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法等科目的普遍开设和教学实习而进入课堂教学中。“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对当时的小学教学法有很大影响,据近代教育家俞子夷回忆:“首次大战前,小学教授法主要从日本输入,而其内容与本质主要是基于五段法的一套。”[11]478“自前清创设学校,规定教科,小学教员始知演习教授方法。当时赫尔巴特之阶段教授法传入中国,小学教员皆‘奉之为圭皋’。虽实际上或用五段,或用三段,不免变通之点,然其教授之原理,均以赫尔巴特派之学说为依据。”[18]当时清政府曾把教师讲课时是否按“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教授作为衡量各地办学水平的标准之一。俞子夷回忆:“初时过程的建立,均参照五段法理论。周维城最善运用,处处以是否合五段法为衡量、取舍标准。但后来师范生与一般教师只对过程有兴趣。”[11]479“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也被运用到私塾教学中。因此,自“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传入我国以来,便成为新式学堂的主要教学方法,曾被视为“科学教学法”的代名词。
(三)以“教案”为组织形式
所谓“教案”,是指“教师为其课业之准备,乃最其概要,造为教案。不徒以表教师之知识,且以示教授之方法。不徒以记将欲教授之事实,且以明教授之条理……故教案中最要之部即可为教师之考案也。至其体裁,则勿繁勿潦,举其要项,述其苦难,使用明了之解说,开发观念之要道,指点铭刻之心象”[19]。这段话对教案的性质及体裁进行了概述,即教案主要是为了教师上课做准备,并按照一定的体裁进行编写,以便教学的开展。如前所述,在《教授学》文末,作者附录6科教案,这些教案为莱茵编写(物理教授案系林德遵编)。教案的形式主要根据莱茵“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编写而成,即为“目的—大意—题目—方法(教学程序)”等式样。这些教案范本为我国教师实际运用“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提供了直观的参照系,使当时的中国教师能仿照这些教案进行具体课程设计。“五段教学法注重教案之编制。”[20]据俞子夷回忆:“南通师范第一班毕业之师范生。有时则忙于做教案,教案之工作,比作任何文章都难……此项教案编竣时,绞尽脑汁,然而缴与日本教师,终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发下重做,最后修改完结,差能交卷。”[20]据资料记载,《教授学》发表三年后,国内教师开始运用“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编写上课指导书,也就是“教案”,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教学参考书。1905年,中国教师“运用‘形式教学阶段’的原始教案,分别为直隶张景山的历史教案、直隶王书堂的修身教案”[12],这两个教案的编写分为“预备—提示—总括—应用”四部分。且每一阶段都是以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回答的形式出现的。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由问答式,行五段教授法’,这就是‘形式教学阶段’最初的中国实践形态”[12]。这即是由孔子式问答法与赫尔巴特五段法结合而形成的一种中国式的“教学阶段”。
除教师上课自编的教案外,教案也发展成为教科书的必备材料。“前清末造,初兴学校的时候,真不知道教授法为何事……所以当时官私编辑的小学教授用书,以及各小学实用的教授方法,殆无一不是适用五段教授法原理的。”[21]当时中学所采用的教学法,“其教授之良否,则纯视教材之是否丰富,说明之是否透辟为断。总之,学生所得,殆出自教授之授与。”[22]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每次出版教科书时,“内地教员多不知应用方法,于是每出一册,皆按照三段教授法次序加入练习、回答、联字、造句等,编辑教授法。而教授法销行之数目,渐见发达。”[23]俞子夷回忆:“书局竞编小学课本……而且教科书外,必备一套教师用的教授书,这又非真内行不可。教授书极详备,每课均有长篇教案,连同习题,教师可拿了径去上课,不必备课……这样,教授书销到哪里,那套教法也推行到哪里,传播面最广。”[11]477这种教学参考书成为教师上课的重要资料来源,一直影响到我们现今的教师教学。此外,为推广五段形式教学,当时《教育杂志》和中华书局竟相刊文征集教案。从教案内容看,主要以“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为依据编写,但也有一些会根据各科实际情况有所变动,或变为三段、四段等。因此,通过教师自编、政府倡导,使“教案”发展成为中国特有的“教学参考书”,成为教师推广“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合法渠道。
总而言之,通过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笔者分析了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由日本导入我国的文化特征与实践形态。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以心理学为基础,第一次构建了教学过程模式,解决了从个别教学向班级教学后如何有效地向更多学生进行班级教学的问题。“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因其操作性、程序性和实用性强,适应清末从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时期缺乏正规师资训练、教师水平较低的情形,使其迅速被国人知晓并运用于教学中。“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学习的心理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知识的讲解,便于学生掌握知识技能,这较传统教育方式有很大的进步。尽管在教学中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过于形式主义,但是这种教学方法一直成为班级课堂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一直影响到现今的课堂教学。可以说,“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传入我国后,以“教材”为载体,以“课堂教学”为实践场所,以“教案”为组织形式,进一步深入全面地渗透到整个教学过程中,促进了清末民初我国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师资培训和教材内容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M].腾大春,腾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65.
[2] 小原国芳.日本新教育百年史·总说[M].东京:玉川大学出版,1970:64.
[3] 小原国芳.日本教育史[M].吴家镇,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67.
[4] 崎昌男.学校の历史·大学の历史[M].东京: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79:34.
[5] 藤原喜代藏.明治·大正·昭和教育思想学说人物史:第1卷[M].东京:湘南堂书店,1970:667.
[6]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681.
[8] 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3.
[9] 田正平,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10] 吕达,杨晓.中日近代教育关系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99.
[11] 董远骞,施毓英.俞子夷教育论著选[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2] 杨晓.清末赫尔巴特“形式教学阶段”传入的中国变式[J].教育科学,2000(1):62-64.
[13] 秦毓钧.教育学[M].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8:79.
[14] 张毓聪.教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36.
[15] 董远骞.中国教学论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2
[16] 朱孔文.教授法通论[M].上海:时中学社,1903:4.
[17]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27-228.
[18] 孙世庆.中国之初等教育[J].北京师大教育丛刊,1923(4-2):21.
[19] 多田房之助.教授指南[M].东京:並木活版印刷,1902:13.
[20] 徐珍.中外教学法演进[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6:54.
[21] 康绍言,薛鸿志.设计教学法辑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21.
[22] 林励儒,程时烩.中国之中等教育[J].北京师大教育丛刊,1923(4-2):20.
[23] 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M]//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