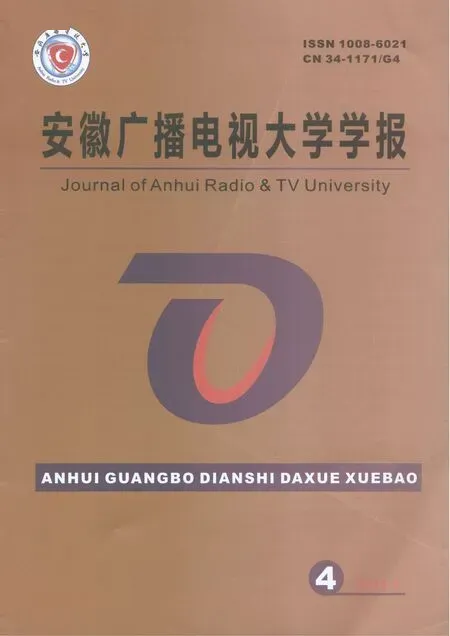魏晋士人重情之思想氛围与现实因缘
2014-03-20陈希红
陈希红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科研处,合肥 230022)
魏晋士人重情,并成为时代风尚,得到学界公认①较有代表性的有冯友兰、宗白华、李泽厚、罗宗强等学人的观点。,与汉代士风相比较,此一特点更显突出。因此考察魏晋重情士风原因,就不得不从大的时代性背景方面去体认。本文从“思想氛围”和“现实因缘”两方面着手此问题之研究②魏晋士人重情风尚的形成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士人的重情直接导源于汉末经学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礼法的破损,这是它出现的历史前提;其次,士族门阀的统治为士人重情乃至纵情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社会保障;再次,魏晋玄学提倡性情自然,为业已产生的士人重情风尚寻求理论依据,推动了重情士风的进一步发展;第四,魏晋时局的变乱,更使士人身寓乱离而自伤多情。关于魏晋士人重情风尚原因考察之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见笔者另文《试析魏晋士人重情之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发表于《合肥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一、思想氛围:玄学的现实人生主题与士人情感的自觉
伴随着两汉经学的衰落,魏晋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为自由”(宗白华语)的时代出现了。一时道、名、兵、法、农诸家重又涌现,东来的佛教也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儒学已从“经”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但也仍为一些人所尊奉。此时的思想界,引用曹丕《典论》的话说,就是“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思想多元,无所定准。一方面儒家独尊的地位已经动摇,另一方面人们急于寻找新的思想依归。伴随着士族的崛起,士人寻求既能表达士族的政治意图,又能解决汉末以来出现的社会问题的良方,便是在老、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玄学。玄学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它的核心是有无本末的本体论,及言意之辨的思维方法等理论问题。但玄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同时,具体地又化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就从理论问题变为现实问题了。在现实生活中,士人用玄学理论去认识、解决了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如“礼教”“仁义”“圣人有情无情”“养生”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任情自然”的新的人生哲学,从而在理论的高度上肯定了汉末以来的重生、重情士风,并使士人进一步地自觉于情。
(一)玄学的产生及其对魏晋士风的影响
玄学的产生,一般认为始于正始时期的何晏、王弼,是他们首先“祖述老庄立论”。老庄之学,原本在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属于官方“罢黜”之列,但在私下一直都有人在研读,有时甚至还被用来作为批判经学的武器。如西汉末的严遵,东汉初的桓谭,以及王充、张衡、冯衍等,一直到东汉末的仲长统,都在利用《老子》中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来反对经学化的僵化了的儒家思想。并且在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些儒家经学大师读老庄的情况,例如前举马融,还有他的学生郑玄,也曾以《老》解《易》。从“反动两汉经学”这一意义上看,他们可以算得上是魏晋玄学的先驱。曹魏以前,老、庄之学是作为一股潜流伏于经学之下的,正始中,道出儒伏,玄学开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士族门阀意欲建立统治。《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唐长孺先生指出,玄学家抬出道家,其一便是“重新发挥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指导怎样做一个最高统治者,这种政治主张随着门阀的发展与巩固,实质上是要削弱君权,放任世家大族享受特权”[1]。基于此,有人提出玄学为“政治哲学”[2]。
玄学在表达了士族的政治意图之外,还有指导士人在儒学价值体系崩溃背景下,如何安顿个人生命的一面,从而影响士风。这从时人对玄学的批评言论中即可见其一斑:“时俗放荡,不遵儒术”,“遂相仿效,风教凌迟”(《晋书·裴頠传》),“游辞浮说,波荡后生”(《晋书·范宁传》),均指玄学影响士风而言。《颜氏家训·勉学》于玄学影响士人风尚叙述得尤为具体详明: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异之度外。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角触死权之网也。辅嗣以多笔人被疾,陷好胜之井也。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无支离拥肿之鉴也。荀奉倩丧妻,神伤而亡,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赃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其余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者,岂可备言乎!
玄学非唯注经与“清谈”,士人引玄学思想为人生指导,见诸为人行事,形成一种“玄学风气”;在玄风的吹拂下,士人纷纷弃周孔之业,心许农黄老庄,唯情适性。即使在颜之推几近丑化的批评言辞中,我们仍能看出这一点。
玄学主要盛行于社会上层,在士族门阀中成为时尚,所谓“世重清谈,士推素论”(《宋书·蔡廊传》),“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梁书·王日柬传》)。在当时即便不是玄学家也免不了谈老庄,尚清谈,甚至反对和批评玄学的人也是如此。如著《崇有论》的裴頠就讨论有无问题,推崇老子,被人认为“仍是一个玄学家”[1]201。此外,许多儒家学者玄礼双修,礼学家往往兼注三玄,都可以说是玄风大畅的结果。这也是玄学能够影响一代士风的原因所在。
(二)玄学的现实人生主题与士人情感的自觉
玄学对魏晋士风影响的具体途径,是玄学士子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探讨。
汉末以来,由于士族势力的增强和政治地位的上升,他们的心态随之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人生理想与重情的士风,这就与传统名教发生了矛盾。因此士人迫切希望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思想观念,寻找理论上的依据。王弼等人通过对传统典籍中容易发挥自己思想的“三玄”——《易经》《老子》《庄子》的注解,借题发挥,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作了解答。如:
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王弼集校注·论语释疑》)
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注)
凡此诸或,言物事逆顺反复,不施为执割也。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老子道德经》二十九章注)
在这里,老子的“道”已化为万物之有,万物有道,自然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这是思想上的重大转变。“道”虽然没有改变其至高无上的造物功能,但并非高不可攀,人人可得而与之同。“道不违自然”,“达性”“畅情”就是顺其自然,就是“体道”。如此逆顺反复,王弼终于以“注”经的方法将名教引向了自然,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从而使得玄学由有无、本末等理论问题转向了现实人生中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说,亦即是顺从人情还是抑制人情的问题。这是士人对自我情感的一种理性反思。
既然“名教出于自然”,从这一思想出发,儒教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王弼在《老子道德经》三十八章注中注释“仁义”时说:
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忧患。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孔子当初是深患礼乐制度流为空疏的形式,故提出“仁”以为本,即以仁爱情感为礼之根据。汉代,统治者因名立教,礼及仁义乖失其本。至王弼,以自然解仁义,认为仁义应该是发自于内的自然本性,如果刻意为之,过分重视形式(“极其大”“盛其美”),就失去了仁义的根本(“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用其末”),就是假仁假义,其于孔子虽为异曲,却有同工之妙。
正始前后,士人在对待仁义孝悌上重自己真情的自然流露而有意识地不看重礼的形式的行为,除了表示对矫情的虚伪礼法的不满之外,实在也是对人类自身感情的内在真实性与外在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的反省,是士人在更深层次上内心情感自觉的一种表现。这也正是嵇康、阮籍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内在依据,是他们任情越礼而又不失“礼意”的根本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阮籍站在自然的立场对现实中名教的批判,是在他们理想中合乎自然的名教前提下进行的。嵇康与阮籍,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是经历了从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结合,再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变化的。如阮籍理想中合乎自然的名教是这样的:
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古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洽,保性命之和。
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阮籍《通老论》)
然而,当他们拿这个理想中的名教与现实相比较,结果却令人失望。嵇康《太师箴》:“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
应该说值王弼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之时,社会政治环境还算大体稳定。自曹爽祸起,以儒学世家为基础的司马氏集团对曹魏政权进行暴力倾夺,迫害残杀正始名士,并重又提倡名教,特别是孝道,以配合其政治统治。于是,名教中消极腐朽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自然与名教的矛盾急剧恶化,士人面临理想与现实的严峻冲突。因此,“越名教而任自然”口号的提出,既表明了士人对外在权威与桎梏的激烈否定和对理想生存方式的执著追求,也是摆在内心高度自觉之后的士人面前的唯一选择。由于名教实际上是一种无法超越的现实,于是他们只能生活在痛苦之中。《晋书·阮籍传》载其:“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其《咏怀诗》和嵇康的《卜疑集》,都反映了作者的这种精神状态。玄学发展到阮籍、嵇康这一阶段,其政治哲学的意味已彻底转变为人生哲学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士人们退回到自身,高扬自我意识,崇尚自然和超脱,在与代表皇权统治的名教的对抗中标榜自我与真情。
玄学中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促使士人对自我的意识不断深入,强调自我即是要顺应自然,即“任自然”。“任自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士人重情,即所谓的“任情而动”。为了溯本求源,给士人重情这一社会风尚寻找理论依据,玄学家们进行了一场关于圣人有情无情问题的探讨。针对何晏的“圣人无喜怒哀乐”,王弼提出“圣人有情”;至魏晋玄学的竹林时期,向秀标榜“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独化论”时期,郭象则以“俗内”与“方外”调和了先前的“有情”与“无情”之争。对圣人有情无情以及情礼关系的讨论,与魏晋玄学相始终。
二、现实因缘:时局变乱与魏晋士人的悲情
(一)时局变乱多死伤
汉末以讫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此“乱”,包括天灾与人祸两个方面。
两汉之际,中国气候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结束,气候自此开始转寒。东汉时期,几次春寒大雪,冻死了京都洛阳的不少贫民。与寒冷期的降临同步,这一时期恰逢太阳黑子活跃期,由此又导致了自然灾害的泛滥。从东汉以来到魏晋南北朝,自然灾害不断,其中以魏晋之世最为频繁。其时“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间中遇灾凡304次,其频度甚密,远愈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疫疾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3]灾荒饥馑,百姓或人相啖食。汉安帝元初六年,会稽郡爆发了大瘟疫。兹后,瘟疫就像无法摆脱的恶魔,在东汉后期频频出现,史不绝书,致使“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后汉书·桓帝纪》),“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后汉书·五行志》注)。频繁且又规模庞大的死亡,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和震撼。张衡于延光四年上封事曰:“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焦心,以为至忧。臣官在于考变禳灾,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营。”(《后汉书·五行志》)注建安二十二年(317年)大疫,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王禹早逝外,余下五人陈琳、王粲、徐干、应瑒、刘桢皆死于此疫,由是曹丕写下了哀恸感人的《与吴质书》。
自灵帝中平元年爆发黄巾起义后,大规模的战争便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其对生灵的摧残远甚于瘟疫。据《后汉书·皇甫嵩朱儁传》:东汉统治者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曾先后“斩首数万级”,“斩首七千余级”“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首获十万余人,筑京观于城南”“斩首万余级”“复斩首万余级”。又同书《董卓传》云:董卓败后,其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击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掠陈留颖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随后攻入长安,“放兵虎掠,死者万余人”;后来李、郭内哄,“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当初董卓逼献帝西迁长安之时,三辅户口尚有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有如下的诗句:
西京乱无象,豹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文选·哀伤》)
真可谓哀痛人寰,使人不忍卒读。曹操面对当时的战乱也感慨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嵩里》)然而,正是这位曹操,在战争中同样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屠夫:“初平四年,曹操击(陶)谦,破鼓城傅阳。谦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人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依谦者皆歼。”(《后汉书·陶谦传》)建安五年于官渡大败袁绍时,“前后所杀八万人”(《后汉书·袁绍传》)。这些尚是史有明载的,至若未记入史书的死亡数当更多。战乱多死难,统治阶级内部的残杀则让士人身不能免。
东汉和帝以降,皇帝多冲龄即位,于是产生了外戚集团同皇帝、宦官集团的拉锯战,一大批洁身自好、除暴镇恶的忧国之士,或惨死狱中,或暴尸街衢。两次“党祸”,更把对士大夫的迫害推向了高峰。曹魏取代后汉,不久又被司马氏所篡夺,其间短短几十年,士族阶级内部不断地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直至永嘉之乱,晋室南渡,渡江的的东晋朝廷仍是不断倾轧。士族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互相结为集团,相互攻难。士人们既处于这种种的利益集团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着统治者内部的互相倾轧。这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地位,甚至是生命。
无论是积极地参与,抑或是被动地卷入,士人面对死亡却是真实的。那不期而至的天灾,与狰狞机诈的社会,政治的播迁,人事的变幻,以及身边同僚的鲜血,亲友的尸骨,在在逼迫着他们思索:什么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何为个体的真实存在?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兼济天下”“修身养性”“建功立业”等等,都淡去了,生命中留下的只是一股悲凉之气。
(二)魏晋士人的生命悲情
在天命与人事的不断变换中,以“悲”为基调,魏晋士人的生命情感有一个不断起伏变迁的过程:由曹魏士人带有明显过渡色彩的忧情,到竹林士人的掩情,再到中朝士人的遗情,最后是江左士人的化情。[4]
曹魏士人,在由建安至正始的几十年间,他们先后经历了汉末军阀混战,瘟疫肆掠,以及曹魏代汉和司马氏代曹的政治倾夺。在他们身上,传统士人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理想尚未褪尽;但在人格风貌上,他们已没有了儒家士夫的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而是表现出清新的个性本色。曹魏士人正处于由儒家传统向魏晋风度过渡的阶段。无论是建安士人的“慷慨悲凉”,还是正始名士的“忧嗟”,都是他们积极的入世思想遭遇时局变乱而有所感发,他们是有志于天下的,但天命无常,人命危贱,使他们对于这个时代充满了忧患。
忧时伤世,感慨人生,使士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多了一份自觉之后的悲伤。曹操一面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前山夏门行》),一面却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而“少年真当努力”(《文选·与吴质书》)本是曹丕的人生格言,但他也不禁感慨“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文选·典论论文》)。曹植“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七首》),使他在悲悯时代的同时,又感怀个人之不遇。《文心雕龙·时序》说建安文学,“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的文情又何尝不是建安的士情?
何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他与王弼、夏侯玄、李丰等正始士人,亦是不忘世情积极仕进之人,但时代同样赋予了他们悲凉的心境。“鸿浩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世说新语·规箴》6条刘注引《名士传》)身居世俗险境,徒羡守宙真境,岂非惘然?
综观有魏一代士人,他们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并将自我与政治与仕途紧密相联系在一起,但时局命运又使他们对这个时代充满了忧患之情。这种忧患充满了儒家士子功业不成的悲哀;但在个性解放这个意义上,又超越了儒家士子舍生取义,将自我消融于大一统的政治生命中而忽视个体生命价值的传统人格精神,充满了对自我生命自觉的悲哀情绪。曹魏士人正是上承汉末士人辗转羁旅,追求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下启竹林士人对生命自觉体认的强烈意识。
由正始士人向中朝士人过渡,竹林士人无疑是整体魏晋士人的“亮点”,“魏晋风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以他们为原形而描摹勾勒的。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士人,在司马氏的名教统治和高压政策下,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正始士人追求自然的主张,并由正始士人的名教与自然的调和而走向对立,一任自然。竹林士人将目光从仕禄功名转向自我本身,对政治采取自觉退避的态度,发展玄学的自我解放意识。他们不仅有任情率真的一面,甚至有一发而为狂放怪诞的一面。但是,在狂放的下面,那一种正始以来的忧患仍然无法泯灭。也许是清醒地看到了政权争夺中士人们被迫害的残酷,这时士人的情感已不再是患得患失的世俗忧虑,而是一种在个性觉醒之后,对社会、对现实失望甚至绝望的沉痛悲凉的情怀。这一点在阮籍、嵇康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轻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此独伤心。”(《咏怀》)“徘徊”“忧思”“伤心”,这才是那率意命驾、醉酒佯狂之士的真实怀抱。放浪形骸如嵇康,欲啸傲畅游于世之表,其内心也有难抑的幽情。《赠秀才入军诗》云:“心之忧矣,永啸长吟。愿言不获,怆矣其悲。旨酒盈樽,莫与交欢。……佳人不在,能不永叹!”
努力超越于现实之外,但又不能真正“忘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始终横亘在他们的心头,这一层悲情,是任凭行为上如何放达也掩盖不尽的。
渡过了竹林士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激烈对抗的“掩情”,中朝士人没有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而是与世沉浮,逍遥卒岁,遗情中朝。他们一味地沉湎于世俗的享受,过着放纵自流的生活,如王衍、胡毋辅之之流。但是,西晋统治集团是一个“以杀夺滥赏始,以杀夺滥赏终的黑暗集团”[5],西晋士人多卷入了统治集团的“杀夺与滥赏”,在权利争夺的阴谋与杀戮中,很多士人死于非命。他们的死,既无东汉党人“一时俱逝”的惨烈,亦无嵇康“顾视日影,索琴而弹”的悲壮,但多少使中朝士人的遗情,带有一种竭力排遗而又无法排遗的忧虑和伤感。陆机临刑时,“欲闻华亭鹤唳”(《世说新语·尤悔》3条);石崇于八王之乱时会文士于金谷,具众士人之官号、姓名、年纪,怕的是“性命不永,凋落无期”(石崇《金谷诗序》)。
更有那“五胡乱华”的悲剧。无论王衍如何地巧设三窟,也无论瘐岂攵如何地慎简保身,两人终究免不了生于乱世的悲剧,一并为石勒所害。身在这样一个时代,士人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保持一份平和的心境。王尼尝叹:“沧海横流,处处不安也。”(《晋书·王尼传》)一语道出了内心的惶惑不安。当危难真的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园,仓皇南渡时,他们剩下的也只有一声悲叹了。一代清言名隽卫王介常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不见喜愠之容。”然而人世沧桑,面对国破家亡,江山沦落,即使再如何地“情恕”“理遣”,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卫洗马(王介)初欲渡江,形神惨卒页 ,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晋书·卫王介 传》)人说中朝士人格外的敏感多情,可谓其来有自。
江左士人可谓风流潇洒。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君主与士族共理国事的政治格局,苟安富贵的生活与江南的秀丽风景,构成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也渐渐消释了他们流亡江南之初的痛楚和尴尬。此时,玄谈风流、潇洒超逸成为江南名士主要的生活情趣,清谈和隐逸之风大兴,连有些皇帝和位重大臣如桓温、谢安等都热衷于此。这时的清谈与隐逸与以往已有些不同。清谈已不多重玄理的探求,更看重的是玄谈时的风度、气质、才情;而隐逸也已没有了以往穷独守节的因素,不仅为怡情养性自适,而且是获得高名的捷径。他们在面对自然山水时,也不再像中朝士人望春春哀,望秋秋悲,他们以玄对山水,面对明丽的风光,表现的是“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谢安《兰亭诗》)的达观与萧散的心境。他们在清谈、隐逸、山水之中,尽量将自我与世俗之累忘却,以清谈的美妙,隐逸的萧散与山水的美好来追求一个超越世俗的精神本体世界。这样,那纠结在魏晋士人骨子里的悲忧之情,表面上看是淡化了,消融在了东晋名士优雅从容的风度气质中,使他们的生命情感表现出那样一种淡泊的逍遥。
然而,“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晋书·王曦之传》),透过江南名士的达观与潇洒,还是让我们听到了他们心底的切肤之痛。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无论是儒家的执著于现实人生,还是道家的重生恶死,抑或神仙家的虚无缥缈的仙境,都无法让人们彻底忘怀现实中死亡的永恒存在,也难以掩饰内心的悸动和焦躁,因为对个体生命而言,死具有绝对的否定意义。这就使士人们在面对死亡这一问题时“欲说还休”,采取较为柔和、平缓、间接的态度,以一种哀怨忧伤的调子表现他们对于生之深情眷恋与对死亡的无可奈何的悲叹。
对于生命的有时而尽,传统的观念认为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让人精神不朽、垂名后世。然而,魏晋却是一个功业难成、德言难立的社会,这又使士人的生命悲叹加上了一重难言的苦痛,尽管他们早已安顿于江南的“佳山水”中,但“河洛丘虚”的噩梦让他们总是“生理茫茫,永无归依”(《晋书·孙绰传》)。悲情就在这其中游荡着,散发着,让千载而下的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苍凉之气。
魏晋士人的重情,不是士人的一时冲动,而是多重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它是对汉代经学礼法走向极端与僵化的反动,人情大过天,束缚人情的礼教终将走向衰败,而礼教的衰亡又成为魏晋士人重情的历史前提;从社会思潮看,以道家思想为源头的玄学,倡导返归自然本性,反对名教礼法,这又进一步推动着士人不拘常礼,率性而为,从而表现出“钟情我辈”的自觉;而魏晋政治变乱又让失去礼法束缚的士人血泪横流,慷慨高歌,进一步融身于性情之中。“情”之一字钟爱于魏晋士人,是有着深切的历史与现实因缘的。中国历史上也只有魏晋士人如此放达大度,潇洒风流,“称情而直往”,正是这一特殊的历史场景的产物。
[1] 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C]//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201.
[2] 杨德炳.魏晋南北朝的皇权与门阀[C]//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188.
[3]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影印版.上海:上海书店,1984:12.
[4] 张华建.从浓烈到淡薄:由六朝诗歌看魏晋名士生命情感的变迁[J].人文杂志,1994(3):107-112.
[5]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M].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88.
[6] 郭向.庄子注[M]//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萧统.昭明文选[M].李善,注.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
[13] 龙必锟.文心雕龙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4] 夏传才.曹操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15]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6]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9] 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1]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2] 王葆玹.正始玄学[M].济南:齐鲁书社,1987.
[23]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