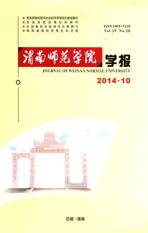食客文学集团与食客文学
2014-03-20杨宁宁
杨宁宁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南宁530006)
古代食客又有门客、门人、舍人、宾客、客等多种称呼,他们以寄食权贵、服务权贵、借助权贵寻找升官发财的途径为主要特征。食客始于春秋,兴于战国,分化、转型于秦汉。以往学术界研究较多的是战国四君子养客、用客以及食客的性质、活动等方面的情况。对食客文学集团及食客文学创作,至今没有人关注和研究。
一、由政治向学术转型
食客投身权贵门下,是希望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步入仕途。他们积极投身于政治外交,为主人出谋划策、斡旋,为君王出使。因为食客的奔走和努力,有时能够改变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外交形势,改变一些权贵的升迁废黜。食客在当时的影响可以用“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1]244来形容。许多食客因为他们为国家和君王的特殊贡献,被君王封赏赐爵,步入仕途,如蔺相如、毛遂等,成为新权贵,完成了他们身份、角色的转换。
汉代是食客转变、分化和衰落的转折期。食客由春秋战国的兴盛、壮大到秦汉开始出现分化,这种分化、转变与当时社会由动乱纷争走向统一稳定有着密切关系。西汉前期,延续战国养客之风,许多诸侯王和朝廷大臣仍以养客为时尚,其门下都聚集了众多的食客。从数量来看,西汉食客并不比战国少,但是从社会影响力来看,已经大不如前了。食客的作为和影响开始由政治转向思想学术及文学领域。
秦、汉时期,君与臣在食客的问题上出现了绝然相反的态度。对朝廷来说,食客成为威胁朝廷安全的危险分子;对权贵而言,食客成为他们对付朝廷的中坚分子,抗衡中央的军事力量。当权贵与朝廷发生矛盾冲突,充当马前卒的一定是食客。所谓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发生在战国末期秦国的嫪毐事件。嫪毐是秦王嬴政母亲的情人。他与太后生了两个儿子。因为得到太后宠幸,“赏赐甚厚,有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童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2]2511。在王政九年,嬴政成年将亲政时,恰好嫪毐被人告发,他凭借数千食客的强大势力敢与君王抗衡的事实给秦王敲响了警钟。嬴政是一个非常崇尚并身体力行君主专制的君王,他不能容忍王权旁落,或者遭遇威胁的情况发生,所以打击铲除食客势力成为他的当务之急。在嫪毐事件的第二年,即王政十年,秦王“大索,逐客”[2]230,在国中下了逐客令。后来因为“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2]230。以往谈到秦王逐客,都依据《史记·李斯列传》所载,因韩国人郑国修水渠的间谍事件引发。但是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来看,秦王政的逐客与嫪毐事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不像《李斯列传》说是因为郑国间谍案,而且《秦始皇本纪》没有提到郑国修水渠的间谍事件。另外,《史记·河渠书》载有郑国修渠的间谍事件,但只字未提秦王逐客。《史记·六国年表》记载郑国修渠的时间是在秦王政元年,而逐客是在王政十年,两事间隔近十年,如果说逐客与郑国间谍案有关的话,那么秦王不会等十年之后再逐客,那样意义就不大了,由此推断秦王逐客与郑国间谍案无关。
到汉代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如果说春秋战国的社会动乱是食客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条件,那么,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社会由动乱趋于稳定,由分裂变为统一。社会发生了转型,政治制度发生了改变。由春秋战国的分封制、宗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制度,向秦汉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转变。这些转变使食客原有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生存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到食客未来发展方向的改变。
汉王朝政权建立之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由过去对政治、军事、外交的人才需求转向对经济、管理方面的需求。社会需求的改变,直接影响到食客的转变。原来怀抱政治理想,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出人头地的食客,政治热情大为受挫。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改变。社会的安宁和谐以及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改变了人们对英雄、偶像崇拜的标准和要求。人们不再欣赏和崇拜那些乱世中脱颖而出的英雄,不再推崇和敬仰那些纵横捭阖、朝秦暮楚的游说食客。曾经倍受赞扬的食客不再受到世人的追捧和舆论的赞扬。到汉代,食客的地位和社会声誉较之战国时期已经是江河日下,呈现衰落趋势。
在西汉,食客虽然能够在权贵门下找到立足之地,谋得一职,但是他们对社会和朝廷的影响力及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他们受到了世人的冷遇。社会环境的改变和理想的破灭,在食客心中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同时也促使他们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这个改变就是由对政治的参与和干预转向对历史及学术的思考、研究与总结上。这种由政治型向学术型转化的倾向,在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食客中已经初露端倪。这种转变既有主人吕不韦的导向作用,也有秦王嬴政对食客干预政治的排斥,秦王下令逐客,就已经是一个信号。
西汉在政治体制上是汉承秦制,仍然延续秦王朝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战国时期那种民主、自由、开放、活跃的政治氛围已经被君主专制所取代。为了适应环境和制度的改变,为了迎合帝王、诸侯王及权贵对文学及学术经典的喜爱和重视,食客们投其所好,将自己的兴趣爱好、聪明才智和理想抱负由政治、外交转向对学术经典的研究。
西汉社会统一,政治趋于稳定,诸侯王不可能像战国时期那样致力于开疆拓土的政治、外交事业。他们将精力转向经济、文化、享乐方面。“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3]185西汉上层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诸侯王及朝廷大臣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学术造诣。从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对楚文化和楚文学都极其热爱。朝廷在思想学术领域,从西汉初期对黄老之学的推崇,到武帝时期对儒学的积极倡导,都得到诸侯王及朝臣的积极响应。朝廷广开献书之路,设立太学,大力扶持和倡导对道家、儒学经典的讲习、研究与传播。朝廷在选拔任用人才时,注重招选任用在道家或儒学经典研究上造诣深厚者,或者招选那些贤良的文学之士。汉武帝时期,“上方向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2]2953,以学问高者优先录用。当时公孙弘前往应征,“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策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2]2949。本来公孙弘在应试者中位列末尾,但是到汉武帝那儿,却被擢拔为第一,遂拜为博士,后又升为丞相。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2]2953,他因上书武帝言《推恩令》等事宜,深得武帝赏识,拜为郎中,“一岁中四迁偃”[2]2960。可见汉武帝在选拔人才方面有自己的考核标准和评价体系。朝廷对学术和文学的重视,促进了食客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集团的产生。
二、食客文学集团
最早的文学集团始于食客,这大概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一个文学集团的形成,是因为这个集团成员之间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如人生经历、理想抱负、志趣喜好、文学观念、审美追求等。这些共同的东西像纽带一样把文人联系在一起。文人们常在一起切磋交流,互相唱和,一起创作,鉴赏、评点佳作,针砭时弊。加上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领袖人物的出现,进而很自然地将这些有共同特点的文人聚集在一起,形成文学集团。
第一个文学集团是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食客文学集团,到西汉又有梁孝王文学集团、刘安文学集团等,这些文学集团的共同特点是其成员都是食客。他们是因为投身主人门下为食客而聚集到一起。这种文学集团与后来魏晋南北朝的各种文学集团有所不同。
什么样的组织称得上“文学集团”?他们有哪些特点?周晓琳对文学集团有如下定义:“所谓‘文学集团’,顾名思义,是由数位文人聚集而成的文学团体。这个团体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其一,它首先是一个文人聚合体,具有自己经常性的聚会活动。……其次,文学创作应当成为联结诸位个体的主要纽带或重要因素,集团成员需有共同的文学活动(常常表现为多同题作品和相互赠答之作)、相近的创作倾向以及较为突出的文学成就,正是这一点将文学集团与一般文人的政治集团或思想集团区别开来。其三,集团的存在与活动具有时空限制性,集团成员之间的文学活动通常以特定的地域为共同的空间背景,并且他们应该生活在大致相同的时代(其主要文学活动应该发生在其主要成员均在世之时)。……其四,文学集团在其形成与存续过程中应有领袖人物发挥组织、感召、凝聚的作用,并对整个集团审美趣味、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4]12-13
以周晓琳对“文学集团”的定义来看,食客文学集团,基本上符合上述条件,唯一不同的是这个集团的成员最初集结在一起的目的是为政治而非文学,他们文学创作的初衷也是为了政治需要。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学自身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由于汉代还没有区分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汉代文人皓首穷经积极从事或钻研的是学术或是经学的研究,而非文学。从食客文学集团集体创作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来看,他们是在主人的主持或召集下进行的集体创作,其目的是为了阐述、传播主人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纲要。无论是吕不韦还是刘安,都希望通过他们编撰的书籍来影响他们年青的君王,从而影响君王治国方略的制定和实施,从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的政治意图。这种情况是符合中国文学一直强调的“文以载道”的基本精神的。
所谓“食客文学集团”,是指那些出身平民,有着较高文学修养、学识及学术造诣,集思想家和文学家品格于一身的食客,在其主人的组织和指导下,进行文学创作,或是集体从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学术书籍的编撰工作。食客文学集团成员并不包含所有在其权贵门下的食客,只有在主人召集下进行学术研究或文学写作的食客,才能视为食客文学集团的成员。食客文学集团与后世各种文学集团相比,有一些不同。就是这些人的身份都是食客或宾客,他们受权贵供养,与权贵之间形成一种供养和依附关系,所以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一定的依附性,这种依附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身上缺少一般文人学者的独立、自由、洒脱和豪放的性情,多了几分世故、圆滑、委婉、屈从和谨小慎微。作家身份角色的不同自然会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一)吕不韦文学集团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载:“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2]2510从记载看,吕不韦招揽食客并组织他们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与其他诸侯国在政治影响和文化方面进行竞争。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却另有说法: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2]223。这里直接点出吕不韦招致食客是为秦国的统一天下做准备。他令宾客撰写《吕氏春秋》,目的是为了在思想舆论上为秦国统一天下造声势,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非文学的目的。吕不韦对于秦国未来的发展,秦统一天下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他有自己的思考和设想。他思想活跃,有开放包容的胸襟,加上他丞相的特殊身份,使一些思想活跃、积极进取,有追求和抱负,又有较高学术造诣的文人知识分子纷纷聚集到他的门下。
吕不韦是主人,又是《吕氏春秋》写作的主持人。由于该书是一部有计划、有目的编撰的书籍。在创作当中,必然会有分工协作、统筹计划和安排。可以推想食客在写作的时候,彼此会有思想的沟通与交流,写作的讨论和评议,甚至互相批评等活动。当时正处于战国百家争鸣的时期,食客之间为写书互相展开探讨、交流和争辩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都可以视为早期文学集团活动的萌芽。虽然这些活动与后世文学集团作家的相互唱和、评议、评点的文学批评活动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文学集团活动的起源和发端。食客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活动中逐渐地形成了文学集团。当时虽然没有文学集团的叫法,但是他们的活动和创作都已经符合了文学集团的基本特征,所以把参与写作《吕氏春秋》的食客称为吕不韦文学集团,应该是无可争议的。
中国文学的自觉和文、笔之分,是到魏晋时期才出现的,所以吕不韦文学集团并不像魏晋时期的文学集团那样,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的特征那么鲜明突出。这不仅反映出早期文学集团的创作活动的最初状态,还说明最初文学集团的形成与政治及政治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从吕不韦文学集团创作的《吕氏春秋》来看,食客们由对政治、外交的兴趣和影响,开始转移到对思想学术及文学的兴趣上。吕不韦文学集团和《吕氏春秋》,给后世食客的发展转变起着一个导向性的重要作用。它的问世,是食客文学集团集体创作的结晶,是食客文学集团集体活动的历史见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梁王文学集团
西汉时期,延续战国的养客之风,王侯贵族招纳食客风气日盛,成为一种时尚。像刘邦的儿子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肥、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太子刘启、儿子梁孝王刘武;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鲁恭王刘余,还有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等,纷纷开馆延客。徐复观指出:“两汉承先秦余绪,游士之风尚盛。此即诸侯王及富贵者门下的宾客。宾客之品类不齐,多随主人之所好而类集。但有一共同特点,他们都是社会上比较富有活力的一群。诸侯王中若有好学自修之人,则其所集者多在学术上有某种成就之士;于是宾客之所集,常成为某种学术的活动中心,亦为名誉流布之集中点。”[5]107
西汉一些诸侯王由于喜爱文学或学术,他们礼贤下士,延揽才华横溢的食客,有意识地招纳那些富有学术思想或文学才华的宾客。“由于藩国诸侯和汉初文人们的共同努力,大约在汉景帝时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人集团。”[6]170其中以梁王刘武和淮南王刘安的食客文学集团最具影响力。另外还有河间献王刘德的文学集团、吴王刘濞的文学集团。河间文学集团以研究、讲授儒家经典为主,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到该集团文学活动的情况。吴国文学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枚乘、邹阳、严忌早期的文学创作活动是在这里开始的,但是后来因为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劝谏无果,才离开吴王,投到梁王门下,成为梁王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
“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3]157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梁王刘武因为喜好文学,他招揽的宾客多以文学著称。唐代顾况曾言:“梁孝王时,四方游士邹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晏处,更唱迭和。天寒水冻,酒作诗滴,是有文雅之台。”[7]5371顾况所言情况“说明了梁孝王艺术旨趣,为众多文人幕僚所倾心,诚如高适说‘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在此文雅之台,邹阳、枚乘、枚皋、司马相如、羊胜、公孙诡、路乔如、丁宽、韩安国等人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文学天才”[8]112。梁王为其文学集团成员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使他们感到自由、舒适和惬意。
梁王文学集团的食客没有留下集体创作的佳篇,但是,其集团成员许多都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像邹阳、枚乘、枚皋、司马相如等。他们创作的散文和汉赋,代表了西汉文学的最高成就。像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大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他们的作品在汉赋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他们都是梁王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可以说梁王文学集团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们创造了汉代文学的辉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
据《西京杂记》卷四“忘忧馆七赋”条记载:“梁孝王与诸文士枚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邹阳、公孙乘、韩安国等游于忘忧之馆,使各人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9]26-28一些文学史对这组汉赋作品多有怀疑,刘跃进认为:“《西京杂记》所述的梁孝王宾客作赋事,虽然不一定确有其事,但是其文化背景还是很有可能的。”[8]116-117这一看法是比较客观合乎实际的。我们对这组赋的真实性可以打问号,但是梁王文学集团的文学活动应当是客观存在、真实可信的。
梁王文学集团名人多,佳作多,许多成员在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家,如枚乘、司马相如、邹阳等。另外其成员有是非观念,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忠于主人,更忠于朝廷。像邹阳、枚乘最初都在吴王刘濞门下为食客,但是当他们发觉吴王有谋反企图时,不是一味愚忠地帮助主子策划。他们出于对朝廷的忠诚,对主子的负责,对吴王委婉、诚恳地劝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劝说无效时,他们都毅然选择离开,另择明主。
韩安国两次为主子梁王排忧解难,更体现出他鲜明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梁王因为“出入游戏,僭于天子。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主所为”[2]2857-2858。韩安国以梁使身份去拜见梁王的姐姐长公主,陈述“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2]2858,在吴楚七国叛乱时,梁王毅然为朝廷解忧,令军队击退吴楚,使“吴楚以故不敢西向,而卒破亡”[2]2858。一再强调,朝廷击破吴楚,“梁王之力也”[2]2858。在此基础上,说明梁王僭越行为,不过是夸耀于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2]2858。并无过多的非分之想,更无藐视朝廷之念。语词诚恳,娓娓道来,说服了长公主。通过长公主的疏通,解开了太后和景帝的心结,“其后梁王益亲欢”[2]2858。
袁盎曾反对让梁王做景帝的接班人,为此梁王派人刺死袁盎及其他议臣十余人。事后梁王将该事件的主谋,他的食客公孙诡和羊胜藏匿府内,躲避朝廷搜捕。韩安国深明大义,不是一味愚忠,对梁王所犯的错误不包庇怂恿,他诚恳耐心地劝说梁王,以太上皇与高皇帝及景帝与太子刘荣的事为例,说明“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2]2860,指出他“犯上禁,桡明法”[2]2860,性质非常严重。使梁王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交出刺杀事件的主使,向朝廷谢罪,使事件得以圆满解决。在朝廷与主子处于矛盾对立的情况下,韩安国能够做到对主子负责,对朝廷尽忠,将矛盾化解,体现出他明辨是非,善于化解矛盾的能力和水平,非常难得。
(三)刘安文学集团
刘安父刘长是刘邦的少子。刘长因犯罪被文帝流放蜀郡,途中绝食而死,当时刘安才五六岁。特殊的身世和家庭对刘安有一定的影响。“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祕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10]2145
从这段史料来看,刘安有着学者、文人的气质,他不像其他诸侯王热衷于政治,或醉心于奢华生活。他拥有一块封地,却没有精力和兴趣去经营它。他喜爱读书、鼓琴,热衷于学术研究,著作颇丰,据《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作有赋八十二篇[10]1747,可见刘安的文学才华非同一般。由于他礼贤下士,学识渊博,“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他是汉武帝的堂叔,“时武帝方好艺文”,非常赏识他的才华,称赞他的学识和文笔。但凡刘安上朝,武帝会见之后都高兴地宴请他,与他谈论古今政治的得失,谈论诗歌辞赋,以及天文地理方术技艺等,兴致之高,常到天黑才作罢。刘安将新作《内篇》献给武帝,“上爱祕之”。武帝连发给淮南国的诏书,都怕行文有不妥让叔父笑话,都要先给司马相如看过修改之后,才敢发出。
武帝曾让刘安写一篇《离骚传》,早晨下诏,他才思敏捷,不长时间即完成。他写的《离骚传》颇含深意,他“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其叙述中所流露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烦冤悲愤之情,不仅是表白屈原,亦实际是表明他自己。这正是把他处境的困惑,及心理的危机感,向一位新即位的青年皇帝的投诉”[11]112。刘安将身世之悲,心中之哀,处境之艰都倾泄于文,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
刘安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礼贤下士的爱才之举,吸引了数千宾客聚集他的府上。据《汉书·伍被传》载:“淮南王刘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10]2167估计在他数千食客中,以学术见长的文学英俊有百数之众。据此推测刘安文学集团的成员当有“百数之众”,具体承担《淮南子》写作的应当出自“百数之众”。高诱《淮南注叙》记录了刘安文学集团的一些活动情况: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12]1。可见,刘安对其文学集团的参与、指导、关心和帮助要超过吕不韦和梁孝王。吕不韦因为是秦丞相,日理万机,对其文学集团的活动及文学创作的关心和帮助,主要在思想理论的宏观指导和物质条件提供保障上。梁王对其成员是礼贤下士,人格上予以尊重和信任,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刘安不同,他是亲自参与文学集团的活动。他与食客经常谈论学术,点评时政,思想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他们谈论时局政治,谈论文学,在切磋交流中不断提升各自的文学修养和学术品味,提高他们文学创作的水平。《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10]1747估计这“群臣”应该大部分或者全部是刘安的食客。这四十四篇赋的篇名现在无法知道,但是它说明刘安文学集团的文学创作成绩斐然。这些赋的作者,有部分可能也是《淮南子》的作者。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学繁荣,往往与这个时代、社会是否出现庞大的文学集团有关;一个文学集团的出现,往往需要一个能够为集团提供文学活动所需的物质与精神条件的人物出现;一个文学集团的存在、发展及其影响力的大小,往往与一个是否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和这个集团盟主的政治权力、经济实力、文学爱好、为人笃厚的程度有关。”[13]113从吕不韦到刘安不过百年时间,就产生了三个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食客文学集团,他们对汉代文学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集团的萌芽和发端。食客文学集团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最直接,据一些学者统计,仅魏晋南北朝各种文学集团就有十多个。食客文学集团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建立、发展和成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食客文学
食客集体创作的作品有《吕氏春秋》《淮南子》。两书有诸多共同之处:其一,都是食客文学集团有计划、有目的的集体创作。其二,都吸收融合了诸子各家思想学说,体现出多元的思想内涵。这是因为食客来源广泛,有受诸子各派的影响,有的本身就是一学派的弟子,他们将自己学派的思想表现于书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了。食客本身就思想活跃,有锐意进取、敢于改革创新的精神,敢于破除条条框框的约束,不墨守成规。其三,融哲学、历史与文学为一体,延续了先秦文学文、史、哲不分的特点,又表现出文、史开始逐步分离的趋势。两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前人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这里不再赘述。
食客个人作品含他们早年为食客时的作品,及从政后的作品。
(一)散文
李斯是最早有名字记录的食客作家。他现存作品主要是散文,有《谏逐客书》《督责书》《上书言赵高》《狱中上书》及7篇刻石文。《谏逐客书》是其代表作,刘勰评价曰:“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14]69这篇文章言辞恳切,以理劝人,以情动人,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对汉大赋有一定的影响。文章打动了秦王,使他收回了逐客令。李斯的7篇刻石文,是他在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七年随秦始皇登泰山、会稽山作的。6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另一篇《峄山刻石文》见于清代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卷一。关于此文,《史记·秦始皇本纪》曾有提到:“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2]242李兆洛曰:“此文《史记》独不载,然其词固非后人所能伪也。”[15]1其言极是。这些刻石文内容基本上是对秦始皇业绩、功德的颂扬。结构除琅琊刻石外,基本三句一章,每句四言,韵脚也是三句为基本单位。语言严谨、庄重、典雅。“李斯刻石文采用的基本都是平铺直叙的笔法,很少运用比喻,在极其有限的运用比喻的地方,都继承了先秦文学所奠定的原型,从中可以看出他与前代文学的渊源关系。”[16]80
《督责书》《狱中骂秦二世》《狱中上书》几篇散文是李斯后期作品,作于秦二世之时。《督责书》作于秦二世元年,是阿谀奉承的违心之作,食客特有的依附、取媚、巴结、讨好、阿谀奉承的特性,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表现了一个委曲求全又卑鄙无耻的御用文人和媚臣的形象。《狱中骂秦二世》是李斯从丞相变为阶下囚时写的。他一改过去奉迎取媚的态度,而是批评中有劝诫,语重心长中显露出真情实感。《狱中上书》是李斯在狱中写给赵高的。他正话反说,表明自己为秦国的发展壮大立下汗马功劳。由于身份角色的转换和处境的不同,文章反而写得真情流露,写出了他内心的真切感受。
邹阳现存作品《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上吴王书》是邹阳对吴王刘濞试图谋反的规劝。食客的身份,使他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进行劝说,常用隐语,意在言外。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10]2343这是邹阳写作《狱中上梁王书》的背景,当时他遭人妒忌诬陷,被下狱,他写了《狱中上梁王书》。在文中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17]339,文章比物连类,词多偶俪,语言铺张扬厉,文采飞扬,真挚动人。梁王看后“使人出之,卒为上客”[2]2478。该文引证史事50 多处,涉及人名100个,用事“是这篇文章典范的表达方式之一,它对后世隶事用典手法的成型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意义并非只现于表达形态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为文学散文观念化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思想方向”[18]40。有学者认为:“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垒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19]1719吴汝纶也说:“此体乃邹生所创,其源出于风骚,隶事至多而以俊气举之,后人无继之者,由是分为骈体矣。”[20]541由此可见,骈体文与食客和食客文学还有着渊源关系。
枚乘的散文《谏吴王书》写于吴王刘濞将反未反时,他以隐语微讽的方式劝诫吴王谋逆之举不可为,若为之的恶果。指陈利害,旁敲侧击,言辞恳切,态度鲜明。他的劝诫没有得到吴王的采纳。吴王刘濞造反暴发之后,他又《上书重谏吴王》。这一次他直截了当向吴王指出:“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10]2362反叛朝廷,无疑是以卵击石,吴王应当悬崖勒马,停止叛乱。文中体现出他对时局冷静的分析判断,为维护国家统一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汉朝廷的耿耿忠心。枚乘文章“以文辩著名”可谓名副其实。
司马相如散文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其散文具有赋体风格,在汉代散文史上较有影响。《喻巴蜀檄》作于武帝元光二年,当时“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2]3044。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巴蜀,调查事件原委,安抚民众。文章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体谅民众诉求,又维护国家的基本利益和大政方针,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使将要动乱的事态得以平息,体现了司马相如的应变能力和处置复杂问题的水平。《难蜀父老》作于元光六年。武帝再次大规模征发巴蜀民众修南夷路,引发民众不满。公孙弘奉命出使归来,“盛毁西南夷无所用”[2]2950。当时汉匈战争已经持续几年,国力难以支撑,公孙弘主张暂停开发西南夷,武帝不仅不接受,还让司马相如驳斥公孙弘。司马相如为此写了此文。文章体现出食客文学家托辞讽谏、左右逢源的特点。他假托巴蜀长老为民请命,以使者语气驳公孙弘“通西南夷不为用”的论调,骨子里却赞同他的建议,停止修建通往西南夷道路,全力对付匈奴。《谏猎疏》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2]3053,劝谏武帝不要因一时的乐趣而忽视突发的祸患,指出“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2]3054,提醒武帝射猎要防患于未然,武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封禅文》是司马相如的绝笔之文,该文直接促进了汉武帝封禅典礼的进行,是古代唯一一篇阐述封禅意义的文献,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二)辞赋
汉代最著名的两位辞赋家都曾是梁王的食客。枚乘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他有赋9篇,今存《七发》《柳赋》《菟园赋》,但是后两篇的真伪尚存争议。《七发》的内容是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视,以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写展开。作品意在劝诫贵族放弃奢华享乐生活,以精神修养取代物质欲望,从物质享受超越到精神享受。《七发》对山川景物的描写极尽铺陈,其中有200字描写音乐。音乐是一种抽象艺术,它丰富的内涵和优美的韵律很难用文字来描写。《七发》对音乐的描写体现出很高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后世许多表现音乐的作品都受它的影响。《七发》在多方面开拓了文学题材,如观涛、狩猎、车马及音乐的描写前所未有,开“劝百讽一”之先河。《七发》的成功,受到众多文人的追捧和效仿,主客问答体逐渐成为汉赋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它脱离了楚辞抒情咏怀的传统,转变为以铺陈写物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文体。它不仅体现了骚体赋向汉大赋的转变,还“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3]188。刘勰称赞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17]124
《七发》写作时间,传统观点认为写于梁孝王处。但是赵逵夫、刘跃进认为写于吴王处。“如果是在吴楚之乱以后所作,当时曾经从吴王濞游者唯恐洗刷不尽同叛逆者的关系,尽管枚乘以进谏吴王二书受到朝廷的嘉奖,恐亦不至于以作为吴王门客往问楚太子疾的事为题材而著为文章。所以《七发》作于枚乘在吴王濞处的时候,可以肯定。”[21]4从枚乘早年曾为吴王食客来推测,赋中的吴客不一定是虚构人物,很可能就是作者本人,是枚乘作为食客外交出使的场景再现。在枚乘为吴王食客时,曾代表吴王探视生病的楚太子,出于使命所需和食客的特殊身份,他探病之时借机委婉劝谏楚太子,使命完成,《七发》也孕育产生。
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代表作家,《汉书·艺文志》录他作赋29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录4篇,《子虚赋》《上林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都将两篇合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到《文选》又被一分为二)《大人赋》《哀秦二世赋》。《昭明文选》有《长门赋》,《初学记》《古文苑》中有《美人赋》,两赋都有序文,皆言司马相如作。但是两赋的真伪尚存争议。
《子虚赋》《上林赋》内容是以楚子虚与齐乌有及亡是公三人的对话,描写诸侯王及天子田猎之盛。《子虚》是司马相如在梁孝王门下为客时写的,故以梁园作为参照物。《上林》是被汉武帝招后所写,故以上林苑作为参照物。两赋通过盛赞诸侯王与天子苑囿的广大、物产的丰饶、田猎场面的壮观,来体现诸侯国的实力与强大,而天子之强盛又在诸侯之上。两赋显示出相互的攀比炫耀、争强好胜的心理。这种心理极其符合食客的心理特征。司马相如的食客身份和经历使他在表现这种心理时如鱼得水,恰到好处。两赋的主旨是为了歌颂、炫耀诸侯王和天子的声威、气势和宏大伟业。它突破了过去中国文学传统的怨怒讽谏的主题表现。这种主题表现与作者司马相如的食客身份有着密切关系。因为食客的从属性和服务性,使他在汉赋创作时把这种服务意识体现于作品中,变成为一种“润色鸿业”,取悦君王的歌功颂德的主题表现了。由于他先为梁王之客,所以写于此时的《子虚赋》是对诸侯王的颂扬、夸耀。当他成为天子宾客之后,《上林赋》自然变成了对天子的赞美与夸耀了。汉武帝“作为一位好大喜功的封建帝王,他更喜欢润色鸿业的作品。这在其对赋的欣赏活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上林赋》重在贬诸侯而扬天子……面对赋的颂美与讽喻,汉武帝更关注的是前者,这也是古代帝王的普遍心理”[22]41-44。
据《西京杂记》记载,邹阳作有《酒赋》《几赋》,但是真伪目前尚未确定。还有枚皋,《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120篇,现在已经一篇不存。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使我们对枚皋的文学成就难以作出恰当的评价,这是非常遗憾的。《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收录有淮南小山作的赋《招隐士》,从中可以看出食客作赋的成就及影响。
(三)食客文学的特点
食客文学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口头文学和秦汉的书面文学两个阶段。春秋战国的食客为主人或君王出使、斡旋,他们游说虽然事先也有准备,但是很多时候都要根据形势需要和现场情况,临场发挥。食客口头文学讲究的是即时性、现场性和随意性。为了说服对手,食客好故弄玄虚、危言耸听,所以久而久之,人人都练就了极强的应变能力和能言善辩的语言表现力。虽然食客和纵横家的游说词后来被《战国策》《史记》等文献记录下来,但是已经被记录者加工润色,它既不是纯粹的食客口头文学,也不是食客的书面文学,只能把它看作食客历史活动的记录。
秦汉时期,随着食客政治、外交活动的减少,他们把人生的重心和兴趣放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食客书面文学也开始形成。综观食客文学(书面文学),有如下特点:
第一,规讽劝谏的责任意识,出谋划策的服务意识。食客文学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关心国事,讽喻劝诫的积极参与意识。无论是散文还是汉赋,食客创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向主人或天子进谏、劝讽,而非抒发个人感怀。所以表现的是食客对主人的讽喻劝诫,对国事的高度关注与关心,而没有后世文学,尤其是诗歌那种感怀伤时、怀才不遇的情怀和基调。
第二,铺排夸张的表现形式,攀比炫耀,争强好胜的虚荣心理。食客作品大量地运用铺排夸张的表现手法,折射出食客强烈的攀比炫耀的主观意识和争强好胜的虚荣心理。由于食客与主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所以他们夸赞炫耀主人的背后,体现的是他们爱面子、好表现的心理诉求。这种好表现,既是为了宣传和表现主人的实力、权势,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食客这种爱炫耀、好表现的特点,无意识中形成了秦汉文学铺排夸张的特点。
第三,语言华丽,词采繁富。食客文学由口头文学发展为书面文学,都非常注重语言词采的运用。它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了文章的语言辞句。尤其是食客在汉赋中对宫殿建筑、山川景物、田猎场面及都市生活的描写,虽然有堆砌词藻、好用生僻字词的不足,但是它对促进文学语言的发展,启发人们的文学想象力和文学表现力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文体以散文和辞赋为主,没有诗歌,这与创作者食客的特殊身份有很大关系。食客的服务性决定了他们有责任和义务为主人出谋划策,对主人的行为过失和错误有提醒、劝说、告诫的责任和义务。所以食客文学创作的目的和宗旨,是为主人的政治前途和未来发展作谋划,说理文和汉赋最适合表现这些内容。
第五,缜密的逻辑性,清晰的条理性,多彩的文学性。因为是书面文学,所以食客在写作时有长时间的思考和谋篇布局,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在写作之前就对书稿编撰作详细的计划和安排,所以两书的结构条理清晰,分析阐释逻辑严密。特别是两书继承并发展了先秦诸子散文运用神话和寓言故事的传统,使这两部哲学著作极具浪漫多彩的文学气息。
综上所述,秦汉社会由战国的动乱趋于稳定,由分裂变为统一。社会的转型,政治制度的改变,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决定了食客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食客政治前途的无望,导致了食客的分化转型。食客在政治上的不幸却造就了他们文学上的成就。不仅促成食客文学集团的产生,同时造就了一大批食客文学家和食客文学作品。食客文学家的产生又一次印证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规律,也是屈原、李白、柳宗元等许多文人的共同经历,即文人政治前途的无望能够成就优秀的文学家。
[1]诸子集成·孟子正义·滕文公下[M].上海:上海书店,1986.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周晓琳.中古文学集团考辨[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2 -13.
[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刘向斌.试论汉初文人集团的地域成因[J].青海社会科学,2008,(1):170 -173.
[7][清]董诰,阮元,徐松,等.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九·宋州刺史厅壁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跃进.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J].深圳大学学报,2008,(1):111 -119.
[9]程毅中.西京杂记: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诸子集成·淮南子注·淮南子叙[M].上海:上海书店,1986.
[13]普慧.齐梁三大集团的构成及其盟主的作用[J].社会科学战线,1998,(2):106 -113.
[14]黄霖.文心雕龙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5]李兆洛.骈体文钞[M].上海:上海书店,1988.
[16]付志红.李斯作品的文学观照[J].延边大学学报,2006,(1):77 -82.
[17]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8]刘国斌.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用事与文学散文的产生[M].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11,(5):38-40.
[1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法海[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0][清]姚鼐.古文辞类篡[M].北京:中国书店,1986.
[21]赵逵夫.《七发》与枚乘新探[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4 -11.
[22]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