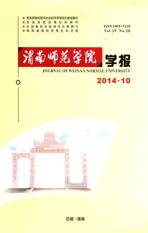《史记》成书的主客观条件
2014-03-20段永升
段永升
(咸阳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司马迁倾其一生的心血完成了《史记》创作,这部著作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因而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435。关于《史记》的创作原因,学界有多种看法,如“发愤著书说”①“发愤著书说”:因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之说法,故从司马迁时代以来“发愤著书说”就一直为人们所认同。“历史条件说”[2]92-95“元动力说”[3]58-63。这些说法都有其道理,从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解释了《史记》成书的原因。然而,这些说法都没有做到对《史记》成书条件的整体观照,故而不免有些零碎和片面。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种伟大创造与发明的出现,都是主客观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聚合的结果,是“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共同促成的,而非单方面原因能够成就。《史记》的成书也符合这样的原则,是主客观两方面条件成熟的必然结果。本文拟从主客观条件两个方面来探究《史记》的成书与创作。
一、《史记》成书的客观条件
《史记》的成书与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以及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临终遗命关系密切。这三者共同为《史记》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诱因,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一)政治历史条件
人常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时势也可以创造出伟大的著作。这里所说的时势,就是政治历史条件。《史记》能够在司马迁时代出现,也是大汉朝当时的时代要求。关于《史记》创作的政治历史条件的问题,陈杰林先生早在1994年就从四个方面作了详细论述,概括起来内容如下:一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史记》的问世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经济的繁荣为《史记》的撰写注入了农、工、商、虞四者并重的经济学思想;三是西汉时期文化的繁荣为司马迁修史提供了条件;四是思想上的开放多元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2]92-95在文中,陈先生认为这四个方面合起来就构成了《史记》创作的客观条件。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可以涵盖在“政治历史条件”这个范畴之内,而冠以“客观条件”的名称,实则有些名大于实了。
的确,汉王朝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在继承秦朝大一统王朝各种典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进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鼎盛的封建王朝。汉朝发展到司马迁时代,在经过高祖、惠、文、景和武帝五代帝王的苦心经营之后,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发达、政治开明的强盛王朝。这样的大一统时代,就需要总结前代兴亡的历史经验,以图自己当朝的统治能够长治久安。为此,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上颁行一系列政策法规,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的统治。司马迁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身为史官,总结前代兴衰变化之迹,撰写一部包罗万象、内容宏富的通史,为当代统治者提供借鉴,既是时代赋予他的伟大使命,又是时代对他提出的要求。于是,司马迁“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4]2723,著成《史记》。司马迁著《史记》,除了以上内容搜罗完备之外,他“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2735。这样博大的胸襟与明确的著史意识也是伟大时代的赋予。正如台湾学者赖明德在《司马迁之学术思想》一书中说:“司马迁是我国继孔子之后,二千多年以来历史文化界最伟大的巨人。他那卓越的历史观点,丰富的人生体验,深刻的社会见解,精湛的学术造诣,以及高度的文学修养,除了一部分得之于秉赋之外,大部分都和他所生长的时代与社会有不可割断的密切关系。”[5]1
总而言之,《史记》的出现是大汉朝伟大时代的要求,与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关系密切。如若没有大一统帝国的赫赫声威与繁荣鼎盛,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这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不可能出现。
(二)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
中国是一个重视修史的国家。《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6]877班固也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也。”[4]1715历代君王都重视对历史的记录。因而,史官在上古时期虽然职位不一定很高,然而其地位却是相当尊贵和重要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职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7]269中国人之重史可见一斑。
我国著史的历史很早,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而且各种史书体例在那时也已基本确立。秦汉以前,早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以各种方式记载历史。这些史书,不仅保存了前代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为后代修史的体例、方法等提供了借鉴。司马迁正是在前代史学积淀的基础之上创作出了《史记》。然而,司马迁创作《史记》并完全没有照搬、照抄先秦时期的任何一种史书体例或叙事的方法,而是做了重新综合、提炼和创造性的开拓工作。白寿彝先生就曾说:“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史记》应该说是综合体。它把过去记载历史的各种体裁都综合起来了。虽然其中任何一种历史体裁都不是独创,但经过综合提炼,使它们相互配合成为一种完整的形式,不是单凭他的能力就能办到的,这同长期以来的历史渊源有关。”[8]11-12的确如此,若没有前代的史书创作经验积累,单凭司马迁个人,是无法创造出《史记》的综合体体例的。我们都知道,《左传》和《国语》是战国初年的重要史书,尤其是《左传》,已经是综合体的史书了。《左传》不仅仅是鲁国一国的史书,而且采用了多种历史体裁,将当时主要国家的历史都做了记录。因此,综合体史书也不是从司马迁开始,从《左传》就已经开始了,司马迁只是将前人的著史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
白寿彝先生从《史记》的五种体例——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角度,对《史记》与前代史书或经书的承继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从题材上说,‘本纪’是从编年体来的。‘世家’是记各国诸侯的历史,是从各国史来的。……以前《诗经》的《生民》、《公刘》以及战国时期史家所纂言行录之类,都是传记。《史记》的‘列传’继承了这种体裁。‘表’就是根据战国时期的谱牒而来的。‘书’是综合论述的形式,也有一些纪事本末的形式,记述典章制度。《顾命——康王之诰》记典礼。《周礼》也是一部记载西周典章制度的书。这些都是《史记》中‘书’体的来源。”[8]20由此看来,司马迁创作《史记》,不仅有对史学传统的继承,还有对经书精华(即《诗经》的叙事方式)的汲取,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史记》的集大成性质。另外,班固批评《史记》曰:“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4]2737也能说明《史记》是在继承前代史书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而完成的。司马迁采撷的书籍除上述班固等人所列之外,还有《大戴礼》《论语》《秦纪》等,极为丰富。然而,司马迁并非一味地照抄、照搬前代史书的体例,而是有自己的创新与发展。正如清王鸣盛评价《史记》所言:“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司马迁取法《尚书》及《春秋》内外传,自言述而非作,其实以述兼作者。”[9]4肯定了司马迁的创造之功。清赵翼更是对《史记》五体的创作之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誌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10]3
我们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前代史学传统的长期积淀,很难想象,司马迁如何能够创作出《史记》这部不朽的史学杰作。
(三)司马谈之临终遗命
司马迁创作《史记》还与他的父亲司马谈的临终遗命有重要关系,这也是《史记》成书的另一个重要的客观要素。
据《史记》记载:“(司马)喜生(司马)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11]3286-3288由此可知,司马谈在建元、元封年间做太史令。建元元年(前140)至元封六年(前105),前后有36年的时间。司马谈于元封初年(前110年)卒,也就是说,他担任太史令的时间至少有24年,而最多可达30余年①因为司马谈是在建元年间任太史令,具体年代不详,卒于元封初年(前110),故曰30余年。。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谈早年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在元朔之际就开始搜集资料,制定自己的著史计划。在长期的史官生涯中,司马谈对著史有了自己的新认识。汉武帝于元朔七年获白麟,改元元狩。司马谈很激动,作了《白麟之歌》,并且进一步明确表示自己要著一部“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11]3301,即起于黄帝,而讫于汉武帝获白麟的史书。这样的个人志向和著史思想都对司马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司马迁是在父亲司马谈去世之后三年,继任为太史令的。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著史本就成了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父亲的临终遗命,在客观上也成了他创作《史记》的另一原因。司马谈在临终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1]3295
这一段临终遗言说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司马谈先对自己不能参加汉武帝封禅泰山的大典表示极为痛心;次则叙述祖业,世典周史;次言自己死后,让司马迁一定要做太史;再嘱咐司马迁做了太史之后不要忘记自己“所欲论著”,并进一步从孝道出发,教导司马迁一定要完成史著,“以显父母”;再次,对自己身为太史而没有能够将“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论载于史册表示遗憾。最后,司马迁俯首流涕,并郑重承诺父亲,自己虽不聪明,但会尽力去“悉论先人所次旧闻”的。
自此之后,司马迁就开始搜集资料,一心著史。司马迁身上也有着士人那种“重然诺”的精神。他对于父亲的承诺丝毫不敢忘记,即使自己在遭受“李陵之祸”之后,也没有忘记父亲的遗愿,未敢轻生,而是忍辱负重,坚持创作并完成了《史记》。
以上三点,我们认为是《史记》创作的客观条件。这三个条件,在客观上促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史学著作的完成。
二、《史记》创作的主观条件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2]302这一著名论断揭示了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辩证关系,并且指出客观条件是以主观条件为依据而发挥作用的。诚然,《史记》的出现,既有其重要的客观条件,如上文所述;也必然有其内在的主观条件,即司马迁自身的条件。上述的客观条件只有通过主观条件才会起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两方面条件同时具备、时机成熟之时,才能成就这部巨著。我们认为,《史记》创作的主观条件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司马迁的史才
司马迁是个非常博学的人。鲁迅先生肯定了司马迁的文才,他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1]431司马迁的博学不仅得益于他的父亲司马谈,也得益于司马迁自己的勤奋努力。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本来就是个很博学的人。司马谈转益多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要旨曰……”[11]3288。所谓“六家要旨”实际上是关于各个学术流派的总评论,带有一定学术史的性质,足见其学识之渊博。司马迁尽传其父所学,且又随孔安国治《尚书》,从董仲舒治《春秋》,授业恩师皆为当时大儒名流。
据《史记》记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11]3293由此可见,司马迁10岁之前,在老家龙门山一带耕种放牧,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司马迁天资聪颖,在他10岁的时候,就具备了诵读古文的能力;在12岁时,就有机会南游江、淮,北入齐、鲁,过梁楚;西征巴、蜀;南至于邛、笮、昆明一带,真可谓足迹踏遍全国的万里河山。这些经历,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游览观光、随军出征,又是一次次有目的地对各地风土人情的实地考察。关于司马迁本人的游历,他在《五帝本纪》《河渠书》《齐太公世家》等篇中,也多有提及。正如梁启超在《〈史记〉解题及其读法》中所言:“吾侪试取一地图,按今地,施朱线,以考迁游踪,则知当时全汉版图,除朝鲜、河西、岭南诸新开郡外,所历殆遍矣。”[13]2这些学习和实地考察工作,为司马迁后来创作《史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后,着力于搜寻资料,撰写《史记》。太史令虽是一个掌管天象历算的小官,但却掌管着宫廷的图书,于是司马迁有机会“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11]3296。也就是说,在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期间,就已经开始接触并缀集史书以及国家藏在石室金匮之中的藏书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若非职务之便,司马迁也不可能看到这些国家的机密藏书,搜集不到至为宝贵的重要资料。
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名师教导,个人的勤奋好学和广泛游历,再加上太史公的职务之便,使得司马迁逐渐成长为一位博学多才的天才史官。他的海纳百川的丰厚学养在《史记》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齐思和在《〈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我们试把《史记》中所征引的书名综计一下,便可发现凡是《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司马迁时代以前的书籍,司马迁几乎都引用过了,而且其中有的是《艺文志》中所没有的。司马迁实在是西汉最渊博的学者,是古代的文化巨人。”[14]9这是对司马迁史学才能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诚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正如班固所评:“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4]2737班固虽对《史记》的疏漏、抵牾之处提出了批评,但对《史记》的“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的优点也予以充分的肯定。
总而言之,司马迁的博学广识成为他创作《史记》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之一。
(二)司马迁的史德
司马迁的史德是其创作完成《史记》的又一重要条件。这里所说的史德是包含胆识和品德在内的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司马迁史德的形成与其秉性有关,也与其对前代史官优秀传统的继承有关。
班固云:“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2738这说明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理由有两点:一是司马迁能博极群书,善序事理,其书文直事赅,即史才;二是司马迁具有“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也即为史德。具有史才,更兼具史德,便可被称为良史了。
其实,良史的提法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良史是指优秀的史官,指能秉笔直书、记事信而有征者。“良史”一词来源于《左传·宣公二年》的一段记载: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①此句意为赵穿在桃园弑杀了晋灵公。赵穿:注曰:“穿,赵盾之从父昆弟子。”攻:注曰:“攻,如字;本或作弑。”。宣子(即赵盾)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15]597-598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赵穿在桃园杀掉了晋灵公,而晋国太史董狐记载是赵盾杀了他的国君,还把这个说法拿到朝廷上公布。赵盾说:“不是这样。”董狐说:“您身为正卿,逃亡而不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叛贼,不是您杀了国君又是谁呢?”赵盾说:“啊!《诗》中说:‘我心里怀念祖国,反而给自己留下忧伤。’这话大概说的是我吧!”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记事的原则是直书而不隐讳。赵盾是古代的好大夫,因为史官的记事原则而蒙受了弑君的恶名。可惜啊,如果他出了国境,就会避免弑君之名了。”
我们且不论赵盾的是非,单从一个史官的立场出发来看,太史董狐是一个有原则的史官。他依照礼法通则,认为赵盾身为正卿,返朝却没有讨伐弑君的乱臣贼子,未行人臣之义,应承担弑君之罪,故而记为“赵盾弑其君”。孔子对董狐这种不畏权势、如实依礼规记录赵盾有罪的作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董狐是良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良史的一个标准就是书法不隐,其核心是“君举必书”和“秉笔直书”,即凡天子、诸侯的言行,国家大事均实事求是地予以记载,毫不隐讳。
历史上关于良史的记载,除董狐之外还有很多,代不乏人。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就有一段关于良史的记载。齐庄公六年,齐国大臣崔杼杀齐庄公,另立景公为君:
丁丑,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婴所不获,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11]1502
齐太史三兄弟皆能秉笔直书而不畏强暴,其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是良史之才所应具备的史德。这种秉笔直书、毫不隐讳、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精神,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并逐渐演变为历代史官所应遵循的一种职业道德、人格追求。对此,宋王钦若总结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书法不隐,所以慎言行,示劝戒也。”[16]6336白寿彝先生也曾指出:“我国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优良传统,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就是这种优良的传统之一。”[17]这就是所谓的良史传统。
司马迁对于良史传统的继承,表现在其著史上便是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表现在行动上则是直言进谏。为李陵辩护便是司马迁崇高史德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正是因为司马迁出于自己的良史之德,在李陵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才会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4]2729
由此看来,司马迁与李陵平常关系不是很好,甚至“趋舍异路”,爱好兴趣也各不相同,替李陵说话,仅仅只是出于司马迁个人的公心而已,自己对李陵平日的观察和了解,认为他有“国士之风”,不可能投降匈奴的。然而,司马迁的不幸在于他在汉武帝盛怒之时替李陵辩护,仅仅因为辩护时机不对,结果被汉武帝认为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而替李陵游说,遂定为巫上,下狱,并处以腐刑。
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种直言进谏的精神,如果没有对书法不隐优良的史德的继承,司马迁是不可能被处以腐刑的,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史记》中那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的酣畅淋漓了。正如元代马端临所说:“《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18]1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司马迁对良史优秀传统的继承,才成就了他的良史之德;也正是因为司马迁有了良史之德,才成就了《史记》的实录与伟大!
(三)司马迁的史志
司马迁著史的志向不仅来自于父亲的遗命,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史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司马迁有着明确的著史理想。正如《史记》所云: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1]3296
在这里,司马迁假借其父之言,实为自己心声,道出了自己著史的目的是要“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后又言:“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1]3319-3320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已经将六经视为《史记》创作的标的了,即其“成一家之言”的依据,并且要“拾遗补艺”,其“拾遗”而“补”的对象是“艺”。秦汉以前,六经又称“六艺”,故而他要以自己的《史记》去补益六经。这是何其崇高的理想!其次,在这里,司马迁已经将自己视为继周公、孔子之后的又一位“能绍明世”之人,并且也愿意承担这一重任,不敢有所推辞,而且司马迁做到了这一点。正如宋代郑樵所云:“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19]1正说明司马迁《史记》是继孔子“六经”之后又一部经典著作,司马迁也是能够与周公、孔子相并列的伟大人物之一。的确,这样伟大的胸襟与气魄不仅是大一统时代精神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以司马迁个人禀赋、胆识和才华作为基础的。
有了伟大的著史理想,才不至于被前进道路上的挫败和屈辱击垮。就在司马迁着手写作《史记》的七年之后,突遭“李陵之祸”。司马迁既是伟人,也是凡人。在遭受腐刑之后,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死。他认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4]2732又认为:“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4]2727遭受宫刑,就是对祖先最大的侮辱,自己还有何面目再立于天地之间呢?难道就这样赴死吗?没有。司马迁必定是伟人,他对自己的生死作了多方面的考虑与评估,最后还是决定“隐忍苟活”。因为,司马迁认为,如果就这样死去,一是有负父亲所托;二是自己于心不甘,遗憾自己的“私心有所不尽”:
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4]2733
司马迁冷静下来,勇敢地承受了痛苦,接受了现实。在痛定之后,他想明白了生与死的价值和意义,“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4]2732。在痛苦之中疗伤,在历史中寻求同道,于是他想到了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并且从他们那里汲取了力量: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4]2735
司马迁在古圣先贤那里寻找到了精神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力量,他发现历史上所有的伟大著述都是在痛苦中酝酿而成,所有的倜傥非常之人都遭受过挫败和困厄。司马迁从这些人身上找到了心灵上的安慰和极度的心理认同感。这种心理认同感能使司马迁竭尽全力去创作一部伟大的著作,以此著作来扬名后世,赢取极大的荣耀,然后以此极大的荣耀来抵兑自身此前所遭受的极大之耻辱,进而获得心理上的补偿和满足。这种创作动力成了司马迁活下去并竭力创作《史记》的深层次心理动因。这也许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发愤著书”的内涵吧!
司马迁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既实现了一次生命价值的升华,也成就了一部不朽的杰作。
三、结语
《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其成书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本文仅仅撮其要者,从政治历史条件、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司马谈之遗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史记》创作的客观条件;从司马迁的史才、史德和史志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其创作《史记》的主观条件。总而言之,《史记》的出现,是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条件在特定历史时期聚合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史学发展至汉代而出现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的承担者就是司马迁,这个结果的形式便是《史记》。
[1]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陈杰林.论“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J].池州师专学报,1994,(1):92 -97.
[3]王长顺.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之元动力[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58 -63.
[4][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赖明德.司马迁之学术思想[M].台北:洪氏出版社,1983.
[6]《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第二十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9][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M].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10][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施丁,廉敏.《史记》研究[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4]历史研究编辑部.司马迁与《史记》论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1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6][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总序[M].校订本.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7]白寿彝.漫谈史学传统三事[N].人民日报,1961-08-12.
[1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宋]郑樵.通志·总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