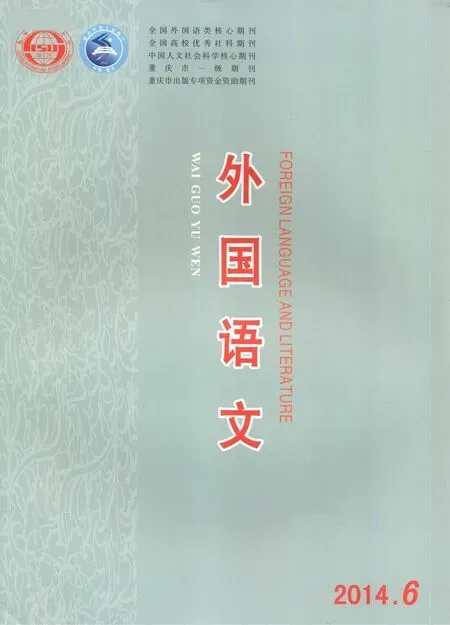幕府末期儒学思想助推西洋文明摄入小考——以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为中心
2014-03-20宋媛媛姚继中
宋媛媛 姚继中
(1.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0507;2.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1.引言
幕府末期(1853-1867),史学界将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湾浦贺港事件视为幕府末期的开端,而将1867年10月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还政于天皇视为这一时期的终结。佩里的“黑船来航”,其目的是要求日本开国,此举给日本朝野上下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幕府的文人志士围绕着是否开国,以及如何看待西洋文明涌入将对日本产生何种影响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与相互对抗。因此,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日本思想史上最为激荡的时期。
“黑船来航”之前的德川幕府,自1633年颁布第一次锁国令开始,便视由西洋传来的天主教为邪教、妖教,甚至认为天主教在日本的布教活动,对幕府的统治会造成潜在危险。事实上,日本的统治阶层自古以来受传统儒学的影响,视中华为世界文明中心,西洋为夷狄。然而,随着汉译西书的传播,以及随传教士而来的西洋学者、专家与各藩文人志士的接触,日本人对西洋的认识逐渐增加。至幕府中期,日本的文人志士,尤其是儒学者对西洋文明基本形成了以下几种看法:一种是荻生徂徕(1666-1728)的“西洋否定论”。荻生徂徕曾说:“那荷兰等西洋诸国之人,性情秉性异于常人,其语言如鸟兽怪叫一般令人难懂,不近人情。”(平石直昭,2001:124)徂徕从西洋人如鸟兽般的语言与性情推断西洋人概不通人情,以此否定西洋文化。另一种是新井白石(1657-1725)的“二分法定义”。他在《西洋记闻》中提到:“他国之学,只在于精通器物,所谓只知形而下之物,却未知形而上之物。”(平石直昭,2001:124)白石将西洋的教义一分为二。他看到了西洋在天文、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具有先进性,并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但并不认可西洋的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具有优越性。
此外,西川如见(1648-1724)提出了“孝之普遍性”的认知观点。西川认为东洋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等同样存在于西洋。他说:“红毛国虽被蔑称为外夷,但却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忠孝。因为孝是自然的天柱,故世界万国之人皆有孝。”(平石直昭,2001:124)红毛国是江户时代日本人对荷兰的指称。西川如见试图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孝”来平视西洋,但其仅仅凭“看到往来于长崎的荷兰人所持有的镜盒盖子上画有亲人的肖像”(平石直昭,2001:124),便认为西洋人与东洋人一般有着同样的道德伦理观。这种基于表象的判断由于缺乏说服力,其观点也因此无法得到普遍认可。
西川如见之子西川正休(1693-1756)则认为,西洋富强的原因在于其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的发达。同时他也锐利地指出荷兰等西洋各国在掠夺他国财富时的贪婪,因而他劝说国民:“应学红毛国的天文学,勿要学其贪欲。”(平石直昭,2001:126)由此可见,儒学者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洋进行了解读,但西洋在多数儒学者眼中的“外夷”身份并未得到改变。直到18世纪前期,对于日本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中华文明依然高高在上。(塚本学,1979(371):10)
时至幕府后期,随着兰学的介入以及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儒学者的“华夷秩序观”逐渐崩塌。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洋列国,幕府是选择攘夷锁国还是迎夷开国,关系着国家的存亡。而一旦选择开国,如何理解西洋文明或者说以怎样的方式去接近西洋文明又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通过对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三位开明儒学者的文献考证,试图挖掘幕末的儒学者在这一特殊时期如何以传统儒学思想为根基,力求重新认识西洋文明,并通过他们的认知,来探讨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在日本摄入西洋文明过程中所起到的助推作用。
2.幕府末期儒学者对西洋文明的观点
幕府末期,有相当一部分儒学者视西洋为夷狄,认为西洋的学术与文化如邪教一般万不可采用,并上书幕府要求“攘夷”。例如大桥讷庵(1816-1862)认为,日本如为防西洋贼而学西洋,就如同与狗斗而自己也要学着撕咬一般。(平石直昭,2001:159)他认为日本学习西洋的做法非但无用,更有可能使自国礼乐崩坏,沦为蛮夷。儒学的一个支派——后期水户学者更是打出“尊皇攘夷”的口号,要求“明神皇之大道,拒夷狄之邪教”(植手通有,1974:26)。然而,西欧势力的强势登陆,迫使幕府不得不选择开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再认识西洋文明,通过对他者的认识反观自我,成了幕府末期儒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一些思想的先驱者,如佐久间象山(1811-1864)、横井小楠(1809-1869)、桥本左内(1834-1859)等纷纷提出了有别于以往的西洋文明认知观,试图以儒学为传统文化根基,以辩证的观点摄取西洋文明。这一思想摒弃了在接受西洋文明过程中的偏激,他们不认为传统儒学与西洋文明势不两立,而是绝对化的思维模式导致人们产生了认知上的错觉。
2.1 佐久间象山
朱子学的忠实拥护者、被称为幕府末期思想家先驱的佐久间象山(1811-1864)在获知鸦片战争中清朝大败于英国这一消息之前,仍一心潜修儒学,并于1839年在江户开设私塾传授儒学。当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他感受到空前强烈的国家危机,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如何认识这个与东洋完全不同的西洋,是象山面临的重要课题。
为了知己知彼,34岁的象山开始学习荷兰语,通过阅读有关西洋军事与学问的书籍来了解西洋。他认为在幕末这个特殊时期,儒学者应从传统“夷狄观”的偏见中脱离出来,将视野扩大至更广阔的世界,并指出锁国攘夷的不切实际,“只有引进西洋的科学技术,才能增强国力”(植手通有,1971:652),开国是必然的选择。他不再将西洋称为“外夷”,而特意称之为“外蕃”(佐久间象山,1971:415),从野蛮的“夷狄”到文明的“外蕃”,足见其对西洋文明认识的转变。这种转变表明象山正逐步走出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开始平视东西洋。
在《省愆録》中,佐久间象山明确阐明了对东西洋的看法,他说:“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精细无遗,表里兼该,因以泽民物,报国恩,是为君子第五乐也。”(佐久间象山,1971:244)“东洋道德”指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与政治制度,“西洋技艺”则指西洋的科学技术,暗指西洋的机械文明。象山认为东洋道德与西洋文明(机械文明)可以相互调和,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儒学者应充分发挥这两者的功效,以达到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窃以为,“东洋道德、西洋技艺”正是佐久间象山以传统儒学思想为根基去推动西洋文明的直接证明。
佐久间象山之所以用这一观点来认识西洋文明,是因为他认为推动西洋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洋学问,与儒家的朱子学并无矛盾,甚至在追求学问之至理上,其目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朱子学的“理”具有普遍性与统一性,“宇宙之间实理无二,理之所在,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百世圣人不能异此。近年西洋所发明的诸多学术,皆为实理,足以资吾圣学”(佐久间象山,1971:401)。在给川路聖謨的书信中,象山进一步阐述道:“西洋的穷理学等学科,依然符合程朱之意。程朱两位先生的格物穷理之说,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佐久间象山,1971:330)
可见,程朱两位圣贤的“格物穷理”,本是以探究事物的“道理性”为核心,去穷尽天地万物之原委与道理,象山却认为“理”之核心并不在其“道理性”,而在其“物理性”的一面。既然“格物穷理”的核心在于其“物理性”,那么注重“实验”与“实证”的“西洋的穷理学”在道理上当然符合儒家的“格物穷理”之意,东西洋的“理”是相通的。
一方面,象山借儒家的“理”之普遍性与统一性,巧妙地西洋的学问放入儒学的知识体系中对其进行了再解读,找到了一条看似合理的途径来接近西洋。另一方面,象山在对“西洋的穷理学”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也从另一个角度对传统的儒家理念进行了再解释。因此,他认为东、西洋文明是可以调和的,是可以互为补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技艺”,即“东西洋调和论”的提出,既有别于冥顽固陋的“锁国论”者,又不同于兰学者的“全盘西化”。
2.2 横井小楠
横井小楠(1809-1869),幕府末期开明的思想家、儒学者,在“黑船来航”之前受水户学的影响,赞同锁国攘夷。1854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以及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令他对西洋文明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在如何认识西洋的问题上,横井小楠注重借用“道”之普遍性,以及“仁义”、“仁政”、“天下为公”等儒学概念来接近西洋。首先,他认为:“天地之间,唯有一道。”(横井小楠,1971:435)在“道”的面前,东西洋各国是平等的。因此,只要“乘天地之气运,随万国之事情,以公共之道治理天下,便万方无碍,今日所忧都不足以为虑了”。(横井小楠,1971:441)况且,“我国之所以被称为优于世界万国之君子国,是因为我国能体察天地之心,且重仁义。所以对待美、俄使节,只要贯彻天地仁义之大道便可”。(横井小楠,1971:434)
其次,在《国是三论》中,横井小楠盛誉美英俄三国在政教民生方面取得的成绩。他(横井小楠,1971:448-449)称赞美国“顺天意息宇内战争”、“求智识于世界万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以求公共和平”的仁政举措,肯定英国“据民情而定政体”、“出兵和亲等皆议于民”的民主体制和俄国“广设文武学校、医院、幼儿园、聋哑院”的民生政策。小楠不禁感叹,美英俄三国的治世堪比“三代治教”。“三代”是指儒家对中、上古时期理想化的社会状态的表述,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实现“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郭丽,2009:54)。可见,小楠仍是从儒家的“仁政”、“天下为公”的概念去理解西洋的政治制度。
此外,横井小楠认为西洋的天主教并非邪教而是正教,幕府应祛除对西洋的偏见,以朱子学“穷理”的学问态度去吸收西洋文明的先进之处。在《沼山对话》中,他认为天主教的教谕具有一种治世穷理的智慧,这种智慧又得益于圣人。他说:“过去人们认为天主教是愚民之教,但那只是我们的浅薄认识。近年来在西洋,其文人未必都信仰耶稣,但他们发明了一种经纶穷理之学,并将其添加于天主教中。这经纶穷理之学利于民生,并不断扩大,大体也得益于圣人。”(横井小楠,1971:502)
用圣人之道利世安民,是横井小楠的政治理想。然而道之所指并不在西洋,小楠在《送左大二姪洋行》中,说道:“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何止富国,何止強兵,布大义于四海而已(清水教好,2008:81)。”“大义”,即“尧舜孔子之道”,他最终的目的仍是要让“尧舜孔子之道”施教于天下。虽然小楠曾把西洋的政教比作“三代治教”,但西洋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替代儒家的政治理念。
“西洋之学也只是实业之学,而不是心德之学。因而国民不分君子小人,不分上下等级皆从事此学,故此学得以兴旺。然其因无心德之学,故不知人情世故,交易谈判执拗于事实约定,其执拗之处最终引发战争。”(横井小楠,1971:516)“若有心德之学通人情世故的话,在当世,应该停息战争。”(横井小楠,1971:517)“无心德之学”是说西洋无道德学。可见,在小楠眼里,西洋文明最终也只是一种器械发达的文明。因此,只有“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合理调和东西洋文明,才能实现富国强兵,将儒家的“圣人之道”传至四海的理想。
2.3 桥本左内
桥本左内(1834-1859),八岁始随藩儒学习汉籍及诗文,10岁前后通读《三国志》,并几乎通晓其大意(别所兴一、赵德宇,2003:328)。1850年,桥本左内师从兰学家绪方洪庵学习兰方医学。1854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促使左内开始关注西洋的政治、教育、贸易等各个领域。
在《西洋事情书》中,他提到西洋各国在政治体制上重视民主议制,“如遇国家大事、修改法令、出兵等事情,必先咨询学校,让其讨论,再通达政府,让其反复议论,在众议一致的基础上,才付诸实施”(桥本左内,1971:591);在学问上“追求实用之学,各州县学校均开设天文、地理、测量、算术、物理、化学、医学、交易等学科”(桥本左内,1971:591);“如出现新的发明,便下达学校,让学校讨论其利弊,有了定论之后再发行相关著书,或是将其制作出来,贩卖至国内外”(桥本左内,1971:591)。左内认为西洋的学问与儒家的“圣人之道”有相通之处,“所谓圣人之道,无外乎人伦日用,并无物外之道”(桥本左内,1971:544-545)。左内强调,圣人之道在于经世致用,西洋的学问不仅经世致用且利人利己。
虽然左内对西洋的政教体制持肯定的态度,但并非全盘肯定西洋的文明,在如何接受西洋文明的问题上,他说:“仁义之道,忠孝之教由我(东洋)开始,器技之功·技术之精从彼(西洋)取之。”(清水教好,2008:81)在其著作《关于学问所事件令原案》中,他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于兵法、器械、物产、水利、耕织等诸般技术,学彼之长,以辅我义理纯明之学。”(别所兴一、赵德宇,2003:328)之所以有此观点,是因为他看到合理地接受洋学固然有好处,但如染上西洋的“奇巧淫行”就成大害了。西洋文明于桥本左内而言终究只是一种“辅我义理纯明之学”的手段。
3.对接受西洋文明程度的思考
“东西洋调和论”主张将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相调和,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辱的目的。虽然它强调儒学在思想道德方面仍具有优越性,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承认了西洋与东洋在文明上的对等地位。形成这个观点的背后,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自中国的明清交替事件(日本称之为“华夷变态”)发生后,儒学者内部对儒学本身早已产生的多重阐释。二是这一时期的儒学者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兰学、国学以及水户学的影响,当西洋文明呼啸而至时,他们能够冷静地从各个方面去审视东西洋文明,发现各自存在的问题。
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西洋文明进行了再认识。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仍是用儒学的概念去理解西洋文明,因此,他们眼里的西洋文明便有了“仁义”、“仁政”等儒家学说的政治色彩。由于他们了解西洋文明的目的也只是想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因此被后人批判其思想始终没有走出封建思维的桎梏。但不管怎么说,在幕末这个特殊的时期,“东西洋调和论”的西洋文明接受法有着它的合理性。因为完全按照西方的政治体制来改造当时之日本社会,反而会激发国内的矛盾。
4.接受西洋文明的意义
植手通有(1974:235)在《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中曾说:“在江户时代,儒学的华夷思想是对外意识的基准。”然而,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与佩里的“黑船来航”,促使日本的文人志士不得不转变旧有的华夷思想,来反思自国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一时期虽然仍有部分儒学者故步自封,不肯面对西洋文明袭来的事实,但多数儒学者正努力地走出传统华夷秩序观的束缚,重新审视西洋的政治、宗教与学问,形成了对西洋文明的再认识。
倘若我们换一种视角去审视儒学者对西洋文明摄入的思维过程,便会发现他们在日本接受西洋文明过程中的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一个国家或民族,不是可以轻易改变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在外来文明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时,往往有以下几种结局:一是强势的传统文化彻底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与渗透;二是已经形成霸权的外来文化以势不可挡的态势彻底摧毁自身文化;三是以自身的传统文化为思想根基,去接纳外来文化的精华,并融入自身文化。本文考证的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儒学者们,正是以第三种方式,即既不彻底放弃传统的儒学思想根基,又不盲目崇拜优于自身的西洋文明,而是以自身的传统儒学思想的辩证观,去重新审视西洋文明、接受西洋文明、以形成“和魂洋才”之趋势。从这一点来看,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等儒学者们,非但没有以顽固的儒学思想阻挡西洋文明的摄入,相反,而是以理性与应有的方式助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等一批具有开明思想的儒学者们,巧妙地借用儒家的“道”、“理”、“仁政”等概念,将西洋的政治与学问放入儒学的知识体系中对其进行了再解读,找到了一条合理的途径来接近西洋。另一方面,通过对“西洋的政治体制”与“西洋的穷理学”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也从另一个角度对传统的儒家理念进行了再解释。因此,他们认为东西洋文明是可以调和的,是可以互为补益。
通过文献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因为日本有了能客观且理性的去看待西洋文明的儒学者们,才使得幕府政权最终意识到“华夷变态”后的世界格局与积极吸取西洋优秀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日本迈向开国的步伐。
幕府末期的儒学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日本的文人志士接受西洋先进政教体制,但其“经世济民”的治世理论和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穷理”精神,着实为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事实上,儒学思想并未阻碍,而是助推了日本摄入西洋文明的进程。
[1]别所兴一,赵德宇.桥本左内的西洋观及日本对策[J].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2]郭丽.幕末日本的西洋认识—开国论者的视角[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9(4):54.
[3]横井小楠.国是三論[M]//佐藤昌介,植手通有,山口宗之.日本思想大系55.东京:岩波书店,1971.
[4]平石直昭.日本政治思想史[M].东京:财务省印刷局,2001:124.
[5]桥本左内.西洋事情書[M]//佐藤昌介,植手通有,山口宗之.日本思想大系55.东京:岩波书店,1971.
[6]桥本左内.学制に関する意見箚子[M]//佐藤昌介,植手通有,山口宗之.日本思想大系 55.东京:岩波书店,1971.
[7]清水教好.日本思想研究会会报别册[M].日本:大阳出版株式会社,2008.
[8]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M].东京:岩波书店,1974.
[9]植手通有.佐久間象山における儒学·武士精神·洋学[M]//佐藤昌介,植手通有,山口宗之.日本思想大系55.东京:岩波书店,1971.
[10]塚本学.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夷」概念について[J].日本历史,1979,(371):10.
[11]佐久间象山.川路圣谟宛[M]//佐藤昌介,植手通有,山口宗之.日本思想大系55.东京:岩波书店,1971.
[12]佐久间象山.省愆録[M]//佐藤昌介,植手通有,山口宗之.日本思想大系55.东京:岩波书店,1971:244.
[13]佐久间象山.赠小林炳文[M]//佐藤昌介,植手通有,山口宗之.日本思想大系55.东京:岩波书店,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