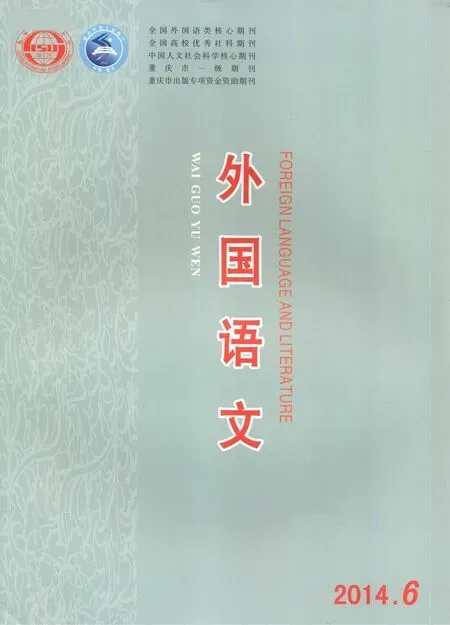“近距离”的《抵达之谜》
2014-03-20俞曦霞
俞曦霞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商贸分院,浙江 湖州 313000)
维·苏·奈保尔 (V.S.Naipaul,1932-)是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印度裔英籍作家,瑞典文学院因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阮学勤,2002)而将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奈保尔创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近距离”(close writing)思想,主要特点是文学叙事体现作家的“现代敏感性”(modern sensibility),表现作家的道德感,反映时代最典型特征,从而逼视历史,与真理对话。本文试图分析这一创作思想在《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中是如何贯穿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
《抵达之谜》是作家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共有五卷,以第一人称“我”讲述一位来自加勒比海的作家(实际是奈保尔本人)来到英国威尔特郡一个庄园定居的经历见闻,描绘庄园里上至庄园主下至园丁杰克等人的日常生活,包括作家由画作“抵达之谜”回忆初到英国在创作上的艰难摸索和对作家成长道路的思考。作品在叙事上具有散文化倾向和抒情风格。小说出版于1987年,其时奈保尔已在英国定居了30多年,被认为是“在世的英国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Gudjoe,1988:3)。评论界对作品纷纷发表看法,国外学者大都认为该作品反映奈保尔已经成功“抵达”英国,为主流社会接纳;著名评论家布鲁斯·金(Bruce King)则认为作品是“对印度流裔的赞颂”(Bruce,2003:138);我国学者梅晓云教授认为作品给人一种“无法抵达的感觉”(梅晓云,2003);杜维平教授从帝国意识形态对奈保尔的影响角度,认为作品反映帝国意识形态对作家的浸淫(杜维平,2008)。上述真知灼见给我们理解作品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和启发。但奈保尔本人对作品的期望似乎要远远高于评论界的反映,在刚刚完成书稿还未出版时就踌躇满志地声称“这是部重大作品”,西印度群岛著名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认为此书“隐藏着某些惊人的贪婪”(索鲁,2001:430-431)。为什么一向对创作苛刻、极少发表评论的奈保尔声称这是一部“重大作品”?作品又有着怎样的内涵而被称为“贪婪”呢?
笔者以为作家的“近距离”创作思想是解读作品的关键,从这一角度对文本各章节及其内在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作家以同名画作“抵达之谜”为切入口,深刻思索自己30多年的创作生活以及对历史﹑生命和死亡的宗教性的感悟,不仅向我们昭示作家已批判性地接受英国文化并融入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历史、社会和自然的深刻思想者的对“抵达”的最深层次的领悟,充分彰显作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以自我为范本﹑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独到体悟和深刻的人文思索。
1.“近距离”创作思想
“近距离”一词提出是在奈保尔2007年出版的散文随感集《作家看人》(The Writer’s People,一译《作家周围的人》)中,但作家并没有就“近距离”创作思想进行专门论述,而是体现在他对自己阅读作品的理解和评论中,这些作品涉及广泛,有古希腊作品,也有他的好友﹑早年提携过他的英国作家安东尼·鲍威尔(Antony Powell)作品,更有对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两部作品褒贬不一的评论,这些体现作家敏锐洞见的评价在书出版后让作家毁誉参半,但作家一颗为文学缪斯献出毕生心血﹑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可谓开一代先河,“近距离”创作思想在评论中若隐若现,但如一根细细的红线贯彻始终。
“近距离”一词在文中出现近五次,概括地说,主要包括以下两层意思:(1)文学作品体现作家的“现代敏感性”,“现代敏感性”是指“(作家)在衡量世界时,调动所有知觉,而且是在理性框架内这样做”(Naipaul,2008:160)。达到这一点,作家必须对生活长期观察。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洛布版诗作最后收录八首短诗,其中一首《莫特姆》(Moretum)①莫特姆,诗题原文为“Moretum”,为拉丁文,指古代罗马人的一种用奶酪加大蒜捣成的糊状佐餐物,抹在面包上吃。共124四行,描绘前罗马帝国时代一个小土地所有者西米卢斯清晨为自己准备一种叫“莫特姆”的早饭的全过程。奈保尔认为这首诗精彩绝伦,其成功在于诗中完全没有超自然手法:
这首诗的具体细节——对一切都不视为想当然——让我们每时每刻都看到﹑触摸到而且感觉到,几乎以一种宗教的方式赞美这个实体的世界——点亮油灯(罗马式灯芯油灯,在罗马帝国的几个世纪中全无改进),磨麦粒,揉面团——这些细节把一个小土地所有者的上午变成一种仪式。(p.164)
这就是“近距离”,能够把表现的东西让读者直接触摸,与读者实现“零距离”,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的读者读来如身临其境。“莫特姆”这种只有在那个时代有的食物在今人眼里也许匪夷所思,但它却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一种历史现实,反映当时下层人民的日常饮食,反映了那个时代最典型的饮食特征。奈保尔认为,作家这种写作在对历史的还原中是对历史的负责,这是一个作家的使命,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伦理道德。(2)叙事简短完整,易于接受,具有普遍性和道德感。奈保尔认为,莫泊桑的短篇总是详细交代时间和地点,就是次要角色,也有名字和家族历史,使他笔下遥远的世界完整,读者不需要了解法国19世纪的历史,就能理解他笔下农民的悲惨境地或普法战争留下的伤口之深,这种描述体现了作家的道德感(p.55)。相反地,奈保尔认为和他有着相似背景的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处女诗集不成功在于“没有一个是近距离的,暮色中在海上远处的渔民;从无家的歌谣中解放出来的黑孩子,彼此混淆不清,几乎是个抽象概念”(p.21)。奈保尔还认为创作《萨朗波》(Salammbo)时的福楼拜是个“深陷在二十世纪东方主义和情节剧中的作家”(p.136),主人公萨朗波她说话很少,不知道她有什么感情,做什么,或者具体怎样度日。她是糟糕的19世纪小说中的创造物,哥特式,东方式,一个世俗之人,本来就只是让人远观,如果她说得太多,就根本不会让人产生错觉。(p.144)
相反地,奈保尔高度褒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认为写得很细致,抓住工业时代法国外省乡间一些最典型特征,这些细节把人带进了作家的思想和经历,让人看到轻盈﹑转瞬即逝的东西:冬日的黎明,带着木头套鞋坐在沟沿边的男孩,农场主的病房,在那里,棉布睡帽扔到地板上一个远远的墙角,四柱大床,卧室里直挺挺排着的几袋小麦。(p.135)
这是小说开头包法利在认识女主人公爱玛前去她家给她父亲治脚伤的几处描写。奈保尔认为,这些细节,尤其是男孩和木头套鞋这一处,“不仅是个有关农村的细节,而且让至此都具有现代性的这一故事带上了工业时代的特点。”(p.132)福楼拜的这种描述让人直接逼视历史现实,接近真理,与真理对话。这就是奈保尔的“近距离”思想。
2.抵达:“近距离”观照人世人生
《抵达之谜》题目来源于作家在威尔特郡租住的小屋里发现的一幅画作“抵达之谜”,作家通过这幅画作“近距离”透视人世,对无数文人墨客描绘的人世通过这一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画作进行“近距离”切入,从而表达他在年过半百后对人世的复杂深沉情感。
“抵达之谜”是意大利著名画家基里科的作品。基里科(C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是西方形而上画派的创始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他的作品旨在发掘主题中居于中心位置的神秘性,将想象和梦幻的形象与日常生活事物,或古典传统融合在一起,使现实与虚幻糅而为一。画作的内容是:
一个经典的场面,中世纪的,古罗马的……一个码头;在背景里,……有一艘古代海船的桅杆的桅顶;在近处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有两个人,都裹得紧紧的,一个可能是那个抵达的人;另一个也许是这个港口本地的人。(Naipaul,1988:98)
这是一个“近距离”的写实画面,一个码头场景,“桅杆的杆顶”部分代整体意指海船,“街道上有两个人,都裹得紧紧的”勾勒出典型的中世纪罗马人装束。这个画面是一个实体世界,能让我们触摸到的古罗马时代的实体世界,但同时这个实体世界又是一个极具隐喻和象征内涵的虚体世界:“它述说着抵达的神秘。它向我述说着这个,正如它当年向阿波利奈尔①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著名诗人,超现实主义先驱。基里科一些超现实主义画作的题目,包括《抵达之谜》是由阿波利奈尔起的。在述说着”(p.98)。无疑最触动作家的是他——一个来自英国前殖民地的作家来到这个前宗主国的心脏——威尔特郡这一特殊经历带来的无尽遐思“以一种间接的﹑诗意的方式,使人注意到我自己体验中的某种东西”(p.98)。自1971年奈保尔开始移居威尔特郡以来已经15年过去了,创作已达30多年的奈保尔已被认为是在世英国最伟大的作家,经典作家地位的确立带给奈保尔的不仅仅是功成名就后的喜悦,更多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更深入思考,画作“抵达”实则寓涵对过去的永远告别和失去,提醒作家他已无法再回到出生地特立尼达和母国印度,他的余生将一直在英国(事实也正如此)。作家不仅用画作上的中世纪日常生活场景﹑更由画作简洁叙述一个生动朴实的故事来昭示他对短促而又凄美人世的深沉情感。故事是对画作上抵达港口旅行者的想象,他为家族的使命来到这座港口城市并终其一生而无所获,最后他想再回到当初带他来的那艘海船,但“那古老的海船已经消逝。这位旅行者已经过完了他的一生”(p.99)。这个故事和画作的画面场景完美结合构成一幅人世的标本,以其高度的象征性阐释了奈保尔关于“人世之谜”的感叹。
人世既然如此,那么,人生又该如何呢?小说第一卷“杰克的花园”凭借杰克和他的花园让读者“近距离”逼视奈保尔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杰克是很普通很常见的英国人,年近半百,是庄园里的园丁,租住在庄园主的房子里,社会地位低下,但他品质高贵,具有“一个本身有着高尚思想的人的特征,一个一切按原则办事而对其他生活方式不屑一顾的人的特征”(p.29)。因为杰克的那份工作随时有丢掉的可能,租住的小屋也不安全,可他却一直管理着自己的那几个精美的花园,不辞辛劳地挖土整地,种植蔬菜和花卉。他没有世俗凡人对名利的虚荣,充分享受着生命和四季所赋予他的东西,以自己一个鲜活的生命享受着上天的赐予,让花园一年四季都呈现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韵味和情致。杰克作为地位卑下者对生活热爱和赞美生活的这种方式,他对生活的满足感使得作家本人情不自禁地羡慕起来,这就是人生!
杰克活得灿烂,死得从容,面对死神的威胁依旧不改其英雄本色,不掩对生活的热爱。在他不幸得肺癌后依然穿着得体﹑胡子修饰得干净﹑整齐,见到“我”这个老邻居“平静地打招呼,表示友好,让我放心”(p.43)。即便在临终前夜,“还是自己挣扎着爬起来,强打精神穿上衣服,开车到酒馆去过节②指圣诞节。,在自己临死之前。”(p.48)这些“近距离”描绘让读者感同身受着杰克,这个凡人的英雄本色,纵然遭受人世间所无法承受的痛苦,依然故我保持对生命的热爱,对理想的坚持。作家在1993年获得英国首届大卫·科恩文学奖(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Prize)后接受专访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时说,这部作品虽然是对自己迁居威尔特郡后对周围人事观察所得,但毕竟是小说,有虚构的成分,“因为你不能用真人真事来表达不断变化的人生的哲学”(Jussa Walla,1997:163)。作家对杰克这一既真实又虚构的形象进行“近距离”描绘,表达他对人的生死这一“人生之谜”的深刻感悟!
在小说第五卷,也即尾卷“告别仪式”的末尾作家回忆在特立尼达参加完妹妹萨蒂的葬礼后与一位老人的谈话
一七八四年,西班牙政府忽视了这个地方三百年之后,出于保卫帝国的需要,向天主教移民开放了这个岛屿③指特立尼达岛。,给那些能够带奴隶来的人以优惠待遇和免费土地;一八四五年,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十年之后,英国人开始从印度引进印度人来开垦这片土地。他①指这位与作家谈话的老人,他是奈保尔妹妹萨蒂的丈夫家的远方亲戚。创造了一个复合的历史。但对他来说那已足够。人类需要历史,这有助于他们知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历史和圣洁一样,可以驻留心中。人们心中只要有东西留存,也就足够了。(p.353)
由人的死亡仪式——葬礼自然地过渡到特立尼达的历史和特立尼达印度人的历史,作家让读者“近距离”体悟到人类通过历史认识自己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作家对历史﹑社会和自然的深刻思索。
3.抵达:“近距离”反思作家之路
奈保尔自20世纪50年代走上文学道路后就一直在思考怎样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哪些因素可以造就一名真正作家,作家在作品主要章节回顾自己创作三十多年经历并从知性层面进行形象化梳理和思考总结,并把自己的作家道路和另两位主人公失败的写作和萎靡的人生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一个作家有无“近距离”的创作意识和“现代敏感性”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关键因素,从而表达对“作家之谜”的独到理解和感悟。
作品第二章“旅程”由“抵达之谜”画作和衍生想象的故事,自然过渡到作家自己早年“抵达”英国以及开始创作前几年的挫败,分析自己何以不能成功﹑不能顺利“抵达”作家成功之路,最终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有着专心致志能力和用心学习各种事物能力的男人”(p.120);但是,成为一个作家的最重要的方面“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还是天真而无知的”(p.110)。奈保尔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人与作家的分离”(p.147),是自己当时仅会用“人”而不是用“作家”的眼睛来看世界,进行写作的缘故。什么是“社会的人?”怎样用“作家”的眼睛看世界呢?在作家本人的实践看来,应当是面对前宗主国不规避自己来自前殖民地的尴尬身份,能正确看待并接受自己的历史和背景,具有“现代敏感性”并在理性框架内将自己的生活阅历化为写作素材,“近距离”地描绘这份生活,才能实现创作上的成功,实现人与作家的合二为一,奈保尔为这一天整整花了五年“(达到)这一天让我等了将近五年时间”(p.147)。五年后,奈保尔创作出了《灵异推拿师》(1957)﹑《埃尔维拉的选举权》(1958)和《米格尔大街》(1959)这三部幽默风趣反映家乡特立尼达人民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小说,这种对前殖民地人民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的“近距离”描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英国文坛犹如一阵清风,题材的创新,叙事的简洁幽默让年轻的奈保尔一举成名。这五年是奈保尔从一个只会学习的人成长为具有创造才能的人的五年,这五年是奈保尔用英语找到自己的声音的五年,在漫长的积累和学习中,从对书本的简单学习和认知飞跃为对现实世界和人生的理性把握,作家因此深悟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自己曾经的生活最能打动人,因为它是你身在其中能进行“近距离”接触的,而这是成就一个“社会的人”的作家的底蕴,只有这样的创作才能走上成功之路。
不仅如此,作家还以自己租所房东的作家之路进行对比,凸显在全球化后殖民时代“作家”命运的巨变及其深刻的历史动因。房东是世袭贵族后代,继承百年来祖先留给他的巨大财富和广袤庄园,优越的生活和聪颖的天资孕育他当作家的野心,但最终无法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只得以自费出书完成心愿。奈保尔把自己和房东进行比照,发现两人颇多相同点,两人的作家梦都与英帝国有着紧密关系:“我与他之间是处于(或者开始于)相对立的两个极端。他富有,拥有特权,而我正好与他相反;我们各自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心。”(p.191)正是这“不同的文化中心”让两者在作家的“现代敏感性”上发生分歧。作家分析,如果20年前他坐在这个庄园里写作,那么,作为一个来自前殖民地流裔面对前宗主国的富饶﹑广博和悠久文化,只能在自己有限的生活素材里进行编造,对宗主国的文化作雾里看花似的描写,无法真诚面对自己贫穷﹑弱小的出生地,也即不具备一个真正作家应有的“近距离”创作意识,也因此只有通过隐瞒自身的某些方面的情况,正是这样的隐瞒,一种在某些叙述中通常采用的隐瞒处理方式致使我(甚至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急于了解情况和获得亲身感受的同时会忽略很多其他的东西。(p.191)
房东的作品也反映了这点。在房东送给作家为数不多的几首诗中提到了印度教神:天神克里希纳和破坏神湿婆,诗作显示房东对印度的爱恋情感不过是继承了英帝国在物质和权力达到顶峰时的一种对殖民地文化的类乎屈尊俯就的垂爱而已。房东也许到过印度,也许根本没到过,不可能对印度生活有“近距离”接触,因此不具备对生活长期观察从而培养起来的“现代敏感性”。最终房东的喜欢创作只能算是帝国文化在他身上自然浸淫的结果。第三章题目“常春藤”寓意深刻,它既是庄园里为数不多的为房东喜爱的植物,更是房东本人的写照,他也不过是英帝国这颗巨树上的一支常春藤而已。
小说第四章“乌鸦”主要叙写房东的一个旧友——作家艾伦的失败作家路。奈保尔在20世纪50年代末牛津大学毕业后在英国BBC广播电台主持“加勒比海之声”,开始步入伦敦文学界与作家们交往,艾伦是其中一个典型。他主持电台文学评论,结交知名作家,但没有影响力的作品发表,最后因人格分裂自杀。在英国居住了近30年后,当年过半百追溯这些往事时,奈保尔顿然发现:自己的过去就是艾伦的现在!“艾伦深受他的作家思想与写作素材的困扰,就如同当年的我”(p.287)。就如同当年的作家一样,艾伦不明白,素材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素材没找准就只有编造,歪曲事实,隐瞒自我。奈保尔回忆“那些日子里,在我写的东西中,我在自己身上隐藏我的经验,在我的经验中隐藏我自己,以那种方式歪曲事实”(p.288)。正因此,写出的文章的语言﹑形式和态度都极平常不过。没有最起码的客观态度怎能发现自我,从而体现一个作家的“现代敏感性”呢?没有对自己素材的准确把握又怎能写出具有普遍性﹑为读者认可的佳作呢?如同当年急于一鸣惊人的奈保尔,艾伦一直在暗示自己正在写一部伟大作品,却又迟迟拿不出作品,因此只有不断重复已写过的题材,而“他所持的文学态度更接近于他对生活的体验”(pp.288-289)。这种创作的曲折﹑坎坷和失败最终导致艾伦对自己只剩下厌恶﹑愤怒和沮丧,导致他分裂的自我,分裂的人格,自己“几乎连自己都不了解了”(p.293)。最终在一天晚上,他服下了足以致命的安眠药。艾伦之死在作家看来,实际上是一种创作死亡,这种创作致命伤口是模仿和重复,重复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创作不出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这是一种文学冒险,一种文学死亡。相反地,作家在经过五年摸索尝试后最终豁然开朗,找到的这种感觉实际是对创作所应具有的现代敏感性的一种顿悟,一种“创作抵达”的感觉,是对“作家之谜”的一种剖译。
4.结语
整部小说构思精巧,在章节组织上呈现出一种圆形结构。全文以杰克和他生机盎然的花园这一人类和生命的象征开始,由妹妹萨蒂的葬礼而引发的对杰克和他的花园的感触作结尾,首尾两章呈遥相呼应之势。在主题内容上体现一个解谜过程,首尾两章是作家对“人世之谜”和“人生之谜”的“近距离”阐释,中间三章是作家“近距离”切入“作家之谜”。
自奈保尔创作以来他一直否认自己是一个“西印度作家”(“conversations”10),也对自己被归于“后殖民作家”不予理睬。本文以为奈保尔是二战后崛起的属于后殖民时期具有自己独特创作审美风格的移民作家,他半个多世纪创作生涯给我们展示的文学世界始终贯穿着他独特的“近距离”创作思想,是作家一直声称自己“讲真话,讲实话”(Jussawalla,1997:154)这一作家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在《抵达之谜》中作家以一幅画作为载体传达他本人在天命之年关于人世﹑人生和创作的“近距离”思考,无疑创作于他绝不仅仅是“‘人与作家’的裂口就只能在他被压抑的‘殖民地—印度的自我’在写作中浮现之时才能得到愈合”(艾勒克,1998:203)。作品充分显示奈保尔是“一个文化上的旅行者,是一个‘超国界的’,而不只限于一个民族。他出生在过去的殖民地,文化兴趣在‘第三世界’,在其他方面则完全是世界主义的”(艾勒克,1998:268)。作品充分反映这位文学大师在全球化时代以自我为范本﹑对人类生存状况所作出的特有的人文思考和其创作上深厚的人文主义倾向。
[1]Cudjoe.R.Selwyn.V.S.Naipaul:A Materialist Reading[M].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8.
[2]Jussawalla Feroza.Conversations with V.S.Naipaul[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7.
[3]King,Bruce.V.S.Naipaul[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
[4]Naipaul,V.S.A Writer’s People[M].London:Pan Macmillan,2008.(文中所标注页码出处均出自本书)
[5]Naipaul,V.S.The Enigma of Arrival[M].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88.(文中所标注页码出处均出自本书)
[6]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7]杜维平.从未抵达吗?[J].外国文学,2008(2).
[8]梅晓云.V.S.奈保尔:从未抵达的感觉[J].外国文学研究,2003(5).
[9]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J].阮学勤,译.世界文学,2002(1):133.
[10]索鲁.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一场横跨五大洲的友谊[M].秦於理,译.台北:马可波罗文化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