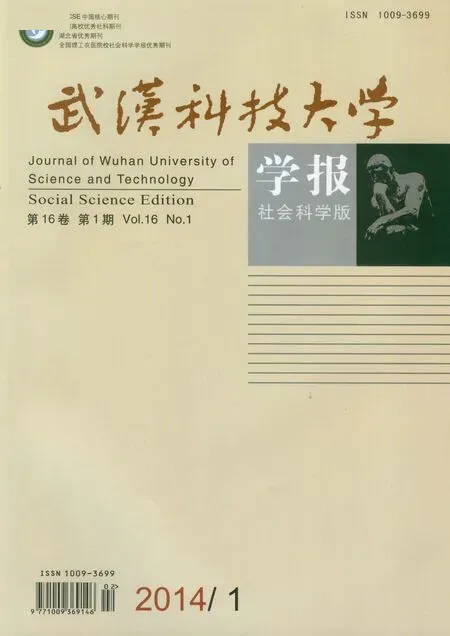论钱谦益的“穷而后工”说
2014-03-20昝圣骞
昝 圣 骞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为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汲古复雅、师心求变的诗学思想截断众流,泽被广远,是研究明清诗学不可绕过的一大关键。从陈寅恪先生发表名著《柳如是别传》至今,钱谦益与虞山派诗学渐渐成为研究热点,拓荒补白、富有新见的论著不断涌现。但由于钱氏《初学集》、《有学集》卷帙浩繁,文学思想丰富庞杂,尚有一些理论闪光点未得到足够关注。如其《冯定远诗序》一文中的“穷而后工”说,往往被研究者用来佐证钱氏论诗主情说或世运说,其在作者整个诗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对“穷而后工”这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要命题的发展和贡献却被忽视了①如丁功谊《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引用《冯定远诗序》并认为“钱谦益把诗人的喜怒哀乐与世人的喜怒哀乐对立起来,诗歌中的性情应该是‘独至之性,旁出之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李茀民《清虞山诗派诗论研究》已将钱说放在“穷而后工”思想发展史中考察,惜未能深入论析,也没有明确提出钱说的理论贡献,而且关于钱谦益“对于那些能自我穷蹇的诗人,他也深表赞扬”的观点与事实有所偏颇(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74-76页)。张炳尉《“穷而后工”说的展开》则认为钱说是强调“由穷愁困悴而生的激烈情感,往往比软沓平缓的情感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长江学术》,2009年第4期)。。从诗学体系而言,钱氏就“穷而后工”发挥出诗人之“性”、“情”、“学”、际遇多元互动而指导创作的观点,是其后来“灵心”、“世运”、“学问”三者结合的成熟诗学观的萌芽。从文学思想发展史来看,钱氏在“穷”和“工”两方面都作出了新的阐释,尤其将“穷”的范围从诗人之际遇扩大到诗人本身并侧重于后者,是对“穷而后工”说的重要发展,并涉及到中国古代关于“诗人”身份的塑造与认同问题,值得重视。
一
钱氏有关“穷而后工”的论说,主要见于《初学集》中《冯定远诗序》和《有学集》中《唐祖命诗稿序》、《李缁仲诗序》等文章,其中以《冯定远诗序》开篇之说最为集中鲜明:
古之为诗者,必有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轮囷偪塞,偃蹇排奡,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者,然后其人始能为诗,而为之必工。是故软美圆熟,周详谨愿,荣华富厚,世俗之所叹羡也,而诗人以为笑;凌厉荒忽,敖僻清狂,悲忧穷蹇,世俗之所訽姗也,而诗人以为美。人之所趋,诗人之所畏;人之所憎,诗人之所爱。人誉而诗人以为忧,人怒而诗人以为喜。故曰:“诗穷而后工。”诗之必穷,而穷之必工,其理然也。[1]939
这一段论证首尾完备、紧凑流畅。第一句话提出观点,二、三、四句从正反两面申说,末尾两句总结升华。“诗之必穷,而穷之必工”,是对“诗穷而后工”的解释:前一句对应着“然后其人始能为诗”,即必须达到“穷”的地步才能作诗;后一句对应着“而为之必工”,即达到了“穷”的地步就一定能作出好诗。“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轮囷偪塞,偃蹇排奡,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这些“古之为诗者”所具备的素质,正是“穷”的内涵所在,也是作者对当下之诗人、诗学提出的要求②通经汲古是钱氏一贯的思想,在其诗学体系中,“古之诗人”和“古人之诗”一直居于典范地位,类似于“学诗之法,莫善于古人,莫不善于今人”(《曾房仲诗序》)的说法在钱著中比比皆是。。
其一曰“独至之性”,指异于常人、孤僻纯挚的个性。在钱文中,这种个性是“敖僻清狂”(骄傲、孤僻、清高、狷狂)的,而非“周详谨愿”(温顺、谨慎、玲珑、从众)的。冯班(定远)“悠悠忽忽,不事家人生产”、“亡失衣冠,颠坠坑岸”、“阔略渺小,荡佚人间”[1]939等表现,即“敖僻清狂”的生动说明。
其二曰“旁出之情”,指充积于胸中却难以言说,每当感于情境、托于外物辄一发之的丰沛诗情。这样的感情“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不同于寻常之喜怒哀乐,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所能尽,所以无处不可发,也无处不在,“喜而歌焉,哀而泣焉,醒而狂焉,梦而愕焉,嬉笑嚬呻,磬咳涕唾,无之而非是”[1]909,“途歌巷舂,春愁秋怨,无往而非诗”[1]932。
其三曰“偏诣之学”,指不同流俗的、精深独到的学问。所谓“人之所趋,诗人之所畏;人之所憎,诗人之所爱”,诗人之所学、所好每每与大众不同,且专精独到,是成就学问的必由之路,“古之人穷经者未必治史,读史者未必解经,留心于经史者,又未必攻于诗文”,今之人“裁经割史,订駮古今”[1]884只是不学且妄的表现。在钱氏看来,文章“与锺鼎彝器法书名画近,与时俗玩好远。故风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邈于世”[1]907,有清雅不俗之爱好的人,往往擅长诗文。且古人之爱好并非玩物丧志,而是性情的表现和体道的途径,其人“追耆逐好,至于破冢发棺、据舩堕水,极其所之,皆可以委死生、轻性命。玩此者为玩物,格此者为格物,齐此者为齐物。物之与志、器之与道,岂有两哉?”[1]952,于其所学往往可以上窥其志。
其四曰“轮囷偪塞,偃蹇排奡”,指物质的贫乏、境遇的困苦和精神上的反抗。对诗人来说,世人羡慕追求的“荣华富厚”的生活是可笑的,世人诟病讥讽的“悲忧穷蹇”的生活反而是可贵的。文学的本质就是表现人性对现实的感受和反抗。“凡天地之内恢诡谲怪,身世之间交互纬繣,千容万状,皆用以资为状”[2]1 557,越是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逼迫和生活的压抑,越能够写出具有充实内容和真挚情感的诗歌。钱谦益在《虞山诗约序》中也说“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畜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囷结轖,朦胧萌折……于是乎不能不发之为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1]923,这里的“奇遇”不是指罕有的冒险经历,而是指怀才不售,不得已而“为退士,为旅人,为乞食之贫子,为对簿之累囚”[2]838的艰难境遇。
此外,钱氏在引文中标举了“凌厉荒忽”的诗风,并与“软美圆熟”相对,以说明“诗穷而后工”之“工”,也就是诗歌的艺术表现和成就。“凌厉”指诗歌慷慨激昂,气势逼人,若风樯阵马,与“软美”相反;“荒忽”则指诗歌意旨深渺,难以尽明,与“圆熟”相反。钱氏评穷老不遇的徐仲昭之诗“雄健踔厉,如虬龙虎豹,攫拏蟠踞于行墨之间,欲与之角,而忽已决去”[1]947,可作“凌厉荒忽”之生动说明;评唐祖命诗“云谲波诡,闻见叠出”、“摆磨跳踔、惊动海内”[2]789,亦与之相类。
上述前三点对应“穷”的极、至之意,第四点对应“穷”的困、乏之意。在钱氏看来,“诗穷而后工”,在于诗人必“穷”,而后其诗必工;而诗人之“穷”,不仅在于其境遇之“穷”,更在于其“性”、“情”、“学”之“穷”,即具有异于常人的孤高纯至的性格、极其丰富的感情和迥于流俗、独到精深的学问。诗人应当自“穷”于世俗,甚至自“穷”于社会,即便不为大部分人所理解,也应当坚持自己的人格、理想与追求。
二
如果仅从《冯定远诗序》这篇文章来看,似乎牧斋推崇狂狷孤傲的个性和凌厉荒忽的诗风,似乎诗人应当是一种际遇沉沦、作风癫狂,不能以常理推断、事事与世人相反的“怪人”;然而若将这篇文章放在明末的大环境中,放在整部《初学集》中,就会发现其所论自有其时代性和针对性。
首先,钱氏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激烈言论,与其崇祯年间的坎坷遭际不无关系。若撇开“凌厉荒忽”、“敖辟清狂”这些偏于一端的评语不论,牧斋本身倒是很符合自己对“穷而后工”的定义。钱谦益虽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探花及第,仕途却异常蹭蹬。及第后丁父忧归里,十年闲置;天启元年(1621年)甫出典试,便落入“科场关节”陷阱,不得已引疾出都。其后又被目为东林党魁而屡遭阉党打击,最紧张时“锢门扃户,块处一室,若颂系然”[1]1 643。崇祯初复被启用,又为周延儒、温体仁所嫉,以旧案遭贬。崇祯十年(1637年),又遭张景良讦奏、温体仁等人陷害,下刑部狱,被诬几死,次年五月方出狱。《冯定远诗序》正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左右①《初学集》未言《冯定远诗序》写作时间。今据陆贻典《冯定远诗序》云“若其问学渊源,才情意象,牧翁先生序之既详且尽……先生序成于崇祯之岁,刻之《初学集》,迄今垂三十年……戊申仲冬陆贻典”(参见冯班《冯氏小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一六,齐鲁书社,1997年),由“戊申” 年(1668年)上推三十年,知钱序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左右。,可以说清白被诬,以“幽囚困踣,慬而不死”的“世之僇人”[1]915自居的钱谦益,发出“人之所趋,诗人之所畏;人之所憎,诗人之所爱”这样的愤激之语是很自然的。同时,钱氏在大狱中的表现,倒真称得上具有“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据程嘉燧《钱牧斋初学集序》,钱氏当“身系囹圄,命如悬发”之际,却“嗜学益力,覃思逾深”,在“圜戸湫隘,暑雨跼蹐,殆井[非]人所居”之地,还能“朝吟夕讽,探赜洞微,孜孜不厌,一如平日,方与其徒瞿生、友人刘敬仲谈艺和诗”,这种性情显非常人所能有。于诗和诗道,钱谦益也算是有“至性”了。钱谦益不但在监狱里吟诗谈艺,还能以诗歌占卜战争之胜败,因为正人君子乃国家之元气,其诗“忧军国,思朋友,忠厚憯怛,憔悴宛笃,非犹夫衰世之音,蝇声蚓窍,魈吟而鬼哭者也”[1]915。“蝇声蚓窍”、“魈吟鬼哭”之类的词语几乎是钱氏《初学集》中排击竟陵诗风的专用语;当竟陵诗学风靡天下之际,钱氏比兴忠爱之诗教说不可不谓“偏诣之学”。钱氏于崇祯、顺治两下牢狱,两度读《史记》、《汉书》,在帖括语录之“俗学”的横流中,倡言经经纬史的汲古之学,又可说是学术上的“偏诣”,而这一“偏”,在明清学风的转变中具有关键作用。
其次,钱氏会有这样一番论说,也与此序是为弟子冯班而作有关。“古之文人才士,当其隐鳞戢羽,名闻未彰,必有文章钜公,以片言只字,定其声价,借其羽毛,然后可以及时成名”[1]941。钱谦益在序文中援引李东阳赠诗桑悦的例子,末尾又云“定远之名,从此远矣”,其以序文为冯班增加声价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史载冯班“性不谐俗,意所不可,掉臂去。胸有所得,曼声长吟,旁若无人。然当其被酒无聊,抑郁愤闷,辄就座中恸哭。班行第二,时目为‘二痴’”[3],同为虞山诗派中人的陆贻典也说冯班“与人交多率其真,或喜或怒,或离或合,人颇以为迂、以为怪,则避而去之”[4],可说是“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其论诗“沉酣六代,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1]939,学习六朝、晚唐之诗,于七子派、竟陵派影响甚大的崇祯诗坛亦可说是“偏诣之学”。概而言之,钱氏关于诗人与世人种种对立之说虽然令人惊骇,却恰恰是冯班之真实写照,而其“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偃蹇之遇”更是对冯班其人其诗的精到概括。
再次,将此序文放在《初学集》乃至钱氏全部著作中来看,其论“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核心仍在对“性情”、“世运”和“学问”的强调,旨归在于诗人应有怎样的修养。何为“至性”?从钱著之语境来看,“至性”当指纯真挚朴的性格①如《初学集·来氏伯仲家藏诗稿序》云来梦得兄弟“内行淳备,兄友弟恭……至性郁勃,怀而不谕”;《有学集·卓去病先生墓志铭》云“少有至性,事三母皆尽孝”;《有学集·故南京国子监祭酒赠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石门许公合葬墓志铭》云“公为人忠信易直,光明雄骏,事亲交友咸有至性”。,“独至之性”当指异于常人的、纯真挚朴的性格。至于“敖辟清狂”云云,当是作者就冯班、桑悦一类狂生、痴人借题发挥的说法,只是“独至之性”的一种表现而已。“修洁如处子,淡荡如道人,静退如后门寒素”[1]906的性格亦何尝不是“独至之性”;更何况有至诚之性的人,往往有出人意表的举止,也往往是世俗之人讪笑的对象,所谓“惟诚故愚,非愚不诚,未有至诚而不至愚者”[1]883,甚至“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凌厉荒忽”亦然,读《初学集》中“余独喜其渊静闲止、优柔雅淡”[1]908、“其为诗终和且平,穆如清风”[1]911等评诗之语,尤其在《徐元叹诗序》中有“宁质而无佻,宁正而无倾,宁贫而无僦,宁弱而无剽,宁为长天晴日无为肓风涩雨,宁为清渠细流无为浊沙恶潦,宁为鹑衣裋褐之萧条、无为天吴紫凤之补坼,宁为麤粝之果腹、无为荼堇之螫唇,宁为书生之步趋、无为巫师之鼓舞,宁为老生之庄语、无为酒徒之狂詈……”的大段设喻,可知钱氏并非独赏凌厉荒忽之诗,而是强调“导之于晦蒙狂易之日,而徐反诸言志咏言之故”[1]925,即真性情、真志意的表达。至于诗歌的艺术风格,自可以“奇正浓淡,万有不齐”[1]926。
钱谦益论诗人当有“旁出之情”,有鼓励言情、赞赏淋漓尽致地表达的一面,更有要求作诗者兼怀天下、关心世运的一面。他主张发抒身世之感,要求诗歌当关乎世运,反对枯寂幽寒的竟陵诗风。其评王元昭“有低徊萌折不可喻之情,有峭独坚悍不可干之志,而后有淋漓酣畅不可壅遏之诗文”,是建立在“有忠君爱友忧时怀古之志意,抑塞磊落,而激昂自命”的基础之上的[1]933。在《冯定远诗序》中,钱氏论冯班诗“其情深,其调苦,乐而哀,怨而思,信所谓穷而能工者也”,“乐而哀”三字值得玩味。乐与哀,本是相对立的两种感情;两者结合,“乐而哀”,并不是不合逻辑,而是安贫乐道、不以一己之穷达易心,有志于古而伤悲于今的境界。钱氏在《秋怀唱和诗序》中,曾借用韩愈的“乐而悲之”来说明这种境界。“旁出之情”,无过于伤春悲秋;而在牧斋看来,同样是悲秋,“悲忧穷蹇,蛩吟而虫吊者,今人之秋怀也”,“悠悠亹亹,畏天而悲人者,退之之秋怀也”,今人悲秋其情不可谓不深,却局促于一身、无关乎世道,不如古人之悲秋悲天悯人、心忧天下更为可取。所以他希望《秋怀唱和诗》的作者能“遗乎”今之秋怀而“志乎”古[1]963,就好像竟陵派幽情单绪之诗,非不“凄清感怆”,但在“光天化日之下”却显得那么不宜[1]929,更无补于岌岌可危的人心与时势。
同样,钱氏所说的“偏诣之学”也有其时代性和针对性。“偏诣”,是相对于驳杂、烂熟、肤浅、舛谬而言的,用世俗流风的眼光来看可能是“偏”,以经世致用的眼光来看可能是“正”。钱氏强调学之“偏诣”,实际上是推举不为明末“烦芜之章句,熟烂之时文,剽贼佣赁之俗学”[2]784所雾笼淹没,能够返古复雅的经经纬史之学,于诗文则是穷源溯流、上继风骚、别裁伪体、有所自立。“偏诣”云云,也有矫枉过正之意。牧斋重性情之真之正,有“宁质而无佻,宁正而无倾”之说;其论学有所宗,也有“宁朴而无冶,宁直而无游,宁狭而无夸”[2]784的说法。从一个人的学问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志向,有真诚朴质、迥出流俗的性格,浓厚宽广、兼怀天下之情感,其必有独到精深、矫俗正流之学问。在钱氏的“穷而后工”说中,“境遇”居于末位,其对诗人创作所起的作用被有意识地缩小了。若以钱氏崇祯十一年(1638年)写作《冯定远诗序》推算,是年三十七岁的冯班尚处盛年,钱氏本不好以“穷”来概括其命运。从其诗学理念来看,钱氏论诗旨归在人,在其人为何人与为何而作诗,至于诗人之命运遭际对创作的影响实际上是第二位的。钱谦益的“诗有本”说和“诗其人”说已为研究者所熟稔,究其义即在于“诗中有人”、“诗如其人”,诗中所表现的诗人的道德志趣是第一位的。南宋中叶的“江湖诗人”,绝大部分都是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之人,牧斋却认为“诗道之衰靡,莫甚于宋南渡以后,而其所谓江湖诗者尤为尘俗可厌”,原因就在于他们“以诗人啓干谒之风”[1]946。其评明代余杭诗人严印持之诗能转出同邑先贤罗隐之上,原因不在于他“不遇与昭谏(罗隐)同,而其穷有加焉”,而是“以印持之诗儗于昭谏,其志之所存,有未可同日而语者”[1]951。在《列朝诗集》闰集卷五中,钱氏评明人朱谋晋“人言诗以穷工,而公退以穷退,殊不可解”,其实原因还是在于朱氏“才名蔚起,颇事干谒”,不再“读书修辞”、“躬耕赋诗”了。
概而言之,在钱谦益自己的学术语境中考察其“穷而后工”说,可知其离不开当时的艰难处境和赠序的对象冯班,更与其一贯的诗学理论密切相连。至真至诚之性,至深至广之情,至精至正之学,以及穷蹇困乏之遭际,四方面之“穷”,才组成了“穷而后工”之诗人。钱氏晚年的文学思想有所整合,在《胡致果诗序》、《题杜苍略自评诗文》等文章中,灵心、世运、学问或再加上性情,几个方面紧密结合成较完善的诗学体系,对此学界已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论说。然而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诗学体系在钱氏的“穷而后工”说中已初露端倪,性、情、学、运四个方面构成了“穷”的四个表现领域,也构成了诗人应具备的素质,可以说是上述诗学体系的前身。诚然,钱氏并没有在《冯定远诗序》中明确这一体系,概括地以“穷”来要求诗人,虽然精悍却有笼统、含混、不易索解的一面,但却为我们理解他前后期的文学思想演进提供了一个角度。
三
钱谦益对“穷而后工”这一命题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穷”的范围从诗人之际遇扩大到诗人本身,并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后者,从而彻底改造了沿袭已久的成说,赋予“穷而后工”新的内涵。
“诗穷而后工”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忧患之书”《易经》,而经过司马迁(“忧愤著书”)、钟嵘(“托诗以怨”)、韩愈(“不平则鸣”)等人不断发展,终于在宋代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中得以明确提出。其后,这一命题得到历代文人的积极响应,成为一个经久不衰、意味深长的流行话题,既有赞同者和推演者,也有反对者和改造者。然而关注此命题的批评家基本都是在“境遇与创作”——具体地说是境遇之穷与创作之工——的逻辑圈子里打转,或强调“穷”对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如陆游),或着眼于文学发生机制而补充逻辑中间环节(如游潜),或讨论“穷而后工”说的适用范围及合理性(如纪昀);在他们的话语中,“穷”的只是诗人的境遇(有时扩大为时代),虽然也会谈到诗人之主观精神,却又有意无意和境遇对立起来,偏离了命题本身①参见:徐达《论“穷而后工”及其原因——读钱札记》(《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吴高泉《“穷而后工”的美学学理机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桂栖鹏、张学成《“穷而后工”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巩本栋《“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张炳尉《“穷而后工”说的展开》(《长江学术》2009年第4期);吴承学《“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而在钱谦益的《冯定远诗序》中,“穷”的内涵既包括境遇的“穷困”,也包括性、情、学的“穷极”,且重点在于后者,在于诗人本身的选择和修养。于是这一命题被彻底改造了。当历代批评家们还在争论“诗会不会穷人”、“穷是否就一定能写好诗”、“好诗不尽出于穷”等等观点的时候,钱谦益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对诗人本身提出了要求,而淡化了环境的决定作用,上面所有那些问题实际上已不必再争论了。
当然,在钱谦益之前或同时,并非没有人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如元代黄溍曾提出“适于先民性情之正”而“不俟穷而后工”[5]的观点,尤其钱氏同时代诗人吴应箕云“陶靖节怀用世之志,杜子美有忠君爱国之心,而时位不称,率多寄意于篇什,于是而谓诗以穷工亦宜。若本非其具,即老死沟壑,方求一言之几于道不可得,其诗又安问工拙哉?”[6],其论诗人之情志本在境遇之穷达与创作之工拙之先,与钱牧斋之说正相类似,只是不及钱说系统而醒豁。更令人遗憾的是钱氏之说虽然截断众流、另起波涛,却未能“沾溉后世”。在他之后,如钱大昕、翁方纲、纪昀等人频翻“穷而后工”之案,却未能继承钱说:
欧阳子之言曰:“诗非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吾谓诗之最工者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卫武公,皆未尝穷;晋之陶渊明穷矣,而诗不常自言其穷,乃其所以愈工也。(钱大昕《潜研堂集·李南涧诗集序》)
予最不服欧阳子“穷而益工”之语。若杜陵之写乱离,眉山之托仙佛,其偶然耳。使彼二子者生于周、召之际,有不能为雅颂者哉?(翁方纲《复初斋文集·黄仲则诲存诗钞序》)
是集以不可一世之才,困顿偃蹇,感激豪宕,而不乖乎温柔敦厚之正,可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矣。穷而后工,斯其人哉?(纪昀《纪文达公遗集·俭重堂诗序》)
斯真穷而后工,又能不累于穷,不以酸恻激烈为工者,温柔敦厚之教其是之谓乎?(纪昀《纪文达公遗集·月山诗集序》)
钱大昕、翁方纲仍然斤斤于境遇与创作的关系,认为诗之工者未必出于穷,也可能达而益工;纪昀倒是对“穷而后工”有新的阐释,只是却将这一命题简单靠向温柔敦厚的诗教,远不及钱牧斋之说深刻。
当代学者已深刻指出“穷而后工”说之中蕴含的文人反抗与超越自身命运的悲剧性内涵[7],钱谦益对“穷而后工”说的改造并没有消解这种悲剧性,而是通过对于“穷”的内涵的新诠释,表达了其对“诗人”这一身份的认知,塑造了“诗人”孤独而崇高的形象。“君子有奇志,而天下不亲焉”(曹学佺《钱受之先生集序》)。“诗人”纵然不必彻底地站在世俗的对立面,以至于“人之所趋,诗人之所畏;人之所憎,诗人之所爱”,但其在性、情、学、运等方面“穷其至”的表现,必然会造成迥出流俗、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结果,这是诗人所必须承担的。“中国诗学始终强调和重视诗人的社会责任,而当‘事业’与‘文章’‘常患于难兼’时,‘失志’诗人不得已就把用世之志寄寓于诗文。诗歌对于他们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而是生命价值的现实体现与历史延续的最佳载体”[8]。钱牧斋之诗学说到底是人学,只有先解决了诗人之道的问题,才能解决诗之道的问题。他的“穷而后工”说,说明了什么样的人才是“诗人”,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对于“诗人”形象的一种认同。“诗人既是孤独的,也是清高的。……虽然孤独,但是诗人具有一种遗世而独立的超凡脱俗”[8]。
[1]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 清史列传:九[M].台北:明文书局,1985:698.
[4] 陆贻典.冯定远诗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二一六: 冯班.冯氏小集.济南:齐鲁书社,1997:498.
[5]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9:4-5.
[6] 吴应箕.楼山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6.
[7] 张炳尉.追寻超越——从先秦儒家性命思想的困境看“穷者而后工”命题的生成与内涵[J].文化与诗学,2009(1):255-273.
[8] 吴承学.“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中国古代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J].中国社会科学,2010(4):178-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