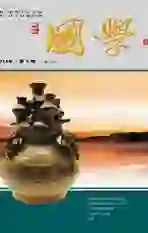曹家的没落
2014-03-20史景迁
[美]史景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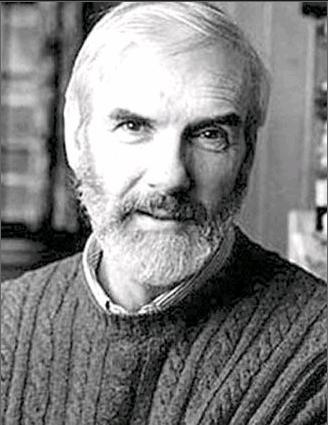
海外汉学家小传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 )美国籍历史学家,生于英国,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原名乔纳森·斯宾塞,中文名“景迁”二字取“景仰司马迁”之意。著作等身,代表作有《追寻现代中国》《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毛泽东》等。其作品文笔流畅,叙事性强。史家汪荣祖说他:“史景迁并不喜欢后学理论,他的书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无艰涩的名词,但他生动的叙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学界随后学而起‘叙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的呼声,使他成为史学叙事再生后的一支生力军。”
康熙死于1722年12月,李煦几乎即刻就被撤去了“苏州织造”一职。这对曹家而言,是在新朝的不吉利的开端。无可否认,李煦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也没有辉煌的业绩,但他曾是康熙宠爱的人,他的去职确实意味着旧的秩序已经变了。
雍正的一些对人对事的态度,对曹家大大不利。作为一个法家式的人物,他对于家奴严厉控制,常常对包衣表现出公开的轻蔑,他视包衣为卑下、不诚实、不听话的。他看轻织造职位的重要性,以为不过是“听得些流言再做传报而已”,他觉得-个巡盐御史“但清楚钱粮”,他激烈反对朋党,对无能和不诫实的惩罚非常迅捷。在他即位的头一年,便撤换了四十五位各部大臣和御史中的三十七位。他对地方上的财政状况非常关切,尤其是江苏,它的经济潜力巨大,然而却一再亏空。他整顿经济及官史行为的尝试从两方面下手:制度上,有1723年至1725年间的会考府;而涉及个人的方面,他授予许多下级官员密折奏报其同僚的权力,大大扩大了康熙开始的密折制度,并且他会申斥那些没有运用奏报地方事务权力的官员们。
雍正初年三位织造的灾难是很好的例子,体现出这位新皇帝如何审查并摧毁那些他认为无能的人和敌对者。李煦的后任、苏州织造胡凤翚,是头一个轮上的。1726年3月15日,江苏巡抚和来自内务府的官员高斌来到胡凤翚的衙门,告知他已被撤职。三月底,胡及其妻子年氏以及妾卢氏一起自杀了。胡凤翚及其全家的死,部分是因为他作为织造不够诚实,但主要是因为他卷入了丑恶的政治斗争:雍正与那些他认为与他为敌的兄弟们争斗不已,尤其是胤禩和胤禟,即康熙的第子与第九子。而胡凤翚的妻兄恰恰是与胤禟过从甚密的年羹尧……
曹家一定惊恐地关注着整个事件的发展,不仅因为曹頫作为一名织造也不是那么成功,而且,在曹家家庙立着的两只镀金的狮子,也正是雍正所痛恨的弟弟胤禟所赠。
李煦在1723年被撤职后又很快被捕了,罪名是向“阿其那”的侍婢馈赠礼物。“阿其那”在满语里意为“杂种”——这是雍正强加给他弟弟胤禩的侮辱性的名字。
同时,另外两位织造并非无事。曹寅的老朋友孙文成,从1706年开始就是杭州织造,在雍正当朝的头年就受到怀疑。1728年1月,孙文成由于不明的罪名受到指控,进而被解职。
曹頫在雍正朝初年成功地避免了触犯雍正皇帝。1723年12月曾有过麻烦的时刻,当时户部决定取消两淮巡盐御史支付江宁织造衙门费用的制度。而当时的巡盐御史接到这一指令的时候,已经将若干款项支付给了曹頫。他于是数次通告曹頫,请他回返这些款项,但没有得到曹頫的回应。最后,他上奏报告说,必须命令曹覜将此款项交还给户部。雍正下旨了。但是曹頫没有因其推拒而受罚,他依然按常规押运丝织品进京,得到皇帝的接见。
曹頫垮台的直接原因,几乎肯定是一件呈给雍正的奏折中报告了他的行为,这惹得雍正大大不悦。以往,在呈给康熙的奏折中,曹家往往有这样的报告;而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回转来针对曹家了。通常情况下,雍正只是看过这些报告之后便留着以备日后参考。不幸的是,这次奏报曹頫的官员正逐渐得到雍正的高度宠爱。这位就是噶尔泰,1724年被任命为两淮巡盐
御史,一位严肃认真而尽责的官员,他奏折上的朱批是曹頫和他的朋友们永远不会知道的。
1727年2月8日,噶尔泰呈递了一件奏折,报告各类地方宫员的能力。所涉及的范围,从盐商的儿子们到江宁和扬州的知府们,直到省级布政使和按察使。曹頫排列在第三,噶尔泰这么写道:
访得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
在这段边上,雍正在行间作了两段朱批,在曹覜的名字旁是“原不成器。”“人亦平常”一句边上是“岂止平常而已?”如果呈递的是这样的一件奏折,而皇帝仔细读过后同意奏报人的判断,那么所言及的为官者的仕途,无疑便很危险了。
曹頫于1728年1月被撤职,同时杭州织造孙文成亦去职。撤职的正式理由是曹頫的欠款亏空。在这些指控之外,还得加上雍正所认可的噶尔泰对他无能的攻缶。雍正仍在进行的对所有与胤禩和胤禟有关人员的清洗,也可能是一个因素。
奉旨査抄江宁曹家的官员隋赫德,上奏报告他发现了曹家与胤禟——对这个兄弟,雍正强加了一个“塞思赫”即猪的名号——之间联系的证据:
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内藏贮镀金狮子一对,本身连座共高五尺六寸。奴才细查原因,系塞思赫于康熙五十五年遣护卫常德到江宁铸就。后因铸的不好,交与曹頫,寄顿痛中。今奴才查出,不知原铸何意,并不敢隐匿。谨具折奏闻,或送京呈览,或就地毁销,均乞圣裁,以便遵行。
曹家覆没的更多详情不为人知。进一步的线索或许来自小说《红楼梦》,然而也没有家庭覆没的直接描写,因为曹雪芹在完成小说的结尾部分之前就去世了。小说中仅仅暗示家族成员犯了死罪,一方面官司失败,另一方面与地方上的几大权贵家族一起垮台了。这些家族当然是富有的,隋赫德查抄曹家之后,报告了有关情况:
房屋及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
这些只是曹家财产的基本部分,在抄家之前,他们一定已经将许多他们肯定拥有的值钱物件转移了。隋赫德在后面列举时没有提及他们的丝绸、书籍和艺术品,没有提及他们的西洋古董和皇上赐赠的礼品等——1727年间,它们一定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
按照雍正的诏令,曹頫的所有地产、房屋以及奴婢都归接任的江宁织造,也就是隋赫德所有。依据皇帝特意的安排,曹家在北京得以拥有部分房屋和奴婢。
经由这场变故,曹頫在历史上就此消失。单到乾隆初年,曹家显然得到了宽宥,曹宜,这位曹寅最小的弟弟还活着,并且担任护军参领兼佐领,他的先人也得到追赠的荣誉。1735年的一份沼令追封曹家兴盛的奠基人、曹寅的祖父曹振彦二品资政大夫;曹振彦的两位妻受封二品夫人。或许也就在这时,曹頫被授予内务府员外郎的小官职。然而,曹家没有能获得长久的复兴,而是旋即继续下坠。1745年,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困居北京西郊,开始写小说。
《红楼梦》第十三章,曹雪芹借一位嫁入贾家而临死的妇人说道:
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年,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成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就在这段中的俗语下面,那位批点曹雪芹手稿的叔叔写了如下的文字:
“树倒猢狲散”之语,余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伤哉,伤哉!宁不恸杀?
此一批语大约作于1762年,所以批者一定是在1727年左右听到此俗语的。那时,是家庭覆没之前的快乐时光。
并不是曹頫自己发现这一俗语的,他的父亲便熟知它了,并乐意在众人间提及。曹寅的一位朋友在一首诗后注语中写道:
曹楝亭公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
这个令人生悲的俗语冋响在整个家族历史中,而曹寅的援引是双重的讽刺。因为,它最初出典于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曹咏收到了寄来的以此俗语为题的一篇赋——在曹咏所依恃而发达起来的大人物死后,他便被流放了。曹寅显然对这个与他名字如此接近的曹咏深有所感。
曹家倚靠它繁荣鼎盛了差不多七十年的这棵大树,枝叶环盖,非常之大;它混合着许多方面,诸如官位、财富、才干、机敏,以及暧昧的包衣身份——它既属仆役又有特权,是满汉两族间的融合。但这棵大树的根向来不深不固,它的挺立只是由皇上的意志决定的。没有皇上的支持,大树必然倒伏,猢狲也就四散了。
这个隐喻并无贬义,毕竟,曹寅自己曾援引过它,他的后人在他之后也一再重复它.树倒了,猢狲就散了,如此而已。但对曹寅的孙子而言,写一部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红楼梦》,是对整个家族历史做最奇异的编织。这部小说改变了原来历史的悲剧性,因为它给家族处境的必然性添加了际遇的因素。因而,将这个隐喻推向它的逻辑结论便是合理的,用中国小说中一个最富魅力的形象的话来告别曹家的历史:
既允了……须与他了这愿心才是哩,为人为彻,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才是个全始全终,不然……反为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