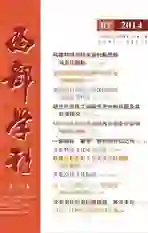汉字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再汉字化
2014-03-19申小龙孟华
申小龙 孟华
提要:汉字的文化属性问题,在普通语言学的文字定义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视角。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其次是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编码性质。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五·四”新文化时期直到上世纪80年代,汉字经历了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的思潮冲击,就是所谓“去汉字化”。上世纪80年代以后,“去汉字化”越来越受到批评,“再汉字化”受到重视。
关键词:汉字;去汉字化;再汉字化;汉字转向
H12
一、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个题目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审视,暗含着一个“制度陷阱”,因为它预设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文字的定义——依西方文化的教诲——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内涵。手头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伦敦应用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对文字的定义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也就是说,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抽出我们的《辞海》,看看它对文字的定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的文明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在西方语境中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独有的汉字感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的分析总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人文的视角。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说是说,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贴了汉民族“物生有两”、“二气感应”、“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心理。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曾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创造。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大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词汇。组义使得汉字具有了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2]183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性。难怪有人说汉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了。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我们就可以体会组义的长处。《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准备上医学院了,却站在介绍课程的公告栏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个将要上大学的人,对要学的专业居然“一字不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人听来匪夷所思。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索绪尔晚年在病榻上学习汉字,明白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汉字对汉语“言语异声”的表达进行观念整合,达到“多元统一”。这样一种“调洽殊方,沟贯异代”(钱穆语)的功能,堪称“天下主义”!一位日本友人说,外国人讲日语,哪怕再流畅,日本人也能发现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国大地,中国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为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在南方,人们则以为她是维族人。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整合性,在这位日本人看来,与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语。(当然,汉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义是不一样的。)汉字的观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极富包容性的谐音将汉语各方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维护其“言语异声”差别性的同时织入统一的文化经纬,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将统一的文化观念传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质文化的规范和力量。由此我们可知,汉字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柏杨所说:“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4]472
与汉字的观念整合性相联系的,是汉字的谐音性使地方戏曲有了生存空间。汉字的观念整合走意会的路径,不涉音轨,客观上宕开了方音艺术的生存天地。在汉字的语音包容下,汉语各方言区草根性的戏文唱腔与官话标准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相安无事,中国几百种地方戏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难以想象的异彩多姿。汉字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也就保护了中国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和家园意识。当然,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戏曲,不再具有汉字的书写性,从而不再在中华“雅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中具有话语权。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凭记忆而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韵文形式的歌舞成为一种“讲史”的仪式。闻一多解释“诗言志”之古义即一种历史叙事。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韵文史”渐渐不堪记忆和叙事之重负,西方产生了散文化的叙事诗,而中国却是诗歌在与散文的“混战”中“大权旁落”,淡出讲史的领域,反过来强化其诗性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汉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复旦大学的张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决定一种诗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与西方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西方艺术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张新认为,“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2003级新闻系同学对汉语是什么的回答,此时听来更有体会:汉语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门,“吹”、“绿”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诗经》,魂兮归来的《楚辞》;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汉字记载了浩瀚的历史文献,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汉字具有很强的民间游戏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们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就会从中找到中西语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的根本分野。此时,我们完全可以重新为汉字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
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三个通融性:
其一是小学(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通融。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其二是经学内部表现为文史哲的通融。苏轼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汉字元编码为传统文史哲提供了统一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经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经、史之所以相通,实际上基于汉字的表意思维或元编码:表意汉字既是一种对事实的照录(“史”的方式),又是一种对世界的形象表达(“文”的方式),还是一种对现实独特的认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实为汉字表意性元编码的体现。
其三是小学内部表现为语言与文字、书写文本与非书写文本的通融。我们分别表述为字词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词通融:汉字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符(语素或词),这要求汉字保持一个有意义的形体、一个音节、一个词义三位一体。这种对应使得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字形与词形之间难分难舍,呈现一种跨界、整体通融性,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独特的既分离又统一的张力关系。再看名物通融:从言文关系看,汉字代表的是一个语言概念单位,而从名物关系看,汉字对应的则是一个现实物,这就要求汉字对现实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绘画性特征。如“仙”这个简化字,字面义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达某个现实物的。汉字的这种意象性打通了书写与绘画、书写与物象的界线。这种书写与非书写之间的越界,进一步造就了汉字书法、文人画这样的书写编码与非书写图像编码相通融的文化景观。
这三个通融显示了汉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说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存在基础,也是中国语文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
中国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主要发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时期。该思潮引进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文字看作是单纯的记录口语、承载语言的科学工具,因此将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和口语看作是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根据此标准,远离口语的汉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话文, 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颠覆,这成为“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汉字化”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6],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7],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8],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9],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10],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12],《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徐通锵1992、1998,苏新春1994,潘文国2002);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曹顺庆1997);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杨乃乔1998);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刘晓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叶秀山1991);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孟华2004)。
“再汉字化”思潮或中国学术的“汉字转向”的核心问题是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在这种关系中的本位性。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了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估价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一方面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又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面临一个“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再汉字化”立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所贡献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再汉字化”转向,也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那里吸取方法论立场。复旦大学的文化语言学在八十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虑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性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又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这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再汉字化提出的汉字文化的新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理念:语言(言)、文字(文)和视象符号(象)三者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条件。中国语言、学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汉字的问题,即以汉字为枢纽,在言、文、象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并将这种以汉字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离又统一看作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学科分治的壁垒,在一个大汉字文化观的格局下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立场也可叫做“新语文”主义。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五个基本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1)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
(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
(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
汉字文化新视角的研究,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将要实现“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古文字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4]柏杨.中国人史纲(上)[M].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5]张新.闻一多猜想——诗化还是诗的小说化//新诗与文化散论[M].学林出版社,1995.
[6]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是思辨录[M].学林出版社,1989.
[7]徐通锵.语言论[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10]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
[11]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12]旻乐.母语与写作[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申小龙(1952―),上海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理论语言学研究室主任,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生导师。撰著出版有关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汉字的文化内涵及建构规律的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要著作有《中国句型文化》《文化语言学》《语文的阐释――中国语文传统的现代意义》《中华文化通志·语言文字学志》《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汉语人文精神论》《汉字人文精神论》《当代中国语法学》《社区文化和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纵横谈》《文化语言学论纲》《语言的文化阐释》《汉语语法学——一种文化的结构分析》《汉语与中国文化》《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申小龙论文集》《申小龙自选集》等。主编《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论集》《走向新世纪的语言学》等论文集。主编高校文科汉语专业主要基础课教材《现代汉语》《新文化古代汉语》《语言学纲要》。主编“文化语言学”丛书、“大千语言世界”丛书、“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
孟华(1954―),山东潍坊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语言符号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汉字符号学》(合著)、《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文字论》等。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