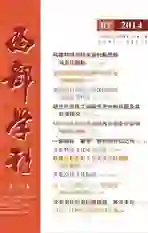一部揭开“秦隶”面纱的开山之作
2014-03-19张二雄
摘要:李甫运先生《秦隶》一书将评史、文字、书法三者有机统一,从多维视角阐释了秦隶的艺术特质和历史地位,是一部集学术考究、艺术审美、关照现实于一体的典范之作。是书的学术价值尤其值得重视,著者对秦隶的演变源流和历史定位提出了有别流俗的观点,指出秦隶从秦孝公至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已成为举国上下的日常用字,秦始皇“书同文”不是指小篆,而是指秦隶,这在文字学史的研究中,将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关键词:《秦隶》;源流;书法;艺术审美
中图分类号:J292.22
李甫运先生的《秦隶》一书于2012年11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大8开本,厚重大气,装帧精美,这是先生十余年来研究秦隶、创作秦隶的呕心之作,也必将是一部嘉惠学林的学术大著!是书内容分为三部分:展示秦隶风采、漫论秦史新见、探究秦隶源流。其中第一二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合观,因为漫论秦史的文字就是以秦隶书法为载体展现给读者的,第三部分以两个专章“秦隶小史”和“秦隶源流略述”于书后。三部分各具特色,每一部分在其所属领域内的学术价值均不可小觑;三部分互为整体,理清秦隶的演变源流,必先对秦史作一梳理,而秦史中体现出来的有关秦人和秦国的历史信息,对准确把握秦隶的特点和精神风貌又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先生的学生,一个同他一样钟情于书法的人,拜读先生的大著后,欣喜之情不能自已,写出以下文字,管窥全豹,权当是读罢先生《秦隶》一书的后感。
(一)
“漫论秦史新见”部分,先生以《史记·秦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为经,沥青秦史发展脉络,对秦史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和关键人物,又佐以《尚书》《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和《史记》中相关篇目做了横向的说明和比较,经纬交叉,点、线、面有机统一,互相印证。这种横向的延展,犹如历史年轮的一个清晰生动的横截面,让我们在审视历史人物和事件之时,形成的认识更加客观。这种叙述体例的安排,也给全书平添了一种顿挫回旋之美。如叙至秦穆公三十六年,穆公大败晋人,报崤山之仇后,在军中发表公开演说,演说具体内容在《史记·秦本纪》中只有“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令后世以记余过”等字眼,语焉不详,穆公其人虚怀纳谏、知错即改的品德未得到充分体现。而穆公演讲的内容就在《尚书·秦誓》中,先生将其230余字分七幅书法录之,则弥补了这一缺憾,秦穆公“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的大度与从容,得到具体的说明。再如,论及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法治状况如何,先生引用《吕氏春秋》中一个很鲜活生动的例子做了说明:“墨者有钜子腹朜,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因为他年长且无他子,故“令吏弗诛”,而腹朜以“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对答惠王,并不领情,卒杀其子。腹朜的思维和行事原则虽然受墨家思想的支配,但“居秦”二字则给我们明确地透露出一个消息,商鞅变法的影响已在秦国潜移默化地生发滋蔓开来,无论贵贱贤愚,法律面前任何人没有特权。这也和《史记》中“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的记载相互印证,合之无间。先生在爬梳商鞅变法这条“线”时,引用《吕氏春秋》中的这个“点”,生动具体地说明了问题,以点带线,颇具匠心效果!
先生在“秦史新见”这四字前,冠以“漫论”二字,除是著者的自谦,我想,更是给读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不故作深奥,不为考究而考究,为当世社会改革和发展寻找一二启迪,是先生的根本着眼点所在。这和当下众多学术论著在价值取向上是迥异其趣的。以此为宗旨,先生在论述时左右逢源,又博观约取。叙述秦史之变,探寻兴替之缘,除正史材料以外,又有民谚和历代文人诗歌,在形式上可谓“漫论”。然读了是书,你会发现先生的态度是异常谨严的,全书的思想精神是异常凝练而颖透的。举书中正史部分而言,评述秦史的材料,皆以关乎秦国兴亡的关键人物和核心事件为标准,并以时间为线索,处处都在关喉。这样,先生用最经济的文字沥青了秦史发展脉络,毫无累赘之感,也将秦在治乱兴亡中给后人的历史启迪揭示出来。从他的论述中,我总结为以下三点:(一)立足实际,创新进取;(二)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三)知错即改,兼容并蓄。先生之所以重新读史、评史,其终极目的又是着眼于当前社会现实的,我想,这是这项工作的最大价值所在。先生立足之高远,用心之良苦,岂不激励我辈!兹举一二例言之。
比如《史记》记载秦穆公卒后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当时社会上的君子即言“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先生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重视人才,重用人才则国强,丧失人才则国必弱,千古一理。”简简单单几句话,可谓辞微旨远,先生之用心,不言而喻。再如,先生总结商鞅变法给我们的启示是:“行义不顾毁誉、不害公,禁私门请托和游说求官,以保证干部队伍的可靠和有效……今日之改革,难道不应当从这里学点什么吗?”将论史的落脚点联系到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上,这就回归到学术最本根的使命上来:经世致用。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不胜枚举,集中体现在大量富有时代气息、醒目活泼的语词的使用上。如文公献岐以东之地给周是“搞统战”,秦穆公大胆起用百里奚是“放手给权”,范雎提拔郑安平是“人情官”,郭开、靳尚在金钱面前失去节义是“丑恶表演”,秦重用年轻的甘罗是“绝无教条气息”,如此等等,这一番生动诙谐的语词和比喻,意在使学术和现实生活接轨,实现学术的正真价值。由是观之,此番“漫论”,岂可等闲视之!
作为形式上的“漫论”,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评述秦史时选录的大量文人诗歌。如言秦襄公救周,引《秦风·无衣》来说明秦人面对劲敌时的同仇敌忾;穆公用活人殉葬,引《秦风·黄鸟》说明“秦不能复东征也”;对商鞅变法的评价,录王安石《商鞅》一诗充分赞扬商鞅“一言为重”和“能令政必行”的改革魄力;对苏秦功绩的评价,则引贾岛《经苏秦墓》一诗,说明苏秦的历史功绩是“使秦十五年不窥函谷关东”,表达后人对苏秦功业的艳羡。正史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交叉,使得在纵向性历史叙述的连续中,又有了暂时性的间断,给读者的思维带来片刻休憩,使我们从历史叙述的惯性中跳出来,再从文学家的角度审视其人其事,两相比较,我们的认识才会更中肯、更深刻,读来也倍感轻松愉悦!
文学家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可以借用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才略》中概括曹丕和曹植文学成就的两句话来说明问题:“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都容易从个人品德和身世遭遇出发立论,会带上强烈的主观情感,若此人德行不佳,他的历史功绩往往易被遮蔽或漠视。太史公评价商鞅“刻薄少恩”,而先生言“置自身一切于不顾,方可言变法”,充分肯定了商鞅“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变法精神和历史贡献。张仪用诈术欺楚,后人都同情楚怀王而对张仪厌恶至极,如果我们的思想认识也仅停留在这一层,岂不偏颇!先生分析李斯对张仪的评价,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并言“若真死于楚怀王之手,岂不可悲”,真是警醒人目之言,令人深思!对秦王杀韩非一事的评价,先生更是运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放在战国时代“群雄并争”这个大背景下思考,立论当然无可辩驳,使人信服。我想,读是书至此,漫论秦史之所以为“新见”,读者自可管窥一二了!
(二)
如果从文字学史角度来审视这部书的价值,“秦隶小史”系列论述和“秦隶源流略述”这两个专题应当引起学界的格外重视。先生着重利用出土文献理清了秦隶发展的源流,并纠正了学界长期在小篆、隶书产生发展问题上的相关谬误。充分肯定了秦隶“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封建帝国的建立及其有效运转”做出的巨大贡献。我想,先生的研究成果,在文字学史的研究中,将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秦隶”一名,最早见于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后人能一睹其芳容,却是时隔千载,“挥动在云梦睡虎地秦墓上的洛阳铲打断了历史的惯性”,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之后发现的四川青川木椟牍、湖南龙山里耶木牍等一批富有代表性的出土实物,使我们得以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叹服于秦隶的绚丽多姿。但随之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秦隶在什么时候产生,作为一种日常用字普及又在什么时候?
秦隶简牍在世人面前一次又一次的亮相,当然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冲击了文字学史的传统观点。比如,裘锡圭先生在其《文字学概要》一书中,就认为战国晚期是隶书的形成时期,笼统的“战国晚期”,表现出著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犹豫与彷徨。拿青川木牍来说,是秦武王时期下层官吏书写的田律,结体严谨,点画规范,已具备了书法艺术的自觉审美性。由此可以肯定一点,秦隶的形成要远早于秦武王,其源头还应向上追溯。先生有志于澄清这一学界公案,通过对出土的各类实物的细心研读,认为秦武公时秦公镈铭文所表现出来的“简练平时而又雄强”的艺术特质,对秦隶的出现具有“道夫先路”的发轫意义。又通过对商鞅方升铭文中“年”、“月”、“乙”、“造”等字结体用笔的分析,提出和秦始皇时所用秦隶有一脉相承的共性,从而得出结论:在商鞅变法后期,秦隶已经在秦国广泛使用。再往下,先生又将目光锁定在秦惠文王封宗邑瓦书上,认为它是商鞅方升到青川木牍之间文字形态上的唯一中介。我们观此瓦书,结体已打破了籀文的严谨与规整,表现出隶书特有的舒展与拓宕,流露出一种自然之美,特别是在用笔上已有明显的方折,起笔和收笔之处也有了明显的粗细变化。先生将此定为秦隶的迅速发展期,是极有识见的。青川木牍和云梦睡虎地秦简,用先生的话说就是秦隶的“第一个成熟形态”和“完全成熟”的标志。于此,秦隶发展的历史脉络便清醒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此处还有一个小细节值得我们留意,青川木牍的许多横画都是逆风起笔,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蚕头”,而且一字之中不避重复,个别字的收笔也出现了略微的波折,即后人所说的“燕尾”。这种情形在睡虎地秦简中更加普遍,举其中的“之”字而言,最后一横作为全字主笔,“蚕头”微敛,用笔逐渐由细而粗,“波折”燕尾的写法与东汉的隶书别无二致。或许以上特点,正是造成青川木牍所在的郝家坪古墓在断代上产生分歧的根源所在。这却恰恰证明了先生在《秦隶》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秦汉文字一脉相承,汉承秦制,秦隶直接就被汉袭用了。
秦统一全国后“书同文”,“文”即小篆,这是两千年来文字学史和书法史的共识。先生弄清了秦隶的源流后,明确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书同文”不是指小篆,而应是秦隶。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他先解决了另一个基本问题:秦隶形成后在秦国和秦朝的地位问题。从秦隶的运用主体来看,秦封宗邑瓦书的书写者是惠文王,商鞅方升的颁行者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青川木牍的持有者是下层政府官吏,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黑夫”是普通士兵;内容有国君的诏书,政府的田律档案,兵士的家信;地域分布从秦的起家之处甘肃天水到荆楚的湖南湖北;时间跨度从战国秦孝公一直到汉初。由此,先生得出结论,无论是从时空分布上,书写的内容上,还是运用的主体上来看,秦隶从秦孝公至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已成为举国上下的日常用字,这就彻底地打破了一直作为共识的“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的传统观点。先生并依据秦史分析提出“秦的官狱职务繁不始于秦始皇,而是始于秦孝公,始于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他运用二重证据法否定了秦始皇时“初有隶书”的立论基础,故而,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秦始皇是否有过形式上用小篆“书同文”的举动已不再重要,而实质上秦隶作为“书同文”的真正“历史当事人”这一事实,岂可辩驳!先生对秦隶历史地位的界定也就显得高屋建瓴:“秦隶对秦国灭掉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功莫大焉!”
(三)
如果我们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拜赏这部厚重的著作,《秦隶》无疑是一座气象万千的艺术宝库,观者无不被先生的书艺深深地打动折服。一者,是因为目前国内书法界很少有人问津秦隶这块处女地;二者,实在是因为先生的秦隶书法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展读《秦隶》,一幅幅绮俏多姿的作品让我们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观先生书法,雄强处让人怒目,纵逸处让人超然,敦厚处让人静穆,流走处让人爽朗!如果借用后人评价《史记》的四个字来概括他的秦隶艺术风貌,再贴切不过:雄深雅健。他笔下的秦隶多姿多彩,仿佛将我们带回了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先生的书法成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对战国的时代精神和秦隶的艺术风貌与源流趣向是心领神会的。当然,作为一位潜心于秦隶的书家在国内书坛上独树一帜,为此而付出的努力与艰辛是鲜为人知的。他曾研临《曹全碑》《张迁碑》三十载之久,对此二帖及东汉重要隶书碑帖烂熟于心后,决心上溯其源,考古界秦隶简牍的发现,最终使他和秦隶不期而遇。如逢故人的感觉让先生欣喜不已,从此更是临习不辍,日不间断。“庾信文章老更成”,先生书艺达到今日之面目,由来非一朝也!
观先生秦隶,结体严谨,质实凝练,简刻省净,自然流露一股肃穆之气,又给人一种清新朗目之感。又缘用笔富于干湿肥瘦之变化,平实肃穆之间,又不乏灵动与活泼。观其润笔,如破土新芽,嘉圆可喜,活泼生动,憨态可掬;其枯笔如寒枝傲霜,劲对朗秋,体骨嶙峋,倍感萧森。各自成体,如月下腊梅,朵朵可采;又气脉贯通,若三春芳甸,春晖绣锦,自成一幅。
秦隶脱胎大篆,结体修长,故书家书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落雨般的下坠感,读者心里未免会觉得“沉重”。而欣赏先生的秦隶丝毫没有这种感觉。这缘自他在结体、用笔、章法上极尽变化,也缘自秦隶本身的一个特点,每字最后的主笔,用弧笔向左或向右荡开去,是为东汉隶书“燕尾”最初的原型。就单个字而言,这种笔法有效地避免了纵向取势所造成的“下坠感”,从整体效果上来看,又使崇尚“简练平实而又雄强”的秦隶不自觉地甩开了长袖,焕发了装饰性的美感。先生在这一弧笔的经营上,是颇具慧心的。有短促厚实的润弧笔,有修长挺硬的枯弧笔,有两端细而中间丰腴的圆弧笔,有左右相对的短直弧笔。按弧笔的弯曲方向可分两类,向外的弧笔和向内的弧笔。而这些弧笔在收笔时的变化又层出不穷,有不加修饰的自然收,有回锋收笔的圆转收,有中锋运笔时的露锋收,也有侧锋运笔时的钩挑收,可谓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每一笔无不收得干净、稳重、凝练。
先生在秦隶创作中,能如此率性所至,又丝毫不失法度,得益于他对出土秦隶简牍的潜心研磨,得益于他对书法创作“守正出新”这条正道的坚守,也得益于向书界老前辈的虚心求教。先生的书法在结体取势上深得睡虎地简牍和里耶木椟的神髓,睡虎地简牍结体严谨,厚重凝练,质实雄强,他的书法中“敦厚”的一面应受其沾溉。相对于睡虎地简牍而言,里耶木椟就显得草率飘逸些,如果说睡虎地简牍显现出后世《张迁碑》的大气厚重的话,里耶木椟则和后世的《曹全碑》的审美趣向有某些相通之处,每个字都是腰部收得很紧,主笔宕得很开,犹如一个束腰长袖的舞女,使观者无不神思飘渺,先生书法中纵横取势的修长弧笔正宗法里耶木椟的这一点,却写得更加规整,讲求整体的美观。
“转益多师”,是一个成功书家的必经之路。卫俊秀老先生是国内上世纪著名的行草书法家,曾和先生同住一楼,先生利用楼上楼下之便,曾长期向卫老请求教益并共同切磋书艺。“弄清每个字的运笔线脉”、“临帖先读帖”、“运笔要点画到位”、“收笔要凝练不浮”,这些都是先生同卫老在书艺切磋和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们明白了这些法则,再来拜赏先生的秦隶书法,对他的书法面貌和书艺精神的领悟岂不更深一层!守正才能出新,不守正的出新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走进死胡同。在日前书法界盲目追求出新的大气候下,先生则冷静地强调“守正”的重要性,尤为可贵可佩!在各种俗书、奇书、怪书、媚世书炫人耳目的今日,一个真正热爱书法的人到底该走哪一条路,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先生的秦隶书法在国内影响日渐扩大,相关媒体曾以《华夏秦隶第一人》为标题作过报道。《秦隶》一书的出版,不仅是书法界的幸事,更是文字学史上的福音。一如他笔下的秦隶,先生给人的一种感觉是弘厚宽博,敦厚之余是随和,更是严谨。“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这也是先生立身行事的标准,他是一个用心做事的人!我们很难揣测先生何以会在书法这条道路上心无旁骛地一直走到今天,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书法让他开心,也给他带来了福音!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作者简介:张二雄(1990―),男,甘肃天水人,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