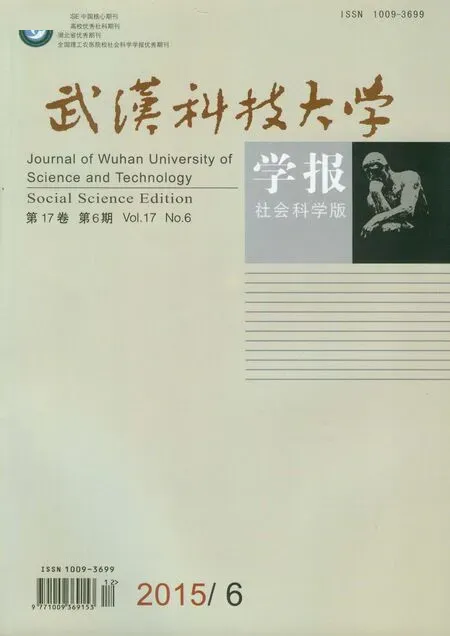与教育历史主体的心灵对话
——心态史学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
2014-03-18申国昌张万红
申国昌 张万红
(1.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纵观中国教育历史长河,不难发现其沿革走向总以一种规律性态势向前延伸,产生这一轨迹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但其中也掺杂着教育历史主体的心理因素。要揭开其神秘面纱,以科学方法探析其中奥妙,运用心态史学法去审视与体认是必由之路。这一史学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走进教育历史主体的内心深处、剖析其提出教育主张的根本动机、还原历史真实面目,而且为未来教育史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方法,使教育史研究趋于更加全面、科学,进而展现教育史学的多元化走向。
一、教育历史主体的心态影响教育发展走向
教育从远古发展至今,在每个发展阶段的重要转折点都会涌现出具有时代影响力的个人或群体,在教育历史舞台上他们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的甚至还影响到了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教育历史主体正是以其深层心理活动与心态展现来影响着教育历史的进程与走向,因此,要深入理解与把握中国教育历史的脉络与走向,有必要深入到教育活动主体的心灵深处,去探究历史主体心态影响下的教育历史实况。
(一)孔子以“内圣外王”的终极追求诠释以“仁”为核心的教育
终极观是人的意义和价值观系统的核心[1]。正如终极观构成对生命意义系统的支撑,“仁”在孔子思想中也担负着这一作用。《论语》中孔子在不同语境下论述“仁”,其含义难以抽象概括,而朱熹将其总结为“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2]。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孔子的“仁”是一种对人生、社会和天道的自我超越性的生命体悟。“仁”具有多重含义,孔子以此为核心构建生命的目标和意义[1],从这个角度看“仁”是人生的最高目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其中“仁”的形成包含着复杂的心理过程,孔子晚年多谈“仁”,“仁”应该是孔子中年以后形成的思想,而这一时期正是孔子人生跌宕起伏的时期,也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的时期。由此可见,孔子“仁”的终极观形成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内心变化,这一心理流变最后外化为儒家理想人格的追求。儒家以“内圣外王”为最高追求,内在修养达到至高境界才能成为所谓的“君子”。牟宗三指出:“‘内圣外王’一语虽出于 《庄子·天下》篇,然以之表象儒家之心愿实最为恰当。”[3]“仁”是孔子个体价值观的凝聚,但投射在儒家思想体系之中便是“君子”的化身,从而也影响着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
(二)张之洞以曲线救国梦勾勒“中体西用”的教育蓝图
在近代,张之洞是新旧体制新陈代谢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时人评论其为:“张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以其后人而旧……然以骑墙之见,遗误毕世,所谓新者不敢新,所谓旧者不敢旧,一生知遇虽隆,而卒至碌碌以殁。”(《张文襄公事略》)的确,他的思想具有守旧与革新的双重性,作为个体其内在心理也同样幻化为旖旎纷呈的世界。如果对其身份进行定位,那么他首先是清廷重臣,其次是洋务健将,然后才是西学领头人,他一生的仕途路是为忠君爱国抱负展开的,借用杜牧的“丸之走盘”来描绘他的心理旅程最贴切,“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樊川文集》)。如果清政府是“盘”,那么张之洞便是“丸”,早期他忠君爱国偏于保守,之后向洋务派转化,仿西法“图富强”的最终目的是“保中国保名教”,“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这道破了“中体西用”的终结目的。戊戌政变后他囿变为卫道士的角色,可以说保守与革新贯穿其一生,他在临终前自称“吾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矣”[4],这就决定了“中体西用”终究沦为其曲线救国的工具,同时也开启了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的潮流。
(三)陶行知以爱满天下演绎“生活教育”的勃发活力
奉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家陶行知曾在诗中写道:“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从侧面反映出他的深层心理,其心理演化为行为就是用爱办教育:爱国家、爱人民、爱学生,秉持这样的信念开展生活教育。①爱教育。1914年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②爱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指出:“教育没有独立的生命,它是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唯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才算是我们的教育。国难教育是要教人救民族之命,则教育之命自然而然地得救了。”[5]③爱人民。1917年陶行知留学归来说“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5]。于是1923年陶行知同黄炎培等人组建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课本。为推行平民教育,他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之职,风尘仆仆奔走全国十几个省市,他说:“凡我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到的地方。”[5]④爱学生。陶行知认为:“为了苦孩,甘当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5]并向教师高呼:“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6]带着爱的信义,陶行知开展“生活教育”,这一教育不仅指出了当时教育的弊端,而且给当今教育改革以深刻启示,散发着生机勃发的生命力。
二、科学分析教育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
历史如同一张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经纬交织而成的网,变幻莫测的历史事件和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都悬挂在这张网上。历史又像一条偶然性与必然性交汇而成的河流,欢歌与呜咽、畅笑与叹息都随波而起。偶然性使历史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似乎充满奇迹、不可捉摸;必然性给历史涂上一层宿命的色调,似乎一览无余、干瘪乏味[7]50。每位教育历史主体的价值取向有其特定时代背景的必然性,也有主体自身的偶然性,揭开这种宿命与神秘的面纱就不得不引入心态史学法来探析他们的心理活动。作为新史学,心态史学从法国走向世界发展至今,它的突出贡献是使历史研究由“无人历史”转移到“有人历史”,把人作为研究主题,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使人物研究由平面性过渡到立体化,使历史主体变得饱满而丰富。
(一)主体选择是映照人物心态的镜子
选择是反映人物心理活动的窗口,窗内藏有多种选择动机的混合物,透过窗户我们可以探寻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主体选择是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在客体的多种发展可能性中收缩自由度的过程。主体能够进行选择的依据主要有两方面:客观环境的可能性空间和主体需求的多层次结构[8]。其中客观环境的可能性空间是事物发展存在和发展中各种可能性、趋向性的集合,反映在主体身上就形成不同的目的和方法,从而对自己的活动作出不同的反思和调整,这正是主体选择活动的前提条件。孔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恰逢王室衰弱、诸侯争霸,所以诸侯国纷纷进行政治改革。而张之洞作为晚晴中枢重臣,当清廷面临生死危机,他义不容辞地忠君效国,内忧外患之际欲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方法企图拯救“风烛残年”的封建帝国,殊不知时局已变无力回天。固然他们的选择受时代激变可能性的推动与制约,同时他们个人需求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作为合力之一影响着历史发展轨迹。因此主体选择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含有必然性的宿命和偶然性的神秘色彩。
(二)个体需要是主体选择的内在动机
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犹如一个异彩纷呈的万花筒,变幻莫测、难以捉摸,但是一个人的追求和需要是呈现心态的外在形式。人的需要是历史选择的主体因素和动力源、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一前提、是人们从事劳动以及各种实践活动的一般目的和内在动机,“人们在争取满足自己的需要当中创造他们的历史”[7]38,因此需要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主体的需要及其对需要的意识是选择的出发点,是人类追求自身需要的满足,需要所派生的欲望、利益和热情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孔子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了“仁”的核心价值观,“仁政”是其理想的治国模式,与之相应的理想人才是“君子”,抱着这样的政治信念,他开办私学教育,把“从政为官”作为教育目的。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活跃人物,他积极筹办洋务工业、大兴新式教育,采用“中体西用”模式来“求富”,但他毕竟是深受儒家传统教育思想熏陶的科举侍臣,骨子里始终涌动着封建因子,所以“自强”是“中体西用”的出发点和归宿。陶行知怀着一颗博大的赤胆之心来实现其教育者的崇高使命,国难教育运动是其“教育传道与救国”的最好诠释。
(三)阶层利益是主体选择的参照标准
一个人的心态的选择或多或少受利益的支配。利益是历史的支点,爱尔维修曾说过:“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7]42,因为有着相同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人们集结成一个利益群体。单独的主体可以有需要,但不能形成利益关系,利益使利益主体不单纯从自己的需要冲动出发,而是把自己所属的利益群体的需要冲动融合起来,将两者的融合体转变为共同的欲望、动机、目的,最后导向行动[7]43。行动是心声的强有力表现,而利益是驱使行动发生的催化剂,其中阶层利益是历史主体选择的参照标准和附加条件。孔子作为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一心想复制周礼,他的言论也只是为卿大夫阶层服务的,因此孔子思想的实质是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上层统治者的利益。张之洞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与清朝的荣辱盛衰息息相关,所以他东奔西走忙于洋务,在曲线救国的同时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陶行知作为爱国知识分子始终在劳苦大众的战线上,所以才有了普及教育的“小先生制”和“育才学校”的出现。
三、心态史学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
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上人们心理状态的一种史学方法[9]。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推动了跨学科历史研究的发展。教育史学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与历史学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应需要从历史学中汲取营养,完善自身的发展。未来教育史学发展的基本走向之一是多元化,而心态史学法给多元化这一走向的实现提供契机。心态史学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新方法为教育史研究在目的、对象和方法等方面提供一种新视角,而对于研究结果的科学性要以辩证的态度去对待,而不能绝对化地去肯定或否定。
(一)研究目的的原生态:还原真实的教育境况
历史有“实在的历史”和“描述的历史”之分,因此“历史”是“往事”本身,也指对往事的记录。胡适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10]1,克罗齐也曾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0]1。所以历史就像沉埋在地下的陶罐,挖出来时已破碎不堪,保存在“史籍”中也只是一堆碎片。因此复原历史“陶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代历史学之父兰克就提出“写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10]1的主张。从心态史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它的起点和归宿是人类的历史过程,它作为一种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认识方式,研究的视角是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关注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探析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人们的精神变化以及重视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0]1,所以心态史学为教育史研究的真实性提供可能。深入教育历史主体的精神层面,通过分析教育主体或集体的欲望、动机和利益来阐释当时教育活动开展的初衷、教育制度颁布的动机以及教育思想提出的目的等一系列问题,为还原真实的教育境况提供一种新视角和新理论,从而可以更好、更准确地把握教育规律,使教育史学研究完成历史使命甚至创造新的价值。
(二)研究对象的人本化:历史人物是教育主角
社会历史的一切过程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共同结果。社会是人的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人。每一社会现象都会留下人的活动轨迹,打下人意志的烙印。“历史现象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人的领域。在人类世界之外,我们不能在这个词的特殊意义上说历史”[11]。黑格尔也提出过“历史是人的作品”这一哲学命题,后来被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地吸收,黑格尔指出:“人们活动的出发点是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性格和才能。”[10]10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这种活动中只有人们的这些需要、热情和利益,才是历史的动力,而且是作为头等有效的东西,出现在历史中的。“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件都不会成功”[10]11,因此,历史是人的作品。自年鉴学派笃力耕耘以来,心态史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代心态史学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深化和扩大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史学注重“无人历史”的倾向,使人的精神活动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因此心态史学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可以实现教育历史人物的“人本化”理念,将教育历史人物或教育流派作为研究课题,深入人物或集团的精神世界,挖掘影响历史人物教育思想提出的隐性因素。
(三)研究方法的心理化:剖析教育主角的内心
历史作为过去,与我们的时代之间横着一个时空上的鸿沟,征服这个鸿沟不仅需要沟通,而且要建立起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在心理、思想和价值等方面的联系。历史研究不仅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与未来的对话,而且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而这种交流只有通过体验和理解来完成。今人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古人,进入古人心灵之中,甚至“重演他们的思想”,是因为古今人性相同,这样才可以体验和交流。“自有史时代以来,人的变化极为有限,人性的共通性,大致为中外学者所承认”[12]。对此,钱钟书认为:“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7]86心态史学作为历史学知识体系与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它的一极是历史学,另一极是心理学,它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历史上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因此,心态史学被应用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心理学来探究教育历史主体的心理层面,为教育史学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费弗尔就指出:在运用心理方法研究历史时,心理学家所起的作用比史学家更为重要,“一种真正的历史学,只有通过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明白协商,才有可能获得一致。心理学家为历史学家指点方向”[13]。
[1] 景怀斌.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4):46-61.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48.
[3]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
[4] 西林.残照记:1840-2000年中国人最后的非常话语[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5.
[5] 顾明远,边守正.陶行知选集:第2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106.
[6] 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15.
[7] 王学典.史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 陆剑杰.历史创造活动中的选择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1991(1):81-98.
[9] 彭卫.心态史学研究方法评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2):25-31.
[10] 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11] 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5.
[12]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9:206.
[13] 吕一民.法国心态史学述评[J].史学理论研究,1992(3):138-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