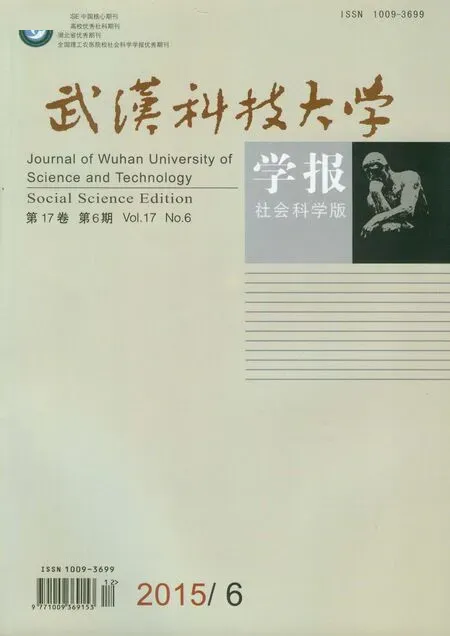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反思
2014-03-18赵志坚
赵 志 坚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对于任何政治共同体来说,稳定与秩序都是其存在的必要前提。而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权如果不想将共同体的稳定与秩序仅仅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确立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及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合法性信仰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传统上来看,这一任务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承担起来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为政治制度或政权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论证、为共同体成员的合法性信仰提供价值上的支撑,从而为共同体的稳定与秩序乃至其存在提供某种保障。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证成的重要性,同时也由于全球化和价值观多元化的日益发展,近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诸神之争”逐渐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并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之争中达至巅峰,而且其影响也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泯。在这种背景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要发挥或继续发挥其政治合法性证成的作用,就必须正视和回应其他诸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挑战尽管激烈且尖锐,但始终还是在“诸神”内部即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之间所发生的“战争”,它们试图批判乃至否定某种或某些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但是却没有对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本身提出挑战。与之相反,另外一股思潮所要挑战的(或其宣称要挑战的)并非任何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本身,是意识形态本身存在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它试图将一切类型的意识形态连根拔起,试图证明意识形态应当或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因此至少从理论上看,相比“诸神之争”而言,它对任何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所提出的挑战都要更加激烈、更加尖锐,这股思潮就是“意识形态终结论”。
一、意识形态终结论
尽管早在19世纪后期,恩格斯就已经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问题[1],而且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随着“世界的祛魅”“对绝对目标的狂热信奉必然破产”的观点也常常被视作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先声[2],但是通常所说的作为一股思潮存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则是在二战之后,尤其是在冷战期间才正式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主要出现于上世纪冷战前期50至60年代和冷战结束前后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它主张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的以“左”、“右”之争为突出代表的意识形态已经或应当被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非意识形态性的“政治”、公共管理、“文明的冲突”等等。其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一些右翼知识分子,代表性论著有冷战前期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54)和《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1960)、马丁·李普塞特(Martin Lipset)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60),以及冷战末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等等。广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除了前述的狭义终结论之外,还包括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等,而其中最具特色的则是意识形态“解构论”。解构论出现于20世纪中后期,其核心主张在于意识形态本身作为一种奠基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等之上的“宏大叙事”,应当而且必然随着这种叙事模式一起被解构。其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代表性论著有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69)、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哲学与自然之镜》(1979)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等等。
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实际上都是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层面展开[3]128。
从事实判断的层面来看,对意识形态本身进行实证性研究的传统实际上自韦伯和曼海姆就已经开始了,尤其是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学的辉煌时代”[4]17的到来,对意识形态的实证性研究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事实层面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常常以“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4]18为前提,主张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政治学甚至是自然科学方法出发对当代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经验性的、实证性的研究,并且从中得出了无论意识形态是否应当它在事实上都已经终结的结论。例如丹尼尔·贝尔就认为,在二战之后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已经失去意义,“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走向了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福利国家”、“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5]。福山也从全世界的选举式民主国家在1974年时只有不到30%与2013年时超过60%等经验性事实[6]3中,得出了自由民主将构成“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这一结论[6]9。
从价值判断的层面来看,对意识形态本身进行规范性研究则自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从价值判断的层面对意识形态展开了深入的批判,并且对二十世纪以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规范性的研究范式也为价值层面的终结论者所继承。从方法论上来看,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显然不可能是完全经验性的或实证性的;而从结论上来看,与事实层面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主张无论意识形态是否应当它在事实上都已经被终结不同,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主张无论意识形态是否在事实上已经它都应当被终结。例如解构论者就认为,意识形态乃是一套人为建构出来的宏大叙事,即使意识形态迄今在事实上尚未被终结,也应当通过一系列的解构策略使其终结。
当然,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实际上很难严格区分开来,而且对于不少终结论者来说,意识形态的终结既是对一种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描述,同时也是对应当发生的事情所提出的价值主张或规范性要求。例如,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不仅在事实上正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而且由于它本身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是“‘现实中’最正义的政体”[6]345,因此也应当成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因此,当福山喊出“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6]1这一口号时,他其实既将之视为一种事实判断,也将之视为一种价值判断。与福山一样,不少终结论者是非常明确而自觉地同时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双重层面来看待意识形态终结论的。
二、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正如前文所述,政治合法性对于任何一种不仅仅依赖于暴力的政治制度或政权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就在于为政治合法性提供道义证成与价值支撑。这一点不仅为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所承认,同时也是他们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一个逻辑前提。对于终结论者来说,正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证成功能、策略等存在着严重乃至根本性的问题,它才应当或者已经被终结。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成因、主张和实质等,有必要从政治合法性视角出发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
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也译作“政治正当性”,它是一个有着客观和主观双重面向的概念[7]8。从传统来看,政治合法性首先是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权合乎某种“权威资源”,如“客观规范”[7]11-12、“道德或理性原则”[8]等等,这些权威资源是客观的,即处于主张者之外或之上的。但是近代以来,随着世俗化浪潮的冲击和个体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政治合法性的客观面向逐渐退隐,其主观面向则日益突出并最终取得支配地位。从主观面向来看,政治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权合乎政治共同体成员的主观意志或意愿[7]11-12,从而能够赢得共同体成员的认同。
一般来说,政治合法性的资源除了意识形态之外,还包括治理绩效、程序合法性等等,而且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权在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证成过程中也往往会同时诉诸多种合法性资源。而在诸种合法性资源中,意识形态由于其独特的“证成”作用而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证成作用,同时体现在对于某种政治制度或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的客观证成和主观证成两个方面。从客观证成方面来看,意识形态总是会以自身主张的某种或某些价值为出发点,将这些价值确立为基本甚至是终极价值,并且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整套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完备性或整全性”[9]的解释与设想,当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权符合这些基本价值、解释与设想时,它就由此获得了政治合法性。而从主观证成方面来看,一方面,意识形态试图通过合理性的或经验性的论证将自身所主张的特殊价值与政治构想包装成普世的甚至是唯一正当的,以此来赢得政治共同体成员对于体现了这种价值与构想的政治制度或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的理性认同,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运用“神圣化”、“公意化”、“远景化”等一系列策略来赋予某种政治制度或政权以崇高性乃至神圣性[10],从而为其赢得共同体成员的情感认同。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来看,意识形态终结论之所以从事实或价值层面得出意识形态已经或应当被终结的结论,也正是从上述两个层面分别或同时展开的。无论是从客观证成还是主观证成的角度来看,狭义和广义的终结论者大多认为这种证成不仅在价值上无法立足,而且在事实上也终将或已经破产,并且给出了各自的理由。但是,既然政治合法性是一切政治制度或政权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那么意识形态终结论如果不想仅仅停留在对既有意识形态的破坏或解构上,又不认同无政府主义,而想要进一步建构起新的、所谓的“非意识形态性”的政治制度或政权的话,就必须解决意识形态终结之后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或策略问题。
从客观证成的角度来看,狭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认为,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客观证成无法成立,首先,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的祛魅”,被意识形态奉为终极价值的那些客观的基本价值乃至超验价值已经越来越难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在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建构起一种对政治制度和秩序的系统、完备、整全且貌似合理的解释和构想,从而使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价值和范畴等去解释现实和构想未来,是因为它采取了“一元化”[10]等策略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删节”、“简化和抽象”[4]15,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对于那些无法被其解释的事实之存在,意识形态只能予以压抑、排斥乃至否认。不少狭义终结论者也认为,极权主义以及冷战时期尖锐对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都不容置疑地宣称自身主张的价值才是基本甚至终极价值,并且毫不宽容地反对和否定与之相异的价值及奠基于这些价值之上的意识形态,这本身就已经证明了它们乃是独断论的产物。其次,从经验上来看,不同意识形态所主张的基本价值也在互相借鉴和融合,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尤其是福利国家的兴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及“苏东解体”,使得冷战时期及之后的不少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看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所主张的基本价值逐渐融合、其对立与冲突逐渐消失的可能性。对于狭义终结论者来说,既然无论是从理性还是从经验上来看,意识形态在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客观证成时所诉诸的那些基本价值要么十分可疑、要么已经逐渐融合,那么它当然也就不再可能依据某种特定的基本价值来为政治制度或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提供解释与证明了。
从主观证成的角度来看,狭义终结论者同样认为意识形态应当或已经被终结。从价值层面来看,不少狭义终结论者将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和封闭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主观认同,是因为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统治者可以利用宣传机器、信息封锁、恐惧心理等一系列手段来欺骗、蛊惑和煽动被统治者。而从事实层面来看,狭义终结论者则认为,意识形态要在全球化时代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认同,已经越来越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不仅知识分子越来越难以认同各种僵化的意识形态,大众也越来越难以被意识形态所欺骗,甚至就连各个国家的执政党本身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解决意识形态终结之后的政治合法性来源问题,终结论者提出了各自的替代策略或方案。总的来看,这些替代策略或方案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
首先,不少狭义终结论者认为,在意识形态终结之后,人们可以用某些非意识形态性的普遍价值为政治制度或政权提供合法性证成。例如雷蒙·阿隆就认为,意识形态终结之后,人们可以去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命运”[3]128。丹尼尔·贝尔也认为,这种普遍价值具体表现为福利国家、多元政治体系等等。而在这样一个已经由非意识形态性的普遍价值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社会中,真正重要的不再是价值问题,而是各种“更加表面的事务性调整”[4]17。这样一个“后意识形态”的社会看上去似乎很美好,但问题在于,这种狭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背后其实蕴藏着某种特定类型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无论从其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应当被终结的理由中,还是从其所提出的替代性策略或方案中,我们都可以鲜明地看出,那种所谓的“普遍价值”其实无非是“服从于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4]19这种意识形态的更加精致的版本而已。而它之所以能够宣称意识形态应当终结并用这种所谓的“普遍价值”来代替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并没有将这种普遍价值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行分析”[4]19。
其次,与狭义终结论者相比,福山的立场就要明确坦率得多。福山旗帜鲜明地赞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并且将之与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对立起来,认为其他意识形态由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而必然且应当崩溃,相反,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在“奠基性原则和制度”方面已经基本完善、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发展”的意识形态[6]10,则必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因此当福山说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消失了,而是说自由民主成为能够为政治制度和政权提供政治合法性证成的最终与唯一的意识形态,成为“诸神之争”的最后赢家。
与上述两种替代方案都包含有较鲜明的价值判断的成分相比,亨廷顿所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之后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则具有更加鲜明的事实判断的色彩。亨廷顿通过对冷战期间和之后的国际格局的经验性分析指出,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除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之外还包括了“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竞争。但是在后冷战时代,“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文化的区别”[11]5,“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也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认同”[11]105。文化认同由此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而文明的冲突也成为不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冲突。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亨廷顿所说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冷战期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他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是指这两种意识形态之对立的终结。而他所说的“文化认同”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民族主义这种独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另一种意识形态。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狭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是不彻底的,它所谓的“终结”虽然貌似是指一切意识形态的终结,但被终结的不过是某些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而已。与之相比,解构论的立场则要激进得多。在解构论者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承担起政治合法性的客观证成任务,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试图赋予政治或历史以本质、连续性、内在意义或道德价值的宏大叙事。而从哲学层面来看,这种宏大叙事之所以可能则是因为它本身就奠基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等传统的思维方式或话语体系之上。这种思维方式首先假定了现象与本质、表象与实在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存在,接下来又假定了在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着边缘与中心、派生与本源、被奠基与奠基的关系。换句话说,它假设了在外在的现象背后还隐藏着某种内在的、作为现象之基础与本源而存在的本质,相对于现象来说,本质更加“真实”、更具“深度”,而且正是这种本质赋予了现象以意义和价值。奠基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上的意识形态也正是首先假设了某些价值在存在论、认识论或价值论上的基础性、本源性乃至终极性的地位,然后以之作为标准来解释和衡量既有的、建构和设想可能的政治制度或政权。这些政治制度或政权作为某种“现象”,其政治合法性有赖于它们是否符合那些作为“本质”而存在的价值。由此可见,解构论者所要挖掘的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基本价值,甚至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所蕴含的宏大叙事本身,而是使得这种宏大叙事得以可能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或话语体系。更进一步来看,对于解构论者来说,甚至政治合法性的客观面向本身也同样奠基在这种思维方式或话语体系之上,因为它本身就假设了主观与客观、主张者本身与外在于主张者的权威资源之间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只不过是进一步为这种权威资源的存在及其具体内涵与意义等提供解释与说明罢了。而解构论者所要终结或解构的,首先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或话语体系。在解构论者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无法成立的,在现象背后并没有隐藏着某种更加真实或更具深度的基础、本质或中心来赋予现象以意义,相反,现象的意义就在于现象自身。对于“深度模式”的消解意味着世界乃是平面化的甚至是碎片化的,而一切试图建构或重建深度模式以赋予政治或历史以连续性、统一性与内在意义的宏大叙事,都只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借尸还魂。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逻各斯中心主义”等所代表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本身的合法性已经被消解了,那么以之为前提的作为宏大叙事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也必然随之被终结或解构。与之一起被解构的还有客观面向的政治合法性本身,如此一来,意识形态所承担的政治合法性的客观证成任务,就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也毫无必要了。
解构论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客观证成作用的解构与其对意识形态的主观证成作用的解构是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在解构论者看来,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奠基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等之上的宏大叙事,事实上只是一种虚假的人为建构。既然如此,解构论者就必须解释为什么这种虚假的人为建构还能够获得许多、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绝大多数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认可,从而发挥其政治合法性的主观证成作用这一问题。对此解构论者的解释是,意识形态本身虽然是一种与物理权力不同的“话语”,但它同样与权力处于一种“合谋”的关系之中,意识形态所表征的其实是一种权力关系。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力甚至是一种话语“霸权”。作为话语霸权的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主观证成作用不仅体现在它对“异己的力量”[4]16的压抑与排斥、“规训与惩罚”作用上面,也体现在其“规范化的整合”[12]作用上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之间常常激烈对抗与斗争,但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的意识形态却总是试图借助其话语权力对“异己的力量”进行规范,将其整合到自身的话语体系中去。如此一来,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的反抗者本身其实反而往往成为了意识形态这种权力话语的参与者、建构者与“合谋者”。尽管解构论者并不认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有可能被解构,并不认为话语有可能被“纯化”为完全非权力的话语,但是如前所述,他们认为意识形态这种特殊话语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应当被解构,因此对于解构论者来说,意识形态不仅不应当再发挥其政治合法性的客观证成作用,而且也不应当再发挥其主观证成作用。
因此,相对于狭义终结论来说,后现代主义解构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否定要更加激进、更加彻底,这种激进性与彻底性也决定了解构论在提供可以替代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证成资源或策略时,将面临着比狭义终结论更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经常遭到诟病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过分强调解构而对几乎一切建构都怀有深深的怀疑甚至是敌意,因此它往往陷入“破而不立”的困境。当后现代主义将其解构的锋芒指向意识形态时,这种困境就更加明显了:如果不能找到替代性的合法性资源或策略,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与秩序甚至其存在都将难以为继,但是任何对替代性资源或策略的求助都必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建构,而这种建构又意味着对于其“解构”策略的一定程度的放弃,并且因此很可能成为新的被解构的对象。面对这一困境,一些激进的解构论者干脆走向了彻底的相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但是还有一些解构论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共同体的存在及其秩序与稳定的必要性,为此他们在不放弃意识形态解构论的前提下,提出了以“普遍共识”或“重叠共识”作为政治制度或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策略,在他们看来,这种“共识”并不诉诸于任何外在于或高于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权威资源,而变成了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的一种“游戏”[13]。对于解构论者来说,普遍共识或重叠共识作为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意义就在于,它既能像意识形态一样保证政治共同体的必要的稳定与秩序,又避免了意识形态的“唯我独尊”的封闭性,从而能够对共同体成员彼此所秉持的不同信念保持开放[13]。
三、无法被终结的意识形态:启示与反思
意识形态终结论对于各种特殊类型的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无疑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我们既不可能也不应当因此否认意识形态终结论所包含的某种合理性,它之所以能够出现,并且形成一股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中间产生了相当影响力的思潮,其中重要的理论与现实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从历史上来看,冷战时期的“左”与“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本身就是极为僵化的。各大政治、经济、军事集团为了论证自身政治制度和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而极力宣扬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并刻意贬低甚至否认对手的意识形态本身的合理性。这不仅会导致意识形态本身的进一步僵化,而且会导致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在这种背景下,终结论者尤其是狭义终结论者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其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超越左右之争,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来打破这种僵化的对立局面,以便创造“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命运”。这本身就是对于现状的一种批判与反思。
与狭义终结论者相比,意识形态解构论不仅更加激进,而且也更具哲学深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批评者指责意识形态解构论不过是一群书斋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的“思想游戏”甚至是“文字游戏”。但是略微深入地考察就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解构论其实既是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观多元化、相对化、碎片化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在自觉地为这种多元化、相对化、碎片化摇旗呐喊。解构论者之所以坚持解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这种宏大叙事过分强调一元性、绝对性与等级性,以致窒息了人类价值信念与生活方式选择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他们之所以提出普遍共识或重叠共识作为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也是为了在保证必要的稳定与秩序的前提下,尽量保留人类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选择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终结论就是无懈可击的。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在意识形态终结的理由方面,还是在替代性的政治合法性策略方面,意识形态终结论都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就狭义终结论者而言,我们已经指出,他们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或是在迂回地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辩护,或是在对民族主义的当代复兴作出一种新的描述。但是自由主义是否真正能够战胜与之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等诸种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本身就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而就民族主义而言,我们姑且不论它是否依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单就民族主义是否真的在当代已经取得了相对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压倒性胜利这一问题而言,它也依然尚难定论。而就解构论而言,绝对化的意识形态诚然有种种问题,但是如果因此就走向相对主义而彻底否认各种价值本身的高下之分、将之都拉到同一个平面上,也同样难以令人信服。此外,所谓的普遍共识或重叠共识究竟能否以及如何达成,这本身就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至于它是否能真正充当政治合法性的资源,更是值得人们追问。
更重要的是,为了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与秩序,政治合法性的证成这一任务必须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解决。而就目前来看,在人们尚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的、真正能够替代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时,意识形态依然必须而且实际上也一直在承担着为政治制度或政权提供政治合法性证成的重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意识形态也依然无法终结。而意识形态终结论最重要的启示或许就在于,它通过其挑战而警醒着人们,在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及其认同方面,意识形态究竟有多么任重而道远。
[1] 吴玉荣.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百年历程及其对立[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2): 69-74.
[2] 苏富强.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J]. 求索,2007(2): 132-134.
[3] 梁建新. 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争论及研究现状述评[J]. 求索,2007(2): 128-131.
[4] 安德鲁·文森特.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M]. 袁久红,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5] 丹尼尔·贝尔. 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M]. 张国清,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87.
[6]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 陈高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7] 周濂. 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8] 安德鲁·海伍德. 政治学核心概念[M].吴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34.
[9] 任剑涛. 政治哲学讲演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2.
[10] 何显明.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诠释功能及其限制[J]. 现代哲学,2006(1): 24-31.
[11]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M]. 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12] 贺翠香. 知识、话语与意识形态——从《知识考古学》看福柯早期的意识形态理论[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8: 173-189.
[13] 张铭,侯焕春. 合法性证明与后现代政治哲学[J]. 学海,2000(3): 10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