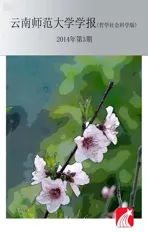资源诅咒还是利民开发
——大渡河上游一项采铅案例的灾难人类学研究*
2014-03-12代启福马衣努沙娜提别克
代启福, 马衣努·沙娜提别克
(1.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重庆 400044; 2. 柏林自由大学,德国 柏林 12249)
在奥米勒斯城一幢高楼里,有一个狭小无窗、阴暗潮湿、长年上锁的地下室。里面关着一个小孩。那孩子看上去六岁左右,其实是个十岁的“低能儿”。他(她)常年弓背,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封闭空间里,奥米勒斯城所有人都知道他(她)在那儿。很少有人知道他(她)成为“低能儿”的原因。但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全城人的安定幸福、邻里的友爱和孩子的健康,全靠那孩子所受的苦。倘若那孩子有了自由和温饱,奥米勒斯城的繁荣富强、安定团结和公民福乐就会化为乌有。这是城堡居民达成的共识,同时也是他们焦虑的根源:谁做善事解救孩子,谁就会把“罪恶”和“灾难”引进奥米勒斯城。*本故事的作者是威廉·詹姆斯,题名为《走出奥米勒斯城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张汉熙主编的《高级英语》(第二册修订本第九课)和Elizabeth A. Povinelli新著《废弃的经济学》,分别摘编了本故事。
我第一次读到威廉·詹姆斯这则故事是2011年7月,当时我在凉山G县*根据研究对象的要求和人类学的田野伦理,笔者对凉山矿产开发中涉及的人名、单位名和公司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C矿区做铅矿工人考察。我的访谈对象大多是在井下挖矿的彝族工人,并且大多来自G县以外的县市,其中一些是吸毒者,还有一些竟然是最讲尊严的黑彝。后来的采访又揭示出一种现象:凉山及周边县市来G县挖矿的工人里,过去已有大约300人患上了尘肺病后失业。尘肺病犹如癌症,无法医治,患者只能等死。我的访谈对象莫沙就是其中之一,他早被医生告知只能再活一年。我见到他时,他手里拿着药。交谈中,他向我倾诉的不是病痛,而是吃药带来的身体反应。我们只见了一次,但他讲的故事却在我脑海里定格并迫使我思考:为什么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文化禁忌长期在矿井下工作?矿业开发对他们的语言宗教、知识生产能力和技艺文化的传承意义何在?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矿难、疾病等“灾难”性社会问题,政府和经济学家为何没有叫停?相反他们还将“采矿”作为少数民族摆脱“贫困落后”的良方。本文以大渡河上游的采铅活动为例,揭示资源开发出现的“灾难”性社会问题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竞赛,而是政治经济学层面内一种权力对另外一种权力的支配。通过采铅案例的人类学分析,希望为灾难人类学的“减灾防灾”研究提供一点实证积累。
一、采矿:脱贫良方?
发展在各种话语中通常被理解为经济增长,却又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中被赋予了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含义。[1][p.169]发展所隐含的假定无非是“不发达”或“欠发达”的一种状态,[2][p.137]而解决或改变这种状态不仅是为了满足经济增长,而且也是为了消除从低级到高级这种线性的和歧视性含义。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在官方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常常被描述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和民族众多之地,但最后都会被定性为“贫困”或“落后”的特殊区域。这种认识不断向各界渗透,甚至在学者间也甚为流行。针对西部地区的“贫困”,一些学者将其归为“富饶的贫困”,[3]还有一些将其归为特殊的社会历史结构和思想观念,[4]但双方都强调西部的“贫困”与“落后”是“原生”的,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原生性“贫困”与“落后”归结于少数民族自身,甚至连他们的文化、历史和自然环境也包括在内。因为在外界看来,少数民族思想保守、迷信和懒散;他们居住的地方自古以来气候恶劣、土地贫瘠,不具备发展条件。[5]但通过开发当地优势“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能使他们摆脱“贫困”与“落后”的状态。[6]这是发展主义解决贫困的一贯手段,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灾难,他们也坚信,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解决。
G县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大渡河上游地区的一个资源城市,其矿产资源开发案例代表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在西部地区开展资源开发活动的缩影。在历史上,G县曾一度属于被西方学界称为“独立罗罗王国”管辖的区域,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却从未独立成国的地区。[7]现今的G县在经历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和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改革之后,于1956年成为凉山彝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级单位,辖管28个乡镇,人口约20万,共有彝、汉、藏、苗等14个民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但G县的民族构成,在大多数彝人看来,只由“诺苏”(彝)、“俄租”(尔苏藏人)和“黑嘎”(汉)三个民族构成。彝人常将藏族以外的人分类为汉人。在彝族社会内部,尤其是在民主改革之前,彝人社会被分为兹、诺、吉火、麻哟、嘎西五个等级,*凉山其他地区将彝族分为兹、诺、曲诺、阿加和嘎西五个层级。各级间不能逾越(纵向),但各层级却又彼此包容(横向),形成了一套“排他性包容”(exclusive inclusion)的社会秩序结构。
G县地处中国大西南,因矿产资源富集,成为国家最先开发的地方。但由于“先天”缺乏技术和交通闭塞等原因,G县的矿业经济秩序并没有迅速建立。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进,矿业经济才逐渐成为G县的支持产业,其矿业生产总值占全县总收入一半以上。铅矿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其他矿种也在不断被发现。目前已被探明的矿产共100多种。关于矿种、分布带和矿在G县经济发展中的话题是我在G县与当地官员访谈时听得最多的话,这也概括出地方政府如何看待彝族地区的发展。
矿业经济在G县发生重大变革始于2003年。在一起8死18人中毒事件后,G县政府开展了采矿史上的第一次矿业秩序整治。因为“死人”和“中毒”是最能诠释民间“无序”、“野蛮”、“掠夺性开采”,以及“缺乏科学开采观和市场机制”的最好答案。而那次死亡中毒事故是对政府领导的矿整运动的合理性解释,也是政府借助“灾难”际遇将资源国有化的一种策略。矿整期间,部分矿产开发权被政府以5.3亿元高价拍卖,这笔收入相当于G县上年财政收入的12倍。参与竞拍的企业有来自河南YG、湖南ZY、四川HD等知名企业。企业的进入,也是民间资本退出矿业开发的开始。
外来企业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引进促进了G县矿业的发展,随之也吸引大量外来矿工参与采矿。同时,矿业的发展也催生了餐饮、娱乐和色情等服务业在矿区和县城迅速发展。街道两边的彝、汉、英宣传文字的店铺招牌、明星广告牌、流行音乐、成人用品专卖店,无时无刻不在展示G县已和现代化接轨。
县城周边房地产的开发、现代交通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是矿业经济在当地繁荣的直接体现。虽然G县因蕴藏丰富的铅锌矿而被国人誉为“西部铅锌之都”,但颇具讽刺的是,G县至今还“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每年定期从国家财政获得扶贫经费。
二、求富:为谁辛苦为谁忙?
随着外来企业陆续入驻G县矿区,新的矿业经济秩序开始逐渐确立。虽然矿区成为城市的扩展和延伸,但资源并未真正服务于地方建设,而是出售到云南甚至更远的省份。矿业开发和初级产品的销售在促进当地GDP逐年攀升的同时,也间接带动了其他省份和中央的财政收入,但这一切“发展”和“进步”的背后常与矿山上突发的一系列伤病、死亡、社会歧视等“灾难性”社会问题相伴。下面分别以个案故事展现“采矿求富”背后所隐藏的“灾害性”社会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减灾防灾之方略。
(一)灾难的敏感性与地方性逻辑
2012年彝族年的前一天,我在街上又碰到36岁的莫沙,他看上去又消瘦了许多,走起路来也略显蹒跚。一见面有关“病痛”和“采矿”的内容成为我们彼此攀谈的话题。对于莫沙来说,“采矿”的工作虽已过多年,但“尘肺病”却日夜提醒着他井下生活和矿工的身份。莫沙在上山采矿之前,一直靠种庄稼维持生计,后来随着G县大力倡导发展矿业经济,莫沙同其他彝人一样放弃农业上矿山。但不幸的是患病使他完全失去劳动能力,也永远无法回到种庄稼维持生计的生活。自从他患病,家里失去经济支柱,生活变得日益拮据。类似莫沙这样因采矿患病的矿工在G县本地就有100多个。这当中,一些人已经死去,一些人正在等死,还有一些矿工很快踏上“尘肺病”患者的行列。这些故事当地人都心知肚明。
莫沙的个体遭遇仅是国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资源开发过程中一个缩影,但他的个体性遭遇却往往与宏大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层集体矛盾往往以个体形式呈现,但个体遭遇的苦难却又与集体紧密相连。来自G县的患者刘勤加告诉我,他不害怕死亡。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对“痛”的解脱,但对他的妻儿则意味着他们将永远失去亲人,失去生活和精神上的依靠。
G县矿工对“尘肺病”的理解也是不对称的。彝人对“尘肺病”的认知大致经历了早期的“尼茨则”(被鬼吃掉的人),后来的“肺结核”,再到“铅中毒”的发展过程。而官方的解释也曾一度游离在“肺结核”和“尘肺病”之间。后来尘肺病患病的原因最终才得到官方的确认,即矿工在工作中因吸入大量粉尘,导致肺部组织病变而患病。在这一系列患病案例和病的概念不断被生产出来的现实面前,依然没有动摇国家停止矿业发展的决心。相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T看来,矿业是地方脱贫的支柱性产业,尘肺病患者是矿整前企业不规范开采导致的结果,它与现行政府推行的矿业开发模式无关。
面对尘肺病对个体带来的痛苦,个体通常会求助彝族民间医师“毕摩”为其占卜、赎魂和举行一些“让果”(驱鬼)和“晓哦布”(吉祥与祝福)仪式。这是当地文化在面对现代开发模式对社区造成破坏或对个体造成伤害而生成的一套“文化图式”。但对患者家庭造成的影响,个体只能求助于实施资源开发的地方政府。因为后者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时刻以“发展”或“国家”的名义动员当地人参与采矿。
此外,伤亡也是矿工一年到头可能面临的灾难。虽然当地文化在应对伤亡时(如应对“尘肺病”一样)生成了一套宗教仪式和行业禁忌来规避或化解灾难,但阴暗潮湿的井洞有许多不可知性。另外,矿山对现代化开采工具的使用,使大面积、深度的井下作业成为可能,这也增加了洞中矿石吊棚、塌方引起的矿难事故。在企业老板看来,这些事故是自然发生的,它是一种经济损失,也是矿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矿山上发生的“事故”和“矛盾”,企业可以调用“中间人”协商和经济赔偿等手段给予解决,从而使新一轮的矿业开发成为可能。
阿曲是矿工伤亡事故赔偿的见证人,也是解决“灾难”的中间人之一。他曾在矿山上帮老板解决过彝汉矿工死亡事件。根据他的经验,他认为伤亡灾难事故的赔偿是可以协商的,赔偿的多寡与死者家支或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通常情况下,本地家庭势力大或与老板周旋久的人往往获得的经济赔偿多。外地的矿工赔偿相对较少,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在本地,家也离矿区远。事故发生后,他们的亲戚很难在短时间内聚集在一起,与矿山老板博弈,形成威胁。正是这样的原因,外地人才有更多机会进入G县矿区挖矿。
在矿山上,“死亡”事故被打造成一种暂时现象。因为在矿业老板看来事故是自然或工人操作不当导致的,这类事故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但对彝人来说,“死亡”是非终结性的,甚至连尸体的处理方式也与老板们理解的不一样,其过程要伴随诸多仪式。在彝人社会里,人们将被石头打死与自缢、投河、服毒、摔死等非正常死亡之人视作凶死,其灵魂不会或暂时不能重归祖地。其葬礼完全有别于正常死亡的人。*凶死的人,在哭丧和送魂等仪式上有别于正常去世的人。对相信“万物有灵”与“灵魂不灭”的彝人来说,这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
此外,参与G县采矿的工人还有一些吸毒,这也暗示了资本逐利空间狭小的情况下,企业通过招聘这些工人,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这是矿山老板缓解经济危机的手段。
矿工们每天面对的工作,与他们的传统技艺无关。他们的劳动与劳动产品分离,既不直接消费这些生产成果,也不从生产原材料中获得技能提升,而更多的是对他们身体的消耗。虽然矿工从工作中获得一点工资,但却为此患上疾病,甚至导致死亡。
(二)跨地域招工与歧视
G县将矿山的开采权通过招、拍、挂等市场手段转交给外来企业,引起了当地村民的不满。生活在G县的大部分彝族人都强调自己没有从国家和企业的资源开发中获得现金收入,也极少有机会在矿山工作。因为企业实行“跨地域”或“去民族化”的用工制度,大量招聘外地工人或外地彝人,使本地彝人丧失了上矿山工作的机会。企业老板们给出的理由是外地人离家远,能长期在矿山工作,也方便管理,而且受伤、死亡等矿山事故也比较容易处理。企业用工偏好,一定程度上催生了G县成为凉山地区少有的人口双向流动县城,即外来工人到G县打工,G县人被迫流动到外地工作。人口双向流动的趋势逐渐把G县现实中的行政边界和管理事务往外移动。来Y市的陈涛和G县约日代表了G县人口双向流动的动态。
陈涛记得当初与朋友一起来G县挖矿时,曾听村里的人讲过彝族的情况。村民说彝人爱喝酒,脾气不好,喜欢打架。于是,第一年他在矿区工作的时间里,一直和彝人保持着距离。后来,因内部工作调动才与彝人真正接触。在交往中,他发现彝人并非像家乡人讲的那样恐怖。相反,他们很好客,也很讲义气。
后来,随着他对当地社会环境的熟悉和彝人的了解,他也陆续带了一些家乡人到G县采矿。现今这些人都赚了钱,回了老家,修了房子,做起了小生意。陈涛说来G县挖矿的人主要是来自眉山、汉源、雅安地区的汉人和“阿都”*“阿都”地区主要包括布拖县、昭觉县南部和普格县东部地区。过去,这些地区属于阿都土司管辖。地区的彝人。
陈涛对“阿都”地区的彝人评价不高,他认为那些彝人“脑子有点笨”,尤其是面临工伤事故时,不知道如何与老板们“扯皮”(理论)。他见证过几次彝人受伤的案例,几千块钱就解决了问题。另外,他也认为“阿都”地区的彝人不像本地彝人那样团结。本地彝人出了事,整个村或整个家支的人都会找老板“扯皮”,能从老板那儿获得较高的经济赔偿。不过,陈涛承认正因为“阿都”地区的彝人“脑子笨”,他们才受矿老板的“喜爱”,否则他们的“下场”和本地彝人一样,极少有机会到矿山工作。
陈涛在G县矿山工作四年,现转行在G县做了客场司机。他转行的理由一方面是井中工作危险,另一方面随着矿业的开采,G县的矿也逐渐面临枯竭,挣钱变得有点困难。
同样是外出打工,来自G县X镇的约日遇到的情况却不同。约日在去成都当建筑工人之前,曾是C矿区的沙工,负责在井洞中“上矿石”(装车)。他每天工作8-9个小时,每月工资在4000元左右。他表示虽然采矿工作极其辛苦,但工资基本上能满足家里的日常开支。
但好景不长,因G县2003年矿整,大部分本地彝族工人被外来企业排除在招工范围之外,仅留下一些有社会关系的人在矿山上从事管理工作。约日就在那时被迫到外地打工。他回忆当初到成都找工作,吃了不少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民族身份。后来,他通过朋友在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获得的工资总比同单位的汉人低。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最后辞掉工作回家。
约日在家待了一年,期间也托关系联系了矿山管理人员,但对方以经济效益不好回绝了他的申请。约日认为汉人老板对彝人存在很多偏见。他们在是否招聘彝族工人方面存在一些矛盾心理。当企业招工困难时,彝人很受欢迎,但工人充裕时,彝人往往被排除在外。
G县的很多彝族矿工,因为不懂汉语,也没有经历过特殊的劳动技能培训,在进入城市后,因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经常遭到就业单位的歧视和排斥,难以获得“合法性”的收入。而今G县的彝族矿工外出打工,大部分只能依靠“工头”组织的形式到外地打工。这种打工形式虽然一定程度上减少或避免了彝人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就业歧视,但在另一个层面却又加重了打工者的经济负担。因为依靠这类组织到外打工的人,除了要出卖劳动力为老板工作外,还得向“工头们”支付一定的费用。此外,如同其他进城务工的群体一样,彝人虽然能在工厂或城市里找到工作,但城市长期以来坚持“包容性排他”(inclusive exclusion)策略,他们极少能在城市里享受到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户籍政策、医疗和教育等),即便是离彝区最近的CD市,对彝人而言,也极为陌生。
三、资源开发:诅咒还是利民?
矿产开发旨在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和恢复当地人的文化生产能力和主体能动性,但开发的结果却出现一系列与目标相反的“灾难性”社会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往往将其归结为“资源的诅咒”,并强调权力的经济网络、资本逐利性以及“资源观”的改造等是造成诅咒的主因。实际上,G县资源开发出现的环境污染、财富分配不均、矿工伤亡等问题,同样发生在G县以外的区域,甚至其他国家。学者们分别从市场机制、灾难人类学和自治角度对“灾难性”社会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资源的诅咒
资源“诅咒”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欧迪(Auty)提出的分析概念,其核心观点认为资源富足国,资源优势并非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相反会成为一种限制。[8]这一研究后来被巴尔特(Erwin H Bulte)等人延伸到制度层面,认为资源越丰富的国家,制度执行越会影响经济的增长。[9]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家凯帖·尕德尼尔(Katy Gardner)强调贫困国家一旦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开发,就会导致其他行业的经济停滞,而且还会面临价格暴跌而导致的金融灾难,掉进“自然资源开发的陷阱”。[10][p.18-20]
中国学界对资源“诅咒”的诠释主要围绕权力的经济网络、资本逐利性、利润分配机制以及“资源观”的改造等层面展开讨论。对“权力的经济网络”的探讨,一些学者分析认为以经济链条为纽带的“权力的经济网络”将社区内外的权力紧密联结在一起,逐步构结成一张“总体性”的权力网,垄断了当地乡村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和享用;[11]而另外的学者强调中央政府为了降低开采中产权交易成本的费用,把所有权分割成为不同的“产权束”,然后通过法律手段分给各级地方政府。[12]实际上,以“产权束”约束“权力的经济网络”的范围延伸是对“弱权力”的制约,使他们在资源开发中不能获得公平的利益分配。
而外国学者更多从资源的“物化”和人的“资源化”方面讨论。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在资源概念的阐释中指出,[13][p.229]随着工业化和殖民主义的到来,“资源”生命的含义被清除,逐渐变成一种无生命的、等待被工业开发的原材料;而资源开发的结果使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关系被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对资源的单向性开发、管理与控制。人与自然的分离,使人与资源的关系变成主客对立的关系,而人也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变成一种劳动力“资源”。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对资本主义和处在这个体系之外的人与魔鬼和商品互动的案例中指出,随着矿业生产和市场交换,人与山神之间的互惠关系逐渐被转化人与市场之间的交易关系,[14]而其中包括了市场对原住民“资源观”的塑造与改造。[15]
学界对“权力的经济网络”、资源观“去魅”和矿业空间再造的讨论和研究,其实都延续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导致了解决资源开发造成的灾难性社会问题更多地带有经济性。实际上,资源开发以及开发导致的灾难性社会问题,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学含义,也有文化学因素,其解决方案也具有多样性。
(二)对“诅咒”的应对机制
面对资源开发带来的“诅咒”,杨丽和朱瑞认为以市场为纽带的资源开发模式可以帮助资源地居民摆脱诅咒,进而获得经济发展。[16]但在大卫·亨德曼(David Hyndman)看来,以市场为主导的开发模式,正是带来“资源诅咒”的根源。[17]亨德曼在Wopkaimin社区对Ok Tedi 矿区的研究中发现,随着矿业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主导的开发模式,不仅彻底改变了Wopkaimin人的居住格局和经济类型,而且开发也带来了诸如酗酒、糖尿病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正是目前Wopkaimin人最大的威胁。[18][p.48-49]
灾难人类学也关注“资源诅咒”研究,只不过学者将“诅咒”理解成一种灾难,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灾难的自然性、技术性或人为性。目前中国学界已形成以应用[19]、象征实践*对灾难的象征意义、日常实践和环境感知方面的研究,彭文斌教授是主要代表学者之一。和历史记忆[20]为主体的三大研究范式,为人们理解灾难和生命,以及减灾防灾提供了诸多智慧。但需要指出的是,针对长期性的灾难或日常性的灾难并不能仅依靠亲属关系和社会组织力量加以解决,而应该从制度层面寻找解决方案。因为长期性的灾难“在另一些时期可能会被忽视或在灾害消解的过程中被放大,”[21]进而引发新的社会问题。灾难问题的反复出现主要与人们对天灾与人祸的关系,以及导致灾难原因的认识错位,使“防灾减灾”经验缺乏针对性。
但资源开发的结果并非总具有灾难性。在一定自治权力保障下的资源开发,也会出现利民的一面。美国人类学瑞查尔德·瑞德(Richard Reed)在瓜拉尼人研究案例中指出:[22][p.54-55]瓜拉尼人在跨国贸易中能控制自身经济规模,延续传统的生计方式,主要原因是自治权为他们经济上的独立和群体的文化认同提供了权益保障。同样生活在美国的雅克玛人,因为拥有经济上的自治权益,即使面临深度的资本主义市场化,他们在森林采伐、管理和利润分配等过程中仍然能保持动植物资源是造物主赐予人类礼物的宇宙观。[23]
上述资源开发案例的启示是:自治并非导致国家分裂或者少数群体独立,相反它能节制市场,防止市场把资源地居民的生态资源、人的身体和文化基业商品化,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这对G县资源开发中面临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结论
通过上述案例的分析与总结可以得出,G县虽然在历史上并未经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但自民主改革以来一直是国家开发自然资源的西部重县。但是以市场化为主导的自然资源开发模式并未引导当地人走上致富之路,相反却带来了诸如当地人权力失衡、生态家园破坏和文化传承危机等社会问题。此外,矿工除了要忍受艰苦的体力劳作外,还要抵御不被“科学预知的自然灾难”和“宗教预知的人为灾难”。
矿山上出现的一系列“灾难性”社会问题能让人们重新理解灾难和生命的脆弱性。一方面灾难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的敏感性,而很容易在经济发展中被遗忘或遮蔽,极难获得社会资源的救济或合法性赔偿;另一方面灾难容易被原子化和资本化(可被商量和计算)。原子化主要表现在企业对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伤亡事件采取个体化处理。他们将个体的伤亡从整体事件中抽离,逐一赔偿,实现灾难的再分配。这样做既避免了处理灾难时可能导致的集体性冲突,也节约了企业对伤亡事故的赔偿成本;而灾难的资本化通常伴随“中间人”的调解与协商,最后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化解灾难。经济补偿的方式是当下企业避灾的主要手段。虽然“避灾减灾”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企业对个体或家庭给予的一种合法性补偿,但在深层次层面灾难的资本化和原子化维持了企业对矿产资源的持续开发,也为地方政府进一步控制地区资源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另外,灾难是想象的,也是心理的。对于那些发生在矿区或井洞中不能用经济化约的矿难,企业老板也会调用民间人士(毕摩或道士)做一些清净和超度仪式,以消除矿工对灾难的想象和建构。企业老板对仪式的操演,其目的既是为了预防新一轮的灾难,也是为了动员矿工继续为公司服务。实际上,相对于伤亡个体化处理而言,矿山上的避灾仪式往往是集体的。整个仪式的搬演,需要矿工集体参与。
由此,本文认为造成“灾难”的原因既不单单限于“天灾”与“人祸”之间二元对立或统一,也不限于自然的、技术的和人为的因素,[24]而是在“天灾”和“人祸”两者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地带,它由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宗教、权力等各种动态的复合体构成。这个动态的复合体是造成当下灾难的关键因素,也是提取“防灾减灾”经验和知识的突破口。
而G县采矿导致的灾难,防灾减灾最佳路径不单单为其提供社会经济救助,*通常这些援助与关怀带有民族性、地域性和歧视性,甚至需要非结构性的感恩。应该“赋予”少数民族一套在经济上自我主导、文化上自我发展的自治权力,为其提供一套公平协商的制度设计。尤其是一套能节制市场,阻碍市场肆无忌惮地跨越国界和族界,将资源地居民的家园、生态、身体和文化商品化的制度设计。因为国家是由共同体组成的,每个共同体成员对国家的建设都有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赋予少数民族一定的自治权,并非像大多数人所焦虑的那样:“罪恶或灾难会引进奥米勒斯城”,进而破坏城市的繁荣与富强。恰好相反,自治权能解决共同体内部出现的社会矛盾,促使社会的整体繁荣与发展。反之,社会繁荣的背后必将伴随着灾难。
本文为笔者博士论文《人、资源与自治:凉山矿产和雅克玛森林开发案例研究》的部分章节摘编。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张海洋教授、彭文斌教授给予了诸多建议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苏发祥.中国民族学论坛[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2](美)迈克尔·贝尔.环境社会学的邀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4]张晓武,陈琦.西部民族地区人们思想观念落后成因探析[J].社科纵横,2007,(3).
[5]侯远高,张海洋等.关于大小凉山综合扶贫与禁毒防艾的意见和建议[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fb5b250100qjwa.html,2013年10月23日.
[6]丁任重.西部发展与资源开发模式的转型[N].四川日报,理论创新(06版),2010.
[7]Barbara L.Grub.Culture,Ecology and Livestock Development in Two Nuosu Yi Villages in Liangshan,China.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12;Alan Winnington.The Slaves of the Cool Mountains:Travels Among Head-Hunters and Slave-Owners in South-West China[D].Birlinn Ltd,2008.
[8]张景华:经济增长——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J].社会科学研究,2008,(6).
[9]Erwin H Bulte,Richard Damania,Robert T Deacon,.Resource Intensity,Institutions,and Development[J].World Development,2005,(33).
[10]Katy Gardner.Discordant Development: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Connection in Bangladesh[M].London:Pluto Press,2012.
[11]张丙乾:权力与资源——农村社区开采小铁矿的社会学分析[D].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2]强世功.科斯定理与陕北故事[J].读书,2001,(8).
[13]Wolfgang Sachs(ed).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Second Edition)[M].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2010.
[14]Michael T.Taussig.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0.
[15]William H Fisher.Rain Forest Exchanges:Industry and Community on an Amazonian Frontier[M].Smithsonian Institution,2000.
[16]杨丽,朱瑞.自然资源富饶的边缘民族山区市场构建的几点思考[J].思想战线,2000,(2).
[17]David Hyndman.Ancestral Rain Forests and the Mountain of Gold:Indigenous Peoples and Mining in New Guinea,Boulder,Colorado[M].West View Press,1994.
[18]Patricia K.Townsend.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From Pigs to Policies(Second Edition)[M].Long Grove,Illinois:Waveland Press,2009.
[19]李永祥.灾害管理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及人类学思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20]王晓葵.灾难文化的中日比较——以地震灾害记忆空间建构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
[21]傅杰利亚·加西亚-奥克萨塔(VirginiaGarcia-Acosta).郭少妮等译.灾难的历史研究[J].民族学刊,2011,(6).
[22]Richard Reed,Forest Dwellers,Forest Protectors: Indigenous Model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econd Edition)[M].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Pearson Prentice Hall,2009.
[23]代启福.人、资源与自治:凉山矿产和雅克玛森林开发案例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4]李永祥,彭文斌.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