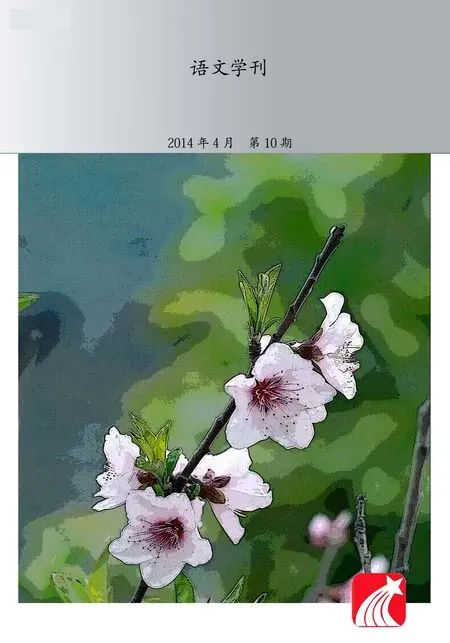从传统文化角度谈中西方修辞学
2014-03-12施艾拉
○ 施艾拉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005)
无论是中国传统,还是西方传统,修辞的概念均有多种不同含义。中国修辞学可谓历史悠久但是一直都是挂在其他许多学科术语之下因为还没有被承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典文献中使用的汉语主要修辞术语包括,名表示符号使用、命名、认识论、合理性,辞表示雄辩、话语类型、文体,言表示语言使用、谈话、演讲,说表示语音、说服、想法;辩表示争论、说服,辩论。虽然这些词汇间有语义上的重复,但是每个词汇均有其特定的功能,让说服性论述呈现不同的含义和语境。例如,说往往指面对面的交流,名是指在社会和认识论的环境中使用标识。
根据修辞理论的相对性,由亚里士多德创建的西方修辞标准,自创建以来,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而发展,因此,并不具有普适性。换句话说,修辞由特定的文化特质决定并受其影响。西方修辞学遗产主要归功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创建的学说。同样,中国修辞学遗产主要归功于在中国文化中的儒教和道教。儒教主要关注道德及讲演者言论和思想品德对道德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影响。道教主要关注“哲学和修辞研究的反理性和先验模式”。修辞学遗产主要归功也于佛教。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不同修辞传统所体现的不同修辞理念和实践有差异也有相似。由于中国文化极富特色,中国修辞与西方修辞差异极大。存在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于书面语,而不是口语。
一、中西方修辞学差异
(一)雄辩
人们认为,雄辩是西方修辞的核心内容。一些学者甚至在各自的著作中试图将“雄辩”与“修辞”等同起来。因此,在西方古代传统中,人们把“雄辩”视为独立的艺术,并且高度重视。乔治·坎贝尔写道:广义上来讲,暂且让我这样描述,除了雄辩或是演讲的艺术之外,没有哪种艺术与大脑器官的功能联系的如此紧密。首先,雄辩应该列入文雅或精美艺术范畴,因为大部分情况下,雄辩需要想象力的帮助。因此,雄辩不仅让人产生愉悦,而且引人注目,激发热情,并且往往最终让对方原先最坚强的决心屈服。(1992 p. xlix)
然而,至少在“雄辩”方面,中国修辞学传统与西方的传统截然相反。在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中,有数处强调修辞的言论。“首先,一般而言,辩论,甚至演讲,是会遭到反对的,往往与非常负面的含义联系在一起。人们觉得辩论都油嘴滑舌,说话迅速,产生噪音,哗众取宠;人们还觉得辩论肤浅,浅薄,耍小聪明,狂妄,自负,伪善,谄媚”(Jensen, 1987)。庄子还说“油腔滑调的人心态浅薄”,认为伪君子“知道怎么进行一场精彩的演讲,为了吸引听众注意力而讲解奇闻轶事,但是自始至终,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所言何物。”(Lin, 1955, p. 678)。庄子还用挖苦的语气写道:“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Lin, 1943, p. 173)。孔子也对“自命不凡的小聪明”持反对态度,“我憎恶聪明健谈的人,因为我担心他不明事理”(Ware, 1960)。
(二)沉默
人们对雄辩和畅所欲言都持反对态度,也就不奇怪老子和庄子的教义提倡谨慎讲话,适度表达,甚至完全沉默。这些神秘主义者强调认同和效仿自然的重要性(Jensen, 1987)。老子说道:“故飘风不终朝”(Lin, 1943)。因此,保持沉默得到提倡,“嘴是心灵的守护者,必须严加看管,以免自己的心思被外人知道”(Jensen, 1987, p. 3)。
虽然自儒家和道家在中国文化中创建至今已有几千年的时间,但是它们的影响还远未消除。中国人每当受邀对公众演讲时,他的脑海边都会萦绕着一句古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甚至政府官员也是如此。当他对一群人讲话时,他会让秘书先准备一份讲话稿;当会议开始时,他的工作就是照着稿子练;练完了,会议也就结束,人们开始离开。人们对这样的讲话有时会感到厌倦,但是一想到官员练稿子时的认真劲,他们的不适和抱怨就会立刻消失。“他们态度认真,值得信赖,因为他们的稿子是事先准备好的,练出来就代表是他的本意。“当西方演讲者或是大学讲师初见中国的这样一种传统,发现中国观众在演讲过程中或结束后大多保持缄默时,都会感到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在西方高校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当需要在课堂上当众讲话时,都会对西方那种滔滔不绝的演讲传统感到不大适应。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西方的这种做法令人沮丧,尤其是他们刚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时更是如此。中西方演讲修辞传统的差异非常明显。他们刚开始时在课堂上比较沉默,互动也比较少。但是,随着他们逐步适应周围的环境和文化,这种情况也逐步改变。
(三)记忆
中西方修辞学理论的第三个区别在于二者对待记忆的态度。在早期的西方修辞传统中,记忆曾得到重视。它位列修辞学创造、排列、风格、记忆和传达这五个组成部分中的第四个。西塞罗认为,演讲者必须具备这五项能力。他将记忆定义为大脑中保留的事件、词汇以及排列。根据西塞罗的理论,有两种类型的记忆:自然的和人工的。自然的记忆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和思想同时产生。而人工的记忆则是经过训练体系训练而形成的。(卡普兰,1989)西塞罗认为,自然的记忆必须经过训练加强,从而变得超常。而另一方面,这种训练而成的记忆又要求有自然之美。(卡普兰,1989)然而,在修辞学的五个组成部分中,记忆是西方修辞学书籍中被提及最少的。(科比特,1965,第27页)科比特认为,记忆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关于记忆的过程,并没有太多可以阐述的理论;而当修辞学主要与书面语联系在一起之后,便再没有必要来处理记忆了。(科比特,1965,第27页)西塞罗从小就认为记忆学是传统修辞学的一部分,但这门学科却被拉莫斯从修辞学中剔除,并且再也没有成为人文科学的一个特殊主题。(兰哈姆,1969,第89页)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修辞学向来把记忆看得很重。对于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们来说,被西方人忽视的修辞学的第四部分即记忆,要比其他部分更为重要。中国有一句古话证实了他们的修辞传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中国诗人杜甫(公元712~公元770)进一步证实了记忆的重要性:“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些批评家认为,杜甫诗中强调的是“破”,而非“万卷”。一位中国学者曾解释道:“一本书读百遍,要比囫囵吞枣读一百本书强。”(Matalene, 1985)。因此,中国人拿到任何文字,都是反复诵读、背诵,而不会改写、分析或是解释。由于学习汉语时老师的要求,学生们甚至在课堂上都背诵课文。边走边大声朗读是学生们学习外语的习惯,他们经常如此。
中国如此重视记忆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中国人已经养成了尊重传统和权威的习惯。因此,他们总是重复形式固定、家喻户晓的格言、说教和类比。中国修辞学的中心目标和实践就是通过参照传统和固定表达,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反应群体观点。时至今日,中国修辞学依然故我。
从哲学上讲,中国修辞对于记忆的强调是由于中国文化反对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儒家学说认为个人应服从集体,道家学说认为集体应服从自然,佛教则否认自我存在。中国“极左派”排斥并谴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因此,中国人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背诵在心理上适应他人,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符合社会规范和政治标准,而这种行为正好与西方修辞中宣扬的创意和个性背道而驰。
二、中西方修辞的类同
(一)记忆
尽管中国修辞传统过分强调记忆有很多弊病,但人们仍然在背诵,这是由于中国学生拥有良好的记忆力,他们在考试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而这需要大量的记忆。看到中国学生在他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取得的骄人成绩,一些西方人也许会后悔长期以来对于记忆的忽视。西塞罗曾热情地倡导这个被称为第四艺术的修辞。虽然中国人在其修辞传统中倡导惯例和权威而非高雅和论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方修辞没有共同之处。西方人的确重视独创性,但正如艾略特所言:“世上只有真正的创意与过去无关”。(1948,第118页)例如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我们无法找到绝对的原创。诗歌中的字、词、意象等也许是常见的,但诗歌整体的结构却与以往任何诗歌都不相同。虽然中国人非常崇尚修辞传统和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作家和批评家也这么想。事实上,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一些成功作家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截然不同,并对中国修辞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样主张独创反对陈腐。有两个有名的例子:杜甫曾写道“语不惊人死不休”;韩愈曾说“力去陈言”。杜甫、韩愈和其他诗人因在句法、诗节或韵律上的创新而广被赞扬,他们强调新颖而非模仿以往古诗。这与西方修辞特征明显相似。
(二)修辞手法
此外,中国人通常缺乏西方人的口才和辩论概念,因在他们的修辞史中没有演说传统。然而,修辞绝不仅局限于口头形式。比如,诗歌就是“某些演讲分支的特殊模式或形式。不管是叙事诗中渲染梦境,还是悲情诗中充满激情,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演讲的终点或目的,有时是即兴或既定目的”(坎贝尔,1992)。换言之,我们可以在中国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看到雄辩,看到论证,或是演说者具备的三才:教化、怡情和动人。
总而言之,汉语中关于含蓄、委婉和谦逊的修辞是非常丰富的,这与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如中央集权、禁锢思想、倡导集体性、鼓励抑制个人情感的审美标准等。中国修辞学的发展环境鼓励间接劝导,而非直接陈述观点,唯恐冒犯听者,但当合乎情理时也可以直接论述观点。然而,西方修辞学的发展环境鼓励直接的、对抗的、论争的交流;尽管如此,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采用类比论证和其他间接方法。在古希腊,直接论证不为人知,间接论证却人尽皆知。而在古代中国,情况却截然相反。总之,中西修辞特点的不同之处在于直接性,这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所致。
【参考文献】
[1]Campbell, G. 1992.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Scholar's Facsimiles & Reprints[M].Southern Illinois: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Caplan, H. (Trans.) 1989. Cicero: Rhetorica Ad Herenium[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Lanham, R. A. 1969. A Handlist of Rhetorical Terms[M].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Corbett, E. 1998. 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4th edition[M].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Lu, X. 1998. 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M].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6]Matalene, C. 1985. Contrastive rhetoric: An American writing teacher in China[J].College English,47(8):789-808.
[7]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8]郑奠.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G].商务印书馆,1980.
[9]陈光磊.修辞论稿[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10]郑颐寿.对比修辞[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2]刘焕辉.中国修辞学的历史源流与新世纪多元取向的思考[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
[13]戴婉莹.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几个问题[J].齐鲁学刊,1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