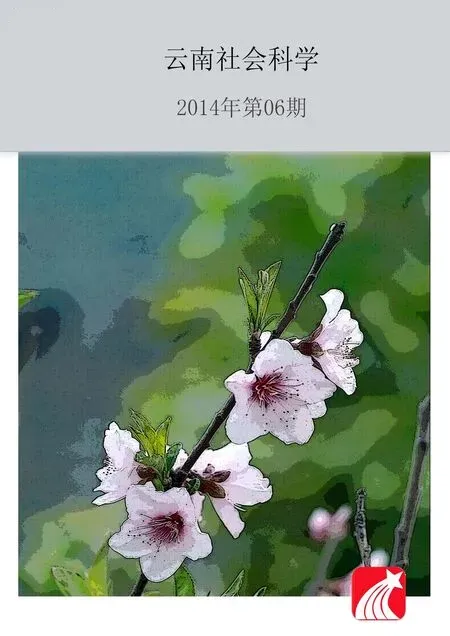论《庄子》与早期禅宗在演变理路上的契合性
2014-03-12周黄琴
周黄琴
在自述宗派的传承中,禅宗不仅以世尊的拈花一笑来论证其传承的合法性,而且还建构了历史久远的宗派传承谱系。然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禅宗在中国化的历程中,却不断卸去原始佛教的色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交织在一起,特别是与《庄子》的关系,一直成为历代儒者批驳之点,以致史上存有“庄禅”之说。如早在唐宋时期,傅奕与朱熹就曾认为禅宗乃是早期高僧剽窃老庄思想之产物。而本文试图对《庄子》与早期禅宗在演变理路上的契合性作一定的探究,以揭示其内在的关联性。
一、祛魅化
无论从马克斯·韦伯对宗教的分析来看,还是从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所指而言,其皆展示出了人类文明在发展道路上的祛魅化走向,即不断剥离神秘,走向理性。以此观念去观照《庄子》与禅宗思想时,其祛魅化色彩亦非常清晰。虽然相比于上古文化而言,整个先秦文化就具有强烈的祛魅化倾向,如庄子对中国传统中的一些神秘观念作了进一步的祛魅化。首先,对于传统的神秘之天与鬼神之说,庄子在承继老子思想的基础上,认为“道”不仅诞生万物,而且“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道”本论思想的观照下,传统之“天”与鬼神之说的神秘面纱被剥离掉,并被还原到自然性上,与万物等同。此举无疑还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祭祀与卜筮的价值与神秘性。
尽管《庄子》篇中充满了大量的神话,但此时的“神话则变成语言的材料,成为用以表达与原意极为不同的含义的寓言”[1](P9)。确切地说,《庄子》借用了神话的形式,来展示其内在深刻的哲理思想。因而,任继愈认为,《大宗师》中“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的思想,是对“古代宗教迷信思想的挑战”[2](P171)。侯外庐亦指出,庄子“更托于古帝,否定了西周以来原始的宗教神,批判了孔、墨的理论的宗教神”[2](P142)。而在张松辉先生看来,庄子“把道置于神鬼之先”,无疑“极大消弱了神鬼的地位”,对古代神学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3](P71)。
其次,在生死问题上,庄子立足于宇宙大自然的层面,重新审视生死,以破除传统上的生死观。据资料记载,仰韶文化的葬具上存有“孔”,齐家文化的死者周边撒有赤红色铁矿粉,这些现象无不折射出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认为人的灵魂具有永恒性,以致形成了一系列的占卜、祭祀等神秘活动。而且,在历史的潮流中,后人又不断给“死”后世界累加了一些阴暗与残酷的可怕色彩,致使世人形成了强烈的“悦生恶死”之观念。
但在庄子看来,“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4](P348)。即是说,人的生死就是一个气聚、气散的自然过程,期间没有任何神秘性。而且,人的肉身不过是一种外在形式而已,是宇宙大道假借外在质料的一个瞬间展现而已,即“生者,假借也”,而“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至乐》)。故一切短暂的假借,就如同“尘垢”一样不值得留恋,其最终必然都要回归于“道”中,就像一个游玩的孩子该回家一样自然。所以,当庄子从宇宙大化的角度去看待生死时,人的死亡就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一种抛弃“尘垢”而回到本真状态的快乐。
庄子消解了对死的恐惧。在《至乐》篇,庄子以空髑髅之梦的寓言来展现死后世界的美好性,即“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这不仅消解了人生中最大的困惑,即对死的恐惧,而且还使人重新认识自身与定位周边的一切。
而在祛魅化方面,禅宗亦有清晰的表现。首先,从高僧们的神通术方面来看,就有一个不断祛魅化的过程。慧皎的《高僧传》,素有反空疏、务求信实之特征,而被誉“永为龟镜”。然其中却记载着大量的神通术,甚至卷九与卷十都是以神异性为主题而编写的。然令人惊异的是,此后为禅宗宗派的法统性所建构的《祖堂集》,却把以往僧传中的神异性逐渐剥离掉,取而代之的是意蕴深远的偈。如文中在描写弘忍大师夜送慧能过江时,并非像《高僧传》所载的耆域者式的神通过江,而是“自把橹”。本来,《祖堂集》就是为禅宗的合法性寻找依据,故出于护宗之考虑,其理应更会通过有意塑造各祖师的神异术,来强化或抬高禅宗。然而,《祖堂集》并没有用神通性来强化禅宗的价值,反而流露出了强烈的祛魅化倾向。
其次,从历代禅宗所奉行的经典来看,亦有一定程度上的祛魅化倾向。众所周知,禅宗所奉行的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发生着演化,如《楞伽经》《大乘起信论》《金刚经》《坛经》等。据《续高僧传》的记载,达摩曾以四卷本的《楞伽经》授予慧可,并云:“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5](P552)然而,从宏观上看,《楞伽经》却有着众多的关于佛力的神奇性描述[6](P2)。然而,《楞伽经》中的神话性的描述方式,并没有在日后禅宗所信奉的《起信论》《金刚经》《坛经》中得以再现。虽然,《起信论》是“《楞伽》思想更加明朗和具体化的发展”[7](P231)。然而,《起信论》不仅剥离掉了《楞伽经》里的大量神奇性的语言,而代之以理性的义理阐述,甚至在“劝修利益分”中,亦没有《楞伽经》原有所彰显的修法开悟的奇异状态,而仅为理性地加以劝示。对于《坛经》来说,其不仅破除了修行的神通性,而且还撕开了成佛的神秘帷幕,把佛凡的距离拉到了咫尺之间,即“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8](P155)。
最后,从因果报应的思想演变来看,禅宗亦存有祛魅化色彩。印度佛教素有“业报说”,认为人的生活状态与业力有关,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此理论在中国早期佛教的传播阶段中亦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如在《弘明集》中就有大量的学人支持报应说与神不灭论。然而,不论因果报应说,还是灵魂不灭思想,却在日后禅宗的思想中被逐步剥离出去。实际上,从达摩对梁武帝企图通过造寺、写经、度僧等来建立功德之举的否定来看,就蕴含了对神秘报应的祛魅,而把修行拉向了人内在的心灵世界。而到慧能时代,这种面向更为突出。据《坛经》的记载,“慧能不仅反对把‘造寺度僧’、‘布施设斋’之行等同于‘功德’,而且还认为佛教‘六道轮回’中的‘地狱’与‘畜生’亦没有什么神秘与可怕之处,其实它们就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即‘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因而,原始佛教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在《坛经》中已经完全褪去了其原有的意蕴与色彩,而直接化为人的不同心境。”[9](P153)
尽管《庄子》与禅宗都存在着祛魅化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一定存有必然的联系,或许这是人类理性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有意味的是,它们在祛魅化之后,都没有像西方思想那样,朝着理性化方向发展,最终却走向了反知性思维,并寻求一种神秘的感悟。因而,《庄子》与禅宗在祛魅化的背后目的上存有一致性,即祛魅化并不是为了凸显理性,而是为了更大的“破”,来扫除前人所构建的障碍,以求新的发展。确切点说,《庄子》与禅宗都是通过“破”来求得出路。
二、反智主义
当现代西方哲学把研究方向转向对工具理性反思的角度上,其后却在西方史上产生了巨大效应。然而,事实上,相对于二千多年前中国传统中的反智思想来说,那是一种多么滞后的反思思潮。其实,对于工具理性的反思,中国传统中的老庄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从多个角度加以揭露,但由于言简意赅,没有构成一个体系,而显得非常的孤寂,并不被人理解,乃至出现后人的歪曲。然有意味的是,老庄对知性的怀疑精神并没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产生较大的反应,而巧合的是,却在近千年后的禅宗思想里重现光辉。
首先,对语言文字的诃毁。《老子》开篇就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实,此句之本意不仅展示了“道”的永恒性,而且也揭示了语言的有限性。实质上,此句话已经向人展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无限与有限的矛盾。然而,老子这种格言式的表述,难以使人从语言缺陷层面上加以理解,而是把侧重点放在对“道”的感悟上。
庄子不仅承继了此思想,而且还对语言文字之缺陷做了深入揭露,即“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与“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因而,若从视、听的角度来理解语言文字的话,则只能获得形、色、名、声,而非意。甚至在《天道》篇中,庄子还通过匠人嘲笑桓公读书之举来佐证以上之论点。事实上,《庄子》中不仅发展了老子的“行不言之教”思想,而且在展示该思想时亦尽量避免语言文字对意的束缚,故而文中采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打破语言文字之束缚。
然对于禅宗“不立文字”之教旨,教界虽一直追溯到佛陀的捏花一笑上,以求寻得法统传承上的支撑。可令人质疑的是,禅宗在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有意的构想呢?据资料记载,汤用彤先生早在《隋唐佛教史稿》中就曾质疑禅宗“秘密相传,不立文字”思想与昙林所记的“入道四行”,以及达摩以《楞伽经》授慧可之事存有相悖之处。[10](P187)而且,虽然《法冲传》亦认为从达摩一直到玉法师都是“口说玄理,不出文字”。然其后却曰:“可师后,善老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11](P24)同时,从资料的记载来看,早期佛教在译经过程中还存在着“会意”与执守文本的激烈冲突。只是“会意”者在当时佛教界处于弱势之方,从而遭到“守文者”之攻击,并被视为异端而得不到大范围的推广。这种现象恰好可以佐证,当时佛经中并没有明显的会意或悟的价值取向,否则的话,竺道生就不会遭到如此大的打击。或许早期佛教的会意路向与执守经教的矛盾,为日后禅宗在语言文字上的革新埋下了种子。
在龚隽先生看来,虽然不能“否认印度佛教传统中具有‘无概念性的’和‘不可言述的’般若智”,可“分别智”在“印度禅”中有比较充分的发展空间,如《俱舍论》《瑜伽师地论》《阿毗达摩俱舍释论》《阿毗达摩俱舍论本颂》都明确地提到“得分别慧”,但“在中国禅的发展中,分别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空间,而消解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主流话语之内,则也是应当承认的事实。而这一反智主义的传统,并非发源于学者们乐以道之的7世纪末到8世纪初中国禅的分化,特别是弘忍门下的倡导,而是有着更为悠远的历史。”然而,当龚隽先生作进一步分析的时候,他却认为“从道安的用语”和“意义分析”来看,道安“受到道家关于言意论辩的深刻影响”。而且“ 6至7世纪中国禅学的演化,又鲜明地表示出不拘文字经教而崇尚玄远虚寂的一流”[7](P66~67)。
而且,即使从禅宗的早期经典内容来看,《楞伽经》亦没有完全排斥语言文字,反而将其视为修行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是担心后人“堕于文字”,执著文字,故而倡导脱离文字,悟得佛法。然《坛经》尽管提到不同根器之人应有不同之方便法门,但其更为凸显上根之人的修行,即“心开悟解”、“不假文字”。甚至为了凸显这一思想,《坛经》《别传》以及日后禅宗的资料都极力强化慧能之不识字但却能悟得佛法之事件。
其次,《庄子》与禅宗皆有破除原有观念系统与经教之意向。据《庄子》的记载,庄子不仅时而对孔子进行批判,还对儒学所彰显的观念与人类原来所建构的一切观念作了质疑与批判。在庄子看来,人类的认知是有着自身类种所限定的界限,因而在人的认知区域之外还存在着广阔的人类所无法认知的境域,致使“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齐物论》)。确切点说,“六合之外”是人无法认知的领域,故只能“存而不论”,保持沉默。但“六合之内”虽为人的生活世界,但其中之论又皆是相对的,故而只能“论而不议”。
由此可见,庄子窥视到了人的观念世界与世界的本来状态所存在的矛盾,即世界瞬息万变,但又息息相通,圆融无碍,而人却在各自的观念世界里自限一隅,然又一厢情愿地把这一隅想象为世界的整体或唯一正确的认知,并以之作为万世的标准。而庄子想通过“破”的方式来消解人为所设定的各种观念障碍,以达世界的融通之境。
对于禅宗来说,破除经教的束缚,有着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实际上,在佛教初传时期,国人就对佛典的繁杂性表现出了厌烦与精简之意向,即“今佛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非一人力所能堪也,仆以为烦而不要矣。……佛经众多,欲得其要,而弃其余。直说其实,而除其华”[12](P18~20)。
从禅宗的演变史来看,不仅达摩放弃十卷本的《楞伽经》,而把四卷本的《楞伽经》传给慧可,而且据吕澂先生所考证,慧可甚至用“四卷本《楞伽经》”来对抗当时的“十卷本《楞伽经》”[13](P306)。同时,即使在传授《楞伽经》的过程中,慧可仍感受到了名相化走向的危险境地,即“此(楞伽)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以致他在传教中采取“行无轨迹”、“动无彰记”的传授方式来消解各种印痕与束缚。期间无疑蕴含了强烈的破除经教繁琐性之趋向。
到慧能时代,这种意向更为凸显,其不仅表现在《坛经》中有大量的理论论说,而且还有自身经历上的佐证。在他看来,“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8](P164)。同时,《坛经》还配有慧能自身“悟得佛道”的实例,来强化自悟成佛的思想。这个实例不仅彻底打破了世人的固有观念,而且还对经教的权威性产生了巨大冲击与破坏,即既然一个目不识丁之人,能胜过一个“博学多闻”的“教授师”,提前悟得佛法,传得衣钵,那么成佛不是靠读经,而是内心上的感悟。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上的革新,还不如说是佛教史上的一种破“繁”趋简意向的最后归宿。
然而,在实际的修行中,慧能还没有彻底抛弃一切经教与善知识。如他认为不能自悟者还需借助经教,“开导见性”,甚至到神会时仍强调“般若波罗蜜”的经教价值。直到洪州宗、石头宗时,则把破经教之意向全面落实到了实践的修行层面。[14](P6)南宗禅为了破除执着,应变无穷,不仅运用了大量的随机公案,而且还以棒喝、搊鼻、打人等方式,以期使人顿悟。
最后,破除繁杂的仪式规范与戒律。就《庄子》而言,从其所记载的鲁哀公与庄子争辩鲁国儒者多少的故事来看,一方面说明了后儒内在本质的丧失和外在形式的走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分离性。正是基于此因,庄子在文中不仅批判儒学背弃人性,卖弄名声,而且还揭露出了儒学规范化的走向所导致人性的迷失与失真,甚至儒学所建构的仁义道德规范反而演化为“大盗”之工具。更为可怕的是,统治者只知执守各种规范,以致本末混淆,更不知“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天运》),从而导致把世人演化为规范的奴隶与工具。致而,为了保存人的本真状态,庄子不仅对各种破坏本性之举进行了大肆批判,而且还反对各种人为设定的外在仪式,以致对儒家所倡导的丧礼都敢直接进行蔑视与批判。
可对佛教来说,戒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佛陀所云:“有戒则有慧,有慧则有戒;戒能净慧,慧能净戒。”[15](P265)因此,禅宗思想的演变无疑对戒律构成了巨大冲击。早在唐朝,作为律师的道宣就对达摩禅有所批评,即达摩禅“诵语难穷,历精盖少”,存有“遣荡之志”,而慧可是“情事无寄,谓是魔语”[16](P2060)。其实,早期南方禅师也并没有完全抛弃戒律。如达摩在修行方面,仍注重“二入四行”,并九年面壁修行禅定。慧可不仅在永和寺受戒,而且为求佛法“自断左臂”,后“兼奉头陀”。即使到道信时代,其仍常劝门人,“努力勤坐”,并传“菩萨戒法一本”。到弘忍时期,则法门大启,不择根机,“齐速念佛名,令净心”。乃至东山门下的北宗、净众宗、宣什宗皆把“念佛净心”作为最通用的禅法。
然发展到慧能及其弟子时代,则不仅反对枯坐,而且还对终日口念佛名之修行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坐”不是“枯坐”,也不是“著心”或“著净”,而是“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而“禅”为“内外自性不动”。故修行只需“心行”,“不在口念”。也就是说,不论“坐禅”还是“禅定”等各种修行,不是一种外在仪式规定下的简单遵循之行,而是只要能达到其内质上的“外离相”、“内不乱”的要求,其具体用什么外在方式都是无所谓的。实质上,这种思想无疑无形地消解了佛教原有的清规戒律。
上述观念被无住、道一、石头等门下,淋淋尽致地展现出来。大珠慧海禅师对律师法明曰:“经论是纸墨文字,纸墨文字者,俱是空寂,于声上建立名句等法,无非是空。座主执滞教体,岂不落空?”“法身无象”,“应物现形”,“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所以,当法明问“如何是佛”?大师却曰:“清谭对面,非佛而谁?”[17](P155~157)而青原系的德山宣鉴禅师本是“精究律藏”,后悟得佛法,将“疏钞堆法堂前举火焚之”。他认为“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并在日后开示弟子的教行中有着大量的棒喝与呵佛骂祖之行。如曰:“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18](P372~374)更为甚者,马祖的弟子丹霞,烧佛像来取暖。由此可见,南宗后系把慧能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并用大量看似荒诞的“机缘问答”与棍棒交加的极为粗俗之肢体语言来启示弟子。
可见,破一直贯穿于整个禅宗的发展过程之中。而这种“旋立旋破”的方式又恰好为禅师们打破一切人为设定的障碍,达到“无念”、“无住”、“无相”的解脱状态提供了出路。因而,《庄子》与禅宗的反智主义背后实质上又都蕴含了一种对灵魂出路的探寻。
三、世间解脱
众所周知,无论是佛教,还是庄子,都不仅对人的生存境遇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且还积极探寻出路,以求解脱。
一提到《庄子》,或许我们脑中浮现更多的是大鹏高飞的自由情状与那些无所不能的“神人”、“真人”和“至人”,以及神秘莫测的“道”。对于这些画面,人们也许更多的是从文学的主观面向去理解,甚至认为庄子以彻底抛弃人世间之方式,来建构神秘的逍遥世界。然实际上,《庄子》中的大鹏高飞不仅蕴含了一种“化”,即由鲲变为鹏,而且还预示着人要获得自由的话,就必然要破除旧视域,并通过自我的提升或高飞来重新获得全新的“道”之视域。即借助于超越之眼来彻底摧毁或消解原有的束缚,从而在现世中就可获得解脱。所以,《庄子》中并没有建构出一个脱离人世间的纯粹的彼岸世界,即使对于本源之“道”而言,其虽不为感性、理性所能把握与认识,具有超时空性,但它亦不是高悬的,而是“无乎逃物”,即蕴含在宇宙万物之中,甚至在极为肮脏的屎溺中都存在。确切点说,庄子恰是通过超时空的永恒本体之“道”的建构,不仅可以反思与批判人类社会的迷失走向,而且还为人类建造出了“生命之根”,并破除掉人为后天所建构的“成心”,即偏执之心,从而在现实世界中就能获得与“道”同在的逍遥之境。
对于佛教而言,为了摆脱人世间的众苦,佛陀力图通过“八正道”等一系列的修行方式,以达快乐的涅槃世界。对于涅槃,尽管学界存有不同的理解,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原始佛教的思想里,涅槃世界乃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后所构设的理想世界。然有意思的是,禅宗在历史的流变中,却把神圣的涅槃世界拉回到了人世间。如据《坛经》的记载,由于“本性是佛”,因而不仅“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而且佛与众生或凡夫之别亦在悟迷之间,即“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确切点说,在《坛经》里,佛的神秘面纱已被彻底卸去,致而成佛亦非在遥远的未来与高悬的彼岸世界,而是就在当下的迷悟之间,所以彼岸与此岸亦非遥不可及,而是在转瞬之间,即“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密”[8](P155)。换言之,人虽生活在人世间,但只要能“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就能达到涅槃的境界。所以,当韦刺史询问慧能念佛能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时,慧能则曰:“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8](P176)
在日后南宗各支派的思想中,世间解脱思想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实施与发展。如大珠慧海禅师认为和尚用功修行就在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日常行为之中。而希运禅师则云:“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14](P54)因而,中国的禅宗,“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向思想方面的延伸,不是思想的体系,而是渗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个体化的内在生命中”[7](P37)。
四、余 论
《庄子》思想与禅宗内在演变理路上所存有的契合性到底是学术上的“家族类似性”现象,还是存有一定程度上的承继性,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呢?尽管对于《庄子》与禅宗的关系,历代都有不同的论说。如早在唐代,傅奕就认为佛教“模写庄老玄言”。而僧界的吉藏、澄观、宗密等高僧则认为老庄思想在深度上不能与佛教相媲美,特别是老庄在本体论方面的论说,若以佛教思想来观照的话,其乃犯了“邪因”与“无因”之错误。确切点说,唐朝儒者与高僧都执于一方,以维护各自之目的。
然有意思的是,吉藏、释法琳、澄观、宗密等高僧的作品中还存在着援引《庄子》思想来阐释佛理之现象。即使到了宋朝,高僧们的作品中仍存有大量援引《庄子》思想之现象。而宋代的儒者们亦没有停止从模写庄老的面向来批佛。如朱熹不仅在《杂学辨》《四书或问》等众多文中存有批佛之举,而且还撰写了一篇《释氏》之文专门对佛教进行批判。在《释氏》篇,朱熹甚至把佛教窃取庄老思想之举作为批判佛教的重要支点,并认为禅宗皆“自庄老来”。林希逸在《庄子口义·发题》中认为“《大藏经》五百四十函”皆是从《庄子》中“抽绎”而出。
即使到近现代,学界与僧界仍有两派不同的声音,即一为禅宗是佛陀精神的回归,二禅宗乃为庄老思想的承继之物。如铃木大拙认为禅宗虽然“抛去了佛教一切历史的和教理的外衣”,但却“把握了使人产生创造力的佛陀根本精神”[19](P33)。印顺则认为,虽然慧能时期的禅宗仍“保持了印度如来禅的特性”,但发展到“牛头禅”时,则在吸取老庄思想的基础上使“印度禅蜕变为中国禅宗——中华禅”,更为甚者,日后遗则的“佛窟学”则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更与玄学相融合”。[11](P103~323)在萧萐父看来,如若说慧能通过心境的清净而从达摩禅中突破出来,那“后来的洪州禅、临济禅注入了庄子的‘逍遥游’精神,主要在于追求幻想中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理想人格”[14](前言P21)。崔大华则指出,构成禅宗“顿悟本心”的两大“基本的方法论因素”,即“整体直观”与“实践体验”,其“观念背景”与“观念渊源”皆“存在于庄子思想中”[20](P536~537)。
由上观之,学界的主流观念认为禅宗在演变的过程中由于承继了《庄子》某些思想,以致出现一定学理上的相似性。但不得不承认,禅宗的演变理路与《庄子》思想的契合性,并不是禅宗对《庄子》思想的简单模写,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为了破解各种生存困境,并为了更好地符合中国人之性情所做的一些演变。如为何禅宗会走向祛魅化与世间解脱的道路?其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还是中国文化理性化的产物与中国人的性情使然。从中国传统儒、道家的修行面向来看,其既侧重于人内在的心灵世界,而不是外在的神秘世界,而且对于修行的出路与结果,亦没有寄托在遥远的来世或神秘境地,而是把修行安放在世间日常当下的所有生活中,并期以获得快乐,致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一些文人对佛教中的神不灭论与神秘的因果报应持批判之论。所以,为了能在中国扎根下来,其必然要针对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做出一些演变,即卸去原始佛教所建构的神秘帷幕而转向人的心性与世间解脱,以求更好地迎合中国人之需求。
同时,从反智主义面向来看,尽管禅宗把“不立文字”之旨追溯到了佛陀的拈花一笑上,但实际上,在佛教初传中国时,既出现了文人大肆批判佛经繁琐性之现象,而且“执守”与“意会”取向的矛盾亦得到了凸显。更为甚者,禅宗在传播的过程中就被名相化所困。破除该问题乃是一大重要问题。然有意思的是,自魏晋以来,老庄的反智主义思想恰好为禅宗破解名相化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催化作用。[21](P196)
而且,从深层次上看,不论是祛魅化、反智主义,还是世间解脱之追寻,其实《庄子》与禅宗演变理路上的契合性折射出了一个重要哲理,即无论对一个学派或宗派而言,还是对个人与国家来说,若要得以发展的话,就必然要一直贯穿着破与立,即破解阻碍发展的一切束缚,并因时制宜地立些新内容。确切点说,只有破茧才能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