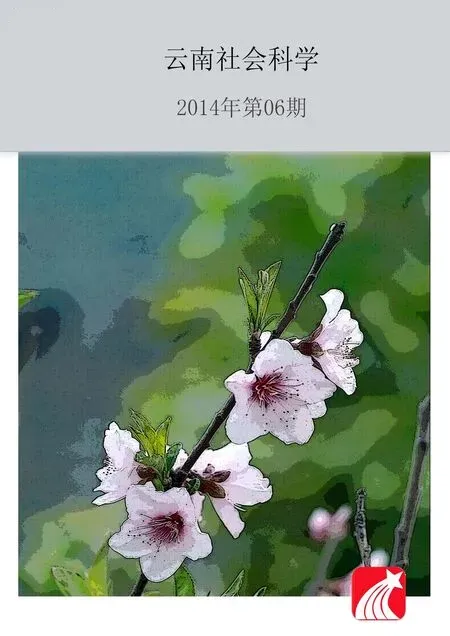论中国传统核心思维方式的分析理性之殇
2014-03-12张万强
张万强
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是探索真理的两种不同的理性思维。分析理性主要通过论证中的逻辑方法和实证精神来加以体现[1],辩证理性则主要通过辩证法来体现。与辩证理性相比,分析理性的一个杰出成就是形成了现代科学方法,如同爱因斯坦所指出的,现代科学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形式逻辑*这里讲的形式逻辑,包含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这个词由康德所造,意即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形式,不研究思维内容。参见桂起权:《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联手运用》,《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和系统实验。中国古代哲学所运用的核心思维方法,强调在说理和论证中,要更多地通过辩证和类比的方法来说辩明理,而甚少运用逻辑分析的哲学方法。传统核心思维方式的这一特点,要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做到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的综合运用。据此,有必要探讨分析理性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的流变,以解释传统核心思维方式的分析理性之殇的具体所在,从而增益传统思维方式所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一、分析理性的特点及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的流变
分析理性的特点,是相对于辩证理性而言的。与辩证理性相比,分析理性具有严格意义的“较真”品格,讲求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它具有客观性和可检验性,即如果遵守逻辑规律,从一组前提出发所推导出的结论,不依赖于论证者悟性和理解力之高低。尽管推理过程可能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却是可以被明确指出并进行更正的。即只要承认前提,就不得不接受其逻辑结论,结论是明明白白的 “似是而非”的。辩证理性则不同,强调从统一到对立再复归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看重“否定之否定”的运动环节,如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可以说,辩证理性着眼的是思维的整体性,看重变化,它力图容纳矛盾并最终实现对立双方的统一。运用辩证法所得到的哲学结论,往往是既不能从经验证实得到,也不能从逻辑推理(严格的)得到,哲学家之间有着很多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笔者以为,与分析理性相关的是逻辑精神的精确性,与辩证理性相关的则是思维的整体性。
但无论分析理性的形式逻辑,还是辩证理性的辩证法,于国人而言,都如电灯、电话、电脑一样,属于舶来品。当然,中国古代智慧形态中,不乏相反相成、执端取中、过犹不及等辩证理性的表述,但尚谈不上是思辨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可以说,辩证法和形式逻辑都是国人自国门开启以降所学得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以先秦名家、墨家的名辨之学比附源自古希腊的形式逻辑,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曾有分析理性的血脉;以辩证法分析传统的儒、释、道等学说思想,使中华传统文化本就熟悉的辩证理性更趋完善。思辨与分析的关系,在国人的科学视野中,不仅在论理的层面加以探讨,更有过以政治理性拒斥科学理性的遭遇。
具体说来,早在20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之危机的国人,不但提倡积极学习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也注意到了学习“逻先生”(逻辑)的重要性。对现代科学和逻辑学的重视,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分析精神之肇始。
然而,20世纪的国人,不单是接受了西方的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对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也逐步产生了很大的争论。这一争论最为集中的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邓拓等先生的“取代论”与潘梓年先生的“方法论与技术论”之间的论争。“取代论”者把形式逻辑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所视作的“形而上学”直接加以否定,而“方法论与技术论”者则为形式逻辑存在的合法性而努力,用心良苦地指出“辩证法是理论性思维方法,形式逻辑是技术方法”,形式逻辑需要认真研究,力图为逻辑所代表的分析理性争得点地盘。
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辩证法——尤其是庸俗的教条辩证法——成为国人从事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不单在人文和社科研究领域大行其事,更不忘对自然科学研究指导一番。这逐渐就形成了第二次的争论,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关系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逻辑的看法与周谷城的“主从说”等之间展开。恩格斯等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视作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而周谷城的“主从说”则强调形式逻辑只研究推论形式,不涉及推论内容,辩证法指导我们获得知识,形式逻辑指导我们进行推论,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二者不能相分离。周谷城等学者的观点当时也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认同。如沙青等人所指出的,这场争论“从理论思维讲,实质上就是辩证理性和分析性理性之争”[2](P1~2)。但这场论争的最终结果,还是辩证理性“战胜”了分析理性,政治理性拒斥了科学理性,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逻辑及其所代表的分析理性精神被定位是“资本主义”的,命运可想而知。论争的结果自然是辩证理性“居高临下”地排斥分析理性。而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等规律则可被用以论证一切事物,包括矛盾双方同时存在的合理性。不难想象这样的后果,曾经以辩证法论证为“真理”的学说,今天也以同样的辩证法论证为“谬误”。
追溯这场历经半个世纪的论争,似乎只能证明一个论点:“分析性理性和辩证理性在中国的不可调和的对立。”[2](P103)这种对立,在笔者看来,倒不是由于辩证理性和分析理性本身有多大程度是冲突的。在更大程度上说,这样的对立是由信念和认知的差异所导致。试想,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奉为信念乃至信仰的哲学家,有多少可能来反思自己,去认真研究逻辑并用分析理性来制约辩证理性呢?在笔者看来,这不是不可能,至多只是一个低概率事件。
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伴随而来的全球化,以及所具有的分析理性仍旧是辩证法所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认真思考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是否可以联手运用,是再次讨论哲学方法论所不能规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分析理性对辩证理性的助益
分析理性何以能够对辩证理性有所助益呢?二者之间是否能够实现统一与和谐?辩证逻辑的出现,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的确,已有论者认为分析理性是辩证理性的一部分。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把辩证理性定义为“在世界中并通过世界而自我构成的理性,将所有被构成的理性融入自身”,辩证理性超越被构成的理性并不断超越自身。分析理性是实证主义理性,是被构成的理性。因此,分析理性是辩证理性的一部分,辩证理性能够把握分析理性,分析理性不能把握辩证理性。“分析理性变成了运动中相对静止的物体的法则,是辩证理性一种特殊的实践契机”[3]。萨特把辩证理性置入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侧重从整体性出发来理解,笔者对辩证理性的理解与此是一致的。不过萨特对于分析理性是什么,分析理性与科学的关系,辩证理性外观上的形式矛盾和分析哲学怀有的“哲学科学化”理想等问题,都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
又如桂起权等认为辩证理性(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绝无反分析理性(形式逻辑)的特性,并进一步提出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的联手运用,是化解社会矛盾和科学悖论的强有力的思想工具[4]。他赞成“思辨逻辑-辩证法成分=知性逻辑,或辩证逻辑-辩证法成分=形式逻辑”一说[4]。这一观点着重区分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的不同,认为包含逻辑矛盾的命题都是直接或间接断定事物既具有又不具有某属性,而辩证矛盾命题断定事物同时具有两种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属性,辩证矛盾命题不是逻辑矛盾命题,具有的是“A∧~A”(永假式)的外观和“A∧B”的实质。似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同根同源的发生学史已经证明了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是互有助益的。笔者以为,按照这种看法,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包含关系,分析理性成为了辩证理性的支柱,或者换句话说,逻辑应成为社会理性的支柱。这一论点,恰与“哲学科学化”的实质相一致。不过,让人犯难的是,怎么从辩证理性中区分出分析理性?
笔者以为,尽管不知道哲学能为科学提供什么,辩证理性能为分析理性提供什么,却能从分析哲学的“哲学科学化”命题中体会到,哲学的发展能够也必须从科学的精确性和严格性那里汲取营养。科学需要分析理性,也可能需要辩证理性。但思辨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则需要分析理性,社会理性需要逻辑。如果说分析理性体现出理性“刚”的一面,辩证理性就体现出“柔”的一面。“分析理性需要辩证理性之柔,辩证理性需要分析理性之刚”[1]是确凿无疑的。辩证理性缺少分析理性的监督,极易迈出“真理变做谬误”的一步,成为了诡辩。显然,对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关系的认识,往往各执一词,未有定论。但对于国人研究哲学而言,辩证理性和分析理性是互助而非对立,应当是一个极正确的认识。
三、中国传统核心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和分析理性的缺失
中国传统核心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一种辩证思维。这一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矛盾性、整体性和实用性,具有浓郁的辩证理性气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矛盾性,并不是说中国传统哲学所使用的核心思维方式本身是矛盾的、不能说清楚的或者含混不清、莫衷一是的,而只是用来突出中国传统哲学特别强调矛盾的普遍存在和互相转化这一基本特点。传统辩证思维的三个特点中,矛盾性居于首要地位。笔者以为,与西方哲学传统中侧重使用形式逻辑分析方法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把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作为客观实在的普遍形态加以承认,并以矛盾的对立双方及其相互之间的运动统一作为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中国传统哲学认为,矛盾不但存在于宇宙世界之中,也存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行为之中,矛盾无时无刻不处于互相转化之中。
首以道家哲学为例,《道德经》第二章揭示矛盾的普遍性时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美与恶、善与不善、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等矛盾,是互相依赖而存在的,没有美也就没有了恶,没有不善也就没有了善。《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揭示矛盾的互相转化时说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以“塞翁失马”的故事为例,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承认,能够在说“失马是塞翁的一件祸事”的同时又说“失马又是塞翁的一件福事”,但恪守形式逻辑的看法,这样说显然是违反矛盾律的。此外,在道家看来,道的主要特征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经》第四十章),也就是说,道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但对道的运动状态的认识,可以借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说道的运动变化不是朝着单一方向的直线运动或循环运动,而是阴阳相反相成的螺旋式运动。
次以儒家哲学为例,儒家的辩证法主要体现在人生的价值观选择上,即以中庸作为君子的人生修养目标和圣人品格。《论语·为政第二》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说,“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庸是德行的极致,狂行和狷行构成了人的行为举动中的一对矛盾,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行则恰到好处地克服了这种矛盾。又如《论语·先进第十一》,“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过和不及也是人的行为举动中的一对矛盾,但都不是恰到好处的中庸之行。孔子强调,狂和狷、过和不及这样的举动都是不可取的,只有不偏不倚的中庸之行才是恰到好处的举动。孔子的这一思想后来在《中庸》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如“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等都一致表达了如上所述的思想。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发现,儒家的人生价值选择就是在矛盾中寻求某种统一。
再以佛家哲学为例,佛教彻底中国化和佛学彻底中国化而形成的唯一一部由中国人所著的佛经——《坛经》,其中也不乏表达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光芒存在。《坛经·行由品第一》中记载了神秀禅师和六祖慧能禅师就各自的佛性认识而呈给五祖弘忍大师的偈子,这两首家喻户晓的偈子就构成了两对矛盾,神秀大师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六祖慧能大师则认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个偈子之间的菩提是树与菩提非树、明镜是台和明镜非台就构成了两对矛盾,这两对矛盾所体现的是两位禅师对佛性认识程度的深浅不同,这类矛盾也终将统一在不二之性的佛性之中。又如顿悟与渐悟,顿悟法门是当下就悟,是快;渐悟法门则需要日积月累的思考与修炼,是慢,顿与渐或者快与慢就构成了一对矛盾,但顿悟与渐悟却都统一于成佛这个目标。还如《坛经·疑问品第三》中提到的众生与佛的区别,“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众生与佛的不同在与自性的迷与觉,众生明了了自性,也就成了佛,众生的自性迷与众生的自性觉构成一对矛盾,迷与觉、佛与众生都可统一到自性中来,统一到佛性中来。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核心思维方式注意到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此相应的是传统思维追求“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注重在变化中追求统一,如上文提及到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思维特征(《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传统文化中的矛盾性与整体性特点,标志着传统文化具有了辩证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传统文化独立发展了辩证法,辩证理性中所需要的分析理性,仍旧是传统文化并不具有的。同时,传统思维还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古人的学问研究更注重 “求人之是”而非“求物之是”。这一点如林语堂所指出,“当中国人看到一只豪猪时,便会想出种种的吃法来,只要在不中毒的原则之下吃掉它。在中国人看来,不中毒是唯一实际而重要的问题。豪猪的刺毛引不起我们的兴趣。这些刺毛怎样会竖立的?有什么功用?它们和皮怎样生连着?当它看见仇敌时,这些刺毛怎样会有竖立的能力?这些问题,在中国人看来是极其无聊的”[5](P46)。显然,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追求“求人之是”的有用性,关注社会的修齐治平等问题,而“求物之是”的学问往往则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极其无聊。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维方式具有矛盾性、整体性和实用性特点,实质上就主要是一种辩证逻辑和辩证思维,体现出的是辩证理性的精神气质。这种辩证理性表现出了矛盾性与整体性的合二为一,也结集出了中国哲学精神的独特所在,如不承认有独立于人类生存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不承认人类的生命和终极价值需要走外在超越的道路。古代哲学的独特魅力,也恰恰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所带来的圆融无碍。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大方地承认了矛盾的普遍性存在的基础,力求在矛盾双方之间互相转化的普遍运动中去认识和把握宇宙世界的统一性及规律性,去认识生命道德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去认识天道和人道的统一性和规律性。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维方式所体现出的这种辩证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传统哲学的深化发展。传统思维更倾向于实用而非“穷理”,对事物的态度和经验讲究的是实用性而非实证性,就连被认可的先秦时期最具逻辑精神的墨家,提出的判断一切言说的标准——“三表法”:“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 (《墨子·非命上》)其也推崇的是“实用”而非“真”。而逻辑精神的求“真”、较“真”品格,显然是不适宜于“实用”的。因为“实用”意味着灵活,即如果观念与事实不符时,推崇“实用”就意味着放弃事实,如墨家之所以非命,不是由于“有命”这个命题的真假,原因之一则是,如果承认“有命”,会对国家、百姓产生极大的危害。可以假设,如果承认“有命”,对国家百姓是有利的,那么墨家是否会赞同“有命”呢?推崇实用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就是用“权威论证”的方式证明我们的正确性,“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而已。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在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时,为什么 “子曰”等教条不好用呢?当然,不是说“子曰”“圣王之事”不能够作为论证的根据,而是说即使援引这些论证,也应遵循分析理性的严格与精确。
又如“李约瑟问题”所指出的,国人所引以为傲的五千年的文化传承,缘何未能产生出现代科学技术?如果说是中国人缺乏进行科学技术活动的才智能力,显然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荒谬结论,何况今日华夏子孙里不乏从事现代科学技术的人物。那么,原因就只能出在传统文化本身,尤其是分析理性的欠发达。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传统哲学从未发展过形式逻辑,没有分析理性。先秦时期的名辩学说,尤其是墨家学说,已经孕育着初等的形式逻辑规律和思想,如表达充要条件的“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墨辩·经说》上)。但这种分析的思维方式,只是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之阙补,未得到独立之发展而已。
分析理性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的流变和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都说明中国传统核心思维方式的分析理性之殇。恰如以“反省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为己任的牟宗三先生,在研读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提出“罗素之数学原理与康德之纯理批判,皆中国学术传统之所缺”[6](前言),并著述《理则学》以为台湾省的逻辑学教材。罗素的数学原理即数理逻辑,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质上都代表的是分析理性。分析理性的精神气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未得到充分发展,传统思维中的辩证理性缺失分析理性的“较真”监督,是中国古代哲学未能发展转型为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分析理性的发达,对于辩证理性有很大的助益作用。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转型,必定要极力汲取分析理性的精神品格。比如对于通常被认为是最无逻辑的禅宗话头,也可借助逻辑手段来加以分析阐述,从而使得话头变得易读易懂。如牟宗三先生的高足付成纶就曾对禅宗话头进行过逻辑分析[6](P243~253),这种分析得到了牟先生的认可。实际上正是分析理性对于辩证理性的一种助益,是传统文化汲取分析理性的一个有益尝试。反之,如果辩证理性试图排斥分析理性,或者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相互对立,则会使得哲学辩证法成了人人都不需思量就能说上两句的“小贩吆喝”,几近于诡辩。这一点,已经在20世纪中叶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争论中得到了充分说明。的确,哲学的思辨需要逻辑的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不单要注意传承辩证理性的精神品格,更需要借鉴学习分析理性的精神气质,才能实现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