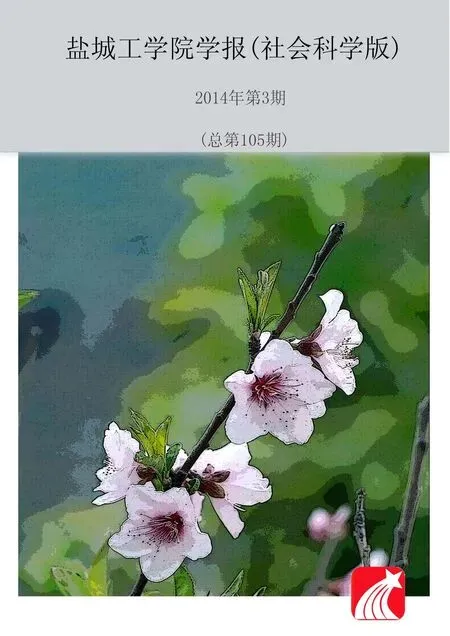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孕育和引领中国模式
2014-03-11蔡瑞艳
蔡瑞艳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科社部,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江苏 南京 2100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孕育和引领中国模式
蔡瑞艳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科社部,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江苏 南京 210000)
中国模式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面发展模式。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在一个核心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孕育和引领下,在相对稳定而持久的社会力量推动下,不断革新和创造,实现社会的进步和繁荣。中国模式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对立统一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模式;孕育;引领
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发展历史进程及其规律进行科学总结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是工人阶级为了自身解放并解放全人类、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行动指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在实践中创新并应用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发展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互动和扬弃。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模式两者互动的过程,不是始终都彼此协调一致、顺理成章的。因此,在探索与创新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如何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中国模式成功与否的核心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的历史起点
19世纪30、40年代,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的扩张阶段,西方列强用先进的枪炮打开了中国封建落后破败的国门,掀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战争强迫中国开放,在被逼迫中中国被拖进全球化的国际浪潮。中国政治的腐朽、经济的极端落后,是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血泪史和屈辱史的根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兴起并取得巨大成功,以及这种成功带给中国的灾难性冲击,同样逼迫着中国人思考他们的现实和未来——如何改变落后挨打和积贫积弱?这就需要找寻一条救中国于民族危亡、变穷困为国家富强的道路。“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1469在这个阶段,中国刚刚正式地睁眼看世界,在探索社会发展道路时是在黑暗中摸索的。总体上说,这些出民于水火的探索艰辛曲折,虽有所成就,但最后都没有真正找到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和复兴的真理和道路。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又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人们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2]5新的社会发展道路需要新的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和实践。但由于历史的因素,更由于道路或方法的选择问题,这时的中国精英阶层没能真切地了解国内外情况,没有能够把握住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所以才没能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没能创造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抛弃了向西方学习的兴趣,转而向俄国学习。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逐渐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的主流。加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1921 年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的传播。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特点加以具体运用,并进行理论性创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第一次飞跃,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最终赢得了名副其实的国家独立。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它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也从此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之一——中国的真正独立自主,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中国模式酝酿、形成的最基本前提。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必然迟滞中国模式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关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健康发展,是党的各项事业成功的保证。否则,就会对党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就会迟滞中国社会的发展。
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面目一新。但究竟应该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就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强调: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3]534。这意味着马克思在中国的具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认识阶段——毛泽东思想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的,首先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国家经济,改变贫穷落后,同时巩固中国革命成果,防止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由于中国共产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且新生的共和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冷战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中国参与国际共产主义援助,与资本主义扩张进行较量。这就使得,一方面中国要对外进行大量的人员和资源的无偿援助以巩固和扩展共产主义在交往国和地区的影响。这样,中国在自身经济和科技等综合国力非常贫弱的情况下承受与自身不相称的超额负担,不利于国家建设需要的物质积累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还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企图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政策。这造成了中国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出现了绝对化和教条主义倾向,在理论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科学论断,从而在现实中不能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及其创造的文明。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于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反馈,又加剧着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视。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相互遏制和敌对的恶性循环。这些国际上的问题应和着国内的阶级论及其具体的唯成分论,中国否定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上与资本主义世界割裂开来。如是造成的后果是,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老朽并即将垂死,从而妄自尊大地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以至于失去了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即便是纯粹的应用科学成果,也难以融入中国的教条主义法眼。处于冷战坚冰时期的中国,不仅失去了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科技文化交流的机遇,而且在国内出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恶劣局面。这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上,出现了教条主义的认知倾向,并把这种错误认识上升到国家内政和外交的具体层面,造成了国家建设在政治上混乱、经济文化上的停滞或倒退。
在社会发展模式上,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模仿苏联社会发展模式。在政治体制建设上,新中国建立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政治制度;在经济体制改造方面,迅速地对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居绝对优势,公有制经济成分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民经济体制;在文化上实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但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并不都适应中国的情况,造成了中国建设的巨大失误和挫折。这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带有深厚的崇拜苏联成分,也不乏照搬照抄。这表明中国还没有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上正轨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奠定基础
冷战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缓和的因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资本主义阵营内部都发生了分化或分裂的剧变。两大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接近尾声,美国在冷战中渐渐处于战略守势。中苏同盟分裂使得美国得以与中国关系逐渐正常化并最终建交。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打破全球化被冷战割裂的畸形态势,有利于中国赢得一个相对平衡的和平发展期。
20世纪7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和科技方面普遍实现了现代化,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东欧经济和科技也取得了良好的发展结果,而且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并列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但中国在冷战分化的大背景下,国内政治没有根据国际政治进行同步调整。当国际社会风风火火地进行着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全球化竞争时,中国正在忙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有效性,在中国建设时期显然不是很奏效。它在很多方面违背了现实状况和社会实践本身,使得整个国家总体上似乎停滞不前且有倒退,成为全球化的落后者。世易时移,世界在变化,中国也需要变革,中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能总是沿袭过往的经验和陈旧的策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已经解决了中国如何革命的问题,但革命胜利之后,它还远没有解决中国如何建设的重大问题。在选择和建构国家发展模式中,中国必须从混乱和倒退中清醒和自拔出来。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实施,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变化了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逐渐科学化,方向日益明确化,思路越来越清晰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逐步与西方世界建立起外交关系,这既加速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又为中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实现国家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是中国国家建设和国际活动的目标。这是针对具体的情况做出的伟大规划。那么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的经验是把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相互糅合和促进,而不是先创造出一种理论,再在理论指导下去具体实施。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指导下,中国进行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经济文化创新。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理想境界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基本国情,审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重新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照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来实行改革开放。这样,在纠正极左思潮和对历史认识的绝对化、僵化倾向基础上,真正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上来,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理论,丰富、补充和完善着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正是坚持着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资本主义的精辟论断,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科技文化成果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实行科教兴国战略;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改变了越穷越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判断。这是转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国家全面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正是在对这些大政方针的背景认识和科学决策基础上,邓小平睿智地认识到经济建设手段的选择应该与国家性质、社会意识形态分离,创造性地提出了商品、市场与计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在思想上为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建设铺垫了理论基础;同时,根据国情和世情,邓小平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国际社会可以长期共生的求同存异主张,改变了冷战坚冰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关系,如此等等。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发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为基准,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丰富、完善,最终创造出邓小平理论,它在拨乱反正中艰难地探索,承接了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部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它也成为中国模式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不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伟大实践。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深推进必将丰富和优化中国模式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速度加快,全球经济文化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拓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了,城乡、地区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却拉大了。这是中国模式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取得丰硕成果中出现的问题,也是第二代领导集体预见到但还没来得及处理的问题。虽然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领导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让沿海和东部地区先富起来,支援和带领中西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这个愿景如何实现,只是中国模式形成过程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中国模式的逐渐形成,成就巨大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发展总体上主要是依靠资源消耗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取得,为了获得短期效应而急功近利地粗放经营、杀鸡取卵、以牺牲环境资源等子孙后代长远生计为代价;改革开放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拜金主义倾向;社会利益分配中的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显现;党员干部中出现了腐败苗头;干群关系中出现的不融洽现象甚至敌对情绪,如此等等。这说明中国模式还存在需要进一步丰富、优化和完善的空间。
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在改革开放的成就中面对诸多的现实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时期党的建设上,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提出了标准和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更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如何始终保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按照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行动,维护和加强党的坚强团结和高度统一,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向前推进。”[4]1-2科学发展观则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面对十六大之后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政治形势中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文化领域中多元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社会领域中大量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以及能源和资源危机凸显,大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等,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对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理论问题。并就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的问题进行长远发展规划,力争建立富裕文明的和谐社会。它不是强调社会发展的量的扩充,而是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的质的提升。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前进中关于中国建设的重大理论突破,是完善中国模式的理论引导。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性,造成了中国在寻找适合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总体上一次比一次更进步,一次比一次更科学,更靠近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模式的形成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摆脱摇摆命运,走向恒常纵深的科学发展时期。它不但使中国成功地远离了因贫穷落后而被全球化抛弃的命运,而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贵的发展经验,为发达国家再发展提供了借鉴。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沈建新)
The Marx Doctrine China Inoculation and Lead Chinese Mode
CAI Ruiya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Postdoctoral Desearch Station,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China model is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model includ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ulture. Whil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 core of the guiding ideology—Marx's China of inoculation and lead, in the relatively stable and lasting social power driven,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China mode cannot do without the Marx doctrine China development, is the unity of opposites among, embodies the principles of Marx about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the Marx doctrine Chinese; Chinese mode; inoculation;guide
2014-04-09
2014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SJB266)
蔡瑞艳(1972-),女,安徽淮南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61
A
1671-5322(2014)03-0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