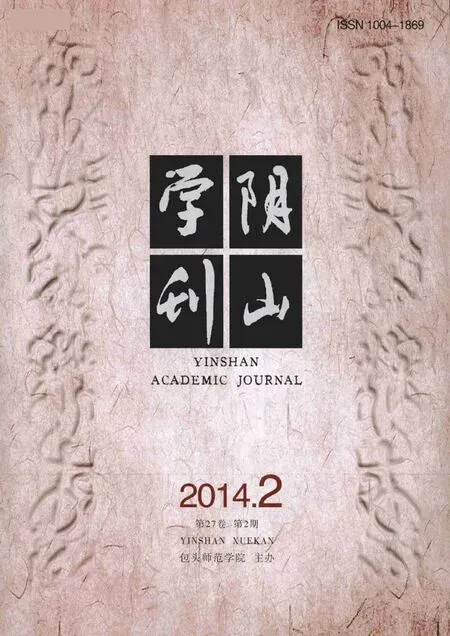“悲剧衰亡”话语的兴起试探
2014-03-11张乾坤
张 乾 坤
(湖南理工学院 中文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悲剧衰亡”话语是风靡20世纪西方戏剧知识界的著名论调。《大美百科全书》在界说“悲剧”一词时明确指出:“二十世纪有关悲剧的许多批评性论著探讨的是其衰落和终结。”[1](P30)无独有偶,2002年英国评论家霍华德·布伦顿在英国著名的《卫报》上撰文评论特里·伊格尔顿的《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时开篇就认为:“悲剧衰亡问题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一个反复被探讨的问题。”[2]应该说,“悲剧衰亡”话语的产生绝不是偶然,必然有其特定原因。这除了与20世纪现代悲剧创作整体状况有关之外,至少还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其直接原因是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悲剧灭亡问题的启发。学者在谈到“悲剧衰亡”这个话题时,一般都是将其追溯到尼采,而不是通常所认为黑格尔在自己的哲学框架内提出哲学最终取代艺术的“艺术终结论”以及别林斯基在《戏剧诗》中提到的观点,即所谓“我们俄国的悲剧是从普希金开始,而随着他而死亡”。例如,沃尔特·库夫曼认为:“悲剧死亡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尼采。……二战以来,尼采关于悲剧死亡的论述越来越有影响,他的观点几乎成为了一个常识。”[3](P163~164)尽管从悲剧理论史上来看,尼采并非是提及“悲剧衰亡”问题的第一人,但他的观点对后世“悲剧衰亡”论者产生的直接启示作用不容小觑。
其次,来自悲剧传统的强大压力。一方面,雅典时代和伊丽莎白时代悲剧创作取得了高不可及的辉煌成就,给后世剧作家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这也就是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提出的“影响的焦虑”问题,即后辈剧作家(强者)作为“儿子”形象,始终生活在“父亲”形象笼罩之下,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无形的压抑,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著名的“悲剧衰亡”者乔治·斯坦纳曾经说:“雅典和伊丽莎白的过去给将来的戏剧想象力投下了很长的阴影。屈莱顿是无数作家中第一个发现在他们自己和戏剧发明的行动之间存在着心理上的障碍。昔日伟大的成就看起来是无法超越了。”[4](P43~44)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布鲁姆认为,他所提出的“逆反式”批评原则不适用于莎士比亚,尽管有自己的理由。但是,这无疑也从侧面表现出布鲁姆自身“影响的焦虑”,即英语诗中莎士比亚是一个比父亲形象还强大的超人,后世诗人无法通过“诗的有意误读”来挑战他的王者地位,只能在巨人的阴影之下抑郁而生。作为一名最擅于挑战传统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身上流露出的“影响的焦虑”尚且无法遮掩,更不用说那些膜拜传统、跟随传统亦步亦趋的人了。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超越时空的绝对影响,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威廉斯所说的“意识形态”。正如人们一提到悲剧立刻使人想起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一样,当有人提到悲剧理论时,很快就使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诗学》。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诗学》时说:“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5](P124)然而无论《诗学》的影响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波及的范围有多广,它毕竟只是古希腊悲剧实践的理论抽象与概括,理所当然地具有一定的理论适应范围。正如在本雅明看来,它只能具有“古代的权威性”,对于德国悲悼剧而言,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本雅明批评道:“评论家们总是想要把古希腊悲剧的因素——悲剧情节、悲剧英雄、悲剧死亡——看作悲悼剧的本质因素,不管这些因素在缺乏理解力的模仿者手里受到多大的扭曲。另一方面——而这对于艺术哲学的批评史将尤为重要——悲剧,即古希腊悲剧,一直被看作早期的悲悼剧形式,以后来的悲悼剧密切相关。据此,悲剧哲学便作为世界的道德秩序理论在一个普遍化了的情感系统中发展起来,而不涉及历史内容。”[6](P72)与本雅明在这里所说的“评论家们”一样,绝大多数“悲剧衰亡”者也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以《诗学》为代表的悲剧理论“真正强大的意识形态”支配。威廉斯指出:“悲剧理论之所以有趣,主要是因为一个具体文化的形态和结构往往能够通过它而得到深刻的体现。然而,如果我们把它看作对某个单一的永久事实的论述,那么,我们只能够得出已经包含在这一假定之中的形而上结论。这里最主要的假定涉及本质永恒不变的普遍人性。”[7](P37)“悲剧衰亡”话语的论者们的失误在于:没有意识到《诗学》是与古希腊活生生的具体的文化形态和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意识到不同时代情感结构的流动性,静止凝固地理解了《诗学》,错误地将其当作了衡量一切的永恒地普遍事实。
再次,就整体而言,现代戏剧理论家和批评家未能成功地建立系统的现代悲剧理论,也就是说,“未能成功地确定现代悲剧的性质、主题内容、表现形式、传达方式、现实功能,也未能界定现代悲剧精神。”[8](P228)面对诸多的现代悲剧创作实践,在比较有影响的悲剧理论文本缺席的情况之下,许多现代戏剧理论家和批评家颇为困惑。于是,有一部分学者尝试重新阐释《诗学》,使之成为现代版本。例如,批评家麦斯威尔·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试图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抽出“突转、有缺陷的英雄、卡塔西斯”三要素作为解释现代悲剧的基石。然而,在JR·乔治·约斯特(JR.George Yost)看来,麦斯威尔·安德森的做法并不成功,只是主观的一厢情愿,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原意。[9](P147)更多的人则纷纷将目光直接投向了《诗学》,试图从中寻找其理论依据。然而,这种做法在本雅明看来,是“不涉及历史内容”,排斥“历史哲学”的做法。同样,在雷蒙·威廉斯看来,这是忽略悲剧中的情感结构,以古论今的做法,“悲剧理论原创性的部分主要出自十九世纪,它先于现代悲剧的创作,后来又被受过学术训练的人系统化了。这些学者习惯以古论今,并且将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分离开来。”[7](P38)
最后,现代文化批判的一种策略。在分析悲剧(精神)灭亡的原因时,尼采认为,无论是欧里庇得斯还是瓦格纳,充其量只是摧枯拉朽,急剧地加速了希腊悲剧(精神)的衰落,而真正挥起屠刀、砍杀希腊悲剧(精神)的罪魁祸首乃是苏格拉底、黑格尔等人所象征的理性。希腊悲剧(精神)的灭亡过程,实际上就是理性逐渐排挤希腊悲剧的酒神精神的过程。因而,悲剧是与理性及其文化形式是对立的。尼采论述悲剧的灭亡,内在旨趣是为了抨击苏格拉底、黑格尔等人所象征的理性及其文化表征。尼采借谈论悲剧死亡话语来批判、否定现代理性及其文化形式的策略在后续论者那里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延续。例如,格罗斯曼在分析现代人为何创作不出悲剧时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文明的时代,人们强烈的情感受到严格节制,甚至一言一行都受到社会法律的严格约束。由于理性文明的普遍节制与约束,现代人丧失了昔日的激情,情感变得更加理智与冷静。由于理性文明的昌盛,悲剧失去了立足之地。同样,克鲁契也认为,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20世纪之交,人类生活在一个异质的世界中,“上帝和人以及自然都以某种方式在世纪的转换过程中退化了”。在这样一个异质的世界里,人类的高贵观念已经荡然无存。即使我们能够部分地想象高贵的观念,但也无法理解它。由于缺乏高贵的观念,我们只能阅读悲剧但不能写作悲剧。由此可见,无论是格罗斯曼还是克鲁契,在言说现代语境中悲剧的可能性时,都着重分析批判了悲剧赖以存在的现代文化。诚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现代对悲剧之可能性的探讨,不以文学分析的面目出现,而或多或少假以文化诊断学之名。直到文学这一学科遭到经验主义者和逻辑主义者的清洗以前,该学科一直侵占着以前归属于哲学的那种活力。情感、行为和信仰的现代困境试图通过文学杰作的讨论得出一个所以然来。”[10](P142)论者们否认现代社会中悲剧的可能性,进而极力鼓吹“悲剧衰亡”,实际上就是策略性地批判甚至否定悲剧得以依存的现代文化。
不容置疑,国内学者早就涉足了“悲剧衰亡”问题并展开了较为集中的研究,但在论及现代西方“悲剧衰亡”话语兴起的时间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它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或是二战之后。例如,陈瘦竹先生说:“从本世纪3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理论家对悲剧的前途持有悲观态度,甚至提出‘悲剧衰亡’的论调。”[11](P300)与之稍微有所不同,陈世雄先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戏剧理论界提出了‘悲剧衰亡’论。”[12](P35)然而有足够的事实可证明,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准确地说,20世纪初“悲剧衰亡”话语在西方学术界就已经相当地流行了。那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伊迪丝·瑟尔·格罗斯曼、弗兰克·劳伦斯·卢卡斯、约瑟夫·伍德·克鲁契。
1906年,伊迪丝·瑟尔·格罗斯曼在《悲剧的衰亡》一文中认为,悲剧在希腊和伊丽莎白时期达到了顶峰,并且创造了唯一完美的悲剧形式。但是,在伊丽莎白时期顶峰之后,悲剧历经两个世纪的激昂言辞与哗众取宠之后,最终作为一种戏剧形式几乎灭绝了。她指出,“悲剧衰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小说排挤了悲剧的地位。二是现代人“情感的衰退”。格罗斯曼认为,虽然在现代社会里悲剧艺术已经衰亡了,但也有例外。例如,在一些文明程度相对较弱的国家和地区,如挪威、匈牙利、波兰、俄国、南部非洲、澳大利亚,悲剧艺术依然比较繁荣。
格罗斯曼认为,现代社会不能创作出悲剧艺术。因为现代文明社会不赞成或禁止强烈情感地表达。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社会法律的严格约束。尽管格罗斯曼认为悲剧艺术已经衰亡了,但她认为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悲剧精神。其理由是,“生活在它的深层意义上来说仍然是悲剧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限度和宇宙的法则时,我们的所思所感仍然是盲目的。”[13](P850)
格罗斯曼大概是20世纪最早专门探讨“悲剧衰亡”问题的西方学者,她的《悲剧的衰亡》一文也几乎都涉及到了后来“悲剧衰亡”话语论者所谈论的核心问题。尽管如此,她的一些观点的确很难让人苟同:其一,她明显地将结局的好坏与否作为了判断是否是悲剧的唯一标准。这是极其狭隘的。就她所崇拜的古希腊悲剧来说,真正结局是不幸的还是比较少。据伊格尔顿的说法,三大悲剧诗人之一欧里彼得斯的悲剧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以欢乐为结局的。亚里士多德所喜爱的悲剧《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结局也是欢快的。因此,悲剧与结局的不幸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悲剧是对某一行动的摹仿,“悲剧行动涉及死亡,但不一定要以死亡告终,除非有某种情感结构使然。”[7](P50)其二,她过于夸大社会上的法律条款对于悲剧情感表达的直接约束作用,仅仅依据大英帝国中心地区的局部事实,推衍出了现代社会创作不出悲剧的武断结论。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格罗斯曼承认在她所处的时代,挪威、匈牙利、波兰、俄国、南部非洲、澳大利亚等一些所谓文明程度相对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悲剧艺术依然比较繁荣。但是,在她眼里,这些国家和地区是边缘地区,是文明程度较弱蛮夷之地,即使取得的成就再高也不能代表悲剧艺术发展的主流趋向,真正代表这种主流趋向的是大英帝国这样中心地区的悲剧艺术发展。格罗斯曼抱着大英帝国的心态,其眼光无疑是极其傲慢的。也正是在这种大英帝国的优越感支配下,格罗斯曼低估了挪威、瑞典、俄国等悲剧艺术的历史成就。悲剧的历史发展也证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挪威、瑞典、俄国等国家的悲剧艺术成就要比同时期的大英帝国成就高得多。格罗斯曼囿于帝国心态,不顾文学的历史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虽然她较早得出了“悲剧衰亡”的结论,但后来无论是在衰亡论者那里还是在质疑者那里,几乎没有人提及她的真正原因了。
1927年,弗兰克·劳伦斯·卢卡斯在《悲剧》一书中认为,今天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多少个世纪以来,与大量涌现的杰出抒情诗和小说相比,真正杰出的悲剧甚至所有种类的戏剧都显得如此的稀少。悲剧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独特的社会环境,理想的观众、精湛的表演、优秀的戏剧家及其广泛的天赋。在谈到悲剧的未来前景时,他惋惜地说:“当我们的社会依然如故,其前景看起来与其说是灿烂的不如说是有趣的。”[14](P156)他认为,之所以现代小说一直占据着长期辉煌的统治地位,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小说自身比较适合表达现代人的情感。尽管悲剧受到了小说的严重挤压,但在卢卡斯看来,悲剧仍然是必要的,“没有什么能够取代悲剧。如果说它是一株几乎不开花的植物,但是它的根扎得很深”。
不可否认,与格罗斯曼一样,卢卡斯所认为的,与悲剧相比现代小说更适合表达现代人的内在情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悲剧由于长度有限、情趣集中、人物理想化,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要求。对于现代知识界读者,长篇小说可以比悲剧更细致入微地描写各种复杂变幻的感情。对一般人来说,高度理想化的悲剧不能满足他们对强烈刺激的渴望;他们离开剧院,宁愿去看电影。曾经被埃斯库罗斯、索福克洛斯、欧里彼得斯、莎士比亚等等伟大悲剧诗人高踞的宝座,现在一方面被陀思妥耶夫斯基、D·H·劳伦斯、普鲁斯特这样的小说家们占据着,另一方面被卓别林、雪瓦利埃(Chevalier)等人占据着。”[15](P21)但就总体而言,卢卡斯的悲剧观还是比较保守的。他所谓的悲剧实际上是基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他认为悲剧“是一株几乎不开花的植物”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古希腊悲剧的再造,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复制。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古希腊悲剧的独特性是真正的,它在许多重要方面是不可移植的。”[7](P8)
他的问题在于过于狭隘的理解悲剧,将古代的标准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一切,把后来的许多悲剧甚至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都统统排斥在悲剧的家族之外,以致妄自菲薄,对悲剧在现代社会中的现状过于悲观。尽管他在行文中没有直接运用“衰亡”、“死亡”之类的字眼,但在字里行间,他的“悲剧衰亡”调子还是极其明显的。卢卡斯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悲剧》一书也于1962年由纽约的Collier Books再版。特别是他将悲剧比作“一株几乎不开花的植物”的说法时常被人提及,如1955年,加缪在《雅典讲座:关于悲剧的未来》中说,“悲剧,毕竟是一株珍奇的鲜花,能在我们时代看到它盛开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1983年英国批评家海伦·加德纳在《宗教与文学》中也有类似的提法,认为“悲剧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植物”。
1929年,约瑟夫·伍德·克鲁契在《现代倾向》第五章“悲剧谬误”中说:“在现代和古代世界里,悲剧的死亡早于作家意识到这个事实。”[16](P136)将现代的文学作品称为悲剧是用词不当,因为它们与古典的类型没有相同之处,而且读起来使人沮丧。克鲁契指出,“我们阅读但是不能写悲剧”,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现代人缺乏必要的高贵的观念。尽管我们可以部分地想象高贵的观念,但是却也无法理解它,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悲剧所表现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另一个异质世界里。二是现代人误解了悲剧的本质。他认为,悲剧本质上不是绝望的表现,而是战胜绝望的表现,通过战胜绝望,确证了人生的价值。因此,在真正的悲剧中,灾难对于结局来说仅仅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它实际上是对生活信仰的确认。但是,现代所谓的“悲剧”作品只是一味地沉湎于悲伤,它的失误在于将悲剧错误地理解为令人沮丧与抑压,将其与悲惨的、感伤的混为一谈。克鲁契比较了《哈姆莱特》与《群鬼》,他认为:“莎士比亚证明了上帝对于人类的正当性,但在易卜生那里没有幸福的结局,他所谓的悲剧仅仅成为了在发现正义不再可能时我们绝望的表达。”[16](P132)因此,《群鬼》不仅是失败的言说,而且是琐碎和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观看时,我们无法从中推断出什么,也无法获得净化与和解。
克鲁契的悲剧趣味是相当古典的,以致完全否定了现代悲剧。针对他对悲剧狭隘凝固地理解,1932年,马卡姆·哈里斯在《悲剧问题》中主张悲剧理解的相对性,后来理查德·H·帕尔默将其对于悲剧的这种理解概括为“社会相对主义”(social relativism)。马卡姆·哈里斯研究发现,以前人们对悲剧的解释主要依赖于三种系统价值,即“超自然主义”(SuPernaturalism)、“人文主义”(Humanism)和“自然主义”(Naturalism),与之对应,每一种对悲剧的理解都担负不同的价值观念:超自然的和解、人类精神的确认、人们改变世界的愿望。由于先入之见的价值观念不同,观众对于悲剧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导致彼此理解之间无法通约。于是,哈里斯试图寻找一种悲剧的普遍定义,使得该定义能够消弭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导致人们在悲剧理解上的隔阂。他所谓的普遍悲剧定义是:“悲剧是个人和集体价值的形象表现,这些价值在悲剧行动中潜在地或实际地出于危机之中;而同时,由于观众忠于这些与之密切相关的价值,它们的危机唤醒了观众的反应,与之相称的积极反应,但是这些价值的内容随着时代和个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17](P182)不过,在伊格尔顿看来,哈里斯的尝试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不算成功,甚至还显得有点笨拙。
克鲁契“众所周知的文章”(well-known essay)“悲剧谬误”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被收入多个悲剧理论读本之中。他的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例如,正如他认为易卜生的《群鬼》不是悲剧一样,约翰·D·赫里尔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易卜生的《罗斯马庄》也不是悲剧,他说:“在《罗斯马庄》里,他给我们展现的不是悲剧性的死亡,而是用最近一本书的标题来说,现代世界里悲剧之死亡。”[18](P124)洛厄尔·A·费埃提指出,克鲁契的观点不仅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几部杰出的“悲剧衰亡”论著作,如乔治·斯坦纳著名的《悲剧之死》,而且还影响了80年代的莱昂内尔·艾贝尔尽管如此,克鲁契的观点还是遭到了肯尼斯·伯克、 罗伯特·W·里甘、艾德尔·奥尔森、雷蒙·威廉斯以及作家阿瑟·米勒等人一致地质疑与反对。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学者在批驳克鲁契的观点时,似乎忽视了他的观点背后隐藏着多个思想维度。也就是说,克鲁契通过对悲剧的论述,夹杂着他对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深层次思考。正如后来洛厄尔·A·费埃提所认为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悲剧谬误》具有“几种重要功能”,但是批评者们往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致在相当程度上误解了克鲁契。[19](P71)可以这样认为,也正是这些功能的多重叠合,造就了《悲剧谬误》具有多维度的价值,使它区别于大多数“悲剧衰亡”论者就事论事单一维度的著述,获得了较长的学术生命力。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持之有据地表明:“悲剧衰亡”话语兴起于20世纪早期,甚至可能会更早,但绝不是通常所认为的30年代或是二战之后。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机缘,除了与悲剧艺术自身的现状有关之外,还与悲剧理论话语以及审美现代性有着深层次的逻辑牵连。因而在本质上来讲,“悲剧衰亡”话语有其自身的复杂性,这就需要研究者客观冷静地思索,认真地检视,才能减少认识上的谬误,避免步入误区。
[1]《大美百科全书》编辑部.大美百科全书(第27卷)[Z].北京、台北:外文出版社、光复书局,1994.
[2]Howard Brenton.Freedom in chaos[N].The Guardian,21 September 2002.
[3]Walter Kaufmann.Tragedy and Philosophy [M].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4]George Steiner.The Death of Tragedy[M].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1996.
[5]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M].缪灵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6]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M].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7]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M].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8]任生名.西方现代悲剧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9]JR.George Yost.A Modern Version of Aristotle’s Poetics [J].Classical Weekly,Vol.37,No.13,1943.
[10]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11]陈瘦竹.悲剧从何处来——50至80年代英美悲剧观念述评[A].朱栋霖,周安华.陈瘦竹戏剧论集(上卷)[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12]陈世雄.悲剧衰亡之谜[J].戏剧,1996,(3).
[13]Edith Searle Grossmann.The Decadence of Tragedy [J].ContemPorary Review,89,1906.
[14]F.L.LUCAS.Tragedy [M].London: Leonard & Virginia Woolf Press,1927.
[1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张隆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16]JosePh Wood Kruttch.The Modern TemPer [M].New York: 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9.
[17]Markham Harris.The Case for Tragedy [M].New York,London,G.P.,1932.
[18]John D.Hurrell.Dilemma of Modern Tragedy [J].Educational Theatre Journal,1963.
[19]Lowell A.Fiet.“The Tragic Fallacy” Revisited [J].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Vol.10,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