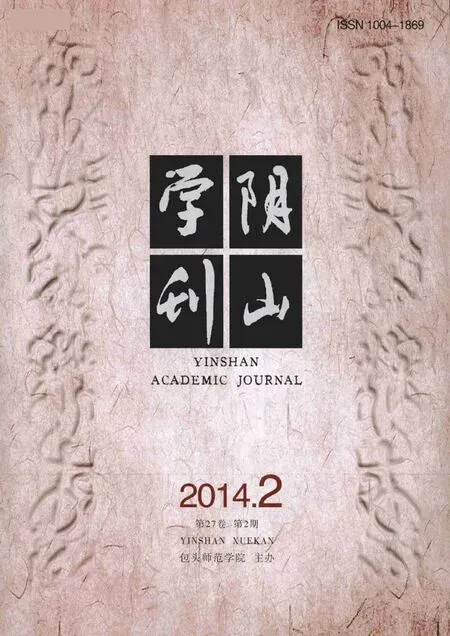古典小说与园林之研究述评
2014-03-11王譞
王 譞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3)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代表了中国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凝聚着古人异乎寻常的智慧和妙思,体现了人们对诗意人生和理想境界的向往。园林作为自然和人文的结合体时常出现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其幽思缥缈的意境和自由美好的形态常为历代文人传唱。在其长久的发展历程中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正如书画艺术家兼造园家的陈从周先生说的那样:“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盘根错节,难分难离,研究中国园林,似应先从中国诗文入手,则必求其本,先究其源,然后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如果就园论园,则所解不深。”[1](P200)周维权也在《中国古典园林史》自序中说:“园林、文学、绘画这三个艺术门类在中国历史上同步发展,互相影响的迹象十分明显,研究中国艺术的发展史,绝不能忽略园林。”[2](P5)诚如此言,二者的关系已引起学界的注意,并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了研究的历程。此时,园林理论和园林美学的研究兴起未久,研究者为数不多,专门性的论作较少,大多集中在文学与园林这一宏观问题上,并未将文学的类型细化。
一、论题形成历程
最早将古典文学与园林联系起来并加以讨论的为陶思炎的《浅谈扬州园林与文学》,文中认为文学是组成园景的重要材料,园林中的扁额碑刻和对联同花木竹石一样,构成园景的重要材料,上古神话给造园艺术以灵感,文学同绘画结合而成的文人画为园林设计提供蓝本,文学对园林有地方风格的影响,比拟与联想的造园手法依存于文学语言,文学为研究园林史提供宝贵资料。[3](P83~87)作者以其敏锐的感知,较早注意到了园林与文学的关系,对两者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不足之处便是作者只是单方面谈文学对园林的意义和影响,并未对两者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双向探索。此后的论作多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中李浩的《论唐代园林别业与文学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以唐代为时间段,探讨园林别业与文学这两种异质艺术之间的双向选择与互动关系:一方面,诗文的题写对园林有点景创意的妙用,园借诗文而传。另一方面园景又可成为诗文的素材,诗文品评多喜以山水自然为喻,作家又多借虚静空灵的园林环境来培养文思,激发灵感。这一研究在之前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此问题的断代研究上有了新突破。此后的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多沿着宏观统揽,双向比较的道路稳步进行,代表性论作有岳毅平的《试论园林与文学之关系》(《辽宁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邱德玉的《试议我国古典园林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和泰华的《论文学与园林的关系》(《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这些都是从诗文与造园的相互影响论述的。园林以诗文而传名,因构园、造园、题园、咏园,均离不开诗文,造园与诗文创作方法、艺术技巧相通,故而园林在艺术、结构、意境、美学等方面都与中国古代文学有共通之处,以上论述均围绕这些范畴来找寻两者间关系的。曹林娣的《中国园林文化》的出现将园林与文学关系研究的高度又提升了一格,此论著设有“园林与中国古代文学”一章,谈及了园林之筑皆出于文思,园林是写在地上的绝妙好词,园林是士人理想的诗化。此章将文学分门别类分别与园林文化比照,两种艺术在作者笔间交合融会的极为自然,使人体会到了来自园林和文学间的诗意美感,是近些年来最具系统性和美感的论作。
然而“文学”与“园林”本身就是两个宏观宽泛的艺术概念,各自所涉及的领域都极为宽广,并且艺术特征的多样更是不容易把握。以上研究虽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最后都免不了向诗文这一形式偏倒,难免论述不深,可见对文学这一概念的细化到了一个紧迫的地步。然而文学体裁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传奇戏曲,对园林的描绘和塑造都是极为有限而零碎的,无法像小说那样,尤其是长篇白话小说那样大容量地展开描写。故而古典小说对园林的展现是最为详尽且细致的,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由于传统研究对小说环境的不重视态度导致对故事背景和场所研究的滞后,通俗类的小说与园林关系的研究开展得相对较晚,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近二十年。可分为宏观上的整个小说文体与园林研究和单个作品与园林研究两大部分。其中前者的研究较为宏观,多为学术论文,尚无专著(只有部分章节谈及),据统计论文的篇数在30篇左右。此类交叉性学科的研究本身是一个开放性很大的论题,领域范围涉及较广,可分为以下方面。
二、园林空间与小说叙事研究
伴随着20世纪末叶所出现的文学“空间转向”的局面,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人文生活的“空间性”,渐渐地从传统的时间线性叙事研究转向了空间叙事,这一点在小说与园林的研究中突现了出来。由于园林物理空间性的客观存在,空间叙事的理论自然而然地被袭用到此研究当中。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茅盾先生就曾用建筑空间美学来比喻古典小说的结构:“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比作一座花园,苑园内一处处的楼台庭院各自成为独立完整的小单位,各有它的格局,这好比长篇小说的各(回),各有重点,有高峰,自成局面,各有重点的各章错综相间,形成整个小说的波澜,也好比各个自成格局,个性不同的亭台、水榭、湖山石、花树等等,形成了整个花园的有雄伟也有幽雅,有辽阔也有曲折的局面。”[4]之后陆文夫在当代小说创作中也有了类似的自我体验。吴士余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思维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其《园林文化与小说思维的空间效应》(《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是有关园林空间与小说叙事研究的开山之作,从之前的对两者基本艺术特性比较的研究中跳了出来,开辟了以园林艺术空间着手来研究审美主体的空间思维的新途径。此文对明清园林美学理论作了系统梳理,认为空间思维被小说创作者运用到了小说的创作之中,使得原本缺乏空间拓展思维的小说叙事模式向多元空间存在的形态发展,小说空间思维与园林思维有着很大趋同性。之后的研究者依照此研究方式接连做出了相应研究。如张世君《古典小说叙事的时空意识》(《暨南学报》1999年第1期)探讨古典小说叙事的时间和空间特点,园林空间较之地方空间具有更多艺术价值和哲学意味。依据世情小说林园多的特点,提出了“庭园小说”的概念。在此类小说中,庭园成为小说叙事的空间坐标系,同时也是情节依托的载体和连接情节的媒介。中国园林空间观念追求形、色、声、香的审美意识在小说中的反映也十分突出。谭刚毅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与传统建筑的空间序列》(《古建筑园林技术》2002年第3期)分别从对偶、主体结构、次结构、拼接图式和纹理几个不同的角度探究了二者相近共通之处。侯润华的《江南园林艺术与晚清狭邪小说》(《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从叙事结构空间,叙事思维等角度切入,讨论了江浙一带园林对晚清狭邪小说的影响。才志华的《神仙窟与后花园——爱情介质与社会心理变迁》(《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将唐传奇中的神仙窟与明清小说中的后花园比作爱情得以生发的两个重要介质,并以此为主线来揭示中古以后社会心理的变迁。实质也是在围绕空间对叙事的影响来展开的。以上论述皆是从园林的空间物理形态入手,探讨其对叙事思维模式的影响,这种方式不失为小说叙事研究的新门径。小说叙事本是一种时空兼具的现象,任何一部作品都会涉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由于中国文化侧重视觉与空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偏重“视觉思维”,是一种典型的“象思维”、“图像思维”或“直觉思维”。因此,中国古代的叙事文本多呈现出各种“空间性”的特征。上述论文套用西方理论的空间叙事分析有一定的可行之处,拓开了研究园林与小说关系的一条新思路,但实质上是空间叙事的一种延伸。园林是富有意蕴和灵气的建筑,不同于一般的空间建筑,因而园林的意象和审美要比其空间性的物理意义大得多,故而在园林意象和审美这一领域的研究占据了主流之势。
三、小说中的园林意象解读
园林是诗情渗透了的自然,小说中的园林更是透着盈盈诗意之美,从而能够在作品中形成独特意象。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文学中,花园意象都是不容忽视的典型意象。它植根于人们对自然美和理想境地的体悟。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更是将“一壶天地”的园林作为缩小了的微型宇宙来寄情怡性,花园同时作为一个桃园圣地的象征来为故事的主人公提供出脱尘世的温床,园林为心灵飘泊苦闷的士人们提供了理想的港湾。小说领域中的意象研究多停留在其叙事功能和美学功能上,着力于此方向的论文研究颇具数量。代表作有杨敏的《“家园”的寻找:明清才子佳人传奇中的花园意象》(《戏曲研究》第63辑)认为“花园是明清才子佳人传奇出现最多的意象。大多数以大团圆结局的才子佳人传奇都以花园为关节来结构故事,发展情节,花园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息息相关,密不可分。”[5](P22)探求“花园意象”的生成原因,着重于对当时社会中的士人的精神状态分析。崔红梅《古典文学中的花园意向解读》(齐齐哈尔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分析了“花园意象”的审美生成和审美接受。其中的一部分对戏曲小说中的“花园意象”进行了功能上的阐释,即这些美妙的叙事场景构筑了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周志波《明清小说中的花园意象》(《名作欣赏》2008年第4期),着重于世情小说,尤其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分析,总结了园林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在明清的小说创作中所形成的叙事模式及其独具的艺术功能,得出了其对于小说的重要意义。总之以上论作多围绕明清时期的小说来展开,并且认为园林意象在小说中的出现,并非是一般性的点缀,往往承担着一定的主题功能和审美功能。其叙事方面的功能便是连接情节,充当叙事的背景,或作为抒情的触媒,最终成为一种叙事手法。其美学功能和意义便是园林拥有诗性的美好,与外界较为恶劣的环境形成对比和美好的象征作用,象征着自由、青春和爱恋。园林意象本是一个综合意象的化身,这里集花木、山水、楼台等意象为一体,因而是一个蕴含丰富的意象综合体,并在传统文化的演进中得以不断充实和更新。冯文楼的《从桃花源、后花园到大观园——一个文学类型的文化透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就是以园林意象流变为主线来展开论述的。另有仇方的《大观园与前期狭邪小说中的园林叙事》(《南都学坛》2006年第6期)此文将前期狭邪小说中的园林叙事与大观园仔细对读,印证了前者对后者的模仿在诸如《品花宝鉴》《青楼梦》《绘芳录》中,分别有怡园、挹翠园和绘芳园等园林,这些均不同程度地带有大观园的影子。作者将其作为一个现象来研究,并从创作者的主观情志,心态目的等方面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可见对小说中园林意象的研究普遍结合了作品的叙事功能来对意象做进一步地发掘。
除了聚焦于意象之外,一些研究者将目光投入到明清之前的时代中,将园林整体作为鉴赏分析的对象,如李浩的《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有唐一代的园林进行断代研究。其门生郭丽的《唐代小说中的园林研究》,从唐代小说的实际文本出发对其中记载的园林资料进行钩沉打捞,分析了不同形态和类型的园林特点和士人们的园林活动,并探讨了唐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和园林关系。这样横截历史时段的研究有利于结合当时社会情形和审美风尚,从而将文本中的园林还原得更为真实和饱满,不失为小说与园林研究的新亮点。
四、两者交互影响和渗透的研究
园林与小说本身是两个不同的艺术概念,彼此之间的渗透和影响是相互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只关注园林对小说文本单方面的影响,对于另外一方则少有提及,有的虽有涉及,但只是零碎的只言片语,未加以深层论述。对双向关系较为关注的有曹林娣的《中国园林文化》,此书设有“园林与中国古代文学”一章,从园林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上来探究园林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作者强调:“园林与文学产生的互动关系,使园林文学更加丰富,也增添了园林的文学与人文色彩。”[6](P260)有关小说与园林的相互影响,书中提出了三方面:从园林角度来讲,园林理论得到了诗化;从小说创作者的角度来讲,作者的人生得到了艺术性的提升;从小说文本来讲,小说中的环境得到了诗化。此章节主要围绕《红楼梦》中大观园来展开论述,其他的小说作品并未有太多涉及。整体说来作者虽意识到了园林与古典小说的关系,并从几个主要方面论证了两者的相互影响,但只限于从两者的基本特点上进行大致的关联与分析,缺乏深层的研究论述。其门生张婕的《明清小说与园林艺术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是关于小说与园林的唯一一篇学位论文,在文中对两者的关系论述较为细致,谈到了园林在小说叙事空间设置、塑造人物性格、情节推动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并从审美的角度分析了历代小说园林的美的历程。不足之处在于作者以明清小说这一庞大的概念作为载体,并未对小说进行系统的分类,这样未免使得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变得复杂繁乱。
以上论作是将小说作为整体来考察与园林之间的关系研究的,阵容虽不庞大,研究成果也有限,但涉及到了主要的领域和范围。作品的时代多集中于明清时期,明清两代无疑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期鼎盛期,人们对造园建园的热爱和造园技法的精湛到了无与伦比的境地,园林被移植入大量的小说作品中,尤其以世情小说最为明显。有关小说作品和园林的研究,多集中于单篇作品上。尤其以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小说和李渔的作品为主。
五、单篇作品与园林研究
因《红楼梦》对大观园的成功塑造和详尽描绘,使得大观园成为小说中最为经典的形象。对大观园的研究史将近二百余年,大致可分新旧两个时期,即旧红学时代和新红学时代。旧红学时代和新红学时代的前期对大观园的研究集中在原址的考证上:以富察明义的《绿窗锁烟集》和袁枚的《随园诗话》对大观园的原型争论为导火线,引来了一股对大观园真址探索的热潮,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研究者有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曹聚仁等大家,并提出了“恭王府说”“拙政园说”“圆明园说”等数十个地点的说法。对大观园平面图的绘制和描绘上也有所进行,如有图说而作者无考的《大观园图说》和国家图书馆藏的《大观园全图》等。到了新红学时代的后期鉴于对大观园的考证过于现实的问题,对大观园的认识偏于理性和客观,一些学者逐渐地将之看作是与真实世界相对的理想境地从虚构虚拟的角度去进行论说,如王利器的《大观园在哪里》、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等。也有从园林建筑的角度来研究的,如葛真《大观园平面图研究》、周善毅的《大观园十议》。以上这些论说只是固着在园林虚实问题的本身探讨之上,并未对作品进行细究,这显然是有所偏颇的。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对大观园的研究角度发生了大的转变,研究者们有意识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进行挖掘,结合作品从艺术、美学、文化等方面对大观园进行研究。论著有顾平坦、曾保全的《大观园的艺术价值》,顾平坦的《红楼梦与清代园林》,俞晓红《红楼梦花园意象解读》(《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较为深层地解读了《红楼梦》中花园的意象,最终得出《红楼梦》对园林意象的塑造是对传统文学意象的一个承继和拓展。张世君的《红楼梦的园林艺趣与文化意识》(《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2期)和《〈红楼梦〉的庭院结构与文化意识》(《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1期)从园林文化的角度来集中矛盾并展现复杂的家庭人伦关系,并从各个角度揭示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建筑构思之美。近些年来,对于大观园的研究热情并未消退,反之有了一个学术转型:由收缩变得开放,由一元到多元。将园林置于中华文化的整个大的背景之下进行探寻,代表作有胡文彬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中国书店出版社,2005年)以《红楼梦》中大观园及其中故事为研究对象,并以中国古代园林艺术发展历史及其造园理论为参照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解读,从园林空间对小说的渗透,园林景象与曹雪芹造园理想,园林的意境创造,大观园的文化意蕴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另外还有王慧的《大观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肖玲玲《红楼梦对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接受》(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都是从大观园对《红楼梦》的影响角度来写。其中王慧在《大观园研究》探寻了园林文学的文化根源,沿着小说史的循序将涉及到园林的作品进行了较为细致而系统的梳理,足见作者对此研究的敏锐之感。
另有李渔作品与园林的研究,这一研究之所以突出,是因为明末清初的李渔有着戏曲小说创作家和造园家的双重身份。李渔曾在《闲情偶寄》中说:“ 予尝谓人曰:生平有两绝技,自不能用,而人亦不能用之,殊可惜也。一则辨审音乐,一则制造园亭。”[7](P5)他既有多次构建园林的丰富艺术实践,又在《闲情偶寄·居室部》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园林美学理论,这些对后人的园林建造和小说中的园林虚构都有较大的影响。他的小说作品《十二楼》以园林中的建筑楼阁来命名,体现了园林意识对其创作的渗透。代表性论作有骆洁芳的《李渔园林美学思想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文章认为:园林美学思想在其小说的构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以《十二楼》为例,李渔在小说创作中同样追求一种园林美,小说以“楼”命名,故事情节也围绕着“楼”展开,小说中的楼亭、台阁、水榭、墙壁、花草、树木等不仅起到了分割空间营造环境美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小说情节的设计、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作者思想情感的寄托。总之在庞大的小说体系中,李渔小说与园林关系是较为突出的,因而研究者给予了较多关注,然而所采用的角度和论述方式依然停留在空间叙事和审美意象之上。
综上所述,同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元素的小说与园林走入了许多研究者的视野,尽管两者有着艺术形式上的巨大差异,一为纵向实践性,一为横向空间性,研究者仍致力于寻求两者之间的共同属性和联系,从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客观来说,此研究的视角较为独特和新潮,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一个发展性阶段,存在的问题也较为突出:首先从纵向时间轴来看,多数研究集中于明清时期的作品,其他朝代的作品则少有关注,对于断代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其次是小说作品分类的问题,多数研究者只是笼统地将小说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空间叙事、园林意境等方面,或只是停留在《红楼梦》和“才子佳人”类小说等少数几个作品之上,殊不知小说类别不同,园林在其中的表现形式和呈现意义也不同,因而对小说类别的细化是必要的。另外对小说中园林的文化根源大多定位于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出脱和对理想世界的追寻上,这一点确实是其根源之一,然未免过于泛化,各个时期的思潮不同会引发作者思维和心态的变化,园林本身蕴含着多样的生活形态和浓郁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彰显着来自市井民间的风俗影像,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作者平生造园、游园、赏园的实践经验容易被投射到作品当中,因而需要将作品放置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量。对此,笔者设想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以历史为引线,沿着小说史的脉络将作品中的园林材料进行采集和梳理。之后对其中的园林艺术进行审美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阐释,最后再将结果放置在整个小说史之上,寻求两者之间更为深层的联系。
[1]陈从周.园韵[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2]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陶思炎.浅谈扬州园林与文学[J].南京师大学报,1980,(3).
[4]茅盾.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J].当代作家评论,1984,(4).
[5]杨敏的.“家园”的寻找:明清才子佳人传奇中的花园意象[J].戏曲研究,2010,(63).
[6]曹林娣.中国园林文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7]李渔.李渔全集(第一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