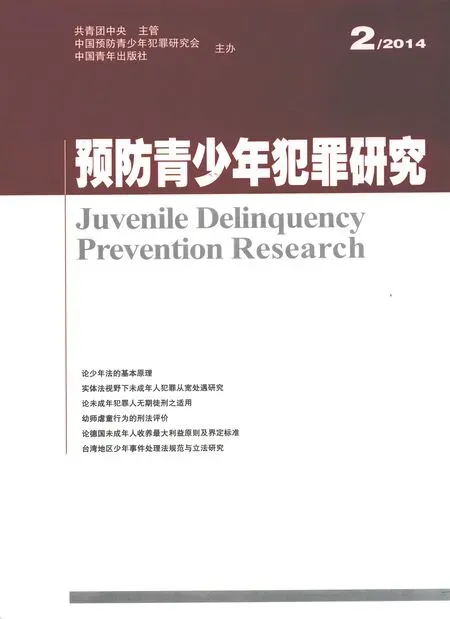幼师虐童行为的刑法评价
2014-03-11夏勇,郭宁
夏 勇,郭 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幼师虐童行为的刑法评价
夏 勇,郭 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浙江温岭发生的幼儿教师虐童事件引起了该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讨论。从实然层面看,该行为涉嫌侮辱罪:颜某在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下,在其任职的教室内,以暴力方式公然贬损幼童的人格,情节严重,构成侮辱罪;同时,虐童行为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属于公诉案件范围。但侮辱罪对儿童人身的保护是有限而片面的。从应然层面看,在有虐待罪的前提下单设虐童罪会将保护对象人为分割,更不能适应社会中类似虐待行为的刑法规制需要。建议将现有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扩展为“监护与照料关系”,并将家庭之外的虐待行为作为公诉案件。
幼师虐童;侮辱罪;虐待罪;家庭成员关系;监护与照料关系
2012年10月24日,浙江温岭女教师颜某以胶带封嘴、拎耳朵悬空、倒插垃圾桶等方式虐待儿童的照片被曝光,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后又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将其无罪释放。①随着该案的尘埃落定,当初的群情激愤在学者的理论分析中渐趋平静。然而,此次虐童事件引出的刑法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学界似乎习惯了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热点,在某种程度上摆出不屑一顾的架势……。我们不禁要问,刑法学怎么了?面对孩子,真的可以不了了之吗?
一、实然分析:虐童行为能否以现行刑法规制?
对于温岭虐童案的司法处理,社会上存在两种声音:有人认为“虐童教师无罪释放并非‘没天理’”,而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②也有人坚决反对,认为这将产生“灾难性”的“案例影响”。③笼统的结论和空泛的议论不能替代理性的刑法学分析。任何现实发生的事件是否构成犯罪,只能应用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标准加以细致衡量之后,才能做出回答。温岭警方在刑事拘留颜某时,曾就其涉嫌的犯罪做了解释:颜某虐待儿童的行为可能涉及的罪名有四个: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其中,颜某虐童行为不符合虐待罪的身份犯要求;侮辱罪要求“告诉才处理”,该案中并没有家长做这种“告诉”;故意伤害罪必须具有轻伤以上的结果,完全不符合本案的情况;颜某的行为一开始被认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但后来又被否定。④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罪名究竟能否规制幼师虐童行为呢?
(一)任何虐童行为都不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有四种表现形式:“(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从颜某的行为表现来看,显然与法条中的后两项无关,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前两种表现。
就“随意殴打”的行为类型而言,“殴打”从语义上看,即是用手或用器具击打。典型的殴打事件中行为主体对他人人身进行强烈的撞击,实施殴打者可以直接利用自己身体的有机部分或利用作为自我力量延伸的外物,如拳打、脚踢或用木棒打击、命令狗咬人等等。包括刑法在内的任何法律条文表述都是以概念的基本语义为基础的,殴打也不例外。据此,一个行为成为刑法规定的殴打,至少应当包括:第一,行为人要以其他人的身体为对象,施加一定的物理上的作用力;第二,行为人以自己的肢体以及使用工具对他人身体进行强烈碰撞;第三,行为人的行为会使他人感觉疼痛并受到一定程度的身体伤害。本案中,颜某拎男童双耳悬空与倒插垃圾桶等,符合上述第一和第三个特点,但并没有产生对儿童身体的剧烈碰撞,虽然属于暴力行为,却不能是殴打,可以说是殴打之外的另一种暴力行为。因此,将其仅视为一种具有强烈冒犯性的行为而不评价为殴打更具合理性,否则就超出了公众对殴打的普遍认识,有扩大解释之嫌。
警方之所以刑事拘留颜某,是认为颜某以寻求刺激为目的,“多次对多名儿童实施拎耳朵、头套垃圾桶、胶带纸封嘴等行为,造成受害人恐慌、害怕等后果”,①为何是"寻衅滋事罪"[EB/OL].载温岭公安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2284351872?topnav=1&wvr=5&topsug=1,访问日期:2013-01-06.即属于寻衅滋事罪中“恐吓他人”的行为类型。本案中需要刑法评价的事实显然没有追逐或拦截,也无证据证明颜某存在辱骂儿童的行为。那么,颜某有恐吓行为吗?“恐吓”意在以恶害相告使对方陷入恐惧的心理,在客观上限制了公共生活中公民的行动自由。典型的恐吓,是以暴力相威胁。本案中颜某对儿童实施拎耳朵、头套垃圾桶、胶带纸封嘴等行为,事实上对受虐儿童产生了恐吓的效果,从颜某所拍摄照片上儿童的惊恐表情以及她题写的“叫你不听话”等表述来看,也证明了她主观上存在着“吓唬”的目的。同时,本来颜某负有保护儿童的特定职责,却为了达到日后管教的顺利而以这些虐待性的行为相威胁,对于处于幼教颜某管理之下的儿童而言,年幼并不能阻止其本身对于可能的虐待行为产生恐惧感。颜某长期恐吓儿童,既是对幼童的伤害,也是对幼教秩序的破坏,具有比较严重的危害性。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行为人颜某在客观上属于寻衅滋事罪中“恐吓”的行为类型。从主观方面看,寻衅滋事罪是1979年刑法的流氓罪分解出的罪名之一,故延续了特定的动机要求——“寻求精神刺激”或“逞强、耍威风、开心取乐”等。②陈兴良.规范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55.陈忠林.刑法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40.事实上,幼师颜某表示,她虐待儿童是出于“好玩”、发泄“对某些人的火”等等,③张莉.曾感情受挫 称要发泄在学生身上[N].长江日报,2012-10-30(A16).警方据此认定其具备寻衅滋事罪的特定动机,是合理的。
既然客观行为类型和主观动机都能够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是否成立该罪就确定无疑了呢?回答是否定的。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对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解读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行为对象。只要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寻衅滋事罪对对象有着特定的要求。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逞强、耍威风”、“寻求精神刺激”,通常会向相对的弱者挑衅,但这里的弱者必须是具有意思表示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也就是说,对于挑衅,具有潜在的拒绝能力和反抗能力,但出于对行为人实行暴力及其后果的惧怕而敢怒不敢言,或者不愿费时费力与行为人纠缠而退让和回避。正是由于被挑衅者的这种“消极”态度,满足了行为人的“逞强、耍威风”心理,也正是由于被挑衅者潜在的拒绝能力和反抗能力,才让行为人感到其行为的冒险性带来的“精神刺激”。反之,对于不具有潜在拒绝能力和反抗能力的对象,就谈不上行为人向其挑衅,因为这样的对象不可能给其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幼师对于幼童而言,处在绝对优势地位,幼童毫无拒绝和反抗能力,幼师不可能通过对幼童的“挑衅”来“滋事”。诚然,颜某的确在幼童身上发泄了空虚情绪,但不是通过挑衅实现的,而是通过虐待实现的。行为对象的重要地位“不仅因为它是受到了某种行为影响的存在物,更重要的是它处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中,表现着这种社会关系”。①李洁.犯罪对象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6.由于幼童不能成为寻衅滋事行为的对象,虐待幼童行为也就不属于寻衅滋事罪所表现的社会关系,任何虐待幼童的行为都不能构成该罪。
(二)虐童行为能否定性为虐待罪
学界一般认为,虐待罪指的是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②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18.行为方式多表现为打骂、冻饿、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予治疗、限制人身自由、凌辱人格等。本案中颜某的虐童行为是对学生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并为民众和社会所不能容忍,具有严重的情节。但是,虐待罪具有身份犯的典型特征,而且是真正身份犯: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之间必须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即家庭成员;反之,则不能成立该罪。当然,关于“家庭成员”的具体范围在法律规范中并无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均未做出具体的说明或补充,但司法实践中一般将其限定于亲属关系或收养关系,并且,共同生活是这种关系中的必备要件。③高仕银.虐待罪及其处遇[J].西部法学评论,2008(6):62-63.显然,发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虐童行为,不能包括在家庭成员的特殊关系群体中,因而不能定性为虐待罪。因此,行为人颜某的行为不能被评价为刑法上的虐待罪。
(三)虐童行为能否定性为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是侵犯公民最基本的身体健康权的行为。我国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以构成《人体轻伤鉴定标准》中的轻伤为前提,是典型的结果犯;伤害行为不具有轻伤结果的,即便在表面上给他人身体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也不得以故意伤害罪论处。温岭虐童事件中的行为人确实因为拎耳朵等行为,而给受害人造成暂时性的肉体疼痛,但经过医学检查,并未破坏其身体健康。因此,就客观结果上来说,虐童事件中的行为只能认为是一般的体罚行为。但也有学者认为,客观的肉体伤害和主观的精神损害都是故意伤害罪的评价范围,甚至造成较轻肉体伤害的行为,在考虑精神伤害因素后,亦可入罪。④任先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我觉得没必要设虐童罪[N].南方都市报,2012-11-19(AA09).而这与我国现行刑法以及各国刑法中以生理健康的损害来确定该罪的立法例不相符合。因此,幼师或任何其他人的虐童行为只有达到轻伤才能构成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
(四)虐童行为能否定性为侮辱罪
侮辱罪是指使用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败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犯该罪的,告诉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那么,颜某的行为是否符合该罪呢?
首先,侮辱罪保护的法益是名誉权。①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83.作为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公民的名誉权因出生而获得,并与人格尊严密切相连。公民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不容侵犯,儿童亦不例外。颜某空间的照片直接证实其多次实施将幼童扔进垃圾桶、强迫幼童相互亲吻、将幼童嘴用宽胶带封住、脱掉幼童裤子等行为,使儿童出丑或增加羞耻感,严重损害了受害儿童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感,人格尊严受到损害的事实不能因儿童感知能力弱而被忽视。
其次,侮辱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的行为。“暴力”,是指不法施加有形力致使他人不敢反抗的强制手段。侮辱罪中的暴力并非直接对被害人人身进行殴打和伤害,而是为贬损人格采取的一种强制手段,包括强行扒脱衣裤、强行撩开衣裙、强行做难堪动作等。“其他方法”,是指以文字或语言的方式损害他人人格,包括口述、张贴、传阅、展示、播映、表演有损他人人格的言论、文字、图画等。②周道鸾,张军.刑法罪名精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395-396.颜某多次强迫儿童在教室内做脱裤子、下跪磕头、亲吻等动作,在其管教之下的幼童无法反抗,是一种以暴力方式贬损儿童人格的行为。“公然”,是指侮辱行为采用可能使不特定或多数人看到或听到的方式进行,如在闹市区谩骂他人的,属于公然侮辱。但是,公然侮辱行为并不要求一定发生于公共场所,在空间相对狭小或封闭、但不特定人或多数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当着多人的面进行的侮辱行为,也具有公然性,如在学校教室、大礼堂侮辱他人的。颜某在浙江温岭蓝孔雀幼儿园任教期间,多次强迫某个或某些儿童在教室内做难堪动作,并有其他儿童观看,属于公然的侮辱行为。可见,颜某的虐童行为属于使用暴力方式的公然侮辱行为。有观点认为,颜某的侮辱行为由于行为对象的不固定而不构成侮辱罪。③幼师虐童事件详情:更多虐童照曝光 虐童幼师被拘[EB/OL].http://www.edu.cn/xue_qian_news_197/20121026/t20121026_861433_6. shtml,访问日期:2013-01-06.确实,侮辱罪的对象必须是特定的,但是并不限定于确定的某个人。特定对象,既可以是特定的一个人,也可以是特定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即特定多数人。不论数量多少,特定个人与特定的多数人均具有确定性和具体性。本案中,行为对象范围限定于颜某所在班级管教的儿童,属于特定的多数人。
第三,侮辱罪要求情节严重。在本案中,颜某的虐童行为多次多样:700多张照片证明其在教学的两年多时间内对多名儿童进行虐待,既有拎双耳、强迫亲嘴、强迫脱裤子,又有强迫做一些危险动作,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儿童的人格尊严,有的还存在侵犯儿童身体健康的危险。而且,幼儿教师颜某与儿童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其本应承担保护和教育儿童的职责,却成为虐待儿童者,这更增加了这种虐待行为的不可忍受性。可见,幼师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情节。
第四,侮辱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本案中,颜某明知自己的虐童行为必然会产生使受害儿童人格尊严和名誉受损的结果,仍然积极实施这些行为,主观上是直接故意。
最后,侮辱罪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温岭警方以该罪必须“告诉才处理”,而本案无家长告诉为由,排除其适用。笔者认为,幼师虐童行为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与侮辱罪构成要件要素“情节严重”中的“严重”程度是一致的,但“情节严重”的行为不一定危害社会秩序。也就是说,与自诉案件相比,公诉的侮辱罪案件情节集中表现为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危害。在现行刑法规范中,工作、教学、科研秩序均作为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并由刑法加以保护,幼教作为儿童教育的启蒙阶段当然不能被排除社会秩序之外。幼师颜某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幼教秩序,因此可以在刑法上评价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已经超出了自诉案件的范围,公安机关可以依职权主动介入。
总之,颜某在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下,在其任职的教室内,以暴力方式公然贬损幼童的人格,情节严重,构成侮辱罪;同时,虐童行为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属于公诉案件范围。
二、应然分析:我国刑法应否规制幼师虐童行为?
从立法上看,对社会上存在的幼师虐童现象,是否应该被刑法单独规定为犯罪?在本案引起的讨论中,有三种观点:一是设立专门的虐童罪;①雍敏.法律专家呼吁虐待儿童罪尽快入刑[N].新京报,2012-10-29(A10).二是扩大虐待罪的范围,将幼师虐童行为包含其中;②李吉斌.虐童事件频发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专家建议适当扩大虐待罪主体适用范围[N].法制日报,2012-11-20(A3).三是坚持刑法的谦抑性,既不新立罪名,也不扩大现有罪名。③李燕.专家称浙江幼师虐童行为入刑有些牵强[N].东方早报,2012-11-13.
最后一种观点关系到如何看待刑法的谦抑性。刑法谦抑是当今潮流。所谓“谦抑”,是指如果能用其他法律解决问题,就不要轻易动用刑法。但是,只要刑法存在,就总是要将一些行为犯罪化,要保持一定的“犯罪圈”,犯罪化并不当然地等于刑法不谦抑。那么,各种严重的虐童行为是否应当在我国刑法中得到犯罪化呢?这涉及到犯罪化的标准,而犯罪化标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本文力所不及。不过,只要在虐童行为与我国刑法已经犯罪化的类似和相关行为之间进行比较,也足以得出肯定的回答。
第一,从刑法规定的虐待罪来看,被虐待的对象包括幼童,当父母或相应的监护人虐待其幼小的孩童且有恶劣情节时,就会构成犯罪。在该罪中,父母和监护人的虐待行为不仅直接侵害了孩童的人身权利,而且违背了本来负有的养育孩童之法律义务,是双重的违法。幼儿园及幼儿教师通过合同形式,实际上接受了家长的委托,有了照管幼童的职责,充当了临时监护人的角色。幼师虐待幼童,同样是双重违法。而且,相对于幼童家长,幼师对幼童的管教行为受到更多的限制,如法律一般认可家长在管教孩子时的某些体罚或粗暴行为,但这种“体罚权”却不在家长委托的范围,家长不会容忍幼师体罚或粗暴对待孩子,而且幼儿园的规章也不会允许。因此,幼师虐待幼童比家长的此类行为更不能得到原谅。既然父母虐待孩童的行为可以犯罪化,为什么幼师实施同样的行为不能犯罪化呢?
第二,从刑法规定的侮辱罪来看,如前所述,已经包含了幼师因侮辱行为而虐待幼童的情况,同样是幼师虐待幼童,仅仅因为不是侮辱即虐待方式的不同,以及虽然是侮辱但不属于“公然”,就无法受到刑法的规制,这种法益保护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幼师公然侮辱幼童可以构成犯罪,幼师私下侮辱或体罚也具有相同的虐待性质,如果情节恶劣,为什么不能犯罪化呢?
第三,从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名来看,在家庭关系之外的虐待罪对象都是成人,或为部属和下级,或为被监管人员,或为俘虏,这些人员处于特殊的管理关系中,受到管理者的较大人身制约,为了防止虐待现象的发生,专门规定了相应的罪名。既然对成年人如此,对于同样是处于特殊监管关系且人身管理色彩更为浓厚的幼童,为什么不能以相应的犯罪化举措来加以保护呢?
笔者认为,包括幼师虐童在内的虐童行为需要系统地加以犯罪化。除了上述比较,还在于以下考虑:一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对于家长分量极重,任何虐待幼童行为都会严重挑战社会容忍底线,容易引起和激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二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城镇化趋势,决定了双职工家长普遍需要将主要是独生子女的孩童,至少在8小时工作时间之内委托给他人照管,这使得幼童脱离父母的时间增多,发生家庭外虐童现象的机会也相应增多。三是我国的幼教、家政服务、特长教育等本来就不够规范,行业人员的素质不高,如果没有严格的责任制约,也容易发生问题。四是虐童行为会给幼童带来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影响整个人格形成和人生进程,造成终生危害,降低国家和民族未来人才质量。此外,正如后面要提到的,国外普遍都将包括幼师在内的各种虐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体现对幼童的全面保护。凡此种种,都说明幼师虐童行为需要系统地犯罪化。那么,是设立单独罪名还是扩大虐待罪的罪名?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两种立法例都存在。对虐童行为设立单独罪名的,如《希腊刑法典》第312条规定了“伤害未成年人等人员罪”,专门处罚下列犯罪行为:“a)对因为家庭、工作、业务关系而由行为人负责照料保护或者因为处于行为人的权力支配之下而由其照看的未满17周岁或者无自我保护能力的人,以持续的严酷行为对其造成身体伤害或者精神损害的;b)恶意地不履行其对上述人员的义务,使其遭受身体伤害或健康损害的。”①陈志军.希腊刑法典[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117.《匈牙利刑法典》第195条规定了“危害未成年人罪”:“有义务对某一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监督、照料的人,严重地违背由这些义务产生的职责,因此危害该未成年人的身体发育、智力发展与道德培养的,构成重罪。”②陈志军.匈牙利刑法典[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83.将虐童行为与针对其他对象的虐待行为规定在一起的,如《葡萄牙刑法典》第152条规定的“虐待罪”中行为对象包括对归其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或教育责任,或者因劳动关系从属于其的未成年人或者无助人,尤其是因为年龄、残疾、疾病、怀孕而处于这一状态的人;③陈志军.葡萄牙刑法典[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73.《德国刑法典》第225条规定的“虐待被保护人罪”中被保护的人包括未成年人或因残疾、疾病而无防卫能力之人;④许久生,庄敬华.德国刑法典[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12-113.《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92条规定的“折磨或不关心儿童、少年或无自卫能力者罪”的行为对象是指受其照料或监护且不满18周岁之人,或因老弱、疾病或弱智而无自卫能力之人。 我国刑法选择哪一种立法方式,还是要看哪一种方案更符合我国情况并更能解决现实的需要。①许久生.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39-40.
应当承认,我国刑法学界主张单独罪名的方案,可以弥补现有侮辱罪的不足。因为以侮辱罪追究虐童行为所达到的法益保护效果是有限而片面的,侮辱罪并非专门针对虐童行为而设置,必然会挂一漏万,对侮辱幼童但不属于公然的行为、体罚幼童但出于管教动机的虐待行为,都无法适用,在这个意义上,立法要有所作为,设立专门的虐童罪就是最直接的选择。同时,将虐童行为规定为刑法中的单独罪名,的确符合我国刑法目前的模式,即根据特定虐待对象来设定各种虐待罪名,包括虐待被监管人罪、虐待部属罪、虐待俘虏罪、虐待罪(实际上是虐待家庭成员罪)等。但是,这种立法模式也带来一个问题——是否有多少被虐待的对象就应该有多少虐待罪名?今天社会关注虐童现象,设立一个虐童罪,那明天虐待老人现象突出,是否又要设立虐待老人罪?甚或,今后还有更多的“虐待某某罪”?这样的立法过于就事论事,缺乏应有的概括性,而且,将本来是同一类的行为琐碎切割,难免罪名之间多有交叉,使得此罪与彼罪界限颇为繁杂。因此,笔者倾向于另一种方案——扩大现有的虐待罪范围。
我国刑法现有的虐待罪实际上是虐待家庭成员罪,对于那些负有法律上的抚养、赡养、扶养义务的家庭成员之间,如果义务人非但不履行义务,反而以积极的行为对义务对象进行非人折磨,情节恶劣的,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其主旨在于对需要抚养、赡养、扶养的弱势对象予以强势保护。据此,幼儿园里的幼童、学校的未成年人、养老院里的老人、家政人员照管的小孩或老人、精神病院的精神病人、孤立偏僻环境中的残疾人、行动不便的伤病人员,都有可能遭到那些对其负有监护或管护义务的人的虐待。这些人员都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缺乏、丧失或者减弱了自我保护和救助能力,甚至比家庭成员更为弱势。随着我国社会向开放且流动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随着我国几代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出现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随着工作和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老、幼、残、病、困等弱势人员将更多地需要家庭之外的机构、组织和人员照料,这种特殊监管关系将更为普遍地存在。相应地,对弱势人员的虐待行为也与虐童一样,有了更多的发生机会。对此,立法不应当就事论事,而应当将视野进一步扩张,未雨绸缪,将各种严重虐待弱势人员的行为统筹考虑,一并立法。这样,“虐待罪”的名称才更具包容。笔者认为,可以对现有虐待罪进行改造,取消家庭成员的限制,将该罪对象扩大到所有法律特别保护的弱势人员,相应地,主体也应当包括所有对弱势人员负有监护和照料职责或义务的人员。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将我国刑法中虐待罪所限制的“家庭成员关系”替换为“监护与照料关系”。所谓监护关系,是指民事法律规定的对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设置的监督和保护制度。从刑法的角度讲,这种监护关系既包括法定(指定)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经法定监护人委托的临时承担一定监护职责的人员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
所谓照料关系,是指那些虽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生活自理上的困难的人员与对其有着照料义务的人员之间的关系,照料义务可以基于法律法规,也可以基于合同委托,或者先行行为等。对于实践中存在的其他虐待行为,受害人作为正常的成年人,有能力积极寻求救济的,如上级利用权力等优势地位虐待下属的,不纳入虐待罪的范围。此外,在家庭仍为个人生活基本单位的社会中,附着于亲权之上的适当的肉体惩戒权往往为社会普遍接受,法律也没有绝对禁止,而家庭外的人员即使受家庭成员委托照料其亲人,通常也不会得到体罚的允许。因此,与家庭中的虐待行为相比,家庭外的虐待更不能令人容忍。笔者建议,相同的虐待行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属于告诉才处理,而发生在家庭之外的,则公权力应当主动介入。综上,可以将现行刑法中的虐待罪修改为:“负有监护或照料他人生活之义务的人员,虐待被监护者或被照料者,情节恶劣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中,虐待家庭成员的,告诉才处理。”
2013-02-14
夏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院长,主要研究刑法学。
郭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刑法学。
①宋识径.温岭虐童幼师:接受警方处罚[N].新京报,2012-11-18(A04).
②王晓民.虐童教师无罪释放并非"没天理"[EB/OL]. http://news.xinmin.cn/shehui/2012/11/19/17233859.html,访问日期:2013-01-06.③蔡方华.虐童女教师真的可以无罪吗[N].北京青年报,2012-11-18(A2).
④警方释疑虐童案:拘她依法 放也依法[N].新京报,2012-11-21(A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