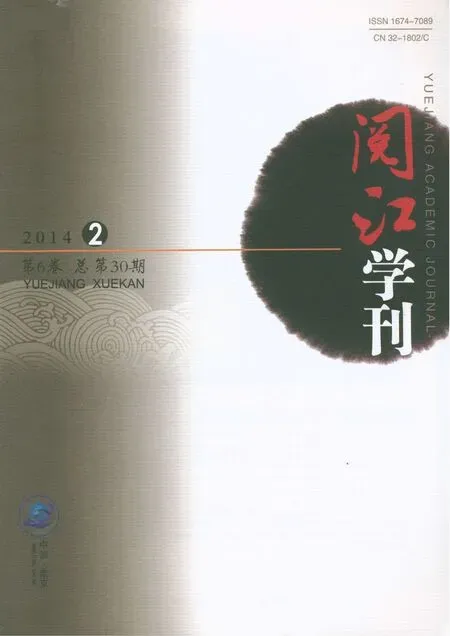傩戏的面具与非物质之“道”
2014-03-10丁淑梅
丁淑梅
(四川大学,成都610064)
傩戏的面具与非物质之“道”
丁淑梅
(四川大学,成都610064)
傩戏面具是傩仪与戏剧表演相结合的民俗艺术形式,作为中国文化的另类记号,它有自己一整套程式化、结构化的记号概念和演述系统。根据傩戏面具的纹样图案、五官造型考察傩戏面具的层级迁延与群落形态的类型学意义及其细节特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知这一借由行动和表演形成的、与固有的文字书写史相区别的另一维度的演述史。傩戏围绕面具完成了艺术与宗教、物质与非物质的转换机制,演述着与人有关、与天堇有关、与神鸟有关、与人类精神愉悦与灵魂自由有关的密码记号——待时而动、知行合一、超越现世苦难、自由在地行走。傩戏面具的背后蕴含着穿透历史与时光的非物质之“道”。
傩戏面具;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学;转换机制
面具又称“社神”、“嚎啕戏神”、“菩佬”或“脸子”,是驱鬼逐疫、消灾纳吉的傩仪与作为造型艺术、审美表现的戏剧表演相结合的民俗艺术形式,面具在傩戏活动中被视为神的载体,在制作、取用、表演、封存时都具有严格禁忌和仪则。戴上面具即代表神灵说话和行动,艺术与宗教相伴相生;面具主宰着一切,表演者似乎作为神的附体形式而存在。但透过神秘的纹样线条、斑驳的图案色彩所显示的角色类型,还有那隆起的额头、空洞的眼睛与张大的嘴巴等细节所呈现的视觉形象与造型艺术,那些面具不仅传递给我们或凶神恶煞,或狞厉恐怖,或正大安详,或谐趣横生的美感,而且作为另类的中国文化的记号,在原型与变体、反差和互补之间,颠倒的形式或许蕴含着某种夸张与真实、肯定与否定的转换机制?考察傩戏面具的层级迁延与群落形态的类型学意义及其细节特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知傩戏面具背后蕴含的丰富而复杂的非物质之“道”。
一、群落形态与层级迁延
一般认为,《周礼·方相氏》提到的“黄金四目”要算是最早的傩面具了。“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吏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1]然而,其实在甲骨文拓片上就已经有了商傩“夹方相四邑”的象形密码。作为图腾信仰和祖先崇拜遗迹的上古傩虽简单粗犷,戴魌头面具的方相氏以殳打鬼、索室驱疫,其四目的造型却非常有讲究;它化入仿黄帝四面(一说仿蚩尤四目)的原型,反映了人类早期最朴素的心理——用更多更远的目力张望身外的四方世界、探秘自然。至《唐戏弄》所说:“汉制大傩,以方相四,斗十二兽,兽各有衣、毛、角,由中黄门行之,以斗始,却以舞终”[2],可见,汉傩在人鬼对峙的冲突中逐步强化神力声威,并增添了打斗十二兽并鼗鼓侲子歌舞的内容。唐傩被纳入军礼,唐宋以来成为国家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傩仪、傩舞、傩技、傩歌到傩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累叠过程,傩戏即蕴生于宋代的社会土壤中。迄今遗存于汉族和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广大地区、遍及二十四五个省、自治区的傩戏,被认为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即因为其保留了最原始的早期扮演形态,又不断融入当地的文化空间和民间的日常生活观念。傩戏面具,以地域与族群为标志,形成了丰富而自成系列的造型艺术;以变人戏、藏地傩戏、傩堂戏、地戏面具作为样本,可以追踪和考见傩戏面具在质地色彩、线条纹样、图案造型等方面文化记号的附着与叠加过程。
贵州威宁彝族的“撮泰吉”(变人戏),是在阴历正月初三至十五的“扫火星”民俗活动中举行的。一群人包布缠头、戴着面具、手柱棍棒、踉踉跄跄从遥远的原始森林里走来,发出猿猴般的尖利吼声,向天地祖先神灵、山神谷神斟酒祭拜,跳“铃铛舞”;然后模仿烧山林、开土地、刀耕火种等农事劳作,伴随怪声答话和动物叫声,最后舞狮子。这段由模拟动作、原始舞蹈、彝语说白诵片及吼喊应答语组成的表演,主要是围绕面具舞展开的。变人戏面具用整块木头刻成长脸,利用木质纹理自然凸起宽厚的前额和长直的鼻梁、眼睛和嘴巴镂空,眼睛斜且大、嘴巴略小、无耳朵、无眼珠、无牙齿,底色涂黑,或饰以横竖变化的白色波纹,或缀以白色黑色胡须。这种造型五官略具、线条单一、用黑白对比色和线条变化标识“撮泰”神灵的身份,如阿布母年岁最大,缀白胡须、一千七百岁,壮年的阿达姆和马洪母分别是一千五百岁、一千二百岁、前者缀黑胡须,青年哼布是一千岁,还有小孩阿戛等,整体形象显示出一种稚拙憨厚、天真淳朴而又神秘怪诞的特质。
藏地傩戏是一个比较敏感而复杂的话题。关于其与藏戏的分属关系,已有不少争议和讨论[3],本文不打算就此展开辩驳,只是想基于已有研究关于原始祭祀的、民间表演艺术的、宗教的、藏戏的西藏傩面具四分法[4],将藏戏看作藏地傩戏较高层级发展的产物,以白面具、咒乌面具与寺院傩面具为例,讨论藏地傩戏面具的特征。白面具用整块原色山羊皮制成,脸部呈平面,额头、眉毛、鼻梁、耳朵用羊皮自然耸起棱道叠成,眼睛嘴巴镂空,粘附在羊皮上的羊毛自然形成头发、鬓毛。整个面具除了红线圈出的眼睛和嘴巴轮廓没有其它装饰,表现出纯朴、和善、悲悯的神色。四川白马藏人的“咒乌”神灵面具则身穿羊毛外翻的白色羊皮,黑带束腰。所戴面具有天眼冠,并用红黄蓝黑四色,用红色涂脸,黄色抹额上牙色,蓝色在额头点缀天眼,黑色四珠上下并置四目,另两目在鼻翼两侧,下巴抹黑,面具四围缀以彩色布条,看起来怒目圆睁、张口獠牙、五官比例怪诧、神色威猛。与白面具和咒乌面具相较,藏地寺院傩的跳神面具则显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红黄蓝白绿,设色对比鲜明,除了天眼之外,加入或平面或立体的小骷髅造型的头顶缀饰,眉形、眼廓、鼻孔、嘴巴都作前突、外开、张大的夸张处理,充满惊怖、狂放、威严的震慑感。
傩堂戏和地戏都是傩戏搬演形态中非常重要的品类。傩堂戏在全国许多省份都有遗存,在不同地域形成了傩愿戏、傩坛戏、端公戏、土地戏等不同的傩堂戏类型,并形成了正神、凶神、世俗人物三大类面具艺术造型。正神如慈眉善目、安详和悦的土地,头顶盘髻、满面笑纹的唐氏太婆;凶神如头长尖角、凶悍逼人的开山莽将,头戴道冠、额点混赤眼的王灵官;世俗人物如端雅清秀、忠厚可爱的甘生八郎,还有歪嘴皱鼻、滑稽多智的秦童等。地戏,与在傩堂、祠堂固定地点搭台演出的傩堂戏不同,是春节和阴历七月在村落院坝间流动演出的队戏,主要流行于贵州安顺及周边屯堡、布依、仡佬、苗族聚居区。地戏演出配戴的面具依其丰富的历史与传说故事系统,形成了将帅、道人、丑角和动物形象四大造型艺术类型。将帅面具形象多取自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如李世民、关羽、岳飞、薛仁贵等,造型线条棱块分明,装扮头盔耳翅,缀以繁复的吉祥纹样和动植物象形图案;道人面具则依反派或助阵人物造型,如戴鸡翅鸡尾道冠、奸诈狡猾的鸡嘴道人,还有飞钵道人、铁板道人等。丑角面具最有名的是歪老二与烟壳壳。至于动物面具则抓住虎、马、猴等动物威猛、驯顺、顽皮的特点象形雕凿。
从变人戏、藏地傩戏、傩堂戏、地戏面具的制作质料、五官造型、色彩运用、线条纹样及图案装饰看,傩戏面具的文化记号有一个不断叠加、层级迁延的过程,形成了以不同地域、不同家族和特定社会人群为标志的群落形态。从原始先民走出蒙昧、从事狩猎农事活动的集体记忆,到藏地日常生活、祭祀习俗、宗教活动的多元错落,面具反映了不同历史时空里变人戏和藏地傩戏的民俗印记与地域风情。从傩堂搭台、邀集族群聚会、建立人伦仪礼秩序,到列队巡演、承载会社乡俗,满足民众日常娱乐,面具昭示了空间移动与文化迁移中傩堂戏和地戏的家缘纽带与民间伦理。依托地缘和亲缘,傩戏的群落形态至今还存在着庞大的地域与族裔群落,如各地的端公戏、师公戏,还有四川梓潼阳戏、安徽歙县打罗汉、江西南丰跳傩,安徽贵池傩戏、河北武安捉黄鬼、福建泉州的打城戏、四川苍溪庆坛傩戏等等,这些傩戏都有丰富而自成类型的面具造型遗存。有意思的是,与文献记载和文字书写的历史系统不同,以傩戏面具为代表的这一行动和表演系统,常常会以变形的或者反向的形式和路径印证中国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承意脉。面具所呈示的原始野蛮的神秘氛围与日常亲切的生活气息,无处不在的神异力量与人对威权的不屑与顽解,成为文化行为对立和颠倒、互补和平衡的一种象喻。
二、天地人秩序向戏剧角色的延伸
基于傩戏搬演与驱鬼祭神、逐疫驱邪、消灾纳吉等民间信仰的紧密联系,作为一种民俗与戏剧艺术的结合体,傩戏面具的群落形态自然呈现了由天地人秩序的象征向戏剧角色的延伸。最早的方相氏面具透露的从黄帝、蚩尤、颛顼到熊、牛、虎、龙以及十二神兽的文化信息,已显示了面具作为图腾信仰与祖先崇拜的记号功能。除了揭示天地自然的秩序,面具还是世袭权力的象征与家族秩序的见证。在傩事与傩戏活动中,作为家族世传的面具,具有邀约聚集族群的号召力、确认族群中德高位重者的权力尊荣和让人望而生畏的膜拜感。无论仪式、傩舞、傩戏都围绕着面具进行。一个家族失去了面具,就丧失了族群权威性和至尊地位。傩戏的表演通过建立婚丧嫁娶、生育饮食、内务外交等乡社伦常秩序,来分配财产、解决纠纷、联络族群力量、融合家缘亲情。傩戏表演作为族群生活的一部分,是娱乐的,也是实用的;傩戏演员与在场观众其实是二位一体的,观众不是看客,而是实现这一搬演仪式的社会功能必不可少的参与者。从安徽贵池殷村姚家面具二十八枚的摆放式看,自上而下分八层,最上层是皇帝,接着是武官、圣帝和文官,然后是萧女、老回、财神、父老、老和尚,第四层是孟女、二回、土地、文龙、小和尚,第五层是吉婆、三回、包公、杞梁、三和尚,第六层是梅香、小回、周仓、宋中,第七层是唐叔、童子、杨兴,最下层是赵虎、张龙。又如江西南丰“跳傩”现存两千三百多枚一百五十多类面具,有驱疫神祇、民间俗神、道释神仙、传奇英雄、精怪动物、世俗人物等层级造型。看上去,天神地灵、宗教神祇、神话人物、历史人物与家族成员、世俗民众、仆役随从层级并存,覆盖了宗族血缘关系和族群聚落向下一路的内在秩序。围绕面具铺展的傩戏表演场合提供了唯一的乡社生活的公共空间,从而实现了为下层民众驱邪、祛病、镇宅、赐福、延嗣、添寿、丰产、纳祥的精神抚慰功能。
当艺术从宗教中逐渐剥离,人与神的关系出现了富有意味的变化,傩戏面具的功能也从敬示神灵向写照人生转换。傩戏面具成为世俗的写照,并构造了戏剧表演所依凭的重要“道具”。傩戏面具中不仅正神形象渐染世俗色彩,而且凶神怪灵和世俗人物的大量出现,尤其是丑角人物自成系列的类型学造型,完成了由天地人秩序的象征向戏剧角色的延伸。凶神是凶悍威猛、镇妖逐鬼、驱疫祛邪的神祗,面具造型咄咄逼人,线条粗犷奔放,或横眉竖眼、眼珠凸鼓,或头上长角、嘴吐獠牙,兼具夸张与写实的精神气质。如败走麦城的关羽封汉寿宁侯,历代官方和民间都累累加封,称王称圣,称公称帝。经由佛道二教“三界伏魔大帝神威天尊关帝圣君”、“伏魔大仙关帝圣君”护法神的民间演义,其民神地位更显赫,变成了傩坛的坛神与傩戏的戏神,面如枣色、卧蚕浓眉、丹凤吊眼、半睁半闭、黑须长垂,以威慑神力镇坛护法、保一方平安。关公面具各族群均备,如清代遗存下来的安徽贵池刘街乡茶溪汪就有逐疫关帝“圣帝登殿”像。傩戏开场必祭奉关公圣像方开演正戏,每逢春节或关公生日,田野村寨中会出现队戏,抬着关公像巡游扫荡、驱邪纳吉。又如开山莽将是最凶猛的镇妖神衹之一,头上尖竖长角、双耳耸起,獠牙外露、眼珠暴突,烈焰浓眉,面目狰狞,嫉恶如仇,与头长三角的开路将军一起手执金光钺斧,砍杀妖魔鬼怪,为人们追回失去的魂魄。还有铁面无私、惩治恶魔、勾还良愿、计算阳寿的判官;额嵌混赤眼、纠察天上人间是非、追捕邪魔妖鬼的灵官;人面鸡嘴、似人似鸡、奸诈狡猾、奇异怪谲的鸡嘴道人;由杨幺投湖水神形象演化而来,怒目圆睁、咬牙怒吼的杨泗将军等等。这些凶神怪灵作为人与神之间的过渡形象,充满了世俗化的意念和人的欲望,显示出神与人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错动——人在神力的保护与吞噬下,成为神的驯众与同谋;又不断从神的阴影下走了出来,与神力形成了某种对抗与询疑,他们不仅在人的世界里优游,甚至对红尘生活有一种瞩望和羡艳。
丑角面具自成体系的类型学造型,是傩戏作为戏剧搬演的艺术功能逐步增强的重要显征。如因相貌丑陋而被黜榜、科举失败撞阶而亡的钟馗,在各族群的傩戏中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据说起源于三四千年前祈雨巫师仲虺,或也出自一个原始部落祭祀巫师——手舞棍棒的终葵。自敦煌出土的唐代写本经文《除夕钟馗驱傩文》描述钟馗钢头银额,身披豹皮,朱砂染身,帅十万丛林怪兽捉拿野魂孤鬼以后,钟馗形象就与年节、端午习俗相结合,明清以来遗存了形态丰富的面具造型,其形象雕造并延伸到了年画、门神画、民间剪纸艺术中。钟馗相貌丑陋,面黑耳大,出场总与阴曹恶鬼相伴,头上长角,大眼暴突,嘴角向两鬓咧开并上翘,獠牙外翻,耳边鬓毛如剑戟,一幅不怒自威、威严难犯、刚正不阿的形容,成为傩仪中统鬼斩妖的猛将,禳灾祛魅的灵符。以钟馗为主角的傩戏更是不胜枚数——跳钟馗、钟馗打鬼、钟馗捉鬼、钟馗斩鬼、钟馗夜巡、钟馗嫁妹、斩五毒、钟馗醉酒等等。安徽歙县郑村的《嬉钟馗》,就是一出典型的“跳钟馗”傩戏。它由拜老郎、钟进士出巡、斩五毒、谢老郎几个段落组成。先烧纸燃鞭拜老郎,握香望空三拜,然后钟馗持玉笏,与持钢叉狂跳的五鬼怒目对舞,在一片“傩傩”声中追五鬼冲出屋外,出巡开始。队前列锣鼓、回避、肃静牌,牌后六蓝旗;旗后横书“钟进士出巡”五个大字;幅后从蜈蚣、蜘蛛、蛇、壁虎、癞蛤蟆五毒(又称“五鬼”),脸部各涂其形;鬼后蝙蝠开道,钟馗打伞执酒坛,骑驴小妹及媒婆殿以锣鼓。钟馗登高鸟瞰,至要冲旷地搭高台,蝙蝠登台“竖蜻蜓”引道,钟馗登台作“金鸡独立”、“智破四门”、“海底捞月”等架式,以示寻鬼驱赶之状。巡至街道村路,蝙蝠入堂屋,钟馗赶五鬼,手持青锋剑,“左青龙,右白虎”,入宅驱邪。复在台作架式,下台巡视而出。入夜锣鼓斩邪除五鬼,嬉鬼至普济桥上,仍打伞执酒坛,小妹媒婆随队逐嬉,钟馗持剑将五鬼逐一斩讫;偃旗歇鼓,全班会桥上,钟馗握香望空拜谢钟神归天。
此外,地戏面具中有一个歪老二,其面具造型五官失衡,非常奇特:发髻上斜插着一把木梳,歪嘴皱眉,呲牙咧嘴,一眼圆睁,一眼微眯,斜眉扯眼,大鼻薄唇,面部涂红,半边下巴走形。传说歪老二是朱元璋远征贵州时在云南当地寻找到的一位民间高人和军事向导,在作战两方阵地穿梭往来而不被怀疑,为朱元璋的战事大捷传递信息、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贵州傩戏中也有一个丑角人物——秦童,是《甘生赶考》中的角色,作为甘生的书童伴行赶考,甘生落榜秦童却高中皇榜。其面具形象头梳歪髻,细眉上挑,两眼歪斜,皱鼻咧嘴,呲牙掉颌,左嘴角歪斜到脸颊半边,右边嘴角皱纹蜿蜒至下巴,一幅似笑非笑、幽默滑稽、愚笨中透着几分威严、狡黠中又抖落出智慧的样子。有趣的是,与秦童的丑角造型形成呼应的还有秦童娘子、歪嘴老娘等几个面具,虽然作为女性面具,有其妩媚和善、喜笑颜开的个性,但都是口眼歪斜、五官失调、脸型左右上下扭曲的造型,还包括地戏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口眼歪斜、脸颊点麻子、面部涂绿、脸部纹理右上左下整体扭曲的挑夫,都将极度扭曲的生理缺陷与内在心灵、德行的美相映成趣,形成了以丑为美、以谑为美、自成一格的丑角面具造型系列。
随着正面神祇、凶神怪灵、世俗人物、丑角形象的次第迁延,傩戏面具形成了它自身丰富复杂、有序延展的类型系列。面具造型通过想象对比、变形夸张、附着更多纹样图案等造型手法,将天神地灵具象化,将风伯雨师、雷公电母、禽鸟蝶蝠、虾蟹龟鱼、龙虎牛鼠等自然名物和飞禽走兽灵格化,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鬼的位置关系有意味地被交错置换了。与此同时,傩戏面具将艺术触角更多地伸向了人的世界,将人作为创造物的摹本加以更真实的表现,铺染了浓重的世俗生活印记。傩戏面具演述了人经由面对自然、回溯神话、探索文明,从而确立自我和内心思维的觉醒历程,成为负载更多文化意涵的类型学记号。
三、面具背后:物质与非物质之“道”
人类早期的面具艺术,其实是一种头颅崇拜意识的积淀。人所有的精神活动和内心生活最集中地体现在头、脸上。身体提供的神经组织、智力系统的生物学属性和肌理,都要经由大脑的聚合、组织、分析与反射,最终通过脸部的五官表情和动作形成智力活动和精神能量。面具用物质质料塑造了高度复杂的精神活动的艺术象形,然而在面具的物质形态下面,抑或并非仅仅如此。傩戏面具带给人作为主体的意义何在?什么是面具的“非物质之道”?据说黄帝胜蚩尤后,悬蚩尤画像以威慑天下。《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5]宾于四门,即将浑沌(或作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四凶的头颅悬挂国之四门,使之从宾从属,亦神亦友,远御魑魅魍魉,近护国之臣民。四凶之一的穷奇,是汉代傩事中的十二神兽之一,其形如牛,四目长着坚硬的刺猬毛,其声如狗(又说像虎,长尾,爪如钩,手如锯),吃恶梦和鬼疫蛊,但却侍奸邪。这种通过败死者头颅完成的奇异能量传递与转换的仪式,出现在汉代傩戏雏形的魌头造型中,或许已预示了傩戏面具艺术的发生学原理。
如果进一步考察傩戏面具的五官构造,尤其是那些凶神怪灵和世俗人物面具的细节特征,我们会发现,附着在它上面的文化记号是如此的怪异而比例失调:轮廓式浮雕,尖竖的犄角,或许还有失落的胡须和羽毛,前凸的硕大额头,五官尤其是眼睛和嘴巴的细节被刻意放大突出、扭曲变形:睁大以至暴突的眼珠或凹陷的镂空的眼窝,从眼窝里伸出来的圆柱形的眼睛?紧闭或线性拉长的嘴巴、外翻的圆张的大口、獠牙外翘、上下倾斜或无牙缺齿掉颌的大嘴?在强烈的装饰性色彩和神秘的线条纹样包裹之下,那些隆起的暴露的部分和凹陷下去的阴影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
首先,来看嘴的类型。傩戏面具人物的嘴形,可以归为闭嘴、张嘴与变形嘴三大类。紧闭或线性拉长的嘴巴,主要是通过左右上下拉伸嘴线,来表现角色或敦厚沉静,或洞察世事,或悲悯人间,或不满愤怒的情绪。外翻的圆张的大口则往往没有舌头和牙齿等口腔附着物,集中展示的是人物惊诧、恐惧、呐喊、张狂的意念。而獠牙外翘、上下倾斜或缺齿掉颌的大嘴,则往往突出与嘴相关的各式各样的舌头和牙齿部件。舌头或是轻轻抬起露一点,或是很厚实的略略前伸,红色,但却绝少长长的伸垂下来的猩红吊舌。牙齿要么是整齐排列的两排,要么是尖利外翘的獠牙,要么是残损不齐的缺齿。而嘴形呲牙咧嘴、缺齿掉颌、左倾右斜、上下扭曲,意在镌刻角色凶神恶煞、勇猛威严、风趣蔼然、愚顽滑稽的个性,如藏于安徽贵池刘街乡源溪缩溪金村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其嘴形就是张嘴和闭嘴的典型。作为社坛演出傩舞、神伞与古老钱的舞者面具,千里眼头上一对大肉角,额上嵌红色的太阳,红色眉毛倒竖,眼眶圆睁,眼球镂空。涂黑的大脸上衬着为了看得更远而极力外张的鲜红的大口,舌头前部抵在上下牙之间立起有寸余,以粗犷奔放、勇武凶猛的印象。而顺风耳则耳廓浑大,下颌宽厚,同样涂黑的面颊上除了眉毛和眉间的烈焰,就是线性闭起的嘴巴造型,为了集中听力谛听远处的声音而紧紧地抿着,最引人注意了。至于獠牙外翘、嘴角歪斜、缺齿掉颌的变化嘴形,在贵州德江傩堂戏中的开山莽将、判官、小鬼、尖角将军、灵官、开路将军,安顺天龙镇屯堡地戏的傩神、孔宣,黔北黔东地戏的秦童、秦童娘子、歪嘴老娘、秋姑婆、唐氏太婆、土地,云南镇雄傩戏的蚩尤、玄黄老者、孽龙,端公戏的丑娘猜、和尚、寿星,江西南丰跳傩的钟馗、啸山、开山,藏族十二相面具等不同地域的傩戏表演中,类型和变体都非常丰富。
其次,来看眼睛的类型。傩戏面具角色的眼睛变例,可以归为半睁半闭、凹陷空洞和暴突伸出三种非正常的眼神。半睁半闭的眼睛,看上去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目光凝滞,略显神秘,在傩戏面具中往往是正神具有的一种俯瞰世界、掌控人间、显示威权神力的眼神。利用面具质料自然镂空的凹陷空洞的眼睛,它被赋予秉性怪异乖张的一些凶神怪灵。尤其是空洞的凹陷的眼睛、向外伸出拉长的圆柱形眼睛,不仅在傩戏中出现,而且在更为普遍的文明发生地带,都有类似的示现:凹陷的空洞的眼睛,如日本考古出土的绳文时代贝制面具、土制与木制假面;[6]藏于柏林民俗博物馆和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夸扣特尔人的皂诺克瓦面具。[7]拉长外伸的圆柱形眼睛,如与悠久的黄河文明相异、属于长江流域文明形态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神;如属于既古老又毗邻南方开放文化圈的闽南木偶戏中的纵目偶人;如藏于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北美考维尚族萨利希人的斯瓦赫威面具,以及藏于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夸扣特尔人的赫威赫威面具,藏于米尔沃基市公共博物馆的夸扣特尔人的赫威赫威面具,还有列维·斯特劳斯所考察和描述的考维尚人与穆斯圭安人的斯瓦赫威面具。[8]这些空洞的眼睛、从眼窝里伸出来的圆柱形的纵目,显示了文明发生学上的异地同源性,它是和失明的眼疾有关,还是和日食、地震的灾难记忆有关?还是和食人剜眼的野蛮习俗相对抗的一种形式?还是人类为了固定与肉眼难以透视的自然天神的距离,而借助身体记号创造的魔法望远镜?有意思的是,古人把观看世界和观看自我联系起来,把倒溯回去的向后看的历史和对未来的世界的瞻望对接起来。傩戏面具的眼睛变例,实现了人类期待不受任何干扰的目力在遥远而广漠的世界里确认自我位置并直接与自然对视沟通的记号系统功能。而在面具的背后,真率的表情、生猛的姿态,延伸到生命潮汐涨落的律动中,在喧嚣和狂欢中遁入沉思冥想的灵魂,追忆着自然的神话与图腾的崇拜,也演述着宗族制度与生与死的仪礼。
傩戏的面具显示了人对宗教沉迷的深度:拥有面具,就拥有了至上神力。一切都在律动动中不能止息,戴面具的傩者似乎受到神的蛊惑和控制,看上去无精打采,却又具有某种征服一切的威力。傩者手指苍穹,俯瞰大地,传达无所不在的天神与先祖的旨意,用长矛刺向想象中的妖鬼邪疫;作为神的奴仆,敲打乐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似说非说,似唱非唱,并伴着群体应答和高声尖叫,驱傩赶鬼,呼唤神灵解除人类活着的痛苦。另一方面,傩戏面具的类型学造型,由现实象征秩序向艺术想象空间延伸,呈现了文明战胜自然过程中最原初的状态:统治宇宙的神怪妖鬼具有野蛮、吞噬、侵害和剥夺的权力,人类被监禁在未知空间里仓皇无助地张望逃生出口,对神顶礼膜拜的同时,夹杂着敬畏和恐惧,也滋生着、凝聚着对立反抗的情绪和征服欲。人与神的关系围绕傩戏面具展开了一次艰难旅程的转换:从敬畏、恐惧、受役,到征服、控制、操纵,再到祛魅、清障、除蔽,人与神终于达成和解。艺术脱离宗教,走向自身的递嬗与成熟,戏剧作为艺术的诞生,构建了新的文化转换机制,治愈的不仅是肉体病患,也是生死的挣扎与困惑,是灵魂的撕扯与痛苦。
透过傩戏面具的视觉类型与细节特征,我们看到了人成为主体的精神活动所打下的深深烙印。傩戏面具成为借由行动和表演形成的、与固有的文字书写史相区别的另一维度的演述史。在面具的种种变异组合体中,戏剧搬演的艺术建立了自身开放与聚合、暴露与消弭、诙谐与庄重、粗犷与细腻、反差与互补的内应性法则。傩戏,围绕面具完成了艺术与宗教、物质与非物质的转换机制,演述着与人有关、与天堇有关、与神鸟有关、与人类精神愉悦与灵魂自由有关的密码记号。如果对照《诗经·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9]的说法来看,或许傩戏所昭示的最朴素的生命哲理——待时而动、知行合一、超越现世苦难、自由在地行走,才是傩戏在文明发展链条中跨越文化的非物质之“道”和穿透时光的“不变量”。
[1]郑玄,注.贾公彦,疏.黄侃,经文句读.周礼注疏:卷三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74.
[2]任半塘.唐戏弄: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221.
[3]刘志群.藏戏和傩戏[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3): 85-90.
[4]刘志群.西藏傩面具和藏戏面具纵横观[J].西藏艺术研究,1991,(1):61-65.
[5]李梦生.左传译注: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19.
[6]大阪府立弥生文化博物馆.仮面的考古学[M].大阪:大阪府立弥生文化博物馆,2010.
[7][8]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8,67,书前彩插;10,107,109,书前彩插.
[9]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7.
〔责任编辑:渠红岩〕
Nuo Opera M asks and Intangible“way”
DING Shu-mei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Nuo operamask is a combination folk art form of Nuo and drama.As an offbeatmark of Chinese culture,it has a set of stylized,structured mark concept and system.To investigate significance and detailed characteristics of persistent and community level of Nuo operamasks from themask patterns and features will contribute to our further cognition of another dimension of the history of differences between Nuo opera which is formed by action and performance,and natural writing history of natural language.By via ofmasks,Nuo opera completes a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art and religion,matter and antimatter,performs a password mask that is related to human being,Days of cordierite,pleasure of human spirit and freedom of soul--Bide one's time,and beyond this life,suffering,free to walk.The Nuomask contains an intangible way that can pass through time and history.
Nuo operamask;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ypology;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J825
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4)02-0128-07
2014-01-13
丁淑梅,女,陕西西安人,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戏剧、戏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