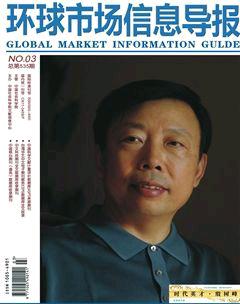诗歌的“合时”“合事”:古代诗歌中的时代烙印
2014-03-09荆有信
荆有信
中国古代诗歌集中反映了中国的历史,是历史在诗人笔下的一种再现,是时代的历史烙印。诗坛领袖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品读诗歌就是和那个时代交流。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的诗歌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应该说,自人类有了语言,诗歌便产生了。原始的诗歌与人类的劳动生活紧密相连,是在集体劳动中为协调动作、减轻疲劳、提高效率而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应倡和之声。它们的创作者,鲁迅称之为“吭育吭育派”。《礼记·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吕氏春秋·古乐》载“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都足以说明远古诗歌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纵观诗坛历史,从《诗经》中“周民族的史诗”“颂歌与怨刺诗”“婚恋诗”“农事诗”“征役诗”到屈原的《离骚》;从汉代“骚体赋”“散体赋”到汉代乐府民歌;从魏晋的“建安文学”到晋宋的山水田园文学;从“初唐四杰”到盛唐的李白、杜甫,再到中晚唐的白居易、杜牧;从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到苏轼、辛弃疾······,他们的种种作品,无不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体现了诗文的“合时”与“合事”。笔者想就诗歌最为兴盛的唐代两座丰碑为例加以阐述。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是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宏大蓬勃的盛唐气象的鲜明写照,是他豪放不羁的个性的生动体现,是开元、天宝之际唐朝盛极一时又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的深刻再现。他的诗歌是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方法高度统一的产物。
李白的诗歌表现了他的理想抱负和性格气质,抒发了他的思想感情和矛盾痛苦,从中折射出社会的精神,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既反映了盛唐的强大、繁荣、昌盛,也暴露了它的腐朽黑暗和危机四伏。李白作为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文人,与上层统治集团既有矛盾,又有依附关系。他蔑视权贵,却又不得不向他们干谒求荐,没有他们的举荐赏识,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所憎恶的,却是他不得不依靠的。所以尽管他清高孤傲,有时只能庸俗地妥协。他以个人的孤傲去反抗现实,去争取个人自由和个性独立,是势单力薄而没有出路的。他在诗中愤怒地抗议封建社会对人才的摧残扼杀:“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尖锐地揭露忠奸不分,贤愚颠倒的现实:“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其三十七)。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总第535期2014年第0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他刚正不阿,不愿曲意逢迎:“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其十二),也不屑于与俗沉浮:“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在这难以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情况下,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但他并不忘记对现实和黑暗的揭露。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文臣武将们便滋衅生事,希旨邀宠,李白指出“乃至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对玄宗不惜牺牲数万士卒去夺取吐蕃石堡加以斥责:“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李白的抱负和气概生成于“一百四十年, 国容何赫然”(《古风》四十六)的盛唐,孕育于“伊尹运元化,卫霍输筋力”(《君子有所思行)社会风尚,体现了“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塞下曲》其六)的时代精神。他的理想抱负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内容,他的英雄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他立志报效国家、建功疆场“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一)。安史之乱爆发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程,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这些诗歌既有李白豪迈自信的个性特征,但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得了高昂奋发的盛世时代精神,诗歌之中已经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与李白不同的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他的诗歌在反映天宝末年到大历年间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时代的动乱和民生的疮痍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被称为“诗史”,更加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杜甫诗歌内容博大精深,安史之乱前后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得到高度的统一。杜甫诗中所反映的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安史之乱前后二十余年的军国大事,不仅可证诸史实,而且可以补充史实。这样正是被称为“史诗”的原因所在。
安史之乱前夕,唐朝已是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潜滋暗长。唐玄宗宠幸杨国忠兄妹,《丽人行》铺陈了诸杨游宴曲江时侍从之盛、饮食之精、衣着之丽,揭露了他们的骄横跋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对唐玄宗骄纵安禄山,杜甫也有所揭露:“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敏感的从诗人这些日渐激化的内外矛盾之中预感到祸乱将作:“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君看随阳雁,各有蹈梁谋.(《同诸公武慈恩导塔》)在《咏怀五百字》中这种忧虑则表现得更急迫、深重了:“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不朽的《三吏》《三别》,不仅深刻广阔地反映了这一现实,对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寄予更大的同情而且能敏锐地把握社稷倾覆,民族矛盾上升,战争由先前的穷兵黩武转为平叛戡乱这一历史变化。如《新婚别》中作者摄取新婚夫妇“暮婚”而“晨告别”这一战乱年代特有的事件,传达强烈的时代悲剧气氛。诗人既写出了新妇生离死别的悲痛,“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歌颂了她们的练达人情、深识大体:“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从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反映出广大人民深明大义、同仇敌忾的爱国感情。
两京收复,杜甫喜不自胜,写下了著名的《洗兵马》一诗。“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命危在破竹中。”表达了广大军民的欢欣喜悦之情,歌颂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人的中兴功绩,并对吐蕃、回纥势张,诸将骄纵等尾大不掉的隐患表示忧虑:“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蒲萄宫”“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安史之乱甫平,吐蕃又洗劫长安,代宗出奔陕州:“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忆昔》二首之一)藩镇割据之势愈演愈烈:“胡灭人还乱,兵残将自疑。登坛名绝假,报主尔何迟。”(《有感》五首之五)诗人揭露官军劫掠,殆同盗匪:“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之三)指斥宦官统军,内嬖乱政:“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诸将》五首之四)“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之一)。诸如宦官擅权、藩镇作乱这些中晚唐社会的政治痼疾,这时方露端倪,但诗人见微知著,所论皆能切中时弊,以“诗史”的形式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使诗歌中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总而言之,古代诗歌中诗人总是将自己的情感、对时代的感悟深深地渗透在诗歌之中,体现了诗歌的“合时”和“合事”,这种诗歌中的时代烙印,使我们在欣赏诗歌的同时也在重温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