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阿毛(外四题)
2014-03-07叶龙虎
叶龙虎
参军阿毛(外四题)
叶龙虎
“参军阿毛”是一个孤儿,他的爹娘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东一餐西一餐,给人放牛放羊、割稻斫柴,总算安然长大。抗美援朝那一年,他十八岁,坚决要去当兵,天天念着要参军,而且非常执着。据说他几次三番去区里的征兵办公室要求,终因个子太小没能如愿。从此,阿毛的名字前面加了“参军”两个字,很多人干脆就喊他“参军”,这一叫就是五十多年。我小时候,他住在别人家的一间窄窄的八尺间(弄堂屋)里,我只是从门口路过时张望过,他住的地方,里面黑咕隆咚的,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台狗头灶。实在太穷了,以致一辈子都没能娶上老婆。
在人民公社的年代里,贫下中农是公社的依靠力量,当时唱得最红的一首歌是这样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参军阿毛根正苗红,自然是公社的向阳花。在农田灌溉淘汰牛车盘、实现机械化后,参军阿毛首先成了大队的抽水机船的机手。每逢干旱季节,全大队所有的高田上,都会出现他的身影。分田承包后,他更吃香了,这边“阿毛哥,我的田水干了”;那边“阿毛叔,快到我家打,我下午还要种”。我至今还能想起他赤着膊、头颈挂一条毛巾摇着机船的样子。
参军阿毛是基干民兵,民兵连只要有活动,他都会积极参加。逢年过节,为了防止所谓的阶级敌人的破坏,民兵连要组织部分民兵集体住宿,夜间还要武装巡逻。在住宿的民兵当中,年纪就数他最大,除了他,一般都是那些没有结婚的小伙子。
文革期间,大队隔几个晚上就要组织政治学习,他一定是最准时到达会场的。坐在放在地上的桁条(没有凳椅)上,一开始似乎还在认真地听着大队干部读《老三篇》:“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没多久就开小差了。我敢肯定,他是听不懂的,不仅不懂“见异思迁”,也不可能知道白求恩是何方人士,不然他就不会炫耀他那只时髦的三节头手电筒,不时地东照照西照照,与旁边的小伙子开玩笑。
参军阿毛在生产队里干活是很卖力气的,尤其是割稻,一些妇女都喜欢与他搭班,只要抬一抬他的“城隍”,他的脚踏打稻机就会转得飞快。他很好讲话,开他玩笑也不发火,经常有人去拍他没后脑勺的“饭撬头”。当然,他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当时生产队的农副产品大多按工分分配,这样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分一筐,他一个人也能分一筐。有一次生产队分脆瓜,不知道什么事惹他生气了,居然将分给他的一筐瓜都砸到晒场上,边砸边叫:“我一个人怎么吃得完,叫我当饭吃啊……”
分田承包后,参军阿毛再没有到田里去,他除了摇着抽水机船打田水,还兼着大队轧米厂轧米的工作。我那时还住在农村,常常要去轧米厂轧米,他时不时会走过来帮我一把,把满箩筐的稻谷与我一起发力倒进轧米机的斗里,把轧好的米帮我扛到风箱旁。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回老家只要碰到他就会递上一支烟,问上一声好。不过,他去世的消息我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参军阿毛就像是一滴水,滴到地上后,不经意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华
大华是我妹夫,一个多月前还来过我办公室。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我发现他的脸色有点暗,比平时黑了许多,当时我还在想,这大概是刚刚忙过“双抢”,在田头晒的。
那天,他来去匆匆,让他吃了中饭再回去也不肯。他告诉我,为了查他父亲当年在余姚钢铁厂工作的档案,已经跑了好几趟了。到过档案局、户籍中心、公安局的档案室。都说数据库找不到信息,真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他说:“自从阿爸知道当年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有生活补贴时,就吃不下、睡不好。我再忙也得来查,不是为了500元一月的补贴,主要是给老人一个安慰。”我告诉他,如果查户籍档案有困难,当年的工资发放清单应该也能作为依据。他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我给国资公司打了电话,那边的领导告诉我,工厂解散五十多年了,会计档案也不一定齐全,先登记名字,查到了再通知你。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劝大华先安慰老人,耐心等待查询结果。如今,他父亲的事情终于解决了,而为父亲奔忙的儿子却已经去了。
大华十二岁就下田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一辈子忙在田头。其间,他也做过木匠,而且手艺极好,还带过好几拨徒弟;也拆过旧屋、卖过旧木料。但是,他始终没放弃田头。他是对得起这块土地的,总把它侍弄得有条有理。邻居们告诉我,他早上五点钟就去几里外的田头了,回家吃口泡饭再去工厂上班,下班后还要去一下田头,哪怕天已经很黑了。他种的水稻产量总比别人要高,毛豆、萝卜、青菜等时令菜蔬四季不断。我经常吃到他种的菜。据说今年早稻收割后,他冒着烈日削草皮,已经在河塘上烧了两大堆的焦泥,准备下半年种菜用。就在他住院的前两天,还在田头忙到天黑。虽然,我们这一代人都肯吃苦,但像他这样勤快的还真不多。
大华的家离我的老家仅隔一条小路,彼此在家里叫一声都能听到。我每次回家,总看见他从我家门口匆匆走过:或拎着两只热水瓶,或背着一把锄头。他的生活节俭得近乎苛刻。为了造房子,几年都不添置一件新衣服,一角五分一瓶的开水也舍不得去冲,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爿花。我妻子每次回家,他都会说:“阿姐,开水你别去冲了,我会烧的。”平时的餐桌上,如果没有客人,大多是自己种的蔬菜,极少见到鱼腥之类。实在感到疲惫了,最多也就对我妹妹说,去买块牛肉。按照大华的说法,牛肉是补的,吃了牛肉会恢复体力。
他女儿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他的一生中,唯一的出远门也就两夫妻在女儿家住了几天。女儿很孝顺,陪着父母去了外滩、城隍庙、植物园等著名的景点,当他看到东方明珠,就对我妹妹说:“老雪,上海真好,这房子真高。等老了干不动活了我们来多住几天。”谁知他第二次去上海住的竟然是医院的病房。
每年回老家过年,吃晚饭时大华必定会捧着茶杯进来坐上一会。今年过年,我在老家住了四天,每天晚上大华都来陪我散步。头一天向北,一直走到相岙水库的大坝下;第二天我们从明德观前面的河塘往西,穿过官桥村,绕鸡鸣山走了一圈,途中还在小河边捡到一只小鹅;第三天过童家桥到上钱,再从红庙山西麓回来,算是走得最近了;最后一个晚上往南走,从魏家桥、云山到缪家绕了一大圈。边散步边聊天,这四个晚上说过的话,或许是过去很多年的总和。平时大家都忙,如果不是逢年过节,大华是没有闲工夫聊天的。春节期间,我们还用了两个下午爬山,一次爬黄洞尖,一次爬望海尖。当然,白天爬山的队伍比较壮观,很多邻居都加入了我们的爬山队伍。记得那天去爬望海尖,我们从俞坊岭进山,车子停在金沙村,到半山还下起了雪。现在回想起来,大华的体力当时已经不济了,比他年纪大很多的老人都走到了前面,他却落后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为了陪我妻子故意走慢的。
听妹妹说,九月下旬,大华感觉没力气。我妹妹陪他到当地的卫生院门诊,下午去拿化验单时,医生建议他去余姚人民医院作进一步检查,因为黄疸指数很高。他想第二天再去,是我妹妹的坚持,才当天下午赶到余姚人民医院。我得知他住院的消息是几天之后的事了。打电话要去看他,他还大声说别来,听我执意要去又说要到门口来接我。他告诉我,胃口很好,饭能吃两大碗,黄疸指数也下降了。我以为是急性黄疸肝炎,于是安慰他很快会好的,趁住院好好休息几天,别急着出院。我妹妹问我要不要去问问医生,我当时还说,急性黄疸肝炎,一星期肯定能出院。我是过于乐观了。
其实,大华得的是“急性肝功能衰竭”,死亡率极高。这种病如果平时不过分劳累,注意营养,根本不会发病。周三(10月24日)我去上海看他,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叫他时,他还是想把头抬起来,尽力睁开眼睛,但似乎什么也看不见。当我问他是否好一点时,他从喉咙底发出声音:“好多了,我快好了。”这是大华最后对我说的话。看他这般模样,我心如刀绞,但也只能故作轻松。听妹妹说,从我离开医院到去世的三天里,他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周五再去看他时,已经喊不应了。周六的中午,他突然间睁开眼睛向四下看,眼眶中充溢着泪水,嘴巴也在微微抖动,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当他的二弟说了一句“阿哥,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情有我们呢!”方才闭上眼睛,两行泪水从眼角流下……
近几天来,我深深地怀念着大华。现在写这篇文字,也是含着泪写的。明年的春节,大华再不会陪我去散步了,以后他只能在我的记忆中了。人生无常,说什么也不能相信,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居然就这样走了,还带着满腔的遗憾。就连大华养的那条狗也在伤心,自从主人去世后,它垂着头不吃不喝,如今已瘦得皮包骨头。焦泥还堆在河塘上,晚稻已经沉甸甸地低下了头,青菜在地里依旧是绿油油的,主人却再也不能去侍弄它们了。省吃俭用造了一幢楼,竟没有住上一天。每当我与妻说起这些,就忍不住要流泪。大华是我的妹夫,也是我的好朋友,对他的缅怀,会陪伴我的终生的。
阿刚伯
阿刚伯是一个普通的农民,高高的个子,剃着平头,黑黑的脸孔,还有沙沙的大嗓门。说是农民,但从未见过他田间劳动,从我记事起,他就兼着好几个生产队的会计。他出身于二六市张姓望族,其父张杏生在老街开有一家叫“回春堂”的药店。他从家族举办的湖塘小学毕业,从小就打得一手好算盘,而且左手打算盘、右手写字,字又写得极工整,像我们家乡的年糕印版一样。我从小就觉得他很有本事,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我的偶像,我现在从事这份职业,多多少少也是受了他的一些影响。
其实,我也算与他共过事。小学毕业后,我就担任了生产队的记工员,因为他是生产队的会计,所以经常会有碰在一起的时候。每到夜晚,只要是他来,生产队仓库后门口的高晒场就格外热闹,老远就能听到他的声音。那时候,农民对有文化的人总是很尊重,我父亲这一辈的人,不管年龄比他大还是比他小都叫他阿刚哥,而我们这些孩子大多叫他阿刚伯。我到现在还一直记得他,前几天还和女儿说起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他就有种亲人般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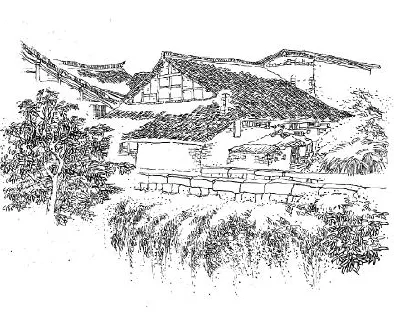
那一年夏天,我还不满十五岁,右耳不知什么原因发炎了,但白天还得坚持劳动。由于是“双抢”大忙季节,父亲没工夫陪我去医院。一天晚上,我正在记工分,脓又从耳朵中流了出来,实在很痛。这时候,阿刚伯就对我父亲说,再不去看医生,龙虎的耳朵会被烂穿的,到时就麻烦了。于是,我父亲掏出10元钱交给阿刚伯,托他带我去余姚的阳明医院门诊,他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火车来到余姚。这是我第一次上县城,来去匆匆,基本上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下了火车,踏上高高的有着五个桥洞的石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季卫桥),在桥上向西望去,看见不远处还有一座水泥桥(候青门桥),上面有很多行人。我像是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紧紧地跟着阿刚伯,生怕走丢。沿着候青江的南岸走,医院门口又有一条小河,过了一座小石桥才走进医院的大门。里面冷冷清清的,没人挂号,一打听说医生们都去造反了,今天不门诊。从医院出来,看见狭长的新建路上到处都是人群,有的人还提着木棍,说南庙有人冲进来了,要去最良桥打仗。我们很害怕,马上返回车站乘火车直接去了慈城。这一天是1967年的7月20日。能记那么清楚,是因为几天后在二六市的老街上,我看到了关于“七二○武斗”的大字报。这时才明白,当时余姚街头为什么有那么多提着木棍的人。
到慈城已经是中午时光了。慈城是旧慈溪县的县城,县政府在十多年前迁浒山后,这里成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古镇,文革的风波虽然也会波及,但与其他地方相比,自然太平了许多。家乡自古属慈溪,慈城的保黎医院在家乡人的印象中并不比阳明医院逊色,我右耳的炎症,自然也是药到病治,并没有耽误第二天的田间劳动。我们在慈城逗留了不到两个钟头,从医院出来去火车站的路上,阿刚伯买了两个馒头,一人一个边走边啃便匆匆回家了。
阿刚伯去世已经十多年了,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突然又想起他,并且把他陪我上医院的事情记了下来。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小事,也许他很快就忘记了,也许他一直是这样帮助别人的。而对于我,这不仅仅是一件阿刚伯助人为乐的事,他让我在遥望青涩少年时代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温暖,充满了感激;在武斗文斗充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年代,这是一缕人性的亮光;在每天都在田间辛苦劳作看不到未来的时候,这是一种无言的激励。
乔伯
乔伯(村里人老老小小都这样叫他)去世已经很多年了。他是我的伯父,他在世时的点点滴滴,我到今天还记得十分清晰,以至于好几回在梦里,仿佛仍在孩提时,顽皮地摸着伯父肩上的那颗“豆腐渣瘤”,缠着他讲故事……
伯父不是真正的农民。年轻时,他接我爷爷的班做过一段时间的“信客”,专门跑家乡到上海这条线。后来随着国家邮政事业的发展,他失业了,于是到“湖桥庵”的公社酒厂做工,再接着以戤社户下放到我父亲当队长的生产队里。
小时候,我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记得伯父从来就没评上过十分(全劳力),最高也就九分吧,尽管他当时才四十来岁。对于农活,他的确不是很熟练,尤其不会耕田之类的技术活,也挑不动两三百斤重的担子。但是,他干活很仔细、很用心。年轻人喜欢与他一起干活,只要有他在,大家就不会觉得太枯燥。他年轻时期的阅历,确实也让当时的农村人开了眼界。直到现在,家乡仍然有一些人经常提起乔伯,学着他的腔调:“好了好了……”他说西郊公园的大象的腿像“明德观”大殿上的屋柱一样粗;他说孔雀开屏时,能将整个“曹田畈”遮住;他说抬头看廿四层楼国际饭店,帽子也要掉下的,如此等等。明明知道他天花乱坠说“大话”,却很少有人来反驳他,毕竟到过上海的人不多。只是大家都要调侃他,学着他的腔调传播着他说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还是深信不疑的,甚至会想象廿四层楼到底多少高?
伯父身体不如父亲、小叔健壮,但他十分勤劳。因为伯母是手工业合作社服装工场(家乡叫铁车店)的工人,平时工作较忙,尤其是我的几个堂兄弟长大都进了手工业合作社的建筑社(家乡叫泥水社),所以伯父忙了田头又忙家,里里外外全是他操心。那一年,他与父亲、小叔商量,要将缪家的三间祖屋拆过来,造在我父亲与小叔的自留地上。兄弟们住在一起自然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父亲与小叔都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伯父不管刮风下雪,只要生产队没活,就挑着三角架满山跑。当时农村造房子,不像现在用新石头新砖头,大多是拆山上无主的坟墓。伯父他不会拆坟,专门捡别人不要的断砖头,破石板,大概经过两年多的筹备,硬是用肩膀将砌墙用的建筑材料都挑齐了。新建的三间平屋,在当时也着实风光了一阵,过路人都说气派,中间堂前两边房,又传统又新式。文革时期的农村建房,大多用水泥桁条、毛竹椽子,而伯父的新屋,用的全是缪家老屋的杉树桁条、杉树椽子。
造好了房子,伯父一家就从“童家里头”搬过来了,兄弟们住在一起比过去热闹了许多。在生产队不出工的日子里,他还是闲不住,不下雨就背着扁担柴绳出门。当时封山育林,山上的柴是不准斫的,他斫山脚下渠道边的刺、草,老老实实,山民也不为难他。我就没有他这份耐心。记得有一次去施岙的沿山渠道斫草,看到渠道上有手指粗的硬柴,就爬上去斩了几根,不料被管山林的人看到了,跑过来夺了我的刀,斩断了我的扁担柴绳。当我苦苦哀求还我柴刀时,那人恶狠狠地说“还你、还你。”用刀斩旁边牌坊的石柱,斩得刀刃全部卷了起来,还丢得老远。那把柴刀是很有名的铁匠师傅打的,一元多钱,第一天就被我给毁了,真是心疼死了。从此,我告诫自己,要像伯父一样老实做人,老实做事。
伯父很能干,每到春天,他挎一只篮子上山,不一会就能捡回满满一篮的野蕈(野蘑菇)。他有一杆土枪,要么不上山,上山准能打来一些野兔、野鸡之类的野味。他给过我两根长长的野鸡毛,真是漂亮,插在帽子上扮孙猴子,让小伙伴们羡慕得不行。那年我要去当兵,临走前伯父约我一起到爷爷的坟头,让我用他的那杆土枪,向天空放了一枪。这以后我使用过很多种枪,打土枪却是唯一的一次。我没问过伯父让我放枪的用意,现在成了永远的秘密。
记得那天我还在梦中,床头柜上的电话突然响起,堂兄告诉我:“我爹爹走了。”我怎么也无法相信。几个月前,我还带着他和伯母、三叔、三婶去爷爷的坟头,他推着三叔的轮车,还爬上坡去,我让他小心下来,在爷爷的墓前合照。如今,这张照片成了伯父最后的照片。其实伯父一直没有什么大病,平时也就喜欢喝一口烧酒,每天的脸都是红红的。听我堂兄说,他是吃饭的时候走的,饭前还喝了一杯烧酒,想起来倒有些许安慰。哭着闹着来到这个世界,吃饱了喝足了平平静静地离开,有些人还记得他,念着他的好,也不枉来这人世走一遭了。
祖法哥
我和祖法哥是一个生产队的。他住在“花园”,我住在“曹家”,两个自然村只隔一条小溪。花园因曾经有过唐昭宗时期(889-904)文林郎孙谅府第的后花园而得名,据考证这里还出过宋大学士孙沔、宋孝子孙之翰和宋侍郎孙梦观等历史名人。旧时,每年的清明,周边的“仙鸡山派”孙氏,都会前来祭拜祖先。祖法哥姓孙,是孙谅的后人。
直到清朝咸丰年间,“长毛”的一把火烧了花园、曹家、里王家及附近的湖塘下市(集市),鸡鸣山东麓成了一片废墟。若干年后,在花园重建的村庄还叫花园,居民仍以孙氏为主。在曹家和里王家重建的村庄叫曹家,居民多从外地迁入,不仅姓氏很杂,建造的房屋也大多是朝向各异的平房。我小时候,曹氏子孙迁徙何方已经不得而知,除了鸡鸣山上曹氏的祖坟露出曾经的显赫外,整个曹家已经没有一户曹姓的居民了。
祖法哥个子不高,也算是殷实人家出身,住的房子应该是咸丰兵燹唯一幸存的老房子,也是当时花园村里唯一的一幢楼房。老屋两层五楹,坐西朝东,四周青砖围墙,大门在围墙的北首,跨进大门一个长方形的天井,阶沿上的廊下是一排格子门窗,后天井很窄,摆着一些水缸。
祖法哥很聪明,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他割倒的稻堆很整齐、均匀、容易脱粒,且割稻非常快;他拔的秧整齐、松散、干净,很容易分株,所以插秧的妇女要抢他的秧种;他插秧也是横是横,竖是竖,没有浮株、不落脚坑,一样种下,别人种的可能还黄兮兮的让太阳晒蔫了,他种的却已经绿油油的了。祖法哥不仅犁耕耙耖粗活细活样样都精,而且还会木工活、还会打猎。木工是无师自通。记得当年稻草要摇草绳、织草包,山上又封山育林不准斫柴,只能掘灰夹泥来当燃料,原本烧稻草的大灶需要改造灶膛并配上风箱后才可以烧灰夹泥,祖法哥不知从哪里学会了风箱的制作,村里大多数人家的风箱都是他做的。尽管他自己也承认木工技术只是“三脚猫”,但仍有人请他干活,因为他做木工可以由生产队转划工分,不用付现钱。我曾经帮他放牛,他帮我修过房间的窗门。
祖法哥很憨厚,虽有一个“祖法憨大”的绰号,其实胆子很小。有一个冬天的下午,我们三个十六七岁的大孩子在“三间头”挑牛粪。三间头是湖桥庵尼姑的老房子,虽然并不差,大概是房子朝北,采光也不好,加上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命案,所以一直没人居住,只堆放一些杂物。公社化后,一度作为生产队的仓库和牛厩。记得那天还下着毛毛细雨,里面阴森森的,我们得知祖法哥一会儿要来烧牛水(用烧开的水泡花饼拌切成段的稻草喂牛,是耕牛越冬的精饲料),就商量好与他开玩笑,于是,等他一到,就绘声绘色地说:“刚才我们进屋时,隐约看见灶沿缸悬空坐着一个人,好像没有脚,揉揉眼却什么都没有了,你烧水时要留意一点呵。”
祖法哥想也不想就说:“那是我的祖宗,没事的。”
他要求我们陪他一起烧水,我们说要清理牛厩间,要把牛粪挑光,否则会被队长骂的,说完就挑起牛粪走了。一到墙外,我们放下土笥担就绕到后窗去看,只见他一边烧火,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祖宗保佑,你是我的祖宗大人,你老人家可别吓唬我。”一条腿还伸到了灶沿缸的外边,随时准备要逃的样子。我们从窗外丢了一块泥进去,他大喊一声,飞快奔到屋外。当我们把真相告诉他时,他并没有发火,只是说:“这几个小鬼头,这种玩笑也会开,灵魂也给你们吓出了。”
后来我当兵去了,退伍后又在外地工作,很少和祖发哥打交道。有几次在路上碰到他,就让他坐我的摩托车回家,他逢人便说:“龙虎人真好,看得起我,半路也特地停下来带我。”说得我不好意思。祖发哥就是这样,人家对他一点点的好就会记在心上。祖法哥是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去世的,大概是中风,这可能与他平时太喜欢喝酒有关系。对于他的去世,我知道后觉得特别惋惜,他平时身体一直很好,况且还不到六十岁,我曾经与他说过,等我退休了要找他下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