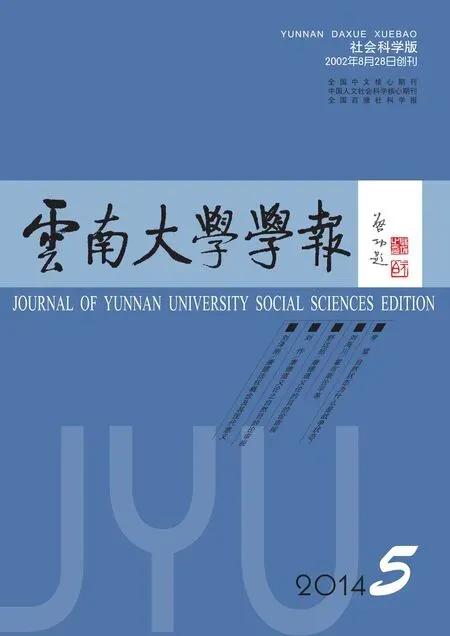康德道义论之自然目的论审视*
2014-03-06刘作
刘 作
[东南大学,南京 211189]
康德的道义论是基于理性的学说,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论证道德的内容和合理性。在康德那里,理性和感性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前者给我们颁布了无条件的道德法则,后者让我们产生追求幸福的倾向。道德的价值不在于行为所预期的目的以及实际所产生的结果,而在于出于义务而行动,道德的基础与幸福无关。由此,康德的道义论似乎与目的论没有关系,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学说。然而,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自然的目的、至善、终极目的等概念。这些概念在康德的义务论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以及具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接受舒远招教授把康德的道义论划分为狭义的道义论和广义的道义论的观点,前者涉及道德学,后者涉及至善学。我将证明:在道德学中,道德性的最高原则与自然目的论无关,在推理具体义务时,自然目的论起到了假设的作用,这种假设在《判断力批判》中得到了详细的探讨;自然目的论在至善论中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自然目的论基于道德目的论,道德目的论的依据是实践理性。由此,康德的道义论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及其结果至善,从而彰显人在宇宙中的价值。[1]
一、道德学与自然目的论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第一章“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中,康德提出了善良意志的概念。他认为善良意志是无条件的善,具有绝对的价值。德性伦理学所理解的适度、节制等虽然看似具有内在的价值,但它们不是绝对的善,只有在一个善良意志的限制之下,它们才是善的。康德还强调了幸福不是绝对的善,由此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幸福主义。幸福只有在一个善良意志的条件之下才是善的。所有把个人的或者普遍的幸福当作最高原则的道德体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善良意志的价值不是基于它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其意愿。即使由于时运不济,甚至无情的自然苛刻,这个意志对于实现其意图一无是处,只剩下这个努力行动的善良意志,那么,它“毕竟会像一颗珠宝一样独自闪闪发光,它是某种在自己自身内就拥有其完全价值的东西”。[2](P13)
康德对善良意志的概念的论证说明:他的学说与目的论是完全不同的。目的论把行为的结果当作行为之道德价值的根据(这里所述的目的论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后果主义的目的论)。善先于正当,一个行为是善的就在于它具有好的结果。善良意志与此完全不同,它不在于行为的结果,只在于行为的意愿。这样,规范性的论断不禁会让人产生怀疑,认为它“只不过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而大自然为什么要把理性赋予我们的意志来做主宰,它在这种意图中也有可能会被误解”。[2](P13)康德从自然目的论的角度来论证了这一点。
他引入了传统目的论的原理:自然不做无用功。如果自然的设计都是有目的的,那么,它为什么会赋予我们理性呢?有两个选择答案:幸福或者善良意志。如果理性以实现幸福为目的,那么它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就是科学和文明。康德接受了卢梭的看法,认为科学和文明与人的幸福是对立的。在卢梭看来,在自然状态中,人本来是自由和平等的。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私有制和财产的出现,人和人之间出现了不平等,道德堕落了,人变得不幸福。康德给二者的对立以一种目的论的解释,即自然如果希望人仅仅过一种幸福的舒适的生活,那么,本能是其更好的选择。在《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中,康德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自然所赋予人的,既不是公牛的角,也不是狮子的爪,也不是狗的牙,人的一切都是由自己来创造的,而不是由本能所引导的。自然并不关心人的生活的舒适,而是希望人通过理性来配享幸福。
既然自然赋予人理性不在于实现人的幸福,康德就得出了结论:“理性就必定具有其真正的使命,这绝不是产生一个作为其他意图的手段的意志,而是产生一种自在的本身就善良的意志”。[2](P6)对善良意志的定义,说明了康德的道义论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作为后果主义的目的论是完全不同的理论。然而,自然目的论在这个论证中起了基础的作用。这个假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比如Timmermann就认为:“康德把他的结论,即道德命令作为理性的诫命是可以辩护的,建立在世界的一个明智统治和自然的普遍合目的性的假设上,这点在康德批判哲学的总体框架之内看起来是有问题的。这样的假设可能在道德信念的基础之上是可辩护的,但是它们在道德性作为理性反对享乐主义的规范性力量中是没有作用的。”[3](P22)他认为,自然目的论在至善论中是有位置的,在道德学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道德学体现的是行为和理性的立法的关系,与自然目的论无关。为了说明这个论证不是康德一贯的立场,他给出了一个解释:“这段话基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而不是严格的哲学,并且其后在第三章更广的辩护计划中,被纯粹实践理性更哲学化的一个论述所取代。”[3](P23)Timmermann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善良意志的概念没有进入“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康德马上从对善良意志的概念分析进入到了对义务概念的分析,从而得到道德性的最高原则。但这并不能够说明,自然目的论的这个预设在道德学中没有地位。*舒远招教授提醒我,在《纯粹理性批判》方法论第二章“纯粹理性的法规”的第一节“我们理性的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中,康德有这样一段话:“既然这涉及我们与最高目的相关的行为,那么,明智地为我们着想的大自然在安排我们的理性时,其最后意图本文就只是放在道德上的。”[4](P531)康德从自然目的论的角度说明,大自然赋予我们理性是以道德为目的的。我赞同舒教授把它做比喻式的理解的看法,因为康德在撰写《纯粹理性批判》时,还没有反思性的判断力的概念。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二章,康德通过对意志概念的分析,得出了定言命令的几个表达式。为了在直观上说明定言命令的运用,康德举了几个例子。在自杀的例子中,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很绝望,他想自杀,幸好他还拥有理性,他可以问问他的准则是否可以普遍化。他的准则就是,在生命的痛苦大于欢乐的条件下,把出自自爱而自杀当作我的原则。康德在论证时,提到了“一个自然,如果其法则竟是通过具有促进生命的使命的同一种情感来破坏生命本身,这将是自相矛盾的,因而不会作为自然而存在了,所以那条准则就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2](P53)很显然,康德使用了自然目的论的假设——自爱的使命(Bestimmung)是促进人的生命。如果将这个准则普遍化的话,那么,自爱就同时在破坏人的生命,这违背了自爱的使命。所以,这个准则不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是不道德的。
在人性论公式运用到发展自己的才能的义务之中。康德认为,不发展自己的才能,可以与人性的保存一致,但与人性的促进不一致。为什么这种不一致违背了义务呢?康德使用了这样的假设:“现在,在人性中有达到更大完善性的禀赋,这些禀赋就我们主体中的人性而言属于自然的目的。”[2](P65)自然的目的是为了完善人的才能,荒废自己的禀赋违背了义务。在其后期著作《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系统地展示了义务。康德在谈到不能够淫欲的义务时,也使用了自然目的论的假设。他认为:“正如自然决定生命的爱是为了保存人格一样,性爱也是为了保存种族;也就是说,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然的目的。”[5](P271)如果一个人反自然地使用性属性,那么他就违背了对自我的义务。
在寻求和辩护道德性的最高原则时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基于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从意志的概念出发而得出定言命令,接着从先验观念论的视角为定言命令的有效性进行辩护;后者是从法则与准则的对比出发,得出无条件的法则只能是形式的法则的结论,接着从理性的事实出发来推出意志的自由的实在性。在道德学的最高原则中,自然目的论是没有地位的,然而,如前所示,在展现具体的义务时,康德会使用自然目的论的假设。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目的论是一种后果主义,把行为的道德价值放在了行为的结果之上,不管是预期结果还是实际上达到的结果。如果说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目的论的主体是人,那么,自然目的论的主体是自然。自然具有某种安排和目的,这种目的是善的,人的行为甚至人类的历史都是为了达到自然的目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把何种目的归于自然?为什么把这些目的归于自然?自然目的论与理性的立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在道德学中依然对我们隐藏着,我们必须从“第三批判”入手考察。*Klemme教授认为,康德在出版《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时,没有反思性的判断力的概念,不熟悉纯粹实践理性与反思性的判断力的关系,无法清晰地解释“自然目的”的概念。然而,他已经意识到我们只能以实践的意图来把目的赋予自然。Klemme教授还认为,如果《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里面的自然的目的论无法得到辩护,那么它会危及意志的自律。[6](P209)我赞同Klemme教授对康德哲学中自然目的论的发生学解释,但是我对他后面的观点持有保留态度。在我看来,自然目的论是否可得到辩护对道德学没有什么影响,康德只是在某些具体义务时,会使用自然目的论的假设。在进入“第三批判”之前,我们有必要从至善的概念开始。
二、至善学与自然目的论
在康德看来,哲学本来的含义就是爱智慧,在实践上规定至善就是智慧学,哲学与至善的概念是紧密相关的。康德把至善的概念放入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之中。在他看来,在他之前的哲学家没有解决好至善的可能性问题,无论是伊壁鸠鲁学派还是斯多葛学派,都错误地认为幸福和道德是同一的。实际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道德是智性的,处于本体界,幸福是感性的,处于自然界。康德认为,至善作为道德律的全部对象,实现它是一个义务。既然道德律是可能的,实现至善也就是可能的。问题是,这种可能性在哪里?从追求幸福来产生德行,是完全错误的;从德行产生幸福则有可能正确。如果我们像其他学派那样,把人的现象存在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至善的可能性。只有在先验观念论的框架内,区分本体和现象,以间接的方式看待幸福和道德的联系,我们才有可能解释至善的可能性问题。这种间接的方式需要预设灵魂不死和上帝。前者确保了德行的完善,后者确保了德福一致。
康德强调,道德律是一个形式的法则,其有效性通过理性的事实已经被确立起来。不管至善能否实现,道德律依然对我们是有效的。然而,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者,如果至善在自然中无法实现,有德者难以获得幸福,作恶的人相反却拥有获得幸福的很多手段,也就是说,这个自然是不合目的性的,在其中找不到德福一致的根据,那么,一个有道德的人会感到绝望,无情的自然会挫败他一以贯之地按照道德律行动的动机。如果他试图继续做一个道德的人,持之以恒地追求至善,那么,他就需要在实践的意图上设想上帝存在。
《纯粹理性批判》已经证明了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自然与可能经验相关,受到知性范畴的规定,是一个机械论系统。自由是超感性的,作为机械论的自然与它是完全不同的,二者互不影响。然而,由意志自由而带来的结果即至善应当在自然中实现,也就是说,自由领域对自然领域应该具有某种影响。这需要自然与自由领域具有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自然是合目的性的,是一个目的论的系统,其最高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意志的自由,以及自由的必然结果——至善。
问题是,我们何以能够以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待自然?“我们在自然界作为感官对象的总和的这个普遍理念中,完全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自然物是相互充当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它们的可能性是只有通过这种类型的原因性才能充分理解的。”[7](P397)要把目的和手段的概念引入到作为感官对象总和的自然界,从而把一种新的原因性(目的论)运用到自然。我们在经验中无法观察到这一点,经验向我们呈现的是机械的决定关系。还有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我们把自然先天地看作合乎目的的。我们需要为这种先天的方式辩护,为目的论找到先天的原则和立法的领域。这里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自然的目的论在人的何种心灵能力(知、情与意)中有其来源;第二,它能够放入批判哲学的先天原则和其立法的领域是什么;第三,这个领域如果不是作为质料的自然,那么,又回到了开始提出的问题,即它何以能够运用到自然之中。
康德认为,自然具有无限多样的形式,我们的感性直观只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直观形式来看待它,然后由知性范畴综合这些感性直观来得到关于自然的知识。我们无法认识自然其他的特殊形式和规律,然而,我们的理性是一种无条件的原则的能力,它试图在偶然性中寻求必然性。反思性的判断力就承担了给这些特殊规律寻找普遍性的职能,确保经验是一个合目的性的系统。当我们从异质的特殊规律中找到了一致性时,我们会感到愉快。相反,如果我们无法把握自然的多样性,自然总是向我们呈现出令人沮丧的或然性,那么我们会感觉到痛苦。由此,自然的合目的性概念与愉快的情感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批判哲学那里,一个有建构性的先天原则是形式的,自然合目的性是质料的,如果要把目的论放入批判哲学体系内,必须找出形式的合目的性的先天原则的范围、界限等。康德恢复了鲍姆加通的ästhetisch的审美含义,为审美领域找到了一条先天的原则——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当我们看到一个美的对象时,我们不需要有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否则这就是知识,只需要对象的形式引起了我们的想象力与知性的协调一致。想象力摆脱了知性概念的束缚,我们感到了直接的愉快。鉴赏判断虽然不以任何概念为基础,但是,它提出了每个人都应当做出类似判断的普遍性要求。这植根于人的共通感。由此,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在人的情感中有其来源,对审美领域是先天立法的,具有建构性的作用。
形式的合目的性在审美领域有建构性的先天原则,然而,康德需要把目的和手段的范畴运用于自然界。借助于艺术的概念,康德实现了从形式的目的论到质料的目的论的过渡。艺术的产生与一个确定的意图相关,然而,美的艺术又不通过任何概念而直接地令人喜欢,“所以美的艺术作品里的合目的性,尽管它是有意的,但却不显得是有意的;就是说美的艺术必须看起来像是自然,虽然人们意识到它是艺术。”[7](P347)通过与艺术的类比,我们有理由把自然看作是合目的性的。
三、终极目的与自然目的论
我们不能够以经验观察的方式来认识自然目的。对事物的评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机械的因果关系,一种是目的论的因果关系。前者是一种作用因,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序列。后者是一种促成作用,作为结果的某物的概念同时又是以之为结果的事物的原因,是一种不断回溯的序列。在目的论的因果关系中,存在着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内在合目的性,结果本身就是目的,可以作为艺术品来看待;第二种是外在合目的性,结果是其他自然存在物的艺术的材料,是一种有用性,也称为相对的合目的性。对自然事物的观察,我们发现,只有先天地确定了某物的实存本身是一个自然目的,它才可以被看作一个外部的自然目的。因为我们说某个事物是其他事物的目的时,这样的关系常常可以用机械的因果关系来解释。比如河流提供了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土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植物是河流与土壤的目的,然而,把这种关系看作自然界本身的机械作用更合适。所以,康德认为:“相对的合目的性尽管对自然目的给出了假设性的指示,却并未使人有权做出任何绝对的目的论的判断。”[7](P405)
为此,我们需要首先确立自然目的的概念。自然目的的概念比艺术的概念要更多。艺术是按照目的的概念产生出来的,它的每个部分都是通过与整体的关系才是可能的。作为自然目的的事物还要求它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它的每个部分都是互为原因和结果的,即它是自组织的。从逻辑上来说,作为自然目的的事物的整体的概念是其各部分的原因;从时间上来说,部分按照其相互的关联的形式交替地产生出作为事物的整体。前者是目的因,后者是作用因,这样,作用因就可以被评判为目的因的手段,机械的因果性从属于目的论的因果性。有没有自然产物是自然目的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产物,那么,自然目的的概念就没有客观实在性。康德认为,有机体就是自然目的的事物,并且给出了相应的论证。有机体的每个部分都是为其他部分及其整体而产生出来的,没有任何部分是白费的。所以,有机体“首先给一个并非作为实践的、而是作为自然的目的的目的概念带来了客观实在性,并由此而为自然科学取得了某种目的论的根据,即按照一个特殊原则对自然科学的客体作某种方式的评判的根据”。[7](P412)
确立了有机物的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外在合目的性运用于自然的系统之中,从而把整个自然界都评价为一个目的论的系统。我们可以认为,植物生长的目的是食草动物,食草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食肉动物提供生存的材料,食肉动物等自然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利用。由此,人是这个自然系统的最后目的。然而,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认为,动物尤其是食草动物的存在是为了抑制植物的过度生长,食肉动物是为了限制食草动物的贪吃,人对自然界的这些存在者的利用是为了保持生态的平衡。这样,人就不是自然的最后目的,在这样的目的论系统中只是处于一个手段的位置。或者从进化论的角度思考,我们会发现,自然界的各种存在根本不能构成一个从低到高的目的论系统,而仅仅是自然缓慢地变化,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机械规律所造成的结果。
康德考虑到了这些问题。他强调,他引入自然目的的概念不是为了促进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因为认识自然是知性的工作,以自然目的的概念来认识自然只会导致理性的狂热。自然目的论是反思性的判断力的调节性的原理,把自然看作一个目的论的系统是为了实践上的运用,是为了认识我们心中的实践理性。当我们的反思性的判断力把人看作自然的最后目的时,人的什么才可以被称作自然的最后目的呢?有两个选择:幸福或者文化。在《判断力批判》第83节,康德对幸福不是自然的最后目的的论证比《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要更有说服力。他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幸福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自然无法制定确定的规律来实现它;第二,与其他动物相比,自然没有特别地优待人;第三,即使自然非常仁慈,让人更加舒适,然而,人自身的相互冲突的非社会性经常把他自己置于灾难的境地。
由此,自然的最后目的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地(因而以其自由)对随便什么目的的这种适应性的产生过程,就是文化”。[7](P465)文化是人设定目的的能力,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必然条件。人的自由在于其意志遵守理性的法则。由于人也具有感性的爱好,他总是会违背理性的法则,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这样,自由首先就在于对感性爱好的独立性,这就是消极自由。由此,康德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自然的最后目的。熟巧虽然发展了科学和艺术,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它加剧了人的不平等,膨胀了人的感性爱好。只有管制的文化才是自然的最后目的。管制的文化是一种否定性的,它“在于把意志从欲望的专制中解放出来,由于这种专制,我们依附于某些自然物,而使我们没有选择的能力,因为我们让本能冲动充当了我们的枷锁”。[7](P465)这种文化只有在公民社会以及世界公民的整体中才可以得到实现。前者是对人的爱好的一种强制性的限制,后者是对国家的无法的自由的一种限制。
对爱好的限制和训练是自然的最后目的,却不是世界的存有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作为它的可能性的条件”。[7](P467)终极目的是自足的、无条件的。何种存在者才是世界存有的终极目的呢?只有作为道德的人才是这样的终极目的,因为他因其意志的自我立法而具有无条件的价值。他能够独立于爱好的规定而把自然界所有存在物都用作手段,赋予这些存在以相对的价值。理性是一种为有条件者寻求无条件者的能力,反思性的判断力把自然看作一个目的论的系统,系统需要有一个无条件者,否则,一个完整的目的论系统就无法建立起来。这个系统的终极目的就是作为本体的人。
区分自然的最后目的(ein letzter Zweck)与世界的存有的终极目的(Endzweck)这一对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然目的论和道义论的关系。前者是在自然的进程中我们使用各种手段可以实现的目的,比如通过法制状态实现对人的爱好的限制;后者是超感性的,外在于自然,仅仅通过自然进程无法实现。在康德看来,自然的最后目的是人真正成为世界的存有的终极目的的必要条件,“但是要发现我们至少可以在人的什么地方放置自然的那个最后目的,我们就必须找出自然为了使他准备去做他为了成为终极目的所必须做的事而能够提供的东西”。[7](P464)美的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虽然没有直接地促进道德的发展,但使人有礼貌和有教养,使人逐渐摆脱本能和感性的爱好,为人性的发展铺平道路。*Paul Guyer在谈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有很深入的见解:“管制的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我们爱好的能力,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在自然中和通过自然的方法发展的、并且使我们的本体的任意的自由在自然世界中有效的能力。康德的观点肯定是以道德律而不是爱好的名义运用我们自由的任意是一个本体的任意,但使它在自然中有效,我们需要通过自然的教育过程和成熟过程管制和控制我们的爱好。”[8](P352-353)我的观点与他类似,即管制的文化是自然目的论的内容,可以在自然的进程中发展出来,终极目的是超感性的,在自然之外,以管制的文化为手段。自然的最后目的不是人成为世界的存有的终极目的的充分条件。人做一个道德的人,实现自由,不能仅仅靠自然的进程来实现,而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意志。如果人的自由仅靠自然的进程就可以实现,那么,自由就不复存在了。同时,世界的存有的终极目的是自然的最后目的的可能性条件,“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终极目的,相互从属的目的链条就不会完整地建立起来”。[7](P468)世界的存有的终极目的使我们可以把自然看作一个从低到高的完整的目的论系统,这个系统的最高点就是人的文化,文化之所以能够是最后的目的,是因为它是实现人的自由及其必然结果至善的必要条件。
自然目的论在时间上先于道德目的论,但是在逻辑上道德目的论则先于自然目的论。我们是出于道德的目的来把这个世界看作一个目的系统的。从道德的视角出发,我们把自然看作以实现人的自由为终极目的的系统,自然与人的幸福是一致的,从而至善可以在自然中实现。我们不禁会追问:谁创造了一个道德的世界?回答是上帝。康德强调这个推论不是出于规定性的判断力,而是出于反思性的判断力。上帝的存在不是一个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出于至善的需要。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上帝是德福一致的公正的分配者,在《判断力批判》中,上帝作为一个道德世界的创造者,使这个世界以实现人的道德为其目的。同一个自然既可以从机械论来看,又可以从道德目的论来看,幸福与道德就是一致的。
我们为什么要实现至善?康德的回答是:“那种必须由我们来实现的最高的终极目的,就是我们唯一因此而能够配得上使自己成为一个创造的终极目的的东西,是一种对于我们来说在实践方面有客观实在性的理念,即一种事业[事实]。”[7](P502)至善是自由的终极目的,只有致力于实现至善,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存有的终极目的,才具有独特的价值。
如果说道德目的论通过引进世界存有的终极目的的概念使自然目的论成为可能,那么,道德目的论与道义论的关系是什么呢?道德目的论是反思性的判断力对自然所作出的判断。与规定性判断力不同,反思性的判断力是为特殊寻求普遍,在运用于自然时,是以自然的客观合目的性作为其原则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纯粹理性诸理念的调节性运用”中谈到了知识的系统化是理性在运用到知识时的一个调节性原则,在《判断力批判》中,为了完成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康德找出了反思性的判断力,并且认为自然的客观合目的性概念“只不过是对于反思性判断力的一条主观的原理,因而是反思性的判断力的一条由理性托付给它的准则”。[7](P433)自然的客观合目的性是理性强加于反思性的判断力的原则,使它承担沟通自然与自由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推出:道德目的论的基础是道义论,我们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看待自然及其目的的。*Weiner Moskopp在谈到康德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时认为:“世界的创造者是道德的。反思性的判断力是按照实践理性的一个概念、而不是按照规定性的判断力的某个概念来进行判断的。”[9](P343)道德目的论是按照实践理性的角度推出来的。
康德的道义论虽然是形式上的,但它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及其必然结果至善为其目的的。自由及至善都是超感性的,何以落实在自然之中,这是康德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判断力批判》中,他把理性的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赋予了反思性的判断力。从自然目的的角度来看,自然是一个合目的的系统,自然的机械作用是发展人的文化的手段,为实现人的自由及至善奠定了基础。由此,自然目的论的驱动是道德目的论,道德目的论的依据是实践理性。
可以看出,康德没有简单地恢复古希腊的自然目的论传统,而是把它放在了实践理性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及《道德形而上学》中自然目的论的位置。当康德在论证具体义务中使用自然目的论的假设时,他的意思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自由以及追求尘世中的至善,我们应当做什么。
参考文献:
[1]刘作.从形式到质料:康德成圣的伦理学[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2]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M].杨云飞译.邓晓芒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Jens Timmermann. Kant′s Groundwork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ommentar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康德. 三大批判合集(上)[M]. 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Kant.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M].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in Hambugr, 1966.
[6]Heiner F. Klemme. Moralized nature, naturalized autonomy: Kant′s way of bridging the gap in the third Critique, in Oliver Sensen (eds.). Kant on moral autonomy [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7]康德. 三大批判合集(下)[M]. 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Paul Guyer. Kant [M].Routledge, 2006.
[9]Weiner Moskopp. Struktur und Dynamik in Kants Kritiken [M].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