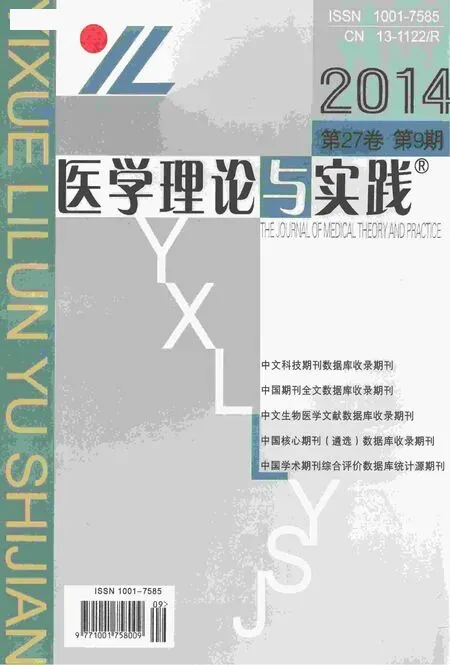缓释化疗在卵巢恶性肿瘤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2014-03-06麦海燕
麦海燕
广西梧州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543000
恶性肿瘤是足以威胁到人类生命的致命疾病,恶性肿瘤带来的不仅是生理上的痛苦,更会伴随着相当大的心理压力、经济负担。因此,对恶性肿瘤的研究从未间断,临床研究者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虽然未能寻觅出治疗恶性肿瘤的特效方法。但不得不承认,恶性肿瘤的治疗技术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化疗作为恶性肿瘤治疗的一线治疗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卵巢恶性肿瘤的治疗中,而对化疗技术研究改进已经进行了20余年,期间各种新化疗方法,新化疗药物剂型层出不穷。缓释化疗属于生物医学工程中的一个新名词,是指使用聚合物基础材料负载化疗药物,使药物按照预定的释放机制持续的释放至机体中,维持性的给予足量药物。该技术不仅使化疗治疗手段丰富化,并且为恶性肿瘤治疗带来了新方向。本文对缓释化疗技术在卵巢恶性肿瘤中的治疗进展进行探讨,现综述如下。
1 缓释化疗材料、药物
缓释材料为缓释化疗的基础,适用的缓释材料并不多[1]。目前常使用的多糖、聚酰胺、聚酸酐、聚酯等均获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2]。并且将其具体分类为多糖和聚酯两大类。其中多糖类具有天然生物降解特性,包括淀粉、环糊精、纤维素、壳聚糖。而聚酯类中包括了聚乳酸以及其共聚物、聚原脂酸、聚酰胺类、聚酸酐类等[3]。聚乳酸以及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是通过一次降解为乳酸和羟基乙酸,第二次通过三羧酸循环,成为二氧化碳和水。聚原脂酸可发生表面降解,为非均相降解机制。将其作为化疗药物载体时,甚至可持续1个月之久,常用于长期给药系统的制备。且由于其对pH值变化具有相应性,适宜制备为口服缓释化疗药物。聚酰胺类具有独特无定型结构,并且浓缩于低温下,作为缓释材料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聚酸酐类可发生迅速的表面降解,小分子给药体系中运用较为广泛,生物相容性也较好。但其可与多种胺类物质在高温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因此多肽、活性氨基药物、蛋白质等药物缓释载体不宜采用[4]。除上述聚酯类缓释载体外,交联聚乙烯吡咯烷酮、烷基取代聚乙烯醇等也可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作为缓释材料应用。
2 药物缓释技术在腹腔化疗中的应用进展
腹腔化疗是较为常规的化疗方式,通过体外配置化疗药剂,通过各种手段,依次、按时的将药物进行腹腔注入,可使药物直接作用于腹腔内癌细胞,对其进行直接杀伤。并且腹腔注入的明显优势在于药剂进入腹腔后,腹腔中药剂浓度远超血浆中药物浓度[5]。化疗药物一般毒副作用较为严重,有效的减轻毒副作用带来的不良反应也非常重要,而腹腔化疗可做到这一点。例如,化疗药物经门静脉进入肝脏中,经过肝脏代谢后,经肝静脉进入循环的药物量极少,带来的毒副作用较轻[6]。并且药物集中在腹腔内,效果较好,因此受到了临床欢迎。但大剂量腹腔化疗也有一定局限性,其通常半衰期较短,难以维持长时间药效。因此,缓释技术的加入在保证了腹腔化疗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对药效持续时间进行了改善,弥补了其不足之处。
腹腔化疗中,缓释化疗药剂的应用应在第一时间进行,并可收到最理想的效果,并且植入部位可选择为瘤床、吻合口、病灶区域内、淋巴回流区等,通过第一时间缓释剂型冲击释放,使短时间内高浓度水平的药剂聚集在局部,并可持续性的保持药效浓度[7]。该治疗方式被运用于胃癌、肝癌、直肠癌、胰腺癌等癌症中,由于卵巢位于盆腔内,盆腔与腹腔相邻,因此腹腔化疗缓释技术也适用于卵巢肿瘤的治疗中。并且根据文献报道[8~10],缓释化疗药剂的运用效果优于常规腹腔化疗,优势主要体现在复发率降低以及癌细胞转移方面,而腹腔化疗的传统优势切口感染少、肝肾功能影响小、骨髓抑制发生率低等优点缓释腹腔化疗一并继承,是一种优秀的腹腔恶性肿瘤治疗方法。
3 卵巢恶性肿瘤缓释化疗研究进展
早在腹腔化疗技术尚未普及前,已有小剂量化疗药剂直接腹腔注射的报道[11],旨在控制恶性卵巢肿瘤患者腹水,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腹腔化疗普及后,卵巢恶性肿瘤的治疗便多了一种途径,并且从理论上讲,腹腔化疗治疗卵巢恶性肿瘤的方式相较于其他化疗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优势体现在局部药物完全达到药效浓度,与癌细胞进行对抗。另一方面,卵巢肿瘤细胞与药物直接进行接触,药物对肿瘤的渗透增加[12]。并且腹腔注射进入血循环中药物浓度极低,带来的毒副作用相对较小。而卵巢恶性肿瘤向肝转移病例较多,腹腔化疗通过门静脉进行药物吸收,可对癌细胞肝转移进行预防或者治疗,为一举多得的治疗方式。
5-Fu缓释剂型为卵巢恶性肿瘤缓释化疗的常用剂型。随着研究较为深入,临床采用了许多种药物进行对照观察。5-Fu作为老一代的抗癌药物,应用了近40年时间,曾一度成为消化道恶性肿瘤首选治疗药物[7]。由于其半衰期仅为3.8h,持续对抗癌细胞能力不足,并且大剂量的给药带来的全身性毒副作用较为严重,后被联合化疗方案所取代[13]。但缓释技术的运用,使5-Fu这种老一代抗癌药物重新走上了为患者服务的道路。缓释剂型5-Fu采用数枚5-Fu药用微囊,并利用膜层技术以及高分子骨架控制5-Fu释放[14]。在5-Fu缓释剂型植入体内后,前期快速释放,达到冲击浓度后,随着体液逐层深入,对微囊内药物进行溶解,形成浓度梯度,促使药物稳定向外释放,并且药效持续时间完全有膜层数控制,药代动力学特性良好[15]。与5-Fu类似的缓释剂型还有缓释阿霉素、缓释甲氨蝶呤、缓释丝裂霉素、紫杉醇凝胶注射型等[16]。发展至今,缓释化疗运用与卵巢恶性肿瘤治疗中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17],一般采用600mg 5-Fu缓释剂型植入,保证靶点病灶区域药物浓度,该剂型一般可维持15d,甚至以上。因此无需连续用药,较为方便,可减轻患者的痛苦。而缓释剂型的植入可拖延术后癌细胞扩散转移速度,该方法带来的毒副反应较低,患者术后采用该方法可得到良好的恢复及调养。且可于28d开始进行全身性化疗治疗,患者可更好的耐受全身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综合多方文献进行总结[18~20],5-Fu缓释剂型的安全性可得到保证,患者术后几乎不会出现吻合口瘘、切口感染、肠梗阻等并发症,并且全身性不良反应如骨髓抑制、肝肾功能损害也未发现。因此为一种较为可靠且安全的治疗方法。
缓释化疗优势较为明显,但虽然缓释药剂植入以后,局部区域维持较长时间的化疗药物浓度,帮助清除手术切除不能及的病灶、微小的病灶转移、脱落肿瘤细胞。但其是否对患者复发时间有延迟作用还尚未可知。缓释化疗技术临床运用时间尚短,并且卵巢恶性肿瘤患者集中复发于初次治疗后2~4年间,时间跨度较大,而缺乏大基数的研究样本。因此,大多数文献报道中[21,22],缓释化疗后,患者复发时间与常规腹腔化疗后患者复发时间进行比较,未显示出统计学差异,仅个例表现出的显著性,尚不足以说明缓释化疗对卵巢肿瘤患者局部复发有明显改善作用。患者发生的远端转移亦是如此。因此缓释化疗对患者近远期疗效、生存率的影响还有待继续研究。
4 小结
目前卵巢肿瘤的治疗方式以手术治疗为主,但手术治疗无法根治恶性肿瘤,数年内患者仍会面临复发或转移的不良结局。因此,在术前、术中、术后的化疗药物辅助治疗已成为目前必要的治疗方法,可提升手术效果,推移复发或远端转移,为患者带来更高的生存率。但化疗药剂通常维持时间较短,连续给药会为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因此缓释技术的运用较好的解决了这一临床难题。与传统的腹腔化疗相比,优势十分明显,但其应用尚短,一些不足之处尚待研究。希望将来缓释技术的运用会为恶性肿瘤的治疗带来更有利的影响。
[1]鲁景元,韩克.氟尿嘧啶缓释植入剂治疗卵巢恶性肿瘤的远期疗效观察〔J〕.广东医学,2011,32(14):1921-1923.
[2]鲁景元,韩克.氟尿嘧啶缓释植入剂治疗卵巢恶性肿瘤近期疗效观察〔J〕.河北医药,2012,34(3):362-364.
[3]鲁景元.缓释化疗在卵巢恶性肿瘤治疗中的临床进展〔J〕.中国肿瘤临床,2011,38(13):808-810.
[4]王杰.氟尿嘧啶缓释植入剂治疗卵巢恶性肿瘤近期疗效探讨〔J〕.中外医疗,2012,31(29):117-118.
[5]江源,韩克,周怀君,等.术中应用5-FU缓释剂治疗晚期卵巢癌的近期疗效观察〔J〕.医学研究杂志,2013,42(9):113-117.
[6]喻金梅,安云婷,郭晨,等.氟尿嘧啶缓释剂对外生型年轻宫颈癌患者的疗效〔J〕.实用癌症杂志,2010,25(5):489-491.
[7]康卫卫.5-FU-壳聚糖纳米粒的制备、检测及其对卵巢癌细胞的抑制作用〔D〕.西安:第四军医大学,2013.
[8]王云飞.纳米级载药系统在卵巢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J〕.国际妇产科学杂志,2012,39(6):624-626.
[9]王艺,李隆玉,等.5-氟尿嘧啶缓释剂在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妇产科进展,2011,20(8):650-652.
[10]张振宇,浦红,董若凡,等.氟尿嘧啶缓释剂在卵巢癌术中的临床观察〔J〕.江苏医药,2010,36(16):1968-1969.
[11]杨扬,陈振东,吴秀伟,等.氟尿嘧啶缓释植入剂治疗恶性体腔积液的临床观察〔J〕.山东医药,2009,49(12):12-14.
[12]王正冬,周爱明,金根培,等.进展期结直肠癌患者术中行氟尿嘧啶腹腔区域性量化缓释化疗的效果观察〔J〕.山东医药,2012,52(27):84-85.
[13]梁寒.进展期胃肠腹腔缓释化疗的研究进展〔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10,25(12):1039.
[14]王琦三,尹东,金博,等.进展期胃癌术中区域性缓释化疗临床效果观察〔J〕.山东医药,2012,52(7):79-80.
[15]高岩,刘文志,郑瑞新,等.结直肠癌术中动脉灌注化疗联合腹腔内间质缓释化疗的临床应用〔J〕.中国医师进修杂志,2011,34(35):36-38.
[16]Raveendran S,Poulose AC,Yoshida Y,et al.Bacterial exopolysaccharide based nanoparticles for sustained drug delivery,cancer chemotherapy and bioimaging〔J〕.Carbohydrate Polymers,2013,91(1):22-32.
[17]Adur J,Pelegati VB,Costa LF,et al.Recognition of serous ovarian tumors in human samples by multimodal nonlinear optical microscopy〔J〕.J Biomed Opt,2011,16(9):096017.
[18]FauvetR,Brzakowski M,Morice P,et al.Borderline ovarian tumors diagnosed during pregnancy exhibit a high incidence of aggressive features:Results of a French multicenter study〔J〕.Ann Oncol,2012,23(6):1481-1487.
[19]Veyer L,Marret H,Bleuzen A,et al.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ovarian tumors using pelvic contrast-enhanced sonography.〔J〕.Journal of Ultrasound in Medicine,2010,29(7):1041-1049.
[20]郑瑞新,刘文志,高岩,等.动脉灌注化疗联合腹腔内间质缓释化疗在胃癌根治术中的临床应用〔J〕.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2012,26(10):1013-1016.
[21]陈章兴,戴益琛.缓释化疗粒子与三维适形放疗治疗晚期直肠癌的疗效比较〔J〕.临床军医杂志,2011,39(5):902-904.
[22]田小林,朱小宝,庞凌坤,等.术中植入氟尿嘧啶缓释剂对进展期结直肠癌患者血清CEA、CA199的影响〔J〕.海南医学,2010,21(24):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