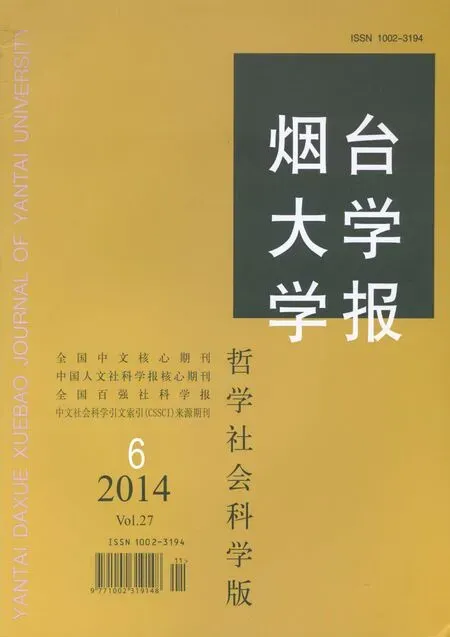耐人寻味的沉默与友善
——论“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胡秋原的态度及其原因
2014-03-06张景兰
张景兰
(淮海工学院 文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1930年代初的左翼文坛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辩,当时被称为“文艺自由论辩”,是一场理论内涵丰富、影响广泛的文艺论辩。研究者一般把“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一概而论,对他们的评价也经历了1980年代之前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1980年代以后视为左翼的同路人乃至友人的变化。但仔细考察历史会发现,左翼理论家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基本上是视胡秋原为敌人而视苏汶为同路人乃至友人的。就在左翼理论家与胡秋原、苏汶展开激烈论辩的时候,鲁迅并没有及时介入,而是到论争发生10个月后的1932年10月10日,才在冯雪峰的邀请下发表了《论“第三种人”》,开头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①《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0页。
有研究者认为,“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是指胡秋原的,鲁迅对胡的性质判断较之对苏汶带有更加严厉的政治批判意味。究其原因,则归结于鲁迅与左联团体的保持一致和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错误判断。②秋石:《胡秋原与鲁迅的论战与纠葛》,《粤海风》2008年第5期。近来学界认为“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指给鲁迅写信的托派陈仲山,并非指胡秋原;“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确系指胡秋原,但事出有因,因为胡主编的《读书杂志》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其老板系国民党十九路军创办人陈铭枢,鲁迅误以为胡与军阀之间有扯不清的关系。因为鲁迅自“4·15”广州清党后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政治立场“向左转”*张宁:《同途·殊途·同归——鲁迅与胡秋原》,《文史哲》2012年第6期。。
但一个事实被忽视了:与左联主要理论家火力强大地密集论战胡、苏不同,作为左翼精神领袖的鲁迅陆续发表了正面回应苏汶的《论“第三种人”》、《再论“第三种人”》等系列文章,但对胡秋原却从未直接提及。而且,就在左联团体停止对胡、苏的论争后,鲁迅对后期“第三种人”却给予了持续关注和严厉批判,对胡秋原则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态度:一是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刊出对胡秋原实施人身攻击和辱骂的诗作《一个汉奸的自供状》后,以为人熟知的“鲁迅”之名(这一时期鲁迅大多用各种其他笔名发表文章)发表了著名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给予批评,并因此还受到左联内部一些成员的攻击*孙郁:《被亵渎的鲁迅》,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二是当论辩结束后,鲁迅专门委托冯雪峰给胡秋原送去了一帧“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照片——这是苏联友人刚刚送给鲁迅的,鲁迅将其送去照相馆经精心翻拍后,赠送给胡秋原。也就是说,鲁迅不仅没有正面批判胡秋原,而且在事后表示了对胡的友善态度,这是一个耐人寻味而又未被充分重视的历史事实。那么,如何理解鲁迅对待胡秋原的态度及其与左联主流理论家的差异?这只有从胡秋原在论战中所表达的文艺思想的诸多合理性、与鲁迅的文艺观在某些方面的相通性上,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在1930年代初政治斗争尖锐、庸俗社会学文艺观盛行的左翼文坛中,这一差异也显示出鲁迅卓尔不群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
一、关于思想和创作领域的自由
以往的许多相关研究往往把左翼文坛与胡秋原的论争视作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体现出二元对立的政治逻辑和思想方法。但事实上二者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对立,左翼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完全一致。
自称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就是“自由”,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左翼主流理论相背离,但他的文艺理论资源和方法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自称“自由主义态度与唯物史观方法”。胡秋原被左翼文坛过激反应的“自由”其实首先是对国民党当局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党治一统的批判否定,是对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提倡和争取。他在文章中反复批判国民党当局炮制的民族主义文艺,称其是新的法西斯主义文学,指斥“民族文艺家凭借暴君之余焰”,“残虐文化与艺术之自由发展”,“是特权者文化上的‘前锋’,是最丑陋的警犬,它巡逻思想上的异端,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之自由的创造。……他们所标榜的理论与得意的作品,实际是最陈腐可笑的造谣与极其低能的呓语,毫无学理之价值,毫无艺术之价值。”*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第7-8页。可以说,胡秋原对民族主义文艺的强烈抨击和同时期左翼方面如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与运命》、瞿秋白的《屠夫文学》、茅盾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在批判程度上是不相上下的。但同时,他也反对一切政治党派包括左联背后的共产党利用文艺之力来助政治之功,他说:“我所谓‘自由人’者,是指一种态度而言,即是在文艺或哲学的领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但不一定在政党的领导之下,根据党的当前实际政纲和迫切的需要来判断一切。”*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01页。胡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方法来解释文艺现象和社会历史现象的,但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党派利用和干涉文艺,坚持文艺的独立自由,是一种非政治的文艺观。
而作为左翼文学精神领袖的鲁迅,正如瞿秋白在《鲁迅杂文选集序言》中所指出的,他是“反自由主义”的,他的反中庸、反调和、“痛打落水狗”、主张“火与剑”式的彻底斗争精神,与30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改良、宪政的自由主义者格格不入。他加入左联,和创造社、太阳社成员联合起来,是想“造成一条阵线”——政治文化阵线,向以血腥屠杀起家的国民党当局和旧社会旧文化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然而,在现实政治层面主张彻底革命的鲁迅,在思想文化、文学创作层面却也是个“自由主义”者。无论是留日时期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与“立心”思想,还是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提倡个性自我,同情绥惠略夫式的“个人的无治主义”,以及左联时期既和左联领导者们在政治上合作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批判思维,乃至和左联后期领导者分道扬镳,都表现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品格。
在主张思想自由、创作自由方面,鲁迅对胡秋原的自由论有着思想共鸣的基础和可能。关于创作自由,胡秋原说:“左翼批评家尽可站在马克斯主义观点,分析他们的作品,但是作家有表现他的情思之自由,而批评家不当拿一个法典去限制他们。只看他们表现得真不真(即是不是真正生动的现实),不要勉强他一定要写什么,怎样写。”*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98页。胡秋原强调创作的真实性原则、尊重创作自由,反对以理论框框乃至政治框框去要求作家,这与鲁迅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对左翼文学青年沙汀、艾芜就创作题材问题的答复是一致的:
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鲁迅全集》第4卷,第362页。
在这里,鲁迅和胡秋原的出发点都是尊重作家的生活经验和创作自由,遵循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正是鲁迅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使他根据现实感受和思想逻辑选择和支持左联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同时,他又始终没有成为任何具体的政治组织和理论的盲目服从者,他从不真正“听将令”。而在此点上,年轻的胡秋原在精神气质上和鲁迅不无相通之处。
二、关于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与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受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中国的左翼理论界普遍存在着庸俗社会学文艺论调,无限强调和夸大文艺的阶级性和社会政治功能,简单地将文学作品作为政治斗争的宣传工具、武器和留声机,包括瞿秋白、冯雪峰等一些具有反思能力和思想弹性的左联优秀理论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瞿秋白就明确提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93-94页。郭沫若、成仿吾等受苏俄“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波格丹诺夫的“组织理论”影响,称文艺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和“超越生活”。胡秋原指出:“以为文艺可以改造世界,这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见解,是以为口中念念有词就能致人于死地的原始巫术崇拜者。……对于文艺之社会机能,不能估得过高,正如不能估得过低一样。……我不是否定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但不可夸张,还原到‘意见支配世界’的观念论,而回避了实际的政治斗争;神游于普罗意识中,创造两篇温室普罗文学,便以为在革命事业上尽了万钧之力。”*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12-213页。在政治斗争尖锐激烈、马列主义思想广泛传播而又鱼龙混杂的1930年代初,庸俗社会学文艺思想被中国左翼理论家们未加反思地接受和传播着。胡秋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对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所作的理解是理性而中肯的,其对左联理论家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同时也与左联前后的鲁迅的文艺观相通。
在1928年创造社扛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旗时,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鲁迅全集》第4卷,第81页。他批评创造社夸大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论调:“这是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鲁迅:《壁下译丛·小引》,《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鲁迅既认为文艺具有阶级性,但反对唯阶级、唯政治的文艺观;他认同文艺具有宣传作用,也看到其有限性:“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吓跑了。”胡秋原关于文学的社会机能“不能估得过高,正如不能估得过低一样”的看法和鲁迅非常相近。鲁迅和胡秋原都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而认同文艺的阶级属性和社会政治功能,但又反对将其夸大到不适当的位置。在左联成立之初,鲁迅又针对一些左翼青年存在的脱离社会实际而只强调思想意识的“奥伏赫变”(突变)问题提出告诫:“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可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谈彻底的主义。”*《鲁迅全集》第4卷,第226页。这也和胡秋原的“温室普罗文学”说相一致。
胡秋原与鲁迅在文艺观上的相通还源自他们都受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父普列汉诺夫的影响。30年代初,左翼文坛受到苏联对普列汉诺夫的政治批判的影响,进而对其艺术理论也持否定的态度。冯雪峰就认为:“朴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是有许多不正确的,特别是同样地渗进艺术理论中去的他的门雪维克(孟什维克)的观念的要素……他对于艺术文学的阶级性的理解是机械论的,是取了机会主义态度的,对于艺术文学的阶级的任务的认识,是并非坚固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来的。”*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59页。瞿秋白也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已经包含着客观主义和轻视阶级性的成分,也包含着艺术消极论的萌芽”。*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84页。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接触开始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期间,他有一段为人熟知的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鲁迅正是从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开始,逐步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左联时期,鲁迅也看到了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变化、与列宁的分歧,但并未因此而对其文艺理论的价值加以否定。1930年6月,鲁迅在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了为普列汉诺夫论文译本而写的长篇序文,客观地介绍了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历程和普氏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及其文艺观,指出:“蒲力汗诺夫对于无产阶级的殊勋,最多是在所发表的理论的文字,他本身的政治的意见,却不免常有动摇的”,但“他的艺术论……不愧称为建立了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的美学的古典的文献”。*《鲁迅全集》第4卷,第254页。
胡秋原早在1927年就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的还是外文原著。在1929年留学日本后的几年里,为撰写七十万字的《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汗诺夫艺术之研究》一书,胡秋原几乎是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在与左联的论争中,胡秋原主要依据普列汉诺夫对于文艺起源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和文学借社会心理而体现阶级性这一观点,反对左翼理论家把文学的阶级性狭隘化、简单化。针对瞿秋白所说“反映某一阶级的生活,就是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他指出:文学作品的阶级性表现常常需要借助中介即社会心理,而同一阶级,又有不同的集团的意识形态,有阶级斗争,也有阶级同化,有阶级的忠臣也有阶级的逆子,“文学上阶级性之流露,常是通过复杂的阶级心理,社会心理,并在其中发生‘屈折’的。”*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99-200页。就文艺论文艺,胡秋原关于文学借社会心理而体现阶级性,指出文学所反映的阶级性有着复杂的情形,这显然比左联理论家的描写哪个阶级的生活就是赞助那个阶级的说法更符合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规律。可以想见,胡秋原对文学阶级性的更加严谨合理的解释、对文学创作及其发生社会影响的规律的认识和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鲁迅更能取得思想观点上的共鸣。我们虽没有看到鲁迅正面回应胡秋原的文字,但从鲁迅赠送胡秋原以普列汉诺夫照片一事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同样汲取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胡秋原的认同和友善。
三、政治态度与文艺思想的关联与错位
必须指出,胡秋原与鲁迅的相同和相通仅止于文艺观层面,类似的观点与话语背后其实包含着不同的意图:鲁迅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和社会现实持积极介入和批判抗争的态度,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意在提醒左翼青年要接触真正实际的社会斗争,而不是关在玻璃窗内空喊革命口号;而胡秋原虽然也是从1927年的大清洗中侥幸逃离,但在30年代初他对现实政治斗争取疏离的态度,尽管也批判统治当局的扼杀思想自由,但却是在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立场——自由立场。这种“自由”虽然非胡适式的自由主义,但也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左翼主流政治话语相左。胡秋原始终以自由为盾牌抗拒一切现实政治力量对文艺的干涉,固守艺术本位论,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炮制的民族主义文艺的批判也只是基于艺术本位而非政治批判。所以,瞿秋白当时就指出“他(指胡秋原)正是要求他们‘勿侵略文艺’,他并不去暴露这些反动阶级的文艺怎样企图捣乱群众的队伍,怎样散布着蒙蔽群众的烟幕弹……”*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83页。总之,胡秋原是在回避、远离现实政治斗争的基本态度下对艺术独立的维护,而鲁迅是在用文艺介入社会政治斗争前提下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性。
但在那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政治环境中,广大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并非如某些左翼理论家们所认为的“不革命即反革命”,也并非因为“不革命”而一无可取。胡秋原所持“自由”的政治立场属于80年代以后许多研究者所说的“同路人”(非革命者,但对革命持旁观和同情的态度)一群,1933年他因参加对抗蒋介石政权的福建“闽变”而被驱逐,流亡欧美各国,并在1935—1936年受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协助王明、李立三编《救国时报》和《全民月刊》,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的起草。还因为其工作的出色,王明曾多次劝其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漱菡:《胡秋原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而鲁迅早在30年代就表达了对“同路人”知识分子的态度:“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1页。鲁迅对待胡秋原的态度正体现了其宽广胸襟和思想独立,与左翼主流理论家们的“唯我独革”的排他性形成对照。
如前所述,胡秋原与鲁迅虽然在政治态度和立场上有明显的不同,但在文艺思想方面有着诸多的相通和呼应。而且,这种相通和呼应由来已久。早在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之时,还是复旦大学学生的胡秋原就以冰蝉为笔名于4月16日《北新》半月刊上发表了长文《革命文学问题》,表达了许多与鲁迅的社会认识、文艺思想有着深刻共鸣的观点。如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认识,胡秋原指出:“正义已不知死了多少年,劳苦民众号哭呻吟遍满全国,青年在绝望痛苦的深渊,红的血涂满了整个的中华;而另一方面,豺狼虎豹在人肉的筵席上,高唱凯旋之歌,叭儿狗和狐狸在旁笑眯眯的喝彩。……”*冰禅(胡秋原):《革命文学问题》,《“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1页。胡秋原对1928年前后的社会现实的黑暗的认识和革命文学倡导者们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的调子完全不同,与鲁迅对现实的感受“杀人如草不闻声”如出一辙,而且,在用语上也明显受到鲁迅的影响。对于创、太二社的革命文学论调,鲁迅着重针对他们的言行对比,发表《文艺与革命》讽刺他们“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鲁迅全集》第4卷,第94页。,在稍后发表的《路》中批评他们的排他性思维:“口头不说‘无产’便是‘非革命’,还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危险了。”*《鲁迅全集》第4卷,第85页。鲁迅当时认为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只是坐在咖啡厅里谈革命文学、“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鲁迅全集》第4卷,第82页。“欢迎喜鹊,憎厌鸱枭,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鲁迅全集》第4卷,第100页。。再看胡秋原,面对热闹一时的“革命文学”,他一方面认为其是“混乱而麻痹的中国的一帖兴奋剂,是萎靡锢蔽的中国文坛的一种新鲜的活力”,但反对排斥抹杀一切“非”革命的文学和文学家,仿佛所有“不革命文学”,都只应该“扔到茅厕里去”的偏激排他态度,指出:“文艺家是时代精神的灵魂,是社会民众的喉舌”,但如果“先树立一个文学的格式,以为没有革命的字样就一无足取,大家也就嚷着‘革命’‘革命’,反而没有看出社会痛苦之真象,也是一样的失去了文艺底真意义之所在了”*冰禅(胡秋原):《革命文学问题》,《“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340页。。这些表述与鲁迅的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
对于创、太二社把劳工(无产)阶级政治上神圣化和道德上理想化,胡鲜明地表明了异议:“不过还有一件在我们同情于工农阶级的痛苦时所万不能忘记的,就是几千年我们不肖的祖宗所遗留累积于我们民族底恶劣的根性和思想。中国之所以陷于近来这样的一个混乱可怕的境遇里,固然也是社会制度的罪恶,而使这个混乱尽量发挥它的罪恶与延长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底寿命的,就不能不说是我们祖传的凶残卑劣,懒惰贪婪的劣根性,以及布满于一般民众的升官发财的思想了。”胡秋原还针对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指出:“阿Q的时代不独还没有‘过去’,就是最近的将来还不会‘过去’……”*冰禅(胡秋原):《革命文学问题》,《“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342页。在革命文学倡导者高举大旗、集中攻击和否定五四文学主将鲁迅时,年轻的胡秋原敢于发出不同声音,表现出深切的现实感和出色的理论素养,其对文学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功能的强调,可谓深得鲁迅启蒙思想的精髓,是对鲁迅文学作品和思想观点的深察洞见。
在政治斗争尖锐严酷的1928-1930年,左翼理论家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的虔诚信仰,深受苏联庸俗社会学文艺思想的影响,难以避免地存在着把文艺作为宣传和战斗工具的政治实用主义思维,使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打上明显的庸俗社会学的烙印。在政治工具论成为主导文艺思想的左翼文坛,鲁迅秉持着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强调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鲁迅的著名话语:“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鲁迅全集》第4卷,第81页。,就是在政治革命的大潮中坚守文艺的主体性。作为左翼文坛精神领袖的鲁迅,虽然在政治态度上旗帜鲜明地站在被压迫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化阵营,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他始终保持着一份深刻的清醒和独立,始终重视和尊重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性和创造性,尊重作家的个性和创作自由。
而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一方面是对国民党统治当局行专制统治、扼杀思想和文艺自由的批判,同时也表达了反对一切政党包括处于被压迫的共产党对文艺的利用,其政治态度和鲁迅有着明显不同,但二者的文艺思想和精神气质却不乏相同和相通之处。这一时期,胡秋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受西方启蒙主义传统的影响,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不受任何权威偶像支配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反对知识分子依附任何政治党派,认为单纯的留声机观念在逻辑上取消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所以,他讥讽左翼批评家是“无产阶级的狗”,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狗”是“万狗打架”,“不是主人的写文章者之流,其为狗则一也”*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04页。。这种言论虽然过于尖刻,但从其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的逻辑出发,又是必然的结论。
总之,在“文艺自由论辩”中,胡秋原主张的文艺创作、思想领域的自由,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辩证看法,对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的接受和运用,启蒙文化观以及敢于怀疑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等,都表现出与鲁迅思想和精神气质的共鸣与相通。其对左翼理论家的某些偏颇幼稚的文艺论述的批评,大都切中要害,对左翼文艺理论具有一定的纠偏补充的意义。但在政治斗争主导文化领域、左翼文艺饱受压迫摧残的1930年代,敏感的政治应激思维和马列主义的思想文化逻辑,使得左翼理论家们对胡秋原的文艺观点往往做不到冷静思考、理性回应,而鲁迅对胡秋原与左翼理论家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的论战保持沉默和事后友善态度正体现了他卓尔不群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在30年代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这种政治态度和文艺观点的关联与交错现象具有典型性,那种非此即彼、“唯我独革”的排他性思维和做法的错误和危害也早已被历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