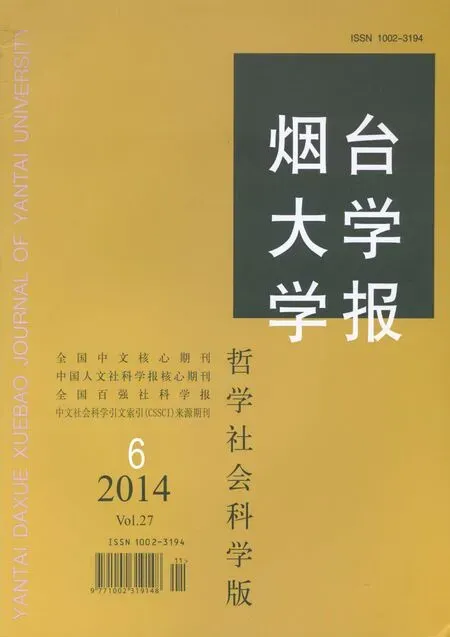论唐前期节度使僚佐的辟召与迁转
——以科举学历拥有者为中心的考察
2014-03-06杨鑫
杨 鑫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节度使制度作为有唐一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不仅对唐代的政治、军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事实上也构成了唐代官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士人的入仕、迁转等密切相关。因而,学界历来对此有较多的关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严耕望先生的《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张国刚先生的《唐代藩镇研究》、石云涛先生的《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等。此外如戴伟华先生的《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著作对相关问题也有所涉及。但总的来说,由于藩镇对唐王朝的政治、社会的影响更多发生于安史之乱之后,因而学者在研究时也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这一时期,而对唐前期方镇的考察则显得比较薄弱。事实上,与唐后期的藩镇割据相比,唐前期的藩镇更多是作为皇权常态下的幕府而存在。因而对唐前期藩镇僚佐的考察更能够看出帝国的官僚政治常态下,幕府僚佐在国家的文官制度中的地位。如石云涛先生的《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等著述虽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我们认为仍可以做进一步的深化。而创始于隋的科举制①关于科举制的起源,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亦有学者认为起源于唐。实则这一争议乃由于论者对判定科举起源持有不同的标准所致。相关讨论参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四章,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94页。在唐代的选举制度结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并最终在宋以后成为帝国品位结构中的主干性位阶。②参见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7-418页。若以此为视角来进行考察,也会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地位及其与藩镇的关系,乃至于不同品位序列以及品位与职位间的对应关系的认识。
因府兵制的衰落及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唐王朝于景云二年(711)开始设置节度使*关于节度使的设置时间,参见张国刚:《唐节度使始置年代考定》,收入氏著《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8-171页。。即《新唐书·兵志》所谓:
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新唐书》卷五○《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7页。
王永兴先生则指出,除府兵制之因素外,节度使制的产生与当时亚洲西北部的军事形势的变化也有着密切关系,是唐王朝对吐蕃强盛的一个应对措施。*参见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第96-99页。
有论者指出,节度使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唐前期的行军幕府制度的一个修正与延续。“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5页。另可参考孙继民:《唐代行军统帅僚属制度及其对藩镇形成的影响》,载《河北学刊》1992年第6期。与行军将军的幕府一样,节度使之下也配置了一系列的僚佐。关于节度使下僚佐之设置,《通典》中有较为明确的叙述:
其边方有寇戎之地,则加以旌节,谓之节度使。……本皆兼支使、营田使,开元九年十一月敕,其河东、河北不须别置,并令度使兼充。有副使一人,(副贰使。)行军司马一人,(申习法令。自汉魏至隋,总戎出征,则刺史、都督、将军等官置长史、司马、诸曹参军,为之寮佐,按官置司。大唐本制,大总管乃前代专征之任,其寮佐亦多同之。自后改为节度大使,署副使、判官以为寮佐,如前代长史以下之任。然长史、司马及诸曹是曰官名,副大使、副使、判官乃为使职。有所改易,合随府主。置大使则有副使以下,今若改名,使府不合设官充其寮吏。盖因授任者莫详其源,既有副使,又置司马,参杂重设,遂为其例。况不标于《甲令》,故须区别著定恒规也。)判官二人,(分判仓、兵、骑、胄四曹,副使及行司马通属。)掌书记一人,(掌表奏书檄。……)参谋无员,(或一人,或二人,参议谋画。)随军四人。(分使出入。)*《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95页。括号中文字为《通典》中小字注释内容,本文引用时予以保留。
不过节度使府与行军将军府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行军将军多为执行某一特定的军事任务而设,因而其僚佐也都是临时性的,即选择一些人来充任这一临时的差遣,事罢即各归本职。而节度使由于需要常驻地方,其僚属势必也需要是专职而非临时性的。但是在唐代的制度架构中,节度使本身又是作为一种使职而存在的,这就在客观上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
一、使府僚佐的辟召
在唐后期,节度使幕府已经成为文人士子步入仕途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所谓“唐世士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署为重”*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唐藩镇幕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3页。。如韩愈“寻登进士第。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5页。如王质“元和六年,登进士甲科。释褐岭南管记,历佐淮蔡、许昌、梓潼、兴元四府,累奏兼监察御史,入朝为殿中,迁侍御史、户部员外郎。”*《旧唐书》卷一六三《王质传》,第4267页。又如韦表微,“始举进士第,累佐藩府。”*《旧唐书》卷一八九下《韦表微传》,第4979页。“进士及第后辟从藩府,入朝为清官,这在宪宗特别是文宗以后,成为士大夫迅速升迁、致位显要的主要方式。辟举成为进士及第者青云直上的一条捷径。因此,晚唐士大夫不论喜欢不喜欢做京官,愿不愿外出,都要到地方去担任幕职。因为文宗以后,这已成为升迁的必由之路。”*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3页。
而在唐代前期,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不仅科举及第者中大多数人没有进入幕府,即使是进入节度使幕府的也基本都是在它官任上受到征辟而入幕的,极少有取得科举学历后即直接进入幕府的例子。如寇洋“弱冠应才称栋梁举,策居第一;又试拔萃出类科,与邵升、齐浣同时超等,授魏州昌乐尉,换洛州兴泰尉。……寻转泾州司马,累充朔方军节度判官。”*《唐故广平郡太守恒王府长史上谷寇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27-1628页。又如权皋“少以进士补贝州临清尉。安禄山以幽州长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为蓟县尉,署从事。”*《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第4001页。又如李史鱼,“开元中以多才应诏,解褐授秘书省正字。……拜公殿中侍御史,参安禄山范阳军事。”*《文苑英华》卷九四四《侍御史摄御史中丞赠尚书户部司郎李公墓志》。又如郭豫,“寻以明经擢第,历洺州平恩县尉,左金吾卫兵曹参军……故幕府三辟,时称得俊。”*《文苑英华》卷九六○《咸阳县丞郭君墓志铭》。又如吕諲,“天宝初,进士及第,调授宁陵尉。本道采访使韦陟嘉其才,辟为支使。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充度支判官。”*《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吕諲传》,第4823页。类似的例子非常多。而获得科举学历后直接进入幕府的则只有李叔明等极个别的例子。*《新唐书》卷一二二《李叔明传》云:“叔明擢明经,为杨国忠剑南判官。”见该书第4757页。综上可见,唐前期进入节度使幕府的科举学历持有者大多数都是在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一个级别较低的职位后再进入幕府的,这是幕府的辟召在有唐一代前期与后期的一个重要差别。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我们认为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唐前期,官职候选人与实际官缺之间的员额差距并不大,士人获得科举学历后可以比较容易地被授予官职,因而不必像唐后期的士人那样因获得科举学历后无法出仕而进入幕府。另一方面,节度使府在唐前期的政治活动与制度架构中的地位远不如在唐后期那样重要,因而士人也就不大会选择把入幕作为自己仕途的起点。下文关于唐前期节度使僚佐迁转的考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些入幕者的科举学历彼此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出身于进士、明经、诸科者皆有。还有像郭子仪这样武举出身的。但从数量上来说,进士出身的要稍多一些。而这应当是与明经科出身者在叙阶时优于进士科出身者有关:
谓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叙,以下递降一等,至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降秀才三等。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降一等。若本荫高,在秀才、明经上第加本荫,四阶以下,递降一等。明经通二经以上,每一经加一阶。及官人通经者,后叙加阶亦如之。凡孝义旌表门闾者,出身从九品上叙。*《唐会要》卷八一《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68页。
而制科及第者,“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王文锦等点校,第355页。相关论述并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90-96页。待遇也是比较好的。因而,在唐前期幕府地位并不甚重要的情况下,拥有较好的仕途待遇的明经、制科出身者是不大会将入幕作为自己优先的仕途选择的。
与之相应的,我们可以看到,与唐后期不同,唐前期的科举及第者很少有主动谋求进入幕府的。他们大多是受到府主的赏识而应辟召入幕的。如王翰:
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蒱酒。张嘉贞为本州长史,伟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吾属嘉贞,神气轩举自如。张说至,礼益加。*《新唐书》卷二〇二《王翰传》,第5759页。从其本传文字来看,似不能确定其入幕经历。然《全唐文》卷七〇八李德裕《掌书记厅壁记》云:“《续汉书·百官志》称三公及大将军皆有记室,主上表、章报、书记。虽列于上宰之庭,然本位从军之职。……自东汉以后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于是选,其简才之用,亦金马石渠之亚。况河东精甲十万,提封千里,半杂胡骍,遥制边朔。惟师旅之威容,为列藩之仪表。典兹羽檄,代有英髦。间者吴少微、富嘉谟、王翰、孙逖咸有制作,存于是邦,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戴伟华先生指出其中孙逖可考证为河东从事,疑王翰亦为河东幕僚。见氏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然据李文中“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一句似可断定王翰等四人皆曾于河东节度使府任书记之类文职。并参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7-48页。
又如郭豫:
公讳某字某……居然宏达,寻以明经擢第,历洺州平恩县尉,左金吾卫兵曹参军,明恕贞恪,清廉仁爱,克施于政,政有经矣。故幕府三辟,时称得俊。御史中丞李处古、侍御史崔希逸、节度使张嵩,爰以将命之务諮焉。*《全唐文》卷四二○《咸阳县丞郭君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288页。
又如蔡希周:
公讳希周,字良傅……起就常调,补广平郡肥乡尉,以廉直闻。劝农使崔公希逸连仍辟书,请公为介,奏课第一,改蜀郡新繁尉。而西南之使臣曰:前张公守洁,后张公敬忠。间以裴公观相踵诣部,虚心能,皆以公职事修理,命公为采访支使或兼节度判官。虽连率比更而封章押至,辞烦不获,无地不芳,未有如公之甚矣。*《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员外郎骑都尉蔡公墓志铭并序》,载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07页。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在唐代前期,科举学历持有者进入幕府,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府主对其才能表示出赏识而主动进行征辟的,而非像唐后期那样士人在获取科名后即谋求进入幕府任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前期,还有一些科举出身者是在仕途遇到挫折后才选择进入幕府的。如杨忠昌“横为酷吏王朂所诬陷,贬授雟州登台县尉。剑南节度使、益府长史韦抗奏公为管记。”*《全唐文》卷二三五《唐故朝请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国高都公杨府君碑铭并序》,第1412页。这样例子的存在更加说明在唐代前期,入幕并非科举出身者的一个较为优先的仕途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士人是以比较被动的姿态进入幕府的。显然,这与唐后期的情况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这一差异的存在主要也是由于在唐代前后期士人取得科名后的仕途前景存在较大的不同,同时幕府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已经具有了科举学历,因而士人进入幕府后大多数都是充任判官、掌书记等比较重要的职务。其中尤以任判官者为多。如倪彬“充安西节度判官”,*《大唐故太中大夫守晋陵郡别驾千乘倪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668页。裴宽“为润州参军,刺史韦铣为按察使,引为判官”,*《旧唐书》卷一○○《裴漼传附从祖弟宽传》,第3129页。杜鸿渐“第进士,解褐延王府参军,安思顺表为朔方判官”,*《新唐书》卷一二六《杜暹传附鸿渐传》,第4422页。刘单于安西使府任判官*参见《岑参集校注》中《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二诗。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8-122页。等。虽然在幕府的职位结构中判官之上尚有副使、司马等,但是“与府主负连带责任者,可为府主代押者,皆为判官而非司马、副使,亦以判官实际佐府主处理政务耳。”*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收入氏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193页。任掌书记者如萧昕“初为哥舒翰掌书记”,*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七,见王仲鏞:《唐诗纪事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722页。高适“充(哥舒)翰府掌书记”*《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第3328页。等。掌书记一职在幕府中的权限虽然并不是很大,但是对士人将来的升迁却是很有帮助的。*参见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57页以下。另外一些没有担任这样比较重要的职务,或是任职情况记载不详的士人在幕府中也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能够参与决策的。如郭豫“爰以将命之务諮焉”*《全唐文》卷四二○《咸阳县丞郭君墓志铭》,第4288页。等。由此可以看出,在唐代前期,科举出身者在入幕后大多都会被府主委以重用,并有可能在幕府中获得较好的职位。
在唐前期,节度使府对科举学历持有者的辟召基本上遵循着府主进行辟署,之后再申报朝廷以获得批准的程序。如孙逖“李暠镇太原,表置幕府”,*《新唐书》卷二○二《孙逖传》,第5760页。权皋“安禄山以幽州长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为蓟县尉,署从事”。*《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第4001页。又如李栖筠“迁安西封常清节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摄监察御史,为行军司马。”*《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第4735页。此即白居易所谓的“古者,公府得自选吏属。今仍古制,亦命领征镇者,必先礼聘,而后升闻。”*《白居易集》卷五〇《授柳杰等四人充郑滑节度推巡制》,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49页。这样一种僚佐的辟召上“升闻于朝”的形式,在唐后期的一些割据倾向较强的藩镇中已经无法保证。而唐前期之所以能够基本上确保这一制度的执行,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幕职的署用,保留了前期行军幕府表奏辟署制度,由节帅表荐于朝廷,经朝廷的最后批准方正式任职。”*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117页。相关论述并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134页;孙继民:《唐代行军统帅僚属制度及其对藩镇形成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向朝廷奏报的制度在唐后期受到破坏,而在唐前期却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除了因政治形势变化导致的藩镇幕府与中央的关系变化的因素以外,还与所辟举对象的情况有关。如前所述,唐前期入幕的科举学历持有者绝大多数都是在其他职位的任上而受到辟召入幕的,因其职位的改变,使府需要报请中央予以批准。而唐后期的入幕者,很多情况下是并没有担任朝廷所授予的职位的,因而使府也就可能会不向中央奏报。
二、使府僚佐的品级与迁转
由于节度使本身是作为一种使职而存在,因而其僚佐并未被纳入朝廷所规定的官品等级,没有列于九品三十阶的品位序列。在这种情况下,为标示其品级,便出现了为使府僚佐加以其他官衔的情况。张国刚先生指出:“士人被引入幕后使府即署其为判官、掌书记、参谋等之类的职位,然后再由本府上报中央有关部门请授某官。”*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134页。此处的“某官”所指的即是用以标示僚佐个人级别的官称。唐前期入幕的科举及第者所兼的用以标示个人品级的官衔主要是朝衔和宪衔。如徐浩“张守珪之节制幽蓟,恩冠诸侯,钦承威名,特以幕僚陈乞,优遂其请,授监察御史。”*《全唐文》卷四四五《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彭城王傅上柱国会稽郡开国公赠太子少师东海徐公神道碑铭》,第4542页。吕諲“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奏充节度判官,累兼卫佐、太子通事舍人。”*《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吕諲传》,第4823页。原本被用于确定官员职能权限的职官名号,在此被用于表示幕府僚佐的个人品级,*相关研究参见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118页以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代原本作为临时性差遣的幕府僚佐的专职化及其对于个人品级的诉求,或许也是导致唐宋间标示公共职能的职事官演变为标示个人品级的本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薪俸也是品秩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130页。我们还可以通过对于薪俸的考察来观察节度使府僚佐的品级。关于唐前期幕府人员的薪俸情况由于缺乏记载,不可详尽考知。以下是《唐会要》中关于大历十二年(777)时使府及地方州县官薪俸调整的记载,或可提供一些参考:
其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得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台事李涵、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使、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刘晏、户部侍郎专判度支韩滉等状。厘革诸道观察使团练使,及判官料钱。观察使、令兼使,不在加给限。每月除刺史正俸料外,每使每月请给一百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五十贯文。都团练副使,每月料钱八十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三十贯文。观察判官,与都团练判官同,每月料钱五十贯文。支使每月料钱四十贯文。推官每月料钱三十贯文。巡官准观察推官例。已上每员,每月杂给,准时估不得过二十贯文。如州县见任官充者,月料杂给减半。刺史知军事,每人除正俸外,请给七十贯文。如带别使,不在加限。杂给准时估不得过三十贯文。州县给料。其大都督府长史,准七府尹例。左右司马,准上州别驾例。支给料钱。刺史八十贯文。别驾,十五贯文。长史、司马,各五十贯。录事参军,四十贯。判司,三十贯。参军、博士,各一十五贯。录事、市令等,各一十三贯。县令,四十贯。丞,三十贯。簿、尉,各二十贯。右谨具条件如前。其旧准令月俸杂料纸笔执衣白直,但纳资课等色,并在此数内。其七府准四月二十八日敕文不该者,并请依京兆府例处分。其中州中县已下,三分减一分。其额内厘务,比正官减半。其州县官除差充推官巡官及司马掌军事外,如更别带职,亦不在加给限。敕旨。宜依。*《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第1967-1968页。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使府长贰及其僚佐的薪俸是要略高于地方官的。而在这之后,使府长贰及其僚佐的薪俸待遇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至于会昌,则又倍之。节度使三十万,都防御使、副使、监军十五万,观察使十万,诸府尹、大都督府长史、都团练使·副使、上州刺史八万,节度副使、中下州刺史、知军事七万,上州别驾五万五千,长史、司马五万,观察·团练判官、掌书记五万,诸大都督府司录参军事,鴘赤县令四万五千,节度推官、支使、防御判官、上州录事参军、畿县上县令四万,诸大都督府判官、赤县丞三万五千,观察·防御·团练推官、巡官、鴘赤县丞、两赤县主薄·尉、上州功曹参军以下、上县丞三万,畿县丞、鴘赤县簿·尉二万。由会昌以前,其间世有增减,不可详也。*《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大历十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45-7246页。
可见,到了会昌年间,幕府职位的薪俸已经明显的高于地方州县职位了。此处所述虽然是唐后期的情况,但对于唐前期多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且前引《唐会要》文字中谓“厘革诸道观察使团练使,及判官料钱”,细味其文意,似是对使府职位之薪俸在原来基础上加以整顿限制之意。故此前使府长官及僚佐之收入或在此之上亦未可知。而且唐代地方官之收入本不限于官方所规定的数目,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9页。可以认为,幕府职位的薪俸收入是高于地方州县政府职位的。
在唐前期的科举及第者中,除了少数人之外,大多数在幕府任职者都只是将入幕作为自己仕途中的一个插曲,经历了短暂的幕职后还是会重新回到朝官与地方官的官员序列中去。*唐前期亦有获得科举学历者长期任职于幕府的情况。如段秀实“天宝四载,安西节度马灵察署为别将,从讨护蜜有功,授安西府别将。……师还,嗣业请于仙芝,以秀实为判官,授斥候府果毅。……改绥德府折冲……嗣业既受节制,思秀实如失左右手,表请起复,为义王友,充节度判官。……元礼多其义,奏试光禄少卿,依前节度判官。……又迁试光禄卿,为孝德判官……又奏行军司马,兼都知兵马使……”见《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传》,第3543-3548页。但是类似的情况很少。这样就出现了士人在经历了幕职之后迁转的问题。
如前所述,幕职本身更多被认定为临时性的差遣,其职位并没有被列入朝廷的品位序列。因此,为标示任职者个人的身份、级别,就出现了使之兼任他官的现象。与其本来担任的幕府职位相比,这些用以表明个人品级的兼官更多具有的是品位的意义。从而,幕府中僚佐的迁转也就可以分为品位与职位两个方面。在品位的迁转中,最常见的是其所加宪衔的升迁,*相关研究参见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144-145页。如高适“拜适左拾遗,转监察御史……寻迁侍御史……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第3328-3329页。又如李史鱼“拜公殿中侍御史,参安禄山范阳军事……复授侍御史摄御史中丞,充河南节度参谋、河北招谕使”。*《全唐文》卷五二○《侍御史摄御史中丞赠尚书户部侍郎李公墓志》,第5289页。这是一种其个人品级的升迁,而与所任职务并无太大关系。与个人品级相关的另一待遇是赐服色,如崔敻“以左卫骑曹参军摄监察御史赐绯鱼袋四镇节度判官”。*《大唐宣义郎行左卫骑曹参军摄监察御史赐绯鱼袋四镇节度判官崔君墓志铭》,载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741页。显然,这也是用以调整使府僚佐个人品级的一个重要措施。
以上是有关使府僚佐品位升迁者,下面再来讨论其职位之迁转。石云涛先生认为在唐代前期,使府为入幕之士人提供了较好的仕途前景,使其具有较好地继续升迁的可能。*参见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143页以下。不过基于对唐前期入幕之科举学历拥有者的考察,我们认为这一判断似乎还有可商榷之处。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士人的升迁更多是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所赋予其个人的机遇,这主要应当归于其个人的机遇与能力,而不能够将之作为这一群体升迁的常态。在唐前期的幕府僚佐中,这种情况就表现的比较明显。很多士人有较好的升迁是由于他们在安史之乱这一政治事件当中有较好的政治表现,从而为朝廷授以重要官职。如杜鸿渐:
举进士,释褐王府参军。天宝末,累迁大理司直、朔方留后、支度副使。肃宗北幸,至平凉,未知所适。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关内监池判官李涵谋曰……鸿渐即日草笺具陈兵马招集之事,录军资、器械、仓储、库物之数,令李涵赍赴平凉,肃宗大悦。鸿渐知肃宗发平凉,于北界白草顿迎谒,因劳诸使及兵士,进言曰……及至灵武,鸿渐与裴勉等劝即皇帝位,以归中外之望,五上表,乃从。鸿渐素习帝王陈布之仪,君臣相见之礼,遂采摭旧仪,绵蕝其事。……肃宗即位,授兵部郎中,知中书舍人事,寻转武部侍郎。至德二年,兼御史大夫,为河西节度使、凉州都督。两京平,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荆南节度使。*《旧唐书》卷一○八《杜鸿渐传》,第3282-3283页。
又如萧昕:
及安禄山反,昕举赞善大夫来瑱堪任将帅,思明之乱,瑱功居多。累迁衔部员外郎,为副元帅哥舒翰掌书记。潼关败,间道入蜀,迁司门郎中。寻兼安陆长史,为河南等道都统判官。迁中书舍人,兼扬州司马,佐军仍旧,入拜本官,累迁秘书监。*《旧唐书》卷一四六《萧昕传》,第3961-3962页。
显然,上述几人的较好升迁主要是由于其在安史之乱中的作为,像其中的杜鸿渐更是有劝立之功。这样因特殊事件、特殊行为所带来的升迁更多只能说是体现了其个人的能力以及对政治形势的判断,而对于使府僚佐的群体而言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事实上,大多数进入使府的科举及第者离开使府之后的迁转情况并不好。如寇洋:
寻转泾州司马,累充朔方军节度判官。……拜冀州长史,移贝州别驾。*《唐故广平郡太守恒王府长史上谷寇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
比较寇洋在幕府前后的任职,的确是有所升迁的。但是这种升迁更像是正常的职官序列内的升迁。即如果他不进入幕府,仍很有可能得到这样的升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担任幕职的经历并没有为他日后的升迁提供较大的帮助。又如王翰:
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蒱酒。张嘉贞为本州长史,伟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吾属嘉贞,神气轩举自如。张说至,礼益加。复举直言极谏,调昌乐尉,又举超拔群类。*《新唐书》卷二○二《王翰传》,第5759页。
王翰以进士、制科及第的身份,在离开幕府后只被授予了昌乐尉一职。这只能说是一个很正常的结果。显然其在幕府中任掌书记的经历,并未对其之后的仕宦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又如薛仅:
紫微令姚公、黄门监卢公特奏有学有文、身材拔萃,起家授洪洞尉。刺史萧瑗许以公辅之器,羽林大将军杨敬述持节河西,以才略奏请充管记,秩满,授江阳丞。*《全唐文》卷三六二《屯留令薛仅善政碑》,第2179页。
薛仅在入幕前任洪洞尉,离开幕府后被授予江阳丞。这当然也是一种升迁。只是这完全属于正常的职官序列的中的升迁,其在幕府中任职的经历,似乎并没有在他离开幕府被授予新的职位时,增加他的任职资历以获取较好的职位。
又如杨仲昌:
贬授雟州台登县尉。剑南节度使、益府长史韦抗奏公为管记……乃授河南府河阳尉。*《全唐文》卷二三五《唐故朝请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国高都公杨府君碑铭并序》,第1412页。
杨仲昌在离开幕府后被授予的新职位与入幕前所任的职位基本一样。这也可以说明幕职并不能增加官员的任官资格。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有些官员在离开幕府后获得的职位比入幕前所任的职位会有一定的升迁,但是这种升迁更多的是正常序列中的升迁。即使他没有进入幕府,依然是会获得这样的升迁机会的。因而,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唐代前期,担任幕职的经历并不能构成官员的官资。在其离开幕府系统而重返职官序列时,朝廷并不会因其曾担任幕职而在升迁上给予特殊的优待。即在官员迁转时,担任幕职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够被列入考虑的范围。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这是由于唐前期的节度使府还处在过渡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仍带有着行军将军府的色彩。节度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被当做一种临时性的使职,因而是与常规的职官序列相分离的。从而在士人离开幕府重新转入职官序列时,这段任职经历不被计算在内,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同时,在唐前期,幕府僚佐加朝衔的待遇也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像唐后期那样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这种人员品位结构上的不完善,影响了入幕者官资的计算,进而影响了其离开幕府后的迁转。
三、结 语
在唐代前期,因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在原有的临时差遣性质的行军将军制基础上,出现了节度使制度。不过在唐代前期,节度使制度还是正处于一个逐渐形成的时期。一方面,节度使对于国家政治的参与程度还不能与唐后期相比;另一方面,节度使府的相关制度也还没有充分完善。
由于在唐前期拥有科举学历的候补官员与实际官缺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因而进入节度使府并不是士人的优先仕途选择,这是其与唐后期的一个重要的差异。大多数士人都是在受到府主的征辟后才进入幕府的,而不是主动谋取幕职。但是士人进入幕府后大多会被委任以比较重要的职位,并受到重用。
唐前期的节度使府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质,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对使府僚佐的个人品位的管理上。由于节度使制度本身的使职差遣性质,因此节度使及其僚属是没有属于朝廷职官系列的个人品级的。一方面,在唐前期已经出现了为僚佐加朝衔、宪衔乃至赐服色以标示其个人品级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一种管理使府僚佐品级的方式还并未形成制度。这就导致了在使府僚佐离开使府被授予新的职位时,其所担任的幕职并不能够被计算为个人的官资。
在唐代,府主尽管可以自行征辟僚属,但是却需要中央对所辟举的僚属的个人品级加以批准授予,这就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掾属有了很大的不同。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掾属的高度品位化而现实职能弱化的趋势不同,唐代的幕府僚佐大多是先具有某一职位,再被赋予一定的品位。可以认为,在唐代,幕府僚佐更多是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而存在的。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掾属结构是以品位为其本位的话,那么唐代的幕府僚佐则是以职位为本位的。促成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加强了对于官员构成群体品位结构的管理。降至明清时代,作为幕客的刑名幕友完全被国家排除在了官僚的品位结构之外,品位的缺失也就使得其失去了基于官员的身份性的内在诉求,而完全成为了国家与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参与者、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