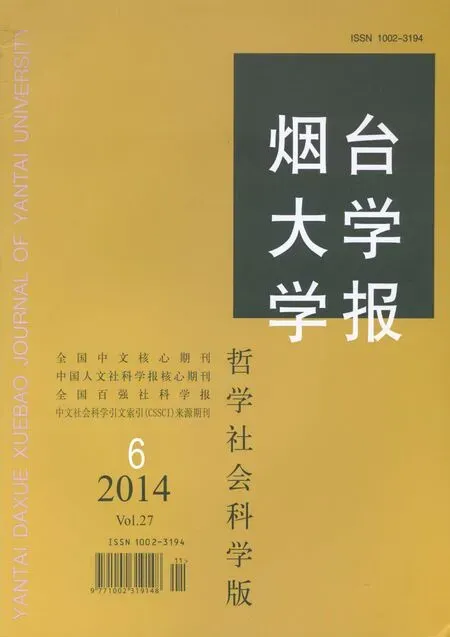古诗:阿阁宫闱背景下的情话
——以曹植为中心
2014-03-06木斋
木 斋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一、本文四个核心关键词的涵义
本文主要有四个核心的关键词:古诗、曹魏、阿阁宫闱和情话,兹分别概说其涵义。
古诗为本文研究的对象,指的是汉魏之际丢失作者姓名也不知其写作背景的诗作,主体为五言诗,也包括一部分这一时期没有作者署名的乐府诗,换言之,指的是狭义的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有关古诗,最为经典的记载,莫过于钟嵘在《诗品上·古诗》下云:“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精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①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1页。根据钟嵘所说,这些失去作者姓名的五言诗作,约有59首。
什么是“古诗”?这近60首的五言诗作都是哪些作品?古诗和一部分没有作者姓名的所谓汉魏乐府诗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需要进行再研究的论题。笔者拟就这狭义的“古诗”问题,进行新一轮的系统梳理。
这些古诗的写作时间,陆机有《拟古诗十四首》,如果我们将所谓《古诗十九首》连同钟嵘所说的诗作视为一体,则“古诗”产生的下限时间不可能晚于西晋,至晚在所谓建安的曹魏时期。更何况钟嵘直接说明古诗的作者“旧疑是建安曹王所制”,因此,不能排除建安曹魏时期,其作者也不能排除曹王。“曹王”,也多有古人直接称之为“陈王”,也就是曹植(参见下文引述)。古诗的上限时间,虽然古人多有枚乘说、傅毅说、苏武李陵说等,但这些说法在梁启超以来,已经基本被否决。笔者自2009年出版《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以及相关系列论文,*相关论文可参见笔者《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论陆机〈拟古诗〉、〈赴洛道中作诗〉等五言诗的写作时间》,《求是学刊》2012年第3期;《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论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1期等。对于古诗产生的时间前限,一一进行排查,彻底否定了其产生于建安十六年之前的可能性。盖因两汉之后的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中后两者在诗歌史上形同虚设,并无五言诗作品流传,而建安这一纪年方式,也不能准确表达包括汉献帝建安到曹魏黄初、太和期间的文学史状况,因此,本文采用“曹魏”这一概念,来表述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时间和空间。2012年暑期,笔者有幸接受台湾中山大学邀请,讲学一年,在此阅读到一些材料,其中《北堂书钞》明确记载《今日良宴会》即为曹植之作,而非一向所说的为曹植“逸文”。赵幼文《曹植集校注·附录一·逸文》中摘引“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两句,并《诠评》说:“《书抄》引为植作,当别有据。”*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44页。赵幼文虽然提出“《书抄》引为植作,当别有据”,但仍然认为可能是曹植的“逸文”,因此,“姑附录以广异闻”。台湾中山大学王清安先生因此将《北堂书钞》全部与曹植相关的诗文进行全面量化整理,整理出来《北堂书钞》总计引曹植诗文72篇(不计入不知篇名与不知文体者与考证非曹植作品《霖雨赋》),共184条,不知篇名与不知文体者22条,不论条目或校语,仅陈禹谟本有引曹植诗文者14条。该文作者逐一检索曹植原作,基本都没有错误,已经可以证明《今日良宴会》即为曹植之作。*王清安:《北堂书钞所载〈今日良宴会〉应可确认为曹植之作》,《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2期。这是本文论题中的第二个关键词:曹魏。
古诗之中,阁台宫闱这一类的宫廷建筑所专有的语汇,屡见不鲜,其中如“阿阁”“章华台”“两宫”“双阙”“重闱”“轩车”“闺闼”等。对于这些建筑语汇,当我在台湾见到元代的《河南志》等文献史料之后,方才真正读懂了这些建筑语汇背后潜藏的意义。这正是本文的第三个关键词:“阿阁宫闱”。
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也同时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建安十六年铜雀台建成之后开始的游宴诗活动,成为了新兴五言诗体写作方式的摇篮,即便在曹魏政权内部,也仅有三曹六子等少数参与游宴诗写作活动的诗人,会写作这种不同于两汉空泛言志的五言诗。曹操在建安十八年开始才被封为魏公,二十二年方才被封为魏王,但曹操自有铜雀台开始,已经具备独立王国的条件,其铜雀台即仿两汉宫廷建制,铜雀台最初的名字就是模仿汉武帝时期的建章宫而为建章台。因此,曹操父子连同建安六子文学创作可以称之为准宫廷的文学活动,为方便论述,将其统归于宫廷文化背景下,以与一向所说的“民间”说在概念上区分。而宫廷文化涵义宽泛,笔者采用“阁台宫闱”这些具体的语汇来指代宫廷文化背景。在笔者视野之下的这些古诗,特别是可能写作于前十年(建安十六年到二十五年)的诗作,显示了浓郁的宫廷文化背景,其中很多涉及宫廷的楼台殿宇。延康、黄初时代的古诗作品,虽然仍然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宫廷文化的气息,但后来之作日益呈现血泪凝结之痛苦,更为注重情感的抒发和呼喊,反而少了宫廷的气息。
笔者此前以十九首古诗为中心的研究中,已经牵涉了很多曹植、甄后之间的恋情关系,指出其中一些作品为两者之间恋情的产物。之后,又发表了对此研究的后续系列论文,以史证诗,反之也以诗证史。*可参见笔者的论文《采遗芙蓉:曹植诗文中的爱情意象——兼论建安十六年对曹植的意义》,《山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论建安二十二年:曹植的人生转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论孔雀东南飞的写作背景》,《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而曹植之作之所以被删除,正由于曹植甄后之间的不伦之恋,不仅为曹氏家族如魏明帝所忌恨,也成为后来史学家、理学家的大忌,这才造成这种奇异的“古诗”现象。笔者当下搜集出来古诗60余首,发现其中关涉恋情的,竟达到五十首左右,占据了“古诗”的绝大多数。这是本文题目的第四个关键词:情话。
冯舒《诗纪匡谬》曰:
乐府起于汉,又其词多古雅,故系于汉:按《宋书·乐志》相和以下诸篇,其无人名者,皆曰古辞,《乐府诗集》灵芝等篇亦然,钟氏《诗品》曰:“古诗之体,源出于国风,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者,疑是建安中陈王所制,则作者姓名既无的定,汉魏之界颇难分。古之云者,时世不定之辞也。昭明所选一十九章,或云枚乘,或云傅毅,概曰古诗,原其体分意亦如此。诗既如此,乐府可知,概归之汉,所谓无稽之言,君子弗听矣。爰及横吹之题,梁清商之题,晋宋齐词,何尝有一定时代而妄作焉。”*冯舒:《诗纪匡谬》,知不足斋丛书之一,台北:艺文印书馆,第3页。
冯舒所论,堪称“匡谬”,可谓振聋发聩,醒人耳目。其论虽首先针对乐府,却涵纳古诗,盖因古诗原本就包含乐府——这些丢失作者姓名的所谓“古诗”,其中一些诗作幸赖乐府的形式加以保存流传,因此,冯舒之论,堪称古人最有创见的“古诗”论。其学术价值主要有:
第一,准确定位了“古诗”的涵义:“古之云者,时世不定之辞也”,而并非必含久远之意,换言之,当陆机写作《拟古诗》,当钟嵘以“古诗”作为一个类别,皆因其为“时世不定之辞”,而“时世不定”,也并非不知其作者和时代,将其称之为“古诗”“古辞”的原因应该是多样的。
第二,古诗的作品,按照冯舒的见解,“《宋书·乐志》相和以下诸篇,其无人名者,皆曰古辞,《乐府诗集》灵芝等篇亦然”,以及“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昭明所选一十九章”(后者应基本在前者之中),皆为这狭义的“古诗”范畴。这一点笔者本文所论之“古诗”,与冯舒所举《宋书·乐志》所陈列者不尽相同。《宋书·乐志》所列之“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也就是一向所说汉魏之际失去作者姓名的五言诗作品,连同部分进入到乐府中篇什,乃为狭义的“古诗”,而《宋书·乐志》随后所说的“吴哥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宋书》卷十九《乐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49页。者,如《子夜歌》等,已经是古诗的第二层引申义,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第三,这些古诗的产生时间和作者:时间方面,冯舒批评了“概归之汉”,“所谓无稽之言,君子弗听矣”,换言之,不仅十九首等不是两汉之作,而且,一向所说的那些两汉乐府诗的优秀五言诗作,也不是两汉之作。之所以归之于汉,一是“乐府起于汉,又其词多古雅,故系于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姓名既无的定,汉魏之界颇难分”。古人经常将曹魏建安时代视为汉末,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汉献帝乃为汉代最后的帝王,建安是两汉最后的年号,这与现代之后认知的建安曹魏为魏晋时代的开端不同。因此,古人将建安之作归并为东汉末年的作品,现当代学者又将古人的这种“汉魏之界颇难分”的记载笼统归并于汉,从而形成所谓十九首东汉说和《陌上桑》等所谓两汉乐府民歌的荒谬说法。关于十九首等诗的作者,冯舒直接指认为“陈王”,“疑是建安中陈王所制,则作者姓名既无的定”。从古人将十九首中的部分诗作“的定”枚乘,到“无的定”,已经是一个进步,为现代梁启超以后定为“东汉无名氏”之作奠定了基础,十九首等古诗的作者年代,无疑是后移了,为后来的建安说开辟了道路。本人这次论证“古诗为建安曹王所制”,有着紧密的学术史继承的源流关系,从钟嵘所提出的原点出发,到冯舒的“匡谬”,再到徐中舒、梁启超、罗根泽、马庸等人的建安曹魏说(其中梁氏之说,徘徊于建安、东汉之间,后人偏取东汉,而成现在的东汉无名氏之说),个人的学识是渺小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加以长时间的艰苦探索,才有了笔者的认知和阐发。
二、宫廷阁闼背景之下的情话
(一)《西北有高楼》之“阿阁”
《西北有高楼》:“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阿阁出现于元代《河南志》所载的洛阳宫城地图中,在《后汉东都城图》中,清晰标明“阿阁”是宫殿名称,位于南宫西侧第三殿,三殿依次为:西宫、长秋宫、阿阁。*徐松辑:《元河南志四卷》,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上海:世界书局,1974年,《后汉东都城图》。此条资料,提供了重要信息:其一,阿阁乃为东汉洛阳宫殿的名称,诗中的人物就是宫廷文化背景之下的人物,不论是歌者还是听者,皆可排除一向所说的民间说或是无名作者;其二,其所发生的地点,应在曹魏的邺城铜雀台。之所以在后汉洛阳宫殿中发现“阿阁”而直接证明为铜雀台,其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元代河南志记载,《元河南志卷二·成周城阙宫殿古迹》下列“阿阁”条:马严《祭蚩尤》:“明帝御阿阁士众”。*徐松辑:《元河南志四卷》卷二,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第4页。因此可知,后汉之阿阁,虽然距离长秋宫不远,但仍然是帝王“御阿阁士众”之政治场所,而非后宫娱乐消遣之所。按照古代严格的礼仪制度,皇帝之前廷,皇帝大臣之政治场所,怎能有“无乃杞梁妻”的女子悲歌弹唱?其次,也非魏晋以洛阳为都城的时代。因为,西晋洛阳宫城图中并无阿阁,同时,陆机拟作古诗,也说明该诗早于西晋,唯一的时间点,正是曹魏的铜雀台。铜雀台是仿造东汉洛阳城的规模体制而修建的,这一点无需论证,乃为常识。至于这首诗作,到底是汉魏晋哪个诗人所作,就要靠此诗提供的其他信息来弥补。从“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来看,其本身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帝王后宫之作。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乃为铜雀台曹植、甄后之作。又,《事类》引《帝王世纪》:“黄帝时白凤巢于阿阁”,*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合集》卷十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00页。应为采用“阿阁”或是“阿”(如秦始皇“阿房宫”)“阁”语汇作为帝王宫殿名称的来源。
曹植《登台赋》说:“连飞阁乎西城”。据潘眉《三国志考证》说:“魏铜雀台在邺都西北隅(见《邺中记》),邺无西城。所谓西城者,北城之西面也。台在北城西北隅,与城之西面楼阁相接,故曰:连飞阁乎西城。”*潘眉:《三国志考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465页。“连飞阁乎西城”之“飞阁”,也就是诗中的“阿阁”,或是以东汉皇宫的阿阁来说铜雀台的“飞阁”。此首“西北有高楼”,也正应该是指铜雀台,而铜雀台也正是曹氏政权宫室之所在,后宫嫔妃居住之所。东汉洛阳宫城中的阿阁,同样在西侧,这是因为,魏晋宫城体制沿袭两汉,后宫皆在西侧。则《西北有高楼》中的女性弹歌者身在阿阁,就说明此一阿阁,并非群臣会聚之所,而是后宫妃嫔居所。《邺中记》载:“铜雀、金凤、冰井三台,皆在邺都北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陆翙:《邺中记》,中华书局据聚珍版丛书本排印本,第2页。
曹植是汉魏诗中记载有关“杞梁妻”的唯一的诗人,如曹植《精微篇》的“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崩”和《黄初六年令》中的:“杞妻哭梁,山为之倾”。*孙星衍辑:《续古文苑》卷五,题为《自诫令》,杨家骆主编:《国学名著珍本丛刊》,1973年,第290页。
细读此诗之风格、语汇、内容,再结合后来《明月照高楼》等篇,则此诗当为曹植于建安二十一至二十二年之间在邺城所作无疑。通过此前对阿阁的辨析,完全能排除此诗为后汉之作,既可排除其为东汉无名氏之下层文人之作,又可排除为东汉宫廷帝王及文人之作,而应该为曹植写作于铜雀台,以阿阁来指称铜雀台。
(二)《涉江采芙蓉》与魏晋洛阳宫城之中的“芙蓉殿”“灵芝池”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建安十七年十月,曹植写作此诗于长江北岸。两者之间盖因“采菱华,擢水蘋”,而发生“弄珠蚌,戏鲛人”的首次突破,采芙蓉、灵芝一类,遂为两者之间的语言暗码。“鲛人”,《艺文类聚》卷六十五“织”条下引《搜神记》曰:“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绩织。”*欧阳询:《艺文类聚》,台北:台湾新兴书局,1963年,第1755页。甄氏平日爱好采灵芝、芙蓉,也爱绩织,因成两者之间戏称之另一语码。另,笔者此前曾经提出,十九首的写作时间,应为211-239年,现在,可以进一步确认,应为212-232年。《今日良宴会》虽有铁证证明为曹植所作,其写作时间,以建安十七年正月为最为合适的时间点。而《涉江采芙蓉》地点、节令、内容,十分清晰。考之古诗其他诗作,其气氛情怀,均在此两首之后。故以此两诗作为十九首之开篇双制,最为详切。另,此诗可与曹植《离友》诗其二(凉风肃兮白雾滋)对比阅读,可谓是一意作两,并皆绝妙。五言诗骚体诗并作同一题材,乃为建安十六年、十七年之风尚。“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与“感隔离兮会无期”,都暴露两者之间不能结合、难以结合的不正当恋情关系,则曹植甄后之间恋情的历史真实,亦不容置疑矣。“寻永归兮赠所思”,永者,长也,也正吻合此次曹植跟随曹操大军东征孙权,长达半载放回魏都之历史实况。《文选》卷二十三《赠士孙文始》诗注“同心离事,乃有逝止”,下注云:“同心离居,绝我中肠”,*萧统撰,李善等注:《增补六臣注文选》,台北:华正书局,1977年,第434页。此四言诗,李善引为张衡《怨诗》,实则应为甄后对《涉江采芙蓉》的回应之作。之所以有曹植或是甄后之作,却引为两汉枚乘、傅毅、张衡、蔡邕等,均应为明帝处理曹植文集的结果。《文选》卷二十四在嵇康诗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句下李善引“愿言不获,终然永思”,作为张衡诗句,同应为甄后回复《涉江》之作。两处合一,则正为《涉江采芙蓉》之“同心而离居”与曹植《离友其二》之“寻永归兮赠所思”。甄后在建安十六年的骚体诗句和十七年的四言诗句,正可见出甄后由两汉传统的骚体、四言学起的渐进痕迹。以上两首皆不见全貌,不知道是否亦在“古诗”之列,兹暂不列入。
曹魏洛阳宫殿中,有名为“芙蓉殿”“灵芝池”者,皆当与甄后有关。“芙蓉殿”见《元河南志》卷二,“芙蓉殿、九华殿、承光殿”条下:“三殿见《洛阳宫殿簿》”。*徐松辑:《元河南志四卷》卷二,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两者出现于《洛阳西晋京城》图,“芙蓉殿”和“灵芝池”均在洛阳宫殿西部,位于九华殿之下,左邻西堂。*徐松辑:《元河南志四卷》附地图,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对比同在该书所附的《后汉东城城图》,*徐松辑:《元河南志四卷》附地图,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这两座建筑均无。灵芝池,文帝“黄初三年穿”,*徐松辑:《元河南志四卷》,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见《魏城阙宫殿古迹》分类之后第3页第一行。黄初三年为甄后死后之翌年,曹丕为甄后所建,芙蓉殿所建时间待考,但仅见于《洛阳西晋京城》图,西晋延续曹魏洛阳宫室,曹叡为其生母甄后所建造无疑。曹叡还建有渭阳馆:“明帝为外祖母甄氏筑馆,侍中缪袭曰: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为名。”*徐松辑:《元河南志四卷》,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见《魏城阙宫殿古迹》分类之后第3页。另,埋葬甄后之地,至今名为“灵芝村”,邺在南北朝北周时代,被改为“灵芝县”,*《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谯郡》云:邺,东魏都。后周平齐,置相州。大象初县随州徙安阳,此改为灵芝县。开皇十年又改焉。亦可再证。
(三)《今日良宴会》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此诗为曹植所作,证据甚多:(1)如前所论,《书钞》中的明确记载,缪钺:“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二句,在《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篇中,《北堂书钞·乐部·筝》中引为曹植作,当别有所据。故《古诗》中是否杂有曹植之作,虽难一一确考,然就上引两事观之,可见昔人视曹植诗与《古诗》极近似,盖二人(指曹植与十九首作者)撰作之途径与态度相同也。*缪钺:《曹植与五言诗体》,《缪钺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1页。逯钦立:“此诗书钞引作曹植诗,当有所据。《诗品》谓古诗旧疑是曹王所著,为说与《书钞》合。”*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年,第330页。胡怀琛:“子建、仲宣作,不肯自承。所以他人不知。”*胡怀琛:《古诗十九首志疑》,《学术世界》1935年第1卷第3期。(2)诗中之“令德”,与曹植其他诗作对曹操(孟德)的称谓吻合。曹植《登台赋》:“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曹植《赠丁仪王粲》:“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声。”李注:“德声谓太祖令德之声也。”*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4页。曹植《橘赋》:“夫灵德之所感”,赵幼文注释:“灵德,象征曹操恩德”,*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61页。“灵德”与“令德”同。传为苏李诗中的“令德”“明德”,如《烛烛晨明月》中的“愿君崇令德”,《携手上河梁》中的“努力崇明德”,也都应指的是曹操。另,陈琳《移豫州檄》,也曾直斥曹操是“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363页。(3)诗中“令德唱高言”的内容,完全是对曹操“对酒当歌”的阐发,并与曹植诗作写法、句式、思想完全吻合。
曹植之所以以“令德”“灵德”等来敬称其父曹操,还有一层含义。“令德”有更为尊贵的含义,蔡邕《铭论》:“《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也。……所谓天子令德者也……周庙金人,缄口书背,铭之以慎言,亦所以劝进人主,朂(勉力)于令德者也。”*蔡邕:《铭论》,孙星衍辑:《续古文苑》卷九,见杨家骆主编:《国学名著珍本丛刊》,第461页。令德,不仅仅和天子发生关系,更和文王、周公发生关系。《诗序》曰:“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人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张阆声校:《校正三辅黄图》,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第37页。可知“灵德”其后的文化意蕴,是与周文王相关,以曹操比附文王,这也是曹操自己的话语。此诗为曹植所作无疑,其气氛情怀,最为吻合于建安十七年正月在邺城铜雀台所作。《今日良宴会》既然为曹植所作无疑,则十九首之整体,皆与曹植关系密切,或进一步说,这些狭义古诗之背景,皆与曹植息息相关。该诗中的宴会音乐描写,同时否定了所谓民间、无名氏之作的可能性。盖因礼乐者,民无与焉。
(四)《庭中有奇树》之“何足贡”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该诗应是曹植于黄初二年春,写给甄氏的诗作。“将以遗所思”,此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前后写给甄氏采遗诗作的反复吟唱,“路远莫致之”,正吻合于两人千里相隔,“莫致之”三字,更说出了两者之间的阻隔绝非仅仅是地理的空间,“此物何足贡”,道出了两者之间名分上的君臣关系。“贡”的本意是“进献方物于朝廷”。而甄氏在黄初二年春天,早已经由世子夫人的身份升格为皇后,虽然甄后并未入京接受这一封号,但作为曹植来说,采用“贡”字,也许说明曹植此时希望和甄氏疏离,这样对双方都有益。“别经时”,曹植于黄初元年四月已在鄄城,至写作此诗思甄,已经是翌年春夏之际,正是分别了一年有余。此诗虽然仍有对甄后敬而远之之意,但“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的情节,暴露作者对于爱者难以离弃的天机。
(五)《青青陵上柏》之“双阙”
“青青陵上柏,磊磊磵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此当为曹植于太和五年、六年之间,重回洛阳京城所作。《水经注》曰:(魏)明帝改雉门为阊阖门,又曰:明帝始筑阙,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门。*徐松辑:《元河南志四卷》卷二,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魏明帝建造阊阖门,曹植诗中多有阊阖门的记载,但说“遂不复筑,故无阙门”,不确,曹植《毁鄄城故殿令》:“伊洛为魏之东京,故夷朱雀而树阊阖”,*曹植:《毁鄄城故殿令》,孙星衍辑:《续古文苑》卷五,见杨家骆主编:《国学名著珍本丛刊》,第292页。大体应该是邺城之朱雀建筑,在曹魏洛阳即为阊阖。汉魏之际五言诗作中,“双阙”共计出现四次,其中十九首一次,曹植三次,并且多和阊阖等连用。十九首(其三):“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曹植《赠徐干诗》:“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五游咏》:“阊阖启丹扉,双阙曜朱光。”《仙人篇》:“阊阖正嵯峨,双阙万丈余。”又《杂诗七首·其六》:“飞观百余尺”。《赠徐干诗》应写在邺城,为建安之作,其余均为曹植晚年之作,可知双阙和阊阖为在邺城和曹魏洛阳均有的建筑。“百余尺”,陆机《洛阳记》:“洛阳城内西北隅有百尺楼,文帝造。”*徐松辑:《元河南志四卷》,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魏城阙宫殿古迹》后第2页。曹植《杂诗》其六“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正相对照。
再查看元代河南志所附后汉洛阳宫图,其中并无“双阙”,足以证明此诗并非两汉之作。其中“两宫”“陵上柏”“王侯”“极宴”(最高等级之宴会)等,更说明此诗并非民间之作或无名氏下层文人之作。
三、简短的结论
以上所选古诗中的5篇,篇篇都显示了宫廷文化的背景,其中《西北有高楼》的“阿阁”,乃为后汉宫殿名称,从而证明古诗并非民间无名氏之作,而有宫廷文化背景。“明帝御阿阁士众”的记载,更证明阿阁在东汉洛阳宫城之中,乃为宫廷政治场所,又怎能将“无乃杞梁妻”解读为歌女呢?结合全诗来看,此诗为曹植为甄后所作无疑。同此,元代《河南志》中同时提供的魏晋宫城中的“芙蓉殿”“灵芝池”,同时证明了笔者此前论证的甄后对芙蓉、灵芝的喜爱,芙蓉就是甄后的代用名称。
古诗作者,“旧疑是建安曹王所制”,其实“曹王”应该含有甄后,曹植甄后名为两人,实为一体,古诗中的绝大多数篇章,均应为两者之间的情话、情书。甄后之作,从本次所引的篇章来看,较之曹植,更接近于乐府诗,更具有如话家常和口语化的特点,更具有人物角色以及相互对话,更为适宜歌唱表演,这与甄后精通音乐的个人文化素养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