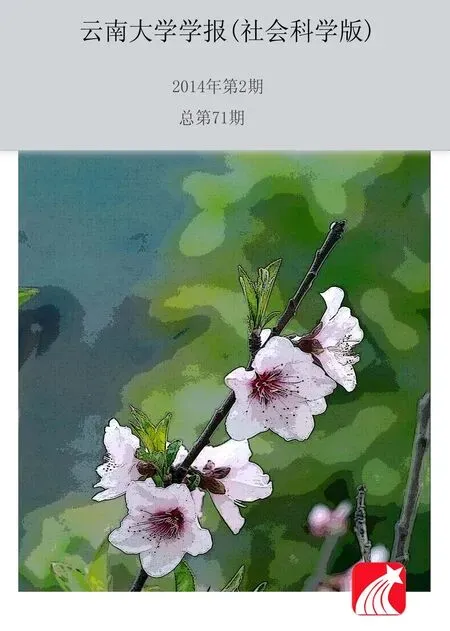乡土情节的颠覆与重构
——以古代小说中归乡母题为中心
2014-03-06李萌昀
李萌昀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在中国诗歌史上,歌咏望乡、思乡、归乡的作品蔚为大观。出于传统深厚的乡土情结,也出于旅途中的坎坷际遇,诗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将故乡塑造为与旅途相对立的理想空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似乎只要回到故乡,一切问题、一切痛楚都会得到解决和释然:“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白居易《长相思》)在思乡情切的诗人眼中,归乡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距离的遥远、路途的艰难都变得微不足道:“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诗经·卫风·河广》)相比之下,古代的小说家们虽然对乡土情怀保持着相当的尊重,但实际上却通过人物的各种遭遇向读者展示了归乡之旅的复杂性,这迫使读者思考:故乡是否真的如此值得期待?本文试图通过对古代小说中的归乡故事的梳理,反思归乡母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含义,并对小说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与方法论加以探索。
中国文化传统通常将故乡与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故乡亦称家乡,指一个人的家庭世代居住的地方。无论“居”还是“游”,人的家庭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始终影响着人的行动。由此,人的内心时常存在两种情绪:一方面,害怕孤独和颠沛流离,依赖于家庭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厌恶身份与责任的束缚,渴望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自由。这两种情绪的冲突和纠结提供了解读古代小说中的归乡之旅的基本线索。
一、“居”与“游”的选择
与一般的旅行故事相反,归乡之旅的起点是异乡,而非故乡。在归乡之旅开始之前,旅行者首先要面对的是“居”与“游”的选择:为什么要归乡?为什么不继续在异乡漫游?
最早对归乡之必要性加以反省的是“误入仙境”题材的系列故事。主人公由于某种机缘误入仙境,与仙人相识。本来,他们可以永远留居仙境,享受精神和肉体的绝对自由,但是却被归乡的冲动所苦:《幽明录·刘晨阮肇》中,刘晨、阮肇闻“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搜神后记·袁相根硕》中,袁相、根硕因思念故乡而“潜去归路”;《博异志·白幽求》中,白幽求闻得仙人为自己在仙境中安排职位时,第一反应居然是“恓惶”,“拜乞却归故乡”;《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中,程宰在海神的帮助下“囊中幸已丰富,未免思念故乡起来”。[1](P667)此时,主人公对归乡的选择是出于本能,是深藏在文化血脉中的乡土情结起作用的结果。他并不知道,一旦选择归乡,便意味着从仙境的永恒坠落。
虽然主人公选择了归乡,但是其选择之后的遗憾和悔恨大大抵消了此种选择的自明性和道德优越感:在《袁相根硕》中,主人公只是“怅然而已”;白幽求则望着仙人远去的背景“悔恨恸哭”;程宰的表现最为激烈,“大声号恸,自悔失言,恨不得将身投地,将头撞壁”。[1](P667-668)归乡的价值由此变得暧昧不清。更重要的是,在故事的结尾,主人公重新出发寻找仙境,归乡之选择的正确性被进一步否定,仙境所象征的绝对自由似乎才是永恒的归依。不过,这些结尾均非实写,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是暗示或推想,只能被看成是对归乡后的主人公的想象性安慰,而非对失去之自由的现实性弥补。
以上故事体现了人们对归乡之态度的复杂性。不过,无论人们如何渴望自由、逃避责任,家庭的召唤在伦理上依然是不可抗拒的。明代通俗小说中有著名的万里寻亲型故事。对于此类故事,研究者多以孝子为中心展开探讨,而本文的着眼点则是那位逃离家园的父亲。以《石点头》卷三《王本立天涯求父》为例。故事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写王原之父苦于里役,抛妻弃子、远走他乡;后一部分写王原走遍天涯,寻找生父。这一故事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旅行者在家庭责任和个人自由之间的挣扎。王原之父王珣被里役所苦,决定“撇却故乡,别寻活计”。妻子张氏尖锐地指出:“你男子汉躲过,留下我女流之辈,拖着乳臭孩儿,反去撑立门房,当役承差,岂不是笑话?”王珣不为所动,因为一家之主的身份与责任已经让他身心俱疲,他对妻子说:“从此夫妇之情,一笔都勾,你也不须记挂着我。”对儿子说:“此后你的寿夭穷通,我都不能知了。就是我的死活存亡,你也无由晓得。”[2](P52-53)显然,他已经决心彻底抛弃丈夫和父亲的身份,断绝与这个家庭的联系。
本来,在通讯落后的古代,王珣的愿望是不难实现的。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一个厌恶家庭与责任的父亲,他却生出一个极端重视家庭与责任的儿子。王原16岁出门寻父,临行前宣称:“若寻得着,归期有日;倘若寻不着,愿死天涯,决不归来。”[2](P64)换句话说,他以死为誓,一定要使逃脱的父亲重新回归家庭伦理之中。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王原终于如愿在一座寺庙中找到了父亲。此时,归乡与否的选择摆在了王珣面前:
昔时为避差役,魆地离家,既不得为好汉,撇下妻子,孤苦伶仃,抚养儿子成人,又累他东寻西觅,历尽饥寒,方得相会,纵然妻子思量我,我何颜再见江东父老。况我世缘久断,岂可反入热闹场中。不可不可。[2](P73)
在王珣看来,如果同意归乡,那么自己就必须重新面对20多年前的那次选择,且必须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这便意味着,这些年的自由全部失去了意义。关键是,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仍然不能说服自己相信,从前的离家是正确的(“不得为好汉”)。他仍在家庭与自由之间纠缠。然而,他的拒绝在孝子以死相逼的强大伦理力量面前显得无比软弱。寺里的师父法林和尚说:“你身不足惜,这孝顺儿子不可辜负。”[2](P74)这句话无情地否定了他的一切挣扎和努力。他终于向儿子所代表的伦理力量屈服,放弃自己的自由,重新回归家庭的罗网。
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清文康《儿女英雄传》。此书为读者津津乐道的通常是侠女何玉凤(十三妹)在书生安骥旅途遇险时拔刀相助的情节。然而,从全局看,这部分内容只是下文安骥之父安学海收服何玉凤、令其还乡并与安骥完婚的铺垫。前者在篇幅上不足全书的四分之一,后者则接近一半。实际上,此书的重点正是描写家庭伦理对旅行冲动的规训。代表旅行冲动的是何玉凤,为报父仇而欲远走天涯;代表家庭伦理的是安学海,为使何玉凤有个好的归宿而竭力鼓动其还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安学海精心设计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不但动用了己方的所有人员,而且将原本支持何玉凤的邓九公等人一一拉拢过来。
小说家使用了大量神魔小说中的意象以形容双方之间的激烈冲突,如第十六回云:“安老爷义结邓九公……为的是先收服了十三妹这条孽龙,使他得水安身。”[3](P257)又云:“且等我先收伏了这个贯索奴,作个引线,不怕那条孽龙不弭耳受教。”[3](P262)回末诗云:“整顿金笼关玉凤,安排宝钵咒神龙。”[3](P276)“孽龙”的典故出自《西游记》第八回与第十五回,观音菩萨救下犯法将诛的“孽龙”,令其化为白马,成为唐僧的脚力。小说家在此以“孽龙”称呼十三妹,有两层意思:首先,龙性难驯,突出了十三妹对自由的坚持;第二,对于担负家庭责任的人来说,自由是一种罪孽。因此,安学海出于对她的爱护,决心如观音菩萨救助白龙马一般,让她“得水安身”。“水”、“金笼”、“宝钵”象征着为她安排的安身之所,即家庭伦理中的位置,然而“收服”、“受教”、“关”、“咒”等一系列动词则透露出此种“理想”安排的强制性。第十九回,在安学海劝说何玉凤还乡的关键时刻,小说家更是连用四个神魔典故,突出了“劝说”行为背后的征服色彩:“好安老爷!真是从来说的:有八卦相生,就有五行相克;有个支巫祁,便有个神禹的金锁;有个九子魔母,便有个如来佛的宝钵;有个孙悟空,便有个唐一行的紧箍儿咒。”[3](P337)
安学海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却有着缜密的心思、过人的口才,更重要的是,他依靠的是不容置疑的“家庭至上”的伦理力量。何玉凤虽然号称侠女,但却并非《水浒传》中那种逃离了家族秩序的豪侠,重孝道、重后嗣等家庭意识形态仍然在无形中影响着她。安学海看准这一点,有条不紊地安排了重重攻势。首先,安学海将仇人的死讯告诉了何玉凤,消除了其旅行的合法性基础(为父报仇);然后,提醒何玉凤她担负着安葬双亲的责任,并以提供坟园为理由,诱使其与大家一起还乡;最后,以延续家族香火为理由,迫使何玉凤与安骥完婚。在此过程中,有两个场景特别值得一提。第十八回,何玉凤得知仇人已死,因而万念俱灰,试图自杀。安学海为打消她的求死之心,故意激她道:
他虽然大仇已报,大事已完,可怜上无父母,中无兄弟,往下就连个着己的仆妇丫鬟也不在跟前;况又独处空山,飘流异地,举头看看,那一块云是他的天?低头看看,那撮土是他的地?这才叫作‘一身伴影,四海无家’。凭他怎样的胸襟本领,到底是个女孩儿家,便说眼前靠了九公你合大娘子这萍水相逢的师生姊妹,将来他叶落归根,怎生是个结果?[3](P321)
在这番叙述中,女性旅行者的前途一片黯淡,其根源恰在于从家庭秩序中的脱离所导致的了无依靠:无父母,无兄弟,无仆妇丫鬟,无天,无地,无家,无结果。何玉凤听了这番话,“字字打到自己心坎儿里,且是打了一个双关儿透”,埋下了她回归家庭的因缘。最终使何玉凤完全屈服的是张金凤在安学海的安排下说出的另外一席话。第二十六回,张金凤向何玉凤揭开谜底:
姐姐你在黑风岗能仁寺救了他儿子性命,保了他安家一脉香烟,因此我公婆以德报德,也想续你何家一脉香烟,才给叔父、婶母立这祠堂,叫你家永奉祭祀。讲到永奉祭祀,无论姐姐你怎样的本领,怎样的孝心,这事可不是一个女孩儿作的来的,所以才不许你守志终身,一定要你出阁成礼,图个安身立命。……再要讲到日后,实指望娶你过去,将来抱个娃娃,子再生孙,孙又生子,绵绵瓜瓞,世代相传,奉祀这座祠堂,才是我公婆的心思。才算姐姐你的孝顺,成全你作个儿女英雄。[3](P488)
对于内心仍坚守孝道的女子来说,延续香火的理由是无法驳斥的。张金凤以不亚于安学海的口才,描绘出一幅家族绵延的史诗图景。“绵绵瓜瓞,世代相传”的许诺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为父母的生命、也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意义。与此相比,浪迹天涯的理想又算得了什么?青灯古佛的愿望又算得了什么?何玉凤最终重新回到了家庭关系之中,彻底放弃了漂泊的冲动。
二、归乡的资格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旅行者终于在“居”和“游”之间做出了选择,决心踏上归乡的旅程。此时他会发现,在决定归乡之后和实际出发之前,还有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需要面对,即归乡资格的确认:在艰难时世之中,谁可以获得归乡的机会?谁必须为此做出牺牲?在此问题上,小说家展现出了深刻的现实关怀和冷峻的思辨力量,代表作品是《醒世恒言》卷十九《白玉娘忍苦成夫》和《石点头》卷十一《江都府孝妇屠身》。对于归乡资格,这两部作品做出了同样的回答:丈夫有着归乡的优先权利,妻子必须为此做出牺牲。
《白玉娘忍苦成夫》的时代背景是宋末元初的乱世。程万里出身宋朝官宦世家,因“直言触忤时宰”,单身出亡,却在路上被元兵掳至兴元府(汉中),成为元将张万户的家奴,得同样被掳来的白玉娘为妻。虽然身在异乡,程万里心中始终怀着逃亡的念头。对他来说,逃亡需要两个条件。首先是树立逃亡的信念,然后是摆脱妻子的羁绊。如回目所示,白玉娘以极大的勇气,忍受了巨大的痛苦,成就了丈夫的逃亡。结婚第三天,白玉娘见到丈夫在房中“自悲自叹”,立刻察觉到其逃亡的渴望,于是不顾嫌疑地向丈夫建议:“何不觅便逃归,图个显祖扬宗,却甘心在此,为人奴仆!岂能得个出头的日子!”然而,她的坦诚并未获得丈夫的信任,反疑心“是张万户教他来试我”。[4](P398)白玉娘两次建议,程万里两次揭发,导致了白玉娘被张万户发卖。至此,程万里才相信妻子的真诚,然而悔之晚矣。由于妻子的牺牲,丈夫不但坚定了逃亡的信念,而且避免了感情的羁绊,最终实现了逃亡的计划。白玉娘虽然与程万里仅仅成婚六天,但却心甘情愿地为其做出巨大牺牲,因为在“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中,这是理所应当的。回前有《西江月》词云:“神仙迂怪总虚浮,只有纲常不朽。”在这一故事中,旅行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成为“夫为妻纲”的典型注解。
不过,《白玉娘忍苦成夫》对旅行伦理的展现显得相对空洞,丈夫与妻子在归乡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最终的结局仍算圆满。相比之下,《江都府孝妇屠身》将夫妻二人置入一个“你死我活”的背景之中,深刻体现出旅行伦理的残酷。小说写周迪与宗氏夫妻二人出外经商,遭遇兵乱,被困扬州城中。等到乱平,二人却因缺少食物和盘缠,无力还乡,因而发生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对话:
周迪说道:“母亲只指望我夫妻在外,经营一年两载,挣得些利息,生一个儿子。那知今日到死在这个地方,可不是老娘陷害了我两口儿性命!”说罢大哭。宗二娘却冷笑道:“随你今日哭到明日,明日哭到后日,也不能勾夫妇双还了。我想古人左伯桃,羊角哀,到冻饿极处,毕竟死了一个,救了一个。如今市上杀人卖肉,好歹也值两串钱。或是你卖了我,将钱作路费,归养母亲。或是我卖了你,将钱作路费,归养婆婆。只此便是从长计较,但凭你自家主张。”[2](P249)
小说家将二人置入一个无论如何“不能够夫妇双还”的死局:一方的还乡必须以另一方的死亡为代价。按照传统伦理,夫强妻弱,夫贵妻贱,丈夫具有还乡的优先权,妻子应该为丈夫做出牺牲。
然而,小说家的高明之处在于,在承认伦理层面上的夫强妻弱的前提下,将夫妻二人的现实性格设计成妻强夫弱,避免了小说沦为意识形态的简单图解,且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和悲剧性。因此,宗氏此时虽然已经决定卖身屠市,却故意对丈夫说:谁生谁死,“但凭你自家主张”。多年夫妻,宗氏不可能不知道丈夫的软弱和胆怯。此举更多是出于一种恶作剧的冲动。果然不出她所料:
周迪见说要杀身卖钱,满身肉都跳起来,摇手道:“这个使不得。”宗二娘笑道:“你若不情愿,只怕双双饿死,白白送与人饱了肚皮。不如卖了一个,落了两串钱,还留了一个归去。”周迪吟沉不答。宗二娘见他贪生怕死,催促道:“或长或短,快定出个主意么。”周迪道:“教我也没奈何。”宗二娘道:“既如此,留我在此,你自归去何如?”周迪吃一惊道:“你怎生便住得?”宗二娘道:“你怎生便去得?”周迪会了此意,叹一声道:“我便死,我便死。”说罢,身子要走不走,终是舍不得性命。宗二娘看了这个模样,将手一把扯住他袖子道:“你自在这里收拾行李,待我到市上去讲价。”说罢,往外便走。[2](P249)
如果周迪此时慨然决心赴死,那么宗氏自然会加以阻止并以身相替,因为她强势归强势,仍然是传统伦理的信奉者。但是,周迪意料之中的胆怯表现仍然让宗氏十分失望,她选择让这个恶作剧进行下去:首先,运用自己在夫妻关系中一贯的强势,逼迫周迪说出“我便死”的违心之言;然后,假称去市上讲价,自己来到屠市卖身。在回家将卖身钱交付周迪时,宗氏仍然不肯说破:“这是你老娘卖儿子的钱,好歹你到市上走一遭,我便将此做了盘缠,归去探望婆婆。”吓得周迪“魂不附体,脸色就如纸灰一般,欲待应答一句,怎奈喉间气结住了,把颈伸了三四伸,吐不得一个字,黄豆大的泪珠流水淌出来”。[2](P250)直到亲眼看见宗氏被屠戮后的尸体,周迪方才得知真相。
宗氏恶作剧式的献身透露出其心态的复杂性:一方面,出于对伦理的信仰和坚持,她愿意为丈夫的还乡牺牲生命;另一方面,丈夫的贪生怕死又使她牺牲心有不甘,甚至产生怀疑。于是,她偏执地将恶作剧进行到底,以小小的恐吓对丈夫进行了有限的报复,表达出了自己的不满。这篇小说的主旨虽然仍是对旅行伦理的宣扬,但其独特的情节展开方式却在客观上对主旨构成了质疑和解构:为了丈夫的归乡,妻子的牺牲是否真的是天经地义?
三、来自故乡的危险
那么,当旅行者下定了归乡的决心,确认了归乡的资格,经过艰苦跋涉抵达故乡之后,是否便万事大吉了?相反,新的危险正在悄然临近。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精确地捕捉到了旅行者初抵故乡时的尴尬:“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正如旅行不但是对日常空间的出离,而且是对家庭的出离一样,归乡不只是回归熟悉的空间,而且是回归熟悉的家庭关系。然而,由于离家日久,旅行者与家庭已经相互变得陌生;从抵家到被接纳,还有很多道关口——这构成了归乡题材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矛盾冲突。
首先,家庭需要对旅行者进行身份和伦理上的审查,判断其是否有资格重新成为家庭的一员。《古今小说》卷二十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是一个关于身份的失去与找回的故事。其中,离乡与归乡是身份转换的两个关键性情节。故事写商人黄老实在妻子死后,将小女儿善聪假充男子带在身边。离乡之后,善聪获得了新的身份,包括:新的性别(男子)、新的名字(张胜)、新的职业(经商)。黄老实死后,张胜无力扶柩回乡,便与隔壁客房的青年商人李秀卿结为异姓兄弟,同食同卧、共同营生。九年之后,张胜长大,决定扶柩回乡,顺便找回自己失落已久的身份。家乡尚有早已出嫁的姐姐道聪,代表着她的家庭。如欲找回失去的身份,就必须获得家庭的认可。见到姐姐之后,张胜坦言自己是其妹妹善聪。道聪虽然表示相信,但却立即从伦理角度提出质问:“你同个男子合伙营生,男女相处许多年,一定配为夫妇了。自古明人不做暗事,何不带顶髻儿?还好看相。恁般乔打扮回来,不雌不雄,好不羞耻人!”这是家庭对张胜的一次重要审查。如欲被家庭接受,那就必须证明自己在伦理上毫无瑕疵,有资格重新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于是,张胜接受了一个颇具侮辱性的测试:
张胜道:“不欺姐姐,奴家至今,还是童身,岂敢行苟且之事,玷辱门风。”道聪不信,引入密室验之。你说怎么验法?用细细干灰铺放馀桶之内,却教女子解了下衣,坐于桶上。用绵纸条栖入鼻中,要他打喷嚏。若是破身的,上气泄,下气亦泄,干灰必然吹动;若是童身,其灰如旧。朝廷选妃,都用此法,道聪生长京师,岂有不知?当时试那妹子,果是未破的童身。于是姊妹两人,抱头而哭。道聪慌忙开箱,取出自家裙袄,安排妹子香汤沐浴,教他更换衣服……次日起身,黄善聪梳妆打扮起来,别自一个模样。与姐夫姐姐重新叙礼。[5](P452)
只有在确认妹妹童身未破之后,道聪方才与她“抱头而哭”,并安排妹妹沐浴、更衣。这一系列具有仪式意味的行动代表着家庭对旅行者的重新接纳。值得注意的是,测试之后,小说家对主人公的指称从“张胜”变为“黄善聪”,恰恰象征着其身份转换的正式完成。黄善聪对失而复得的身份极其珍惜,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不但在与李秀卿重聚时严守男女大防,而且为了证明之前并无私情,严词拒绝了李秀卿的提亲。归来者在伦理问题上的如履薄冰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被家庭重新接纳的艰难。
来自家庭的伦理审查是旅行者归乡之后将要遭遇的困难之中较为无害的一种。更危险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家庭在旅行者缺席期间已经形成了新的稳定结构;旅行者的归来势必招致新结构的既得利益者的嫉恨,有时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最典型的例子是留守妇人的私情故事:男子久不在家,妇人因与旁人通奸;男子归后,奸夫淫妇为求长久,设法将其谋杀。此类故事在通俗小说中颇为常见,主角多为长期在外的行商。如《珍珠舶》卷一,赵相出外经商,将家事托付蒋云。后者趁其不在,先后与其母、其妻勾搭成奸。赵相归后,察觉了诸人的奸情。为了逃避惩罚,蒋云与王氏先发制人地将赵相告至县衙,险些使其死于公堂。又如《百家公案》第八回《判奸夫误杀其妇》,梅生经商归来当晚,其妻被杀。梅生被告上公堂。包公判断:“汝去六年不归,汝妻少貌,必有奸夫。想是奸夫起情造意,要谋杀汝。”后来果然捕得奸夫一名,“本意欲杀其夫,不知误伤其妻”。[6](P452)不过,从上述故事也可以看出,旅行者在与敌对者的斗争中并非绝对的弱势,因为伦理站在他的一方。
私情故事之外尚有争产故事,虽然在数量上相对较少,其反映的问题实际上更加普遍:旅行者与家人的财产纠纷。代表作品是宋元话本中的《合同文字记》,后被凌濛初改编为《拍案惊奇》卷三十三《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合同文字记》写汴梁城外有刘氏兄弟二人,某年饥荒,刘二携妻儿赴外地趁熟。临行前,二人将老家财产立为两纸合同文字,作为回归时的凭据。后来,刘大续弦王氏,带前夫之子来家,时常自思:“我丈夫老刘有个兄弟,和侄儿趁熟去,倘若还乡来时,那里发付我孩儿?”[7](P452)15年后,刘二夫妇客死异乡,其子安住果真携父母骨殖与合同文字归乡。显然,与王氏之子相比,安住拥有刘氏家产的优先继承权。为了保护自己孩子的继承权,王氏唆使刘大拒不承认安住的身份。
《拍案惊奇》对此段情节的改写颇为精彩。刘大之妻先假装与侄儿相认,骗得合同文字藏起;之后不但翻脸不认,而且用杆棒残忍地打破侄儿的头颅。后来幸亏包龙图设计将合同文字赚出,安住的身份与财产继承权方才得到确认。此故事展现出旅行者和家人在财产争夺上的残酷与激烈。凌濛初在结尾称,此故事的创作目的是“奉戒世人,切不可为着区区财产,伤了天性之恩”。[8](P452)也就是说,正因为世人大多热衷财产争夺而不顾“天性之恩”,才促使小说家创作此故事以为劝诫。面对家人手中的杆棒,旅行者发现,故乡已经变得比异乡更加陌生。
四、作为故乡的异乡
既然归乡之路坎坷漫长,故乡也变得危险而陌生,对旅行者来说,留居异乡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尤其在家国沦陷、归乡的希望彻底断绝的时候,旅行者只能在异乡安住,并将异乡作为故乡来经营——此时,这种经营行为本身就具有了归乡的性质。
将异乡经营为故乡的第一种方式是空间上的复制。客居异乡的旅行者常常会下意识地在异乡寻找故乡的影子:风景、建筑、风俗、时令……然而,最相似的地方恰恰是最不似的地方,因为从对比中旅行者更容易发现其中的差异。以《古今小说》卷二十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为例。杨思温本是东京人,因靖康之变流落燕山。燕山在城市布局与风俗上均效仿东京,但是,风俗上的相似性引来的却只是小说家的嘲讽:
那燕山元宵却如何:虽居北地,也重元宵。未闻鼓乐喧天,只听胡笳聒耳。家家点起,应无陆地金莲;处处安排,那得玉梅雪柳?小番鬓边挑大蒜,岐婆头上带生葱。汉儿谁负一张琴,女们尽敲三棒鼓。[5](P452)
当姨夫邀杨思温看灯时,他回答说:“看了东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间元宵?”[5](P452)后来,虽勉强上街游赏,却依然情绪索然。模仿大相国寺的悯忠寺、模仿樊楼的秦楼,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只有在邂逅旧日大相国寺的行者、旧日樊楼的过卖以及“未改宣和妆束”的妇人时,他才感到欢喜。这恰恰说明,可以给人故乡的安慰的并非空间上的复制,而是熟悉的人际关系。
在《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主人公正是通过对故乡之人际关系的寻找和经营,而将异乡转变为故乡的。靖康之变时,秦重的父亲带着他从汴梁逃难至临安,后将他卖与朱十老为嗣。虽然秦重被卖之时只有十三岁,却始终记挂着自己的父亲。被养父逐出之后,他便将寻找父亲作为自己的第一个生活目标,“把盛油的桶儿,一面大大写个秦字,一面写汴梁二字”。[4](P50)这副写着故乡名字的油桶是秦重的旗帜,清晰地表示出其重建家园的意愿,也是解读此故事的关键。不久,秦重恋上名妓莘瑶琴,将其树立为自己的第二个生活目标,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莘瑶琴的同乡身份:“秦重听得说是汴京人,触了个乡里之念,心中更有一倍光景。”[4](P52)莘瑶琴的双亲同样流落临安,听说秦重也是汴京人,前来投奔。“乡人见乡人,不觉感伤”,秦重立刻留下他们,“只当个乡亲相处”。[4](P65)最后,秦重往天竺寺送油,他的父亲见到了油桶上的“秦”和“汴梁”字样,与他相认。通观全篇,汴梁乡谊是情节发展的核心线索。凭借对乡谊的尊重和经营,以秦重为中心,来自汴梁的两户人家在临安重聚、扎根、日益兴盛。既然故乡已经不能复返,那么就在异乡重建家园吧。在这个语境下,“直把杭州作汴州”获得了某种积极的意义。
至此,本文梳理了古代小说中的归乡题材故事,分析了归乡所引发的矛盾冲突及其思想含义。我们看到,虽然古代小说从未否定古典诗歌所树立的“恋乡”情感范式,但却通过对归乡之两难、归乡之资格、归乡之后果的揭示,从客观上消解了笼罩在故乡之上的理想化色彩。作为士大夫阶层之思想趣味的载体,古典诗歌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某些固定的写作模式和关注焦点,致使“故乡”失去了其平实的含义,沦为含义单一的情感符号;与之相比,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相对保持着较强的民间趣味和底层视角,反而具有了反思归乡之复杂性的可能,构成了与古典诗歌迥异的文学景观,也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阅读以上故事之后,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故乡”是否必须单纯美好,才成其为“故乡”?
参考文献:
[1]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天然痴叟.石点头[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文康.儿女英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5]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安遇时.百家公案[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7]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0.
[8]凌濛初.拍案惊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