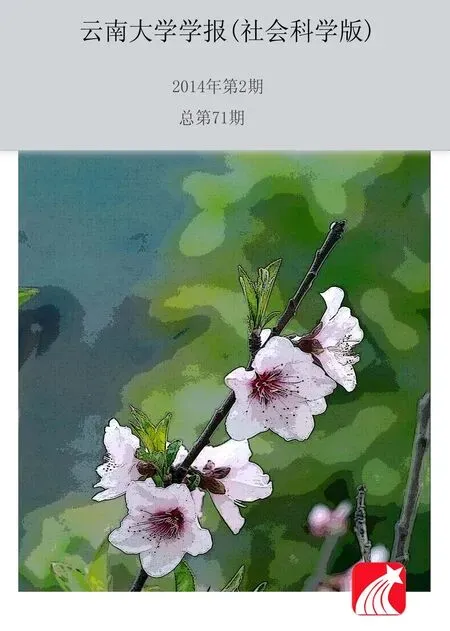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
2014-03-06辛晓娟
辛晓娟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在中国古代诗歌辉煌的成就中,主体是抒情诗,叙事诗是第二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叙事诗歌没有坚固的、自我完善的、强大的系统。这种系统并非通常意义上从《诗经》到乐府的一脉相承的一个系统,而是具有《诗经》和乐府两个不同的源头,分别代表了官方与民间的不同体系,互为补充。如果将这两个系统叠加起来看,则可以完整地体现出中国叙事诗的源流。
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两大源头——诗经传统与乐府传统
《诗经》中保存了中国大部分的早期叙事诗歌,无论是史官对《生民》等重大题材叙事诗的直接创作,还是《国语》中关于“公卿至于列士献诗”[1](P9)的记载,又或“采诗说”、“删诗说”中透露出官方音乐机构对搜集而来的民歌的整理改造,都能看到这类叙事诗不可忽视的官方的背景。出于儒家传统对“史”的推崇,要求“以诗存史”、“诗心史笔”,让原本产生于民间的叙事诗带上了浓重的官方色彩。这一点在《诗经》成为经典后尤为突出。从汉代直至清代,文人又以“诗史”的观念去阐释解读这些诗作,因此《诗经》中保留的叙事诗,无论其诞生的初衷如何,在漫长的经典阐释过程中,都以官方的形式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故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民歌。
“诗史”观代表了中国叙事诗歌的官方系统。此系统有如下特色:官方性、题材重大化、纪实性、史学批判性、伦理性和道德力量。对于这一点,前代学者已有了较多研究,故不再赘述。
与诗经不同的是,汉乐府大部分作品都曾在民间长期传唱,且多数未经官方修订、阐释、经典化,①自汉武帝始,统治者设立乐府机构、采集歌谣,“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看出汉乐府亦经历了官方收集整理,并带有“观风俗”的政治目的。但汉乐府由于未如《诗经》一样被经典化,所以基本保留了其在民间流传时的原貌,并且也未经过后世学者的层层阐释解读,基本仍可视为民间作品。[2](P1756)故较多地保留了其原生状态。其直接表现为,乐府中更富于情节性、传奇性的叙事诗的比例远远大于以抒情诗为主的《诗经》。明代徐祯卿《谈艺录》:“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3](P99)可见乐府诗与《诗经》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更强调叙事性。现存汉乐府大概有一百余首,叙事之作竟多达三分之一,实在是一个可观的比例。正因为看到了汉乐府叙事诗的繁荣,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继“诗言志”之后,提出了“诗缘事”的概念: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2](P1756)
“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乐府诗的重要特点,亦是和《诗经》的重要区别所在。受《诗经》传统影响,班固所缘之“事”,并非简单的事件本身,而是掺杂了“观风俗,知薄厚”的伦理意义。但考察现存的乐府诗作,我们可以看出乐府叙事诗与“诗史”观的不同之处:伦理教化意义并非在一开始就存在,也非作者刻意为之。它们诞生的最初目的自然而朴素:作者用传奇的、戏剧性的、虚构的,甚至掺杂了浪漫与神话色彩的情节来吸引听众,给听众讲述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这才是缘“事”而发的真正意义。而其中体现的伦理和道德意义,并非主题先行、刻意为之,而是随着讲述故事、塑造人物潜移默化地完成的。
总之,汉乐府产生于民间,长于叙事,并不承担记录重大史实的责任,经过民间艺人一代代的整理,呈现出与《诗经》迥异的“娱乐化”特质。这体现为汉乐府中人物形象生动毕肖,事件典型猎奇,叙事委婉生动、高潮迭出。汉乐府篇制短小精悍,题材上也不表现重大史实,却重在情节娱乐性。与诗经传统各自代表了早期叙事史诗的一个方面,发展出迥异的特色,成为中国古代叙事诗两大并生的源头。
二、以娱乐性为标志的乐府叙事传统
民间的流传过程,使得娱乐性成为乐府叙事传统区别于诗经传统的最重要方面。钱志熙在《汉魏乐府音乐与诗》中曾指出:“乐府艺术从整体上来看,是一种娱乐型的艺术……乐府诗确实很好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并且揭露了汉代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从总体看,汉乐府诗表现出汉代社会普遍的伦理观念。但这伦理是通过娱乐功能而取得的。可以说在乐府艺术中,娱乐功能是第一性,伦理功能是第二性,应该说这是乐府诗的一大特色,甚至是带有经典性的特色,为后来的文人拟乐府诗所难以企及。”[4](P96)与强调伦理价值的“诗史”观不同,汉乐府作品(尤其叙事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娱乐性,这是由其发生、流传的需求所决定的。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各种叙事文学作品要想得到广泛传播,除了记录有价值的历史史实外,更要叙述一件典型的、传奇的、可看的事件。由于民间流传的传播特质,娱乐性在这些作品中至关重要。不能取悦听众便不可能生存,这是一种天然形成的、以文艺作品娱乐价值为核心的选择机制。为了在这一机制中生存,乐府叙事诗作于叙事手法、故事情节、戏剧冲突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均较《诗经》有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叙事的情节化、传奇化、虚构化,人物和事件的典型化、戏剧化等几方面。
(一)情节性、戏剧性
情节是否精彩、引人入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乐府作品在当时能否受欢迎,能否被广为流传。对于乐府作品的创作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为民间艺人)而言,这可能决定了作品的生死,他们自然会在创作上多加注意。如《孤儿行》[5](P270)中记述父母双亡、被兄嫂虐待的孤儿,在家要忙活做饭、喂马、打水、采桑等各种各样的家务,还被驱使收瓜,瓜车行到半路时不幸翻覆。情节十分丰富,甚至还写到瓜车翻覆后,路上行人“助我者少,啖瓜者多”的细节。最典型的要属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5](P283)全诗长达1785个字,全景式地记叙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情节张弛有度,一波三折。刘兰芝被驱逐归家后两度有贵公子求婚,刘兰芝再三推辞,但刘兄威逼利诱,刘兰芝被迫答应婚事,婚事定在三日之后。婚礼举行前的傍晚焦仲卿告假归来,与刘兰芝见面。内容冲突集中,情节起伏,极具戏剧性。
为了强调戏剧性和冲突,乐府中往往带有“设为问答”的方式,即假托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以增强情节的戏剧性与冲突感。如古乐府《上山采蘼芜》[6](P1)中女主人公与故夫的对答;《东门行》[5](P269)中因家贫而铤而走险的丈夫与妻子的争论;《陌上桑》[5](P259)中罗敷对太守无理要求的反击。这种“设为问答”的方式,增加了叙事的生动性、戏剧性,也加强了矛盾冲突,使读者身临其境。这和乐府文学来自于民间传唱,听众要求更生动曲折的情节、更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更鲜明具体的人物形象是分不开的。
(二)传奇性、虚构性
汉乐府叙事传统与《诗经》传统的另一项重大区别,就是表现出极强的虚构性与传奇性。乐府诞生于民间,其传播方式也以下层艺人口耳相传为主,因此需要适合以普通民众为主要阶层的审美情趣,讲述有虚构性、传奇性的情节;塑造理想、动人、传奇性的人物。汉乐府中所讲述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物,决不能简单地看作现实记录,而应该看作是一种小说化的创造。
《孔雀东南飞》中的爱情悲剧,《陌上桑》中太守与美女的言语冲突,《妇病行》中男子因家庭窘困而铤而走险的社会事件,都让叙事具备了传奇、可看的一面。如果说这种传奇性还在现实的框架之内,是对现实的甄选、再加工,那么将传说、寓言等引入叙事诗歌,就实实在在地给乐府叙事诗加上了虚构的色彩,富于浪漫主义。如《孔雀东南飞》结尾处写两家合葬于华山旁,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和鸣。这显然不是实写之景,而是具有浪漫和神话色彩的想象。这种带着神话色彩的“物化”情节,和其他民间传说如梁祝中的“化蝶”、牛郎织女中化为星辰两两相对的典型情节是一致的,反映了源自民间的大众审美期待和道德取向。《战城南》[5](P157)中,已死去的将士与前来啄食尸体的乌鸦对话的情节,也带有明显的虚构性,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
人物塑造方面亦是如此,《陌上桑》中的美貌无双、口才过人的秦罗敷,《陇西行》中不让须眉的健妇,《东门行》中拔剑而起的丈夫,都具备一定的传奇性,他们不一定真有其人,而是根据当时听众的爱好,在现实基础上遴选、荟萃加工而成的。正因塑造了鲜明而传奇的人物,这些作品才能给听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具备生命力。塑造出当时人民喜闻乐见的理想人物、理想情节,正是乐府叙事的特征之一。
(三)非主题先行,伦理价值与娱乐价值的自然统一
后世文人对汉乐府诗歌极为推崇,认为其中包含了极高的伦理价值。但汉乐府诗歌中的道德伦理价值,并不如后世文人拟作的乐府诗一样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大众接受的娱乐文本中,本身就反映出了当时纯朴健康的道德价值。正如钱志熙指出的:“乐府诗文本包含的伦理功能……不是以文本独立地发挥出来,而是借整个娱乐艺术体制发挥出来的。因此,乐府诗的伦理功能是依附于娱乐的。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是在娱乐活动中自然而然进入文本意义系统中,自然而然地得到教益。”[4]
《妇病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等叙事名篇中,文本娱乐价值与道德价值高度统一,但这个统一并非刻意为之。乐府诗歌的作者并非有意确立道德主题,主观上也不以记录史实或宣扬教化伦理为目的,乐府文本中呈现出的令后世推崇的伦理道德价值,其实是一种暗合——当时大众对乐府诗文本娱乐性的要求,本身就包含了道德价值的要求。也只有符合大众道德取向的作品,才能真正打动受众。
总之,叙事诗歌由于有完整的情节、传奇的人物,更易被大众接受,也更易改造为说唱、表演等其他艺术形式,它们不是文人的案头经典,而是在民间被反复传唱表演,是诗歌中最具鲜活生命的一类。这些叙事诗歌诞生的最初目的是自然而朴素的,作者用传奇的、戏剧性的、虚构的情节来吸引听众,满足大众一定的猎奇心态,同时也满足大众的审美(包括道德审美)取向,从而起到娱乐的效果。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娱乐性应该理解为更丰富的层面,不仅包括“喜”,也包括“悲”的方面,如《孤儿行》中对身世的悲叹,《战城南》中对战争惨状的控诉。汉乐府中的“娱乐性”其实是一种对观众情绪的正向引导,除了让听众得到欢喜愉悦外,让听众的悲伤、愤怒、郁结得以抒发、宣泄也是重要方面。听众在聆听戏剧性情节,欣赏传奇性人物的同时,有浪漫及神话色彩的场景以满足其想象力,感受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奇妙境界,从感受、同情、共鸣到抒发、宣泄自己心中的悲喜,这是人类一种原生态的审美本能,是诗歌娱乐性的真正内涵。这种本能的抒发与释放,造成了汉乐府审美上的独特价值。
三、汉魏文人拟乐府:对两大 叙事传统融合的一次尝试
汉魏文人本能地感受到了乐府叙事传统的独特魅力,创作出了一大批的拟作。这些作品从题目、题材、艺术手法上全面模拟汉乐府,选取有传奇性的故事,典型事件,塑造典型人物,丰富了古代叙事诗艺术。
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文人一方面惊叹于汉乐府叙事的神奇莫测、变幻诡谲,一方面又感到模拟时的力不从心。因为这些拟作者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乐府叙事传统的民间性和娱乐性特质,文人案头创作无法还原汉乐府产生的整体背景和流传状态,也就无法真正把握汉乐府以娱乐功用为特质的叙事艺术。而出于对儒家文艺观的服膺,拟作者常常以《诗经》传统的官方性、批判性、主题先行性来指导“拟乐府”的创作。可以说,魏晋文人往往用《诗经》叙事传统,去指导模拟乐府叙事传统。最典型的如左延年、傅玄的同名作《秦女休行》。
左作叙述燕王妇女休为宗报仇,杀人于市的故事。全诗语言上明显模仿《陌上桑》:“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7](P410)叙事上情节曲折跌宕,且加入杂言对白,颇具乐府风貌。左延年是黄初乐工,在黄初年间“以新声被宠”,[8](P679)其地位大致相当于汉武帝时代的李延年。他的创作目的与后世文人拟作有所不同,娱乐多于教化,故最能接近于乐府叙事传统。胡应麟赞之为“叙事真朴,黄初乐府之高者。”[9](P16)所谓“真朴”,一定意义上是指该诗符合了乐府的叙事传统,更为本色真纯。傅玄同名之作则有显著不同。傅作叙述了庞氏烈妇为父母复仇,持白刃杀人于闹市的故事。题材与左作类似,具有相当的传奇性,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典型鲜明,亦有大量对话穿插其中,甚至还有“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10](P563)等细节描写,比左作更为生动详细。但两相对照,可以明显看到文人作品与乐工作品的区别:傅玄受诗经叙事传统的影响,伦理道德批判不仅时常现于行文之中,如“一市称烈义”、“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等,而且这种价值判断在本诗中显然比情节更具主导意义,是作者用意所在。诗作最终以伦理阐释结束:“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孙孙咸享其荣。今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鲜明地体现出,在《诗经》传统主导的叙事创作中,再精彩的故事也是为伦理价值服务的。
在汉魏文人心中,乐府“缘事而发”的初衷被加上了道德含义,似乎“缘事”并不是讲述一个有审美和娱乐价值的故事,自然而然地创作出来,而是心中先有了道德批判,再选取故事表现之。叙事诗作的教化意义仍是第一位的,娱乐性是无关紧要的点缀,这就违背了乐府作品诞生之初的本意。
总之,汉魏文人在拟作乐府诗的过程中,其实并未意识到“乐府传统”的真正魅力所在,而是以“诗经传统”去指导“乐府传统”,因此在这次整合中,并未真正拟作出符合乐府叙事诗审美风貌和创作规律的作品。
四、两晋—初唐,乐府叙事 传统的相对低谷
随着诗歌逐渐和演唱等表演方式分离,走向对立发展,诗歌技巧也越发走向成熟,诗人们这种原本对发自民间的乐府叙事传统逐渐感到陌生,难以揣度把握,故从拟作走向了独立创作。从正始到南朝,玄言、田园、山水次第主导了一代诗风,乐府叙事传统乃至整个叙事诗都进入了相对低谷的状态,只有鲍照《代东武吟》等零星篇章。
初唐时期的叙事之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咏史,其二是自传,都是极为传统的题材。王硅的《咏淮阴侯》、《咏汉高祖》咏汉初风云人物;宋之问的《浣纱篇赠陆上人》咏西施;卢照邻的《咏史四首·其四》分别咏怀汉代四位名人季布、郭泰、郑泰和朱云。其特点都是简略记录历史人物一生行迹,而将大量的篇幅放在描写及议论上;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批判评价,展现作者的史学观点。相对于中盛唐以后的叙事诗作而言,其故事情节并不完整,人物性格亦不算鲜明。另一类是富有自传性质的叙事篇目。如骆宾王的《畴昔篇》、沈佺期的《答魑魅代书寄家人》,篇幅虽长,却整体以抒情议论为主,情节性显弱。
盛唐时由于国力强盛,诗歌艺术走向繁盛,叙事艺术也得到了发展。除了咏史、自传等传统题材外,一部分盛唐名家将目光转移到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关注上来,诞生了一批叙事性较强的诗作,如李白的《秦女休行》、《陌上桑》,高适的《秋胡行》,王维的《桃源行》等。
其中以李白《东海有勇妇》最为传奇化和富于民间特质。诗中记述了一位烈女为夫报仇的故事。而和传统的《秦女休行》不同,这位烈女并非寻常女子,而类似于唐传奇中聂隐娘、红线一类的仙侠,不仅贞烈勇敢,而且武艺高强,“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复仇场面“十步两躩跃,三呼一交兵。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极具画面感和可读性,完全得到了乐府叙事的精髓。但最后的议论却颇为繁琐,占去全诗三分之一篇幅,其中“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等论缺乏新意,和傅玄《秦女休行》“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如出一辙,对全诗艺术性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害。
还有另一类作品值得关注:诗人通过对一位现实人物人生经历的描述,选取典型事件、塑造典型人物,通过对个体悲剧的书写,映射出整个时代的盛衰。如崔颖的《江畔老人愁》。作者以设为问答的形式开篇,叙某位少年邂逅了一位栖身青溪口边的老翁,鬓眉皓白,孤苦衰朽。询问后却发现他的家族是陈梁时候的显贵,因隋代战乱而窜身荆棘,战争结束后避居深山以渔樵为生。全诗情节完整,描写生动,虽然结尾处亦有议论,但并非赤裸裸地作道德评判,而是基于人物命运悲剧而发的沧桑兴亡之感,故较为自然。“人生贵贱各有时”、“说罢不觉令人悲。”通过讲述可看故事、通过塑造可爱可悯的人物,自然彰显作者的道德立场及对时代兴衰的看法。这类作品从真正意义上继承了乐府传统,也对杜甫乃至元白的叙事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
整体而言,从六朝到初唐的数百年间,乐府叙事传统甚至说整个叙事传统都处于低谷状态,直到盛唐才有所改观。但在杜甫之前,盛唐诸家对乐府叙事传统的继承并不够全面。或过多的关注于抒情描写,冲淡了叙事的情节性;或主题先行,议论显得冗长且较为生硬。这与中国诗歌尤其文人诗体系中,叙事诗处于从属地位的整体状态密不可分。在诗人心中,诗歌的主要目的是抒情言志,叙事只是辅助手段。再生动的叙事写人,也是为议论、抒情乃至道德批判服务的。这种情况直到杜甫叙事诗中才得以突破。
正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言:“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11](P411)
五、杜甫对乐府叙事传统的继承
杜诗被誉为“诗史”,在叙事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杜诗中在记录重大史实、承载史学批判、彰显道德伦理之美的方面,继承了《诗经》传统,其情节性、娱乐化的方面,则来自于汉乐府传统。
《兵车行》中大量生动逼肖的细节;《石壕吏》中设为问答的叙事方式;《哀王孙》《丽人行》中鲜明的人物形象;《义鹘行》如传奇小说般跌宕起伏的情节;《朱凤行》《沙苑行》《渼陂行》夸张神奇、浪漫诡谲的情境,无疑都是向乐府叙事传统学习的体现。杜甫还进一步增强了叙事诗歌的情节性、戏剧性、虚构性、传奇性,创作出《兵车行》、《丽人行》、《哀王孙》、《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叙事名篇。这些辉煌创作成就的取得,除了杜甫有意吸取乐府传统的叙事手法外,更重要的是继承了乐府传统中思想性上的特点:将道德伦理价值通过具体的、可看的、具备情节性与传奇性的事件和人物去呈现——即在叙事写人中,自然地展现诗歌的伦理价值。
杜甫叙事诗中固然有很多直接议论之作,但亦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往往是歌行体)是将史实本身以丰富的、富于细节和传奇性的笔调呈现,让伦理判断自然地包含于其中,诗人的议论起到的只是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石壕吏》,通篇不见作者论断,而是以典型的情节来表达对统治者征求无度的批判。杜甫投宿石壕村,恰好在一户没有青壮年的人家,只有老翁老妪儿媳及“乳下孙”。这不是巧合,而是作者有意选取的典型人物,暗中已包含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夜晚恰好有吏捉人,则选取了典型事件,激发矛盾冲突。这家的男主人“老翁”逾墙而走,只留下老妪出门与吏周旋,矛盾得到充分发展。吏不见老翁,果然大怒,矛盾被推向高潮。老妪不慌不忙,恳切呈辞,言三子从军,两子战死,实已为这场战争家破人亡,余生的姑媳亦衣不蔽体。最后老妪提出可以随吏前往军中做饭,应付差役。到了第二天,老妪果然被带走,诗人只能独自与老翁作别。老妪被抓走从军役,这个情节本身就有不合理处,历代论家亦多有论辩。其实这个情节大可不必落实,很可能有虚构的成分,是杜甫故意强化了矛盾,以表现“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危哉!”[12](P530)全篇皆为叙事,无一句抒情,无一句议论,但诗人的立场判断都已在其中。寓自己的美刺褒贬于一个曲折生动的故事,因而不会带来生硬和概念化之感。
夔州时期所作《负薪行》,亦通过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讲述有地方特色的故事,表现作者的伦理判断。“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通过记述中原人看来颇为奇特的当地风俗,呈现了一个辛勤劳作的妇人的形象。其年纪已半百,两鬓华发,却仍没有找到夫家,只好以负薪买盐维持生计。既写其人“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面妆首饰杂啼痕”;也写其事“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贫女形象贫老既可怜,服饰又带有鲜明的当地特色,而其所操之业对于封建时代的女性而言更属罕见,故非常典型,具备相当的可看性。但这种“可看”,又是可悲的。诗中指出了造成“夔州处女”悲剧的原因:“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这一句是全诗关键所在。老女不嫁,不是因为“巫山女粗丑”,而是天下丧乱造成的。《杜臆》:“至云丧乱嫁不售,更堪流涕。盖男子皆阵亡,无娶妻者。”[13](244)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不必多下议论,已呈现在读者眼前。
综上所述,杜甫叙事诗歌中的优秀篇章,既有深刻的道德伦理价值,又有典型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伦理道德判断的实现,不是如魏晋文人拟乐府时生硬地加在结尾处,亦非仅仅给字句附加上褒贬美刺的深意,而是在叙事写人中去呈现。即用典型的事件、鲜明的人物自然而然地体现道德价值,从而让叙事诗的审美性、可读性大大增加,真正实现了“《诗经》传统”与“乐府传统”的结合,诞生了诸多叙事名篇。
六、中唐叙事诗对乐府传统的开拓
杜诗叙事作品对乐府传统的继承与回归,启发了中唐元白等人的叙事诗作。而结合《诗经》、乐府两大传统的尝试,发源于魏晋文人拟乐府,发展于杜甫长篇叙事诗,并在元白手中最终定型。
元白等人高举新乐府运动的大旗,推崇风雅比兴传统,提倡诗歌应关怀民瘼,具备现实主义思想性。在创作实践中,元白的确创作了大量真正以关怀民瘼、讽刺时弊为目的的诗歌,如《秦中吟》、《新乐府》中的叙事篇章。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沿着杜甫开创的路线,回归乐府传统,强调叙事诗的情节性、传奇性、虚构性,因而进一步加强其娱乐性。元稹《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即此中代表。在这一类诗作中,作者虽大力标榜讽喻,但其伦理价值实际上相当薄弱,能广泛流传主要是依靠诗中体现的娱乐价值。因此,无论作者创作初衷如何,就此类作品本身来看,其娱乐性无疑比思想性更加重要,是更纯粹的继承乐府传统之作。
仅以《哀江头》和《长恨歌》的对比为例,两诗同为吟咏杨妃之死,布局及用语上亦有很多相似之处。
杜甫“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即白居易“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14](P659)杜甫“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即白居易“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杜甫“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即白居易“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而杜甫以“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作结,将主题回归到家国大事之上,并未对玄宗与杨妃的爱情悲剧做过多吟咏。白居易之作则描画了明皇回宫后对杨妃的思念,以至于以法术招魂等离奇不经的情节,最后归结于“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发展了杜甫所继承的乐府传统,更进一步强调了叙事诗歌的娱乐价值。
《杜诗详注》引黄生言:“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天宝之乱,实杨氏之祸阶,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陈,又不敢曲讳,如此用笔,浅深极为合宜。”指出杜甫此诗尺度拿捏得当,立意在哀婉与讽刺之间,用语较为隽永,不至过于直白。《哀江头》写杨妃容貌,只用了“明眸皓齿”四字,比《丽人行》简洁含蓄,更比《长恨歌》中的描写得体,自然更符合持君臣纲常的封建文人口味。张戒《岁寒堂诗话》赞曰:“其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15](P457)
而对于《长恨歌》中杨妃的容貌服饰描写,大部分封建文人都认为失之轻佻。如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其叙杨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15](P458)宋魏泰《临隐居诗话》云:“白居易曰:‘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噫!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礼矣。”[16](P324)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先生谓《长恨歌》‘回头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白居易直千古恶诗之祖。”*清·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先生谓《长恨歌》‘回头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白居易直千古恶诗之祖。” 收入《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632页。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白居易宣称《长恨歌》有讽喻时弊的作用,其道德力量实际上是很薄弱的,就史学批判价值而言,远逊于《哀江头》。此诗得以成为“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17](P555)的名篇,知名度不仅超过了《哀江头》,甚至影响海外,主要还是其娱乐价值在起作用。
《长恨歌》相对于《哀江头》而言,更强化其叙事性、情节性、传奇性,呈现出传奇小说般的色彩。正如陈寅恪《〈长恨歌〉笺证》一文中所言:“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18](P4-5)可以说,《哀江头》是正史版的《长恨歌》,而《长恨歌》是小说化的《哀江头》。
总而言之,杜诗立意更正,最后归于家国之恨,更有“诗史”的价值;而白居易情节曲折,极力刻画,细节生动,颇具传奇性和娱乐色彩。《哀江头》归根到底,还是主题先行的。而《长恨歌》中表现的所谓美刺褒贬,其实建立在提供一个美好故事的基础上。这种美刺褒贬不是刻意给予的,而是暗合的。这和汉代乐府的伦理之美一脉相承。可以说,杜甫在歌行体中将汉乐府情节化、传奇性的色彩加以发挥,但对于汉乐府中“娱乐化”的学习还只是浅尝辄止。真正将杜甫的这一尝试推到更远的是白居易。
中唐时期其他叙事歌行中也明显地呈现出传奇化的特质。如韦庄《秦妇吟》*此诗不见于韦庄《浣花集》,《全唐诗》亦不收录,敦煌写本发现时得以重见天日。有天复五年张龟、贞明五年安友盛写本等,异文较多。本文采用张龟写、陈寅恪校笺本。[18](P122)写黄巢起义时攻占长安,主人公“秦妇”被义军掠走,辗转多年最终逃出生天的故事。叙事一波三折,极具可看性。长安城破时,上至王侯公卿下至平民百姓,都遭到了无情的屠杀,而秦妇幸运地“全刀锯”,在军中度过三年不堪回首的日子后,趁乱逃出长安,奔往洛阳,九死一生。好不容易逃到洛阳,却又见四周也已化为赤地,盗匪横行。正值走投无路,她又幸运地遇到了金陵客的指点,继续向南逃亡。经历不可谓不传奇。叶圣陶在给俞平伯的书信中,就曾提到诗中的虚构性:“重读《秦妇吟》,意谓韦庄此作实为小说,未必真有此一妇。东西南北四邻之列举,金天之无语,野老之泣诉,以及兄所感觉‘仿佛只她一个人在那边晃晃悠悠的走着,走着’是皆小说方法。”[19]其实,无论史上是否真有“秦妇”其人,主人公形象之典型,遭遇之离奇曲折,都明显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加工,是战乱之中人民苦难遭遇的一次汇总,呈现出传奇小说的特质。
除了在现实基础上加工外,亦有一部分叙事歌行纯粹出于虚构。如元稹的代表作《连昌宫词》。根据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连昌宫词》中的考证,“《连昌宫词》非作者经过其地之作,而为依题悬拟之作”。[18](P74)考察元稹当年行程,并未真正路过连昌宫。此诗篇首讲述作者路遇年老宫人向自己讲述宫中当年盛况的情节,纯粹出于虚拟。陈寅恪进一步考证,唐明皇与杨贵妃生前也未曾临幸此地。可见《连昌宫词》中:“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等细节描写的都是想象。故陈寅恪认为:“元微之《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18](P65)同样的还有《琵琶行》的故事情节。洪迈《容斋随笔》云:“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娼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舟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尔。”[20](P92)指出其情节有虚构性的一面。
此外如白居易的《古冢狐》写妖狐魅人的故事,元稹《出门行》写少年龙宫盗宝的故事,涉及鬼灵精怪,离奇玄虚,更是充分体现了传奇化、虚构化的特色。这些特点除了中唐时期诗歌受到传奇小说的交互影响之外,也是对汉乐府叙事传统的继承。
从汉乐府到杜甫叙事歌行,直到中唐长篇叙事诗,可以看作是一条完整的链条。诗歌中的情节性、虚构性、传奇性渐渐增加,篇幅增长,细节更为完善,叙事手法更加多样。最终形成《秦妇吟》、《长恨歌》等歌行长篇。它们真正做到了“缘事而发”——即以曲折生动的情节、典型鲜明的人物来承载道德判断,强调故事本身的可看性,而非主题先行。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歌中,诗经传统和乐府传统是相互影响但又互相区别的两个部分。古代文人出于对诗经的尊崇,将诗经传统视为主流,但又感性地意识到了汉乐府的价值,希望将两者建立脉络的联系。从魏晋拟乐府到初盛唐,诸多文人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更多的是以诗经传统去指导乐府传统,以伦理价值去掩盖叙事作品的娱乐特质,因而未能真正掌握乐府叙事传统的妙处,直到杜甫的出现。老杜携集大成而开千流的不世之才,吸取了魏晋人拟乐府的得失,在叙事上向被忽视的乐府叙事传统回归,从而创作出一批写人叙事与伦理价值完美融合的杰作,是诗经传统与乐府传统的一次结合。白居易等中唐诗人则沿着杜甫回归乐府叙事传统回归的进一步探索,创作出《长恨歌》等叙事名篇,无形中进一步强化了叙事诗作的娱乐功用,标志着乐府传统的彻底复兴。
从魏晋文人拟作,到杜甫叙事歌行,再到元白作品,都是乐府叙事传统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并对唐以后的叙事诗产生了深远影响。强调诗歌娱乐功用的乐府传统与强调伦理价值的诗经传统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完整源流。
参考文献:
[1] 国语·周语[Z].召公谏厉王弭谤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汉]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明]徐祯卿.谈艺录[A].学海类编(第58册)[C].上海:上海涵芬楼,民国九年(据道光十一年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本)影印。
[4]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乐府歌辞的娱乐功能和伦理价值[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唐]房玄龄,等.晋书·音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
[10]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Z].[清]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Z].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明]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4][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二)[M].朱金城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5][宋]张戒.岁寒堂诗话[Z].[清]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Z].[清]何文焕.历代诗话[Z].北京:中华书局,2006.
[17][唐]元稹.白氏长庆集序[A].元稹集(五十一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 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9] 俞平伯.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A].文史[C].1982年13辑.
[20][宋]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七)[Z].琵琶行海棠诗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