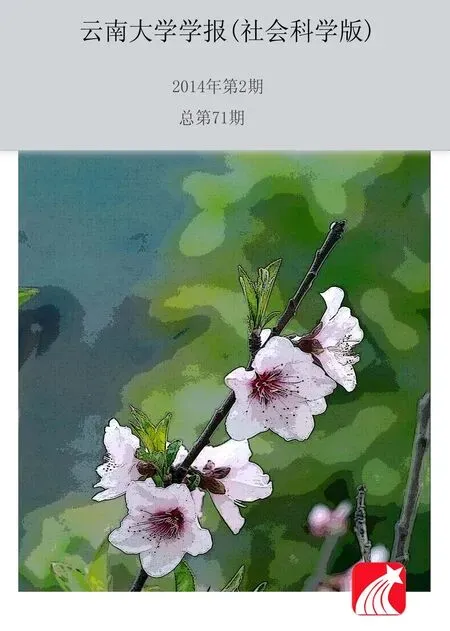《诗经》中的时间意识探析
2014-03-06许迪
许 迪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五经”之一。因此,《诗经》不仅具有重大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大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价值。对《诗经》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除了字词训诂、义理考辨之外,对《诗经》的思想研究亦洋洋大观。但是,从时间意识切入,进而探索《诗经》的思想史内容的另一侧面,至今未见有分量文字。本文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爬罗剔抉,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诗经》中的时间意识做出初步探讨。笔者认为,《诗经》中的时间不仅与自然时序相关,也与生命、历史关切有关,展示了先人世界观中深层的观念。
一、 时间:自然的时序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科学知识的匮乏,先民尚没有形成对时间概念的抽象认识。他们在农耕和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感知物候、天象,将与狩猎、采摘、祭祀、庆典等日常生产与生活密不可分的时间知识载录于册或吟咏成歌。王国维在《殷礼征文》中指出,殷之先王从上甲开始,即以十干的日为名。[1](P1)“以日为名”的殷制“说明时间观念的发现,是人类最初的意识生产”,[2](P61)也“反映了对于自然环境变化的把握,特别是对于时间概念的掌握”。[2](P61)
这种通过对自然时序的把握而呈现的时间意识为周人所承继。在《诗经》中就有诸多诗篇是将对自然中的时间意象的感知吟咏成歌,或为农耕生活提供客观的时间指南,或兴起诗人的某种特殊情感。
《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时间记载,便属于这种素朴的口头流传的农时歌谣,时间在此时被理解为“时令”或者“节令”。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3](P406-415)
《豳风·七月》是迄今所见最早描述季节与农耕生活的文献,诗歌从七月开始,依次描述了每个月的物候、天象、农事活动(如:春分后采桑,八月织布、收割,十一月田猎等)以及人们在农忙、秋收、酒宴、祭祀等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喜乐哀苦。此外,《大雅·韩奕》、《大雅·泂酌》、《周颂·天作》、《周颂·思文》、《周颂·臣工》、《周颂·噫嘻》、《周颂·丰年》、《周颂·载芟》、《周颂·良耜》、《周颂·清庙之什》等篇,也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生活。其中的时令记载反映出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是同日月星辰这些天象变化的周期性相适应的。以素朴的物候、气象来表征的自然时序,是人们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客观时间尺度,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
二、对于时间的感受内容
除了上述对生活实践的实用意义外,《诗经》中对自然时序和季节时令的描写,还有一些是为了寄情于自然之景,正如刘勰所说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1.望夫。如“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卫风·伯兮》),叙写独守空闺的妇人像干旱时盼望雨泽一般急切盼望丈夫归家;“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邶风·雄雉》),写尽妇人对远行丈夫的怀念。
2.悼亡。“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唐风·葛生》)妇女悼念亡夫,愿死后共归一处,然夏之日和冬之夜都如此漫长,身处异处,相见何难。
3.感逝。“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小雅·出车》)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用时间意象反衬从军远戍之凄苦以及安然归来之欣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二月初吉,载离寒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岁聿云莫。……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还?政事愈蹙。……”(《小雅·小明》),叙写小官吏久服远役,抚今惜往,悲悯自己经年不归、思友不得的沉郁心情;又如《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到“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自然时序之发展过程,正暗合了主人公从恋爱、结婚、受虐到被弃的过程。
4.悲秋。在一些寄情于景的比兴中,尤以描写秋天的无尽寂寥之味为最多。*这成为汉赋及其后文学中大量“悲秋”诗之滥觞。“在汉代诗歌中,秋的季节感即已被利用;但在魏晋时代,秋景被更经常地利用来表现悲哀、忧愁的感情。”[4](P30)譬如,魏文帝的《杂诗》如下:“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廻西流,三五正纵横。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文选》卷二九《杂诗上》[5](P67-68)李善注云,这首诗是诗人在抱中的西征之旅中,因思念故乡而作,诗中的秋夜写景“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廻西流,三五正纵横。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引出了“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的浓厚情感以及思归而不能之“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的喟叹。而“这种描写,却并不是为了抒发秋天的无限的寂寥之味,而多半是为了借此而抒发忧愁悲哀的感情”。[4](P29)如《诗经·小雅·四月》之“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郑笺有“凉风用事而百草皆病,兴贪残之政行,而万民困病”。描写的就是一位常年行役在外的大夫,过时而不能归祭,悲愤忧乱之情郁结于心,与寒凉秋风的侵袭互为融洽,加之江汉泉水等景物的促发,发而为伤时伤己之喟叹。又如《诗经·豳风·七月》之“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郑笺有“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5.行乐。《唐风·蟋蟀》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今我不乐,日月其迈……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作者于“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之岁暮感怀,宣扬人生当及时行乐,但又自警不要享乐太多,万不可彻底堕落。正如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人“强作旷达,又不敢过放其怀,恐耽逸乐,致荒本业。故方以日月之舍我而逝不复回者为乐不可缓,又更以职业之当修、勿忘其本业者为志不可荒”。[6](P252)
较之《唐风·蟋蟀》的矜持节制,《唐风·山有枢》所力倡的及时行乐则更加恣纵,“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放浪形骸之态与晋昭公时期的“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的风气迥然相异。
又如,《秦风·车邻》之贵族妇人咏唱享乐生活,“今者不乐,逝者其耄。……今者不乐,逝者其亡。”;《小雅·頍弁》之“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都极言人生几何、及时行乐的思想,“行乐之词,乃以斥(涩)苦之音出之,开后来诗人许多忧生昔日之感。”[7](P309)
以上诸篇都力倡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成为《古诗十九首》和魏晋六朝时期之诗歌中频繁出现的因对人生苦短的喟叹,转而游山水或隐逸以优游之思想的滥觞。
与此相反的则是行乐另一方的痛苦。《邶风·柏舟》抒写诗人在黑暗势力打击下的忧愁和痛苦;《邶风·终风》叙写一个妇女受男子的调戏欺侮而无法抗拒或避开,诗中以天阴、刮风、下雨、打雷比喻男子的欺侮行为。
三、天命观其一:“权命”
《诗经》中的时间意识,既有“自然之天”所包蕴的自然时序和时间意象,为先民的农耕生活提供指南,也有“兴”激起人们的丰富情感。同时,由自然生活的支配者与个体生命掌控者的推演,古人自然把时间与“天命”沟通起来,因而有对“宗教之天”的关切,并产生“天难谌,命靡常”的天命观。
该天命观的构成可分为“天”和“命”两个方面,“天”既是人世王朝之政治权利和政治寿命*陈来认为,“这里所说的‘命’不能仅仅作‘令’来解释,应当是指运命、权命。”[8](P164)的授予者,又是人世历史及命运的主宰者;相对应地,“命”既是指国家的政治权命,也是指个体生命的时运。周人对命运的观念,便是依附于此天命观发展而来,以下两节,将通过对“天”与“命”的交互阐发,从对国之“大我”和人之“小我”两方的关注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人对待历史和现实生命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日渐凸显的理性精神和忧患意识,另一方面是对个体生命深深的焦虑之感。
“敬天、尊上帝、配天命”是周人所秉持的宗教。[9](P126)这里的“天”、“天帝”和“天命”合而为一,如《大雅·烝民》篇中“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胡承珙《毛诗后笺》云“有物指天,有则指人之法天”。[10](P1443)首先,这个“天”是运命、权命的授予者,而君王受命于天,其德行应该配于天命。*《尚书》商书中已有天授赐人世王朝以权命的思想,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尚书·汤誓》)“先王有服,恪谨天命。罔知天之断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尚书·盘庚》)[11](P112、156)然而,这里的“‘天’与‘上帝’都只是一种作为自然与人世的主宰的神格观念,这种纯粹的主宰神格观念,未曾涉及德、民、人等,应属早期。”[8](P167)而在周人的宗教观里,君王要持续保有天命,必须做到“敬”、“仁”、“诚”,此外“天命”是有明确的道德意涵的,如“敬德”、“保民”。陈来据此认为,“商人的世界观是‘自然宗教’的信仰,周代的天命观则已经具有‘伦理宗教’的品格。”[8](P168)如《大雅·维天之命》篇“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周颂·昊天有成命》篇“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周颂·时迈》篇“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都认为昊天祚周以天下,是自有明令和定命,文武为王,是受藉天命而为之。
其次,上帝的威仪不仅表现在它有作为权命授赐者的绝对权力,而且“天”或“天道”是有神格的存在,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方面,天是人事的护佑者,如《小雅·桑扈》篇周王宴会诸侯,席间感叹“君子乐胥,受天之祜”,认为众诸侯的喜乐是受上天的庇佑赐福,而这种庇佑又是可以随时流逝的,如“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另一方面,可惧可畏的天意会通过民情而传达,会因嗔怒于君王的不作为而暴虐降灾于人间,使人民“无敢戏豫”、“无敢驰驱”。如《大雅·板》所载:“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天之方虐,无然谑谑。……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天之牗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诗中之第一个“上帝”是诗人不敢直称厉王,而以上帝来暗喻,此后的“天”及“昊天”均指有神格的“宗教之天”,昊天在上,自有威仪,因而诗人告诫周厉王要敬畏上天的变怒。
最后,时王为了保有权命,就不仅要敬畏上帝的威仪,所谓“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卡西尔认为,人类“把神性看作强于自身的一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不能以巫术的强制手段而只能以祈祷和献祭的牺牲形式获得。”[12](P244)周人也借由祈天、禘神之礼来表达对上天的敬畏,如《大雅·云汉》篇是周宣王当政之时,在“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的状况下,仰天求雨的祷词,诗中有宣王的“事天之敬”,也有“事神之诚”,而祈求降福的神明有很多,包括天神、地神、前代诸侯的神(群公)、前代贤达的神(先正)、死去父母的神以及祖先的神。《大雅·抑》亦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认为神明的到来是不可预测的,人们应该对其敬畏而笃信。更要“明德慎罚”、“用康保民”,使其德行上配于天。在周公写给卫君康叔的告诫书《康诰》中,周公反复强调“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有身,不废在王命”,“敬哉!天威棐忱,民情大可见。”[11](P276)《诗经》中也有“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文王》);“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大雅·皇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等表述。
可见,从时间意识的角度来看,周人对权命的认识,已经有了强烈的现实感和忧患意识,不再像殷人那样盲目地信从上天的授命,认为人世现实的一切安排以及权命都是上天的永恒授予;而是更理性地认为人必须主动地实际参与历史的进程,并从自身的行动中寻找历史变革的前因后果,将“服命”与“敬德”相结合,这是防止帝命迭迁的谨小慎微,也从效果上打破了对天命的必然性和永恒性的执念。*陈来认为,“西周的天命观是‘有常’与‘无常’的统一,‘无常’是指天所命赐给某一王朝的人间统治权不是永恒的,是可以改变的,‘有常’是指天意天命不是喜怒无常,而有确定的伦理性格。”[8](P193)而周人对于命运的观念(第四节将要论述)正是依附此“天命观”发展而来的。
四、天命观之二:“时运”
正是因为理性精神的凸显和忧患意识的兴起,具有永恒意义的上天意旨在周人那里变得不再那么确定,他们转而相信天命是变动不居的;加之《诗经》所记载的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正处于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时期,当世之时,频有幽王、厉王等昏暴之君当政,时有卑劣臣子谄媚辅政,加之贵族贪婪成性,战争频仍,徭役繁重,构怨连祸。人们在此时运之下常喟叹时运不详、天命不佑,常恐罹谤遇祸,产生“天命靡常”的生命观,如:
天命靡常。(《大雅·文王》)
天难忱斯,不易惟王。(《大雅·大明》)
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小雅·十月之交》)
“忱”,三家诗作“谌”,感叹天命靡常,难以相信,为王不易,这些思想与《周书》中之“天命不易”、“天命谌”、“惟命不于常”的思想是一致的。
“天命靡常”的危机感,促发人们或逃避厌世,或祈命永年,凡此种种个体生命体验也是《诗经》中时间意识的重要内容。
1.叹不济之宿命。
《小雅·小弁》篇载:“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假寐永叹,维寐用老。……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诗人失去双亲而无所归依,将“我独于罹”的痛楚归之于天,认为生时不善,因而时运不详。《召南·小星》亦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小官吏为朝廷办事,夙夜征行,作诗自述勤苦,却也把这种辛劳归结为“不敢慢君命”之宿命。在《唐风·鸨羽》篇中,劳动人民常年经受无休止的徭役压迫,居处无定,征役无极,旧乐难复,更不得养其父母,怨愤至极,只能将忧闷归之于天,《史记·屈原列传》云:“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13](P5376)这也是对难逃之宿命的悲痛呼告。
2.厌世。
更甚者是产生以厌世的生活态度来面对“各敬尔仪,天命不又”(《小雅·小宛》)的自伤无奈,《王风·兔爰》就完整地从侧面描写了没落贵族的厌世思想,“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崔述《读风偶识》认为,“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是诗人“逢此百罹”的社会背景,如此构怨连祸使得部分贵族失去了土地和人民,地位突变,家室飘荡,因而产生了不乐其生的厌世思想。
3.祈天永命。
同样是斤斤于个人沉浮,有些人厌不乐生,有些人却祭祀以求长寿,这类祈天永命的思想,多见于为贵族颂德或贵族祭祀祖先的诗篇中,“在这些诗篇中祖先神被理解为可以来到宗庙享用祭献的存在,并赐福和保佑子孙。”[8](P133)如: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乐只君子,万寿无疆。……乐只君子,德音不已。……乐只君子,德音是茂。……乐只君子,遐不黄耇,保艾尔后。(《小雅·南山有台》)
报以介福,万寿攸酢。……永锡尔极,时万时亿。……使君寿考。(《小雅·楚茨》)
寿考万年……曾孙寿考,受天之祜。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小雅·信南山》)
君子万年,福禄宜之。……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君子万年,福禄艾之。……君子万年,福禄绥之。(《小雅·鸳鸯》)
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君子万年,介尔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终。令终有俶,公尸嘉告。……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君子万年,景命有仆。……从以孙子。(《大雅·既醉》)
五、祭享:链接古今时间
除“天命谌,命靡常”的天命观及其引发的对生命和命运的思考而外,《诗经》中还有许多追念先王之德、祭享祖先的篇什,既有托古讽今之辞,也有褒赞先王德行之誉。从时间意识的角度看,海德格尔曾指出历史性是“此在的演历的存在建构”,“此在的存在在时间性中发现其意义。然而时间性也就是历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而且历史性则是此在本身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14](P25)也就是说,历史也是时间性展现自身的一种方式。所以,祭享祖先是通往过去的时间,但指向现世存在,具有链接古今时间的作用,反映了周人对历史的看法。
1.托古讽今。
如《大雅·瞻卬》篇: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
讲述周幽王乱政亡国,诗人慨叹“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上天渺茫难测,令人敬畏,若幽王能不忝其祖(指文王、武王),悔过自新,那么天意还是可以扭转,子孙亦可蒙福。
又如,《大雅·烝民》篇中“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和“缵戎祖考”即是称颂仲山甫能效法先王和祖先之遗典,有礼有节,恪居官次而不懈于其位。再如《大雅·召旻》载:“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于呼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官吏在幽王之政行将覆灭之时,感慨今昔君王各承受天命而为王,然行政之效能差异迥然,刺今王之余不免流露出对先王之政的眷念。《大雅·荡》亦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天降滔德,女兴是力。……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人哀伤厉王无道,天下荡荡,假托周文王批评殷纣的口气,告诫厉王殷之明鉴不远,要引以为戒。
2.赞先王之德行。
《诗经》的《雅》和《颂》中有若干诗篇是对先王之德的追念,通过追溯开国历史赞誉先王,告诫时王要效法先王的德行,效法旧制典章,而文王、武王是最常被提起的先王典范。
《大雅》中有六首诗,叙述周人从始祖后稷创业至建国的历史,具有史诗的性质。如《大明》篇唱道: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保右命尔……(《大雅·大明》)
以天命难测,殷商失国领起,“明明、赫赫”赞文王之德,通过追溯武王伐纣的历史,力证“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又如: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上帝耆之,憎其式阔。……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域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帝谓文王,无然畔援。……帝谓文王,予怀明德。 (《大雅·皇矣》)
此诗通过“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15](P184)追念周王室先祖的“明德”。
追述先王之德是为了给时王树立施行德政的标杆,以告诫时王效法先王之德。如《大雅·下武》篇云:
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徳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於万斯年,不遐有佐。
关于“下武”,毛诗序云:“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即武王能顺德,以成其祖考之功。《大雅·维天之命》也赞美文王之德之纯,於穆不已,曾孙之辈应该对之敬笃之,就是告诫时王要顺从并执行文王的美政善道。
周人除了对先王的德行追慕不已,更是对旧制典章赞赏备至,毕竟为政治国,兴国安邦,不仅要有德行兼备的君王,更要有行之有效的典章规制。如《大雅·抑》篇有:
于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天方艰难,曰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毛诗序认为此诗是卫武公刺周厉王之诗,厉王“颠倒厥德,荒湛于酒”的作风与先王的“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形成强烈反差,卫武公于是苦苦劝解厉王如若执行旧的典章制度,还有济世救国之希望。
又如《周颂·我将》篇载:“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高亨《周颂考释》认为,《我将》篇是“叙写武王在出兵伐殷时,祭祀上帝和文王,祈求他们保佑”,[13](P945)祝祷词中,武王自许要学习效法文王施政的典章,用它来平定天下。
而在众多祭享、追念中,文王、武王是《诗经》中最常被嘉许的先王典范,《文王》中唱道: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文王》)
歌颂文王“受命作周”,“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即是说文王的神明在天上,一升一降之间,无时不在上帝的左右,以使子孙蒙其福泽。又如《周颂·闵予小子》唱道: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于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成王于武王之丧时,告于祖庙,思慕父亲、祖父,警戒自己的诗篇。这里的“皇考”指武王,“皇族”指文王,“皇王”兼指文王、武王。
斯宾塞曾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这种远祖崇拜,他说:“凡超乎寻常的东西,初民都认为是超自然的或神圣的;都认为是其本族中的一个非常人物。这非常人物,也许只是一个被认为该族之创业远祖,也许只是一个有力气有勇气的头目,也许只是一个有名的医病的人,也许只是一个发明了某些新事物的人……也许只是战争得胜的外来氏族或异族之一员。……久而久之,便成一定的崇拜仪式……凡对死者崇拜,不论死者为同族或异族,都可视为广义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可以说是一切宗教的根源。”[16](P204)
祖先崇拜在殷人那里既包括对先公先王的享祀,也包括求帝降命,殷代还因此产生了“先妣皆特祭”、“先王和先妣合祭”以及“甲日祭甲”等特殊祭礼。侯外庐认为“殷人的宗教不论崇祀先公先王,或求帝降命,帝王都是指的祖先神”。[16](P205)
周人因袭商人旧俗,所谓“人惟求旧”、“启以商政”,即周人依然尊崇“先哲王”,但在周人那里,先王和上帝发生了分离,据上文“国之‘时运’”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诗经》中又被称为天、皇天、昊天,这个“天”是“自然之天”,先王是受了皇天之命才得以称王而施化天下,有美行善德才能克配于天。所以,周人的宗教观是在“先王以外另设一个上帝,再由上帝授命给先王,使先王‘克配上帝’。”[16](P207)先王是受了皇天大命的,于是后王必得“享孝先王”,以求先王赐福。于是,便出现了上述所概括的追述先王之德的篇什,或为祈福,或为讽喻以刺后王。
六、结语
“时间”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重要的哲学问题。人类历史在时间中展开,个体生命也必定具有时间的存在测量尺度。
《诗经》中的时间意识,第一是指向日常生活形式。我们看到,由于科学知识的匮乏和农耕生活的需要,“以日为名”成为先民对时间概念的最初表达,这种对自然时序和时间意象的敏感,发展至周人并得以扩展和丰富。
其次,时间意识不仅是生活的时间指南,也具有感知生命和表达情感的内容。望夫、悼亡、感逝、悲秋、行乐等是《诗经》中人们借自然景态、时间意象以抒发感念的重要主题。
第三,周人将个体生命延伸到现实之外,因此,对于时间的关切自然延展至权命、时运,先王等三方面。《诗经》中对权命和时运的关注,代表了周人在“天难谌,命靡常”的天命观影响下而产生的对生命、命运的看法,是周人的生命观的集中体现;而对先王之德的追述、*由于周人“先王与上帝分离”之宗教观打破了殷代宗祖与祖先神合一的一元宗教观,在先王与宗族之外另辟“上帝”,这个“上帝”也被称为“天”或者“昊天”,他不仅是有情感的,而且是帝命的授予者。对此一观点,王国维和郭沫若均有论述和考证,在《观堂集林·释天》中,王国维通过考查卜辞中之“天”和“帝”二字的写法,加之确定卜辞中只有祀祖祀帝的记载而无祀天的记载,以及先王被通称祖帝的事实,断定商人的宗教是帝祖一致,并统一到祖先崇拜里。祭享,是通往过去的时间,但又指向现世存在,反映了周人的历史观。以上两种时间意识,都是古代社会宗教观念的必然反映。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殷礼征文·殷人以日为名之所由来[A].王国维遗书·第九册[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2]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蒋见元,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日]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M].邵毅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魏宏灿.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6]方玉润.诗经原始[M].李先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7]蒋见元,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9]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0][清]胡承珙.毛诗后笺[M].郭全芝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9.
[11] 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12]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3] 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1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5][宋]朱熹集注.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6]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