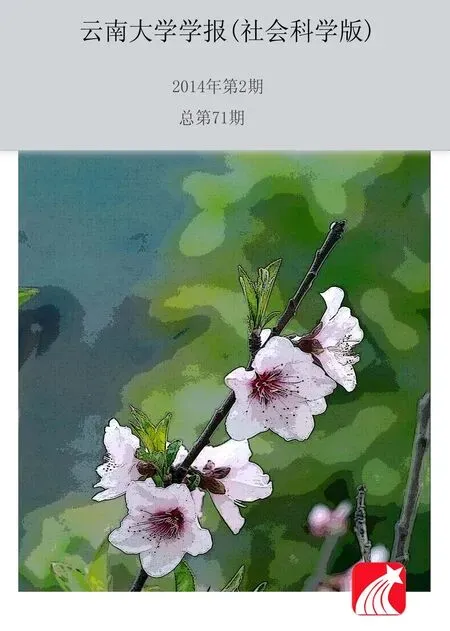《韩诗外传》中的神灵与祭祀
2014-03-06孟庆楠
孟庆楠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神灵或鬼神的观念起源甚早。而随着先秦时期的宗教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演进,人们对神灵或鬼神的理解与态度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这些思想积淀构成了汉初学者重新梳理、塑造社会思想文化的基本素材。而《韩诗外传》作为罕有的流传至今的汉初文献,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神灵与主宰
如果暂且搁置神灵观念形成过程中所出现或涉及到的各种复杂因素,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认为,神灵意味着一种超越于人事之外却能够主宰人事的人格化的行为主体。宗教即是围绕神灵观念展开的,体现着人们对于神灵的态度和行为。借用宗教人类学的观点,宗教就是“对被认为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或抚慰”,也就是“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1](P52)这种对宗教的“勉强”定义也明确了神灵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人们通过祭祀等宗教活动取悦、安抚神灵,以求取神灵赐予福禄、避免神灵施降灾祸。这样一种神灵观念在殷商时期的文献材料中已有着充分的表现。
而随着宗教及社会思想的发展,原始宗教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蜕变:道德原则被引入到了神人关系之中。神灵不再是喜怒无常、肆意妄为的,其对人事的干预以人的道德状况为依据,为善者报之以福,为恶者报之以祸。人们为了获享福报、避免灾祸而修德向善。神灵的干预构成了对人的道德行为的一种功利化的诱导。当然,这也使得人们有机会在赏善罚恶的原则下通过个人的德行努力来改变自己所收获的福祸报偿。这通常被看作是原始宗教理性化的标志。在集中反映西周社会思想的《诗经》、《尚书》等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天命惟德、以德配天之类的表述。[2](P49-51)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一赏善罚恶的原则往往会与人们的善恶之行所遭遇的实际报偿相背离。在社会危机加剧的背景下,这种原则与现实的背离就会招致人们对神灵信仰、亦即对传统神人关系的质疑乃至批判。《诗经》中出现的各种怨天之辞就是传统的神人关系遭受冲击的一种体现。徐复观先生曾据此断言,有关人格神的命令在西周后期已经消亡。[3](P25)当然,我们并不一定完全接受徐先生的论断。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有关神灵及其赏善罚恶之行的论说。如《墨子·明鬼下》中就对鬼神观念有着详细的阐述。墨子首先明确“鬼神之有,岂可疑哉”,进而又指出“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4](P222、227)在儒家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如“大德者必受命”的表述。[5](P1339-1340)这很显然是传统的神灵观念及神人关系的延续。而《韩诗外传》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
《韩诗外传》卷三载:
传曰: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害于粢盛,延及君地,以忧执政,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仁,斋戒不修,使民不时,天加以灾,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孔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矣。”弟子曰:“何谓?”孔子曰:“昔桀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王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过而改之,是不过也。”宋人闻之,乃夙兴夜寐,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岁,年丰政平。乡使宋人不闻孔子之言,则年谷未丰,而国家未宁。诗曰:“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6](P99-100)
此事见于《左传·庄公十一年》,又见于《说苑·君道》篇。但对于其中所记孔子之语,《左传》认为是臧文仲之言,《说苑》则认为是“君子”之语。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姑且忽略这一差异,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宋人在回应鲁人吊慰时所表达的对水灾的认识。在宋人看来,水灾发生的缘由在于宋君不仁、斋戒不修以及使民不时,上天因宋君的这些失德行为而加灾于宋国。另卷十载:
晋平公之时,藏宝之台烧,士大夫闻,皆趋车驰马救火,三日三夜乃胜之。公子晏子独束帛而贺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国之重宝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趋车走马而救之,子独束帛而贺,何也?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公子晏子曰:“何敢无说?臣闻之:王者藏于天下,诸侯藏于百姓,商贾藏于箧匮。今百姓之于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虚而赋敛无已,收太半而藏之台,是以天火之。且臣闻之:昔者桀残贼海内,赋敛无度,万民甚苦,是故汤诛之,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灾于藏台,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变悟,亦恐君之为邻国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请藏于百姓之间。”诗曰:“稼穑维宝,代食维好。”[6](P360-362)
晋国的藏宝台在火灾中被焚毁。据晋平公及公子晏子所言,这场大火是“天火之”,也即是上天使之燃。《左传》载:“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孔颖达疏曰,天火是“自然而起”,[7](P674)一般也即是由雷电所致。晏子意图借由这场天灾劝谏平公。他指出,这场火灾是“皇天降灾于藏台”。降灾的原因在于平公赋敛无度,以致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而无论是上条材料中的“天加以灾”,还是这里所谓的“皇天降灾”,都通过加、降的动作表达了明显的人格主宰的意义,同时施为的主动性也彰显了上天对人事的控制。实际上,《韩诗外传》在另外的材料中更明确地使用了“天罚”一词:
晋灵公之时,宋人杀昭公。赵宣子请师于灵公而救之。灵公曰:“非晋国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顺也。今杀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灾焉。晋为盟主而不救,天罚惧及矣。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而况国君乎!”于是灵公乃与师而从之。宋人闻之,俨然感说,而晋国日昌,何则?以其诛逆存顺。诗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赵宣子之谓也。[6](P23)
此事见于《国语·晋语五》。宋人弑其君主,赵宣子为此请晋灵公发兵救宋国之难,以履行晋国作为盟主的责任。宣子在劝说晋灵公时指出,宋人弑其君主,晋国作为盟主而不救难,皆有悖德行。这样的失德行径将遭受天灾、天罚。当然,在这一劝谏的情境中,天罚还未发生,赵宣子以天罚劝诫君主正是依凭于人们对天罚观念的共识,亦即是对赏善罚恶的神灵的信仰。
与上述主宰之天的观念密切相关的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即妖祥。《韩诗外传》对妖祥有着明确的界说。当然,这一界说是围绕着一个具体事例展开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材料:
有殷之时,谷生汤之廷,三日而大拱。汤问伊尹曰:“何物也?”对曰:“谷树也。”汤问:“何为而生于此?”伊尹曰:“谷之出泽,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汤曰:“奈何?”伊尹曰:“臣闻:妖者,祸之先;祥者,福之先。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臻。”汤乃斋戒静处,夙兴夜寐,吊死问疾,赦过赈穷,七日而谷亡,妖孽不见,国家昌。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6](P80-81)
谷生于庭之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不过,《外传》及《吕氏春秋》以为在汤时;其他一些文献,或说在中宗太戊时,或说在高宗武丁时。所记细节虽有差别,但主旨相同。《外传》在这里借伊尹之言,定义了妖祥的概念。妖是遭遇灾祸的先兆,祥则是获享福祉的先兆。妖祥本身并没有构成对人事的直接影响,其对于人事的意义体现为对可能到来的福祸的预示。同时伊尹还指出,妖祥虽然是祸福之先,但并不必然导致祸福的发生,其间的变数取决于人的行为。若见妖而能为善,则祸不至;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臻。这实际上是以妖祥所预示的福祸来激励人们为善去恶。具体到这条材料所记述的事例,商汤、伊尹所面对的妖象表现为谷生于庭、三日大拱。谷物本生于野泽,今生于天子之庭,即被认为是一种妖孽之物。此妖象预兆将有祸患。为了避免遭受灾祸,君主应该勤勉修德。商汤听从了伊尹的劝谏,终免于祸。妖祥对于人的德行的影响模式与上天的赏善罚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二者都是以功利的结果、报偿来引导、激励人的道德行为。实际上,《韩诗外传》对妖祥与天的关联有着明确的表述:
昔者周文王之时,莅国八年,夏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有司皆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者,君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国郊,群臣皆恐,请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见妖,是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罚我也。今又专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请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遂谨其礼节祑皮革,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有功。遂与群臣行此,无几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之后四十三年,凡莅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践妖也。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6](P81-83)
文王卧病而遭遇地震。不过,从“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的表述来看,这并不是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性地震。因此,在文王看来,这只是妖,只是一种对真正的灾祸的预兆。而这条材料的特别意义在于,将这种地动的妖象置于天或天道的掌控之下,即是文王所谓“天道之见妖”,认为是上天令妖象显现。因此,妖象也就很自然地承载了上天的赏善罚恶之义,妖象的显现被认为是“罚有罪也”。这一表述凸显了天与妖祥观念之间的联系。妖祥之象体现并遵循着上天的意志和原则。妖祥所预兆的福祸就是上天对人事所施加的赏罚,而妖祥无非是提醒并促使人们对上天的赏罚提前做出反应。这种提前量的设定,实际上为人的德行努力预留了更大的空间。
二、天道与天人感应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到,《韩诗外传》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的神灵信仰。人格化的神灵以其超越性的威能干预、控制着人世的生产和生活。在多元化的神灵形象之中,天或天神对人事发挥着最为重要的影响。而神灵对人事的影响则遵循着赏善罚恶的原则,这条原则规定了神人关系的基本形态。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传统的神人关系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矛盾。我们知道,将神灵对人事的干预规定为赏善罚恶,意味着神灵不再是喜怒无常、肆意妄为的。人们为神灵选择了一种固定的道德取向,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神灵的约束。人们一方面要借重于神灵的权威来维系赏善罚恶的准则;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在用赏善罚恶之则来约束神灵的绝对权能和自由意志。这一矛盾在传统的神人关系的架构中很难获得彻底地解决。
试图维系传统的神人关系的春秋战国时人,只能在这一矛盾关系中调整神灵的权力意志与善恶报偿的道德原则之间的平衡点。而一种比较明显的倾向,即是在强化善恶报偿原则的同时淡化神灵的权力、意志。其表现之一就是以“天道”来表述原有的“天命”观。《国语》载“天道赏善而罚淫”、[8](P68)“天道无亲,唯德是受”。[8](P396)“天道”较之于“天命”之称,淡化了施命的拟人化内涵,更侧重于表达客观规则之义。如果将这一倾向发挥到极致,就会彻底倒向对神灵的否定而单纯地保留善恶报偿的原则。《文言》传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表述[9](P31)就已接近这一极端。《文言》此说强调了为善而获福、为恶而遭殃的逻辑,但却回避了对福祸施予者的论说,同时又不再以赏罚解释福祸的报偿,这也就摆脱了“赏罚”之辞所包含的人格主宰之义。
很显然,《韩诗外传》也表现出了对削弱神灵主宰的思想意图。当然,《外传》并没有像《文言》那样彻底舍弃上天对善恶报偿的影响,而仍然试图在天人关系中来安顿和维系善恶的报偿。
首先,《外传》使用了“天道”这样一种客观化的称谓。而在上文提及的有关妖祥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天道之见妖,是以罚有罪也”的说法。由此来看,在《外传》中,天道的观念仍然具有一种赏罚的意味。此外,《外传》还对天道观念做出了一种创造性的解读,即将天对人的影响解释为某种自然的感应。卷三载:
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人事备乎下,天道应乎上。故天不变经,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其寒暑,万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国用。故国有所安,地有所主,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橶,以通四方之物,使泽人足乎水,山人足乎鱼,余衍之财有所流。故丰膏不独乐,硗确不独苦,虽遭凶年饥岁,禹汤之水旱,而民无冻饿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转尸,夫是之谓乐。诗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6](P102-103)
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条材料中的一句话:“人事备乎下,天道应乎上。”这即是明确了天与人之间的关联:人事或人的行为会引起上天的反应。同时,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看到天或天道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运作、山川寒暑的变化、群生的长育,都从属于天或天道的范畴。这些事物或现象是天或天道的具体表现。当然,这条材料侧重于论说上天对治世、亦即对有德之行的反应。民役、婚配、孝养的适时,父子、夫妻间的相成相保,以至整个社会群体的和平安宁,是一种符合道德要求的良好的人事状态,这种人事的完备就会引发出各种有利于人的天道变化。而在《外传》的另一条材料中,我们还会看到上天对失德行为的反应:
传曰:国无道则飘风厉疾,暴雨折木,阴阳错氛,夏寒冬温,春热秋荣,日月无光,星辰错行,民多疾病,国多不祥,群生不寿,而五谷不登。当成周之时,阴阳调,寒暑平,群生遂,万物宁,故曰:其风治,其乐连,其驱马舒,其民依依,其行迟迟,其意好好,诗曰:“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6](P74)
这条材料将有道、无道之行所引发的不同的天道变化进行了对比。若治世有道,则天时有序,天气有常,生物丰美;相反,若乱世失道,则上天应之以失序无常的天象,扰乱群生。就善恶报偿的逻辑而言,上述天人关系与西周以来的天命惟德之义并无差异。但是,原本借由命令、赏罚等文辞所呈现的人格化的主宰却没有出现在以上两条材料中。这样一种自然化的天人感应论无疑更进一步地削弱了天所具有的人格主宰之义。
三、阴阳之化
由此来看,《韩诗外传》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神灵的存在及其对善恶之事所施加的赏罚。但同时,《外传》也在以某些方式削弱着神灵的权能及意志。《外传》除了用“天道”取代“天命”之称,更发明了天人感应之说,从而回避了带有人格意味的“赏罚”之辞,转而将上天对人事的影响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在这种天人感应中,人的善恶之行仍然会获得相应的福祸报偿。有德之行会引发对人事有利的天象,失德则会招致各种天灾。但是,天不再是主动的施为者,而只是对人事做出回应。天的人格主宰之义被进一步削弱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的神人关系架构下,对人格化主宰的削弱、消解是带有危险性的。过度淡化乃至消解神灵的权力和意志,将使得善恶报偿的原则丧失神灵所提供的超越性的依据。当上天不再具有主宰的权威,那么,善恶报偿及其赖以实现的天人感应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针对这一问题,《韩诗外传》对传统的神人关系做出了独具特色的阐论。《外传》的解决方案借用了荀子对天地、自然的某些说法:
“星坠木鸣,国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6](P37-38)
这一引自荀子的说法,试图将那些原本归之于鬼神之力的现象解释为阴阳变化的结果。这种解释消解了可敬可畏的主宰者,而更重要的是,它为没有主宰的世界提供了一种运行的新依据,即阴阳之化。《外传》借用了这种阴阳的元素,但同时也表现出了与荀子思想的一个关键差异:在荀子“天人相分”的理论背景下,天地、阴阳的变化法则并不涉及人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与人的道德表现无关;而《外传》则将人的道德因素纳入到了阴阳消息的变化之中:
传曰: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地奉养,而生物丰美矣。不知为政者,使情厌性,使阴乘阳,使末逆本,使人诡天气,鞠而不信,郁而不宜,如是,则灾害生,怪异起,群生皆伤,而年谷不熟,是以其动伤德,其静无救,故缓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为治。诗曰:“废为残贼,莫知其尤。”[6](P262)
这条材料将人的性、情区别对举。在这种对举中,情主要指源自于身体官能的情欲,而情欲的放纵则会造成对人的性命的伤害,也即是卷一中所说的“触情纵欲,反施化,是以年寿亟夭而性不长也”。[6](P20-21)如果从德礼的角度来看,情欲对性命的伤害,也即意味着背德、违礼的恶行。[10](P434-435)因此,“循性情之宜”实际上包含着某种道德的、合礼的因素。而《外传》在这里特别为性、情赋予了阴阳的属性。情为阴、为末,性为阳、为本。性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天地万物“阴阳之化”的一个环节。而“性情之宜”所体现的道德因素,也借由这种阴阳的法则,与整个自然世界建立起了内在的关联。如果为政者能够使性情各得其宜,言行合于德礼,阴阳有序,则天地万物和谐顺畅;但如果为政者放纵情欲,失德悖礼,使情厌性,则会由此触动天气的变化,引生灾害、怪异之事。《外传》通过这种阴阳之说,解释了道德因素对人事吉凶的影响。这实际上是维系、强化了善恶报偿的原则,但传统的神灵对人事的干预已经被转化成了一种以阴阳之化为本质的天人感应论。这一理论设计的意义在于:《外传》借助于这种感应论的表述,削弱乃至消解了人格主宰之天,善恶的报偿也因此失去了原本由主宰者所提供的超越性依据;但阴阳之说则为天人感应及善恶的报偿赋予了新的依据。
从引述旧说的情况来看,《韩诗外传》以阴阳解释天人关系的思路可以看作是对荀子思想的发挥。但如果从思想的内在关联来说,《外传》的这种阴阳之说或许更直接地来源于《易》学的思想传统。《庄子·天下》篇在评述儒家六艺之学时曾言: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11](P1067)
在这里,阴阳说被看作是战国时期《易》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朱伯崑先生在《易学哲学史》中也曾指出,今本《易传》作为先秦《易》学的代表著作,“在《易》学哲学史上的主要贡献,是以‘阴阳’为范畴,说明卦象、爻象以及事物的根本性质,并且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为其《易》学哲学的基本原理。”[12](P831)据朱先生的考察,《易经》和春秋时人解《易》并未提出阴阳的范畴。直到战国时期,以《易传》为代表的《易》学著述才开始以阴阳来解读《周易》。不过,《彖》、《象》以及《文言》中的阴阳说尚未充分展开,以阴阳解《易》多集中出现在《系辞》的论述中。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9](P303)
《系辞》以阴阳来解释奇偶二画,并通过奇偶二画所组成的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卦象体系,将阴阳的对立与变易贯彻为整个世界的本质与法则。日月的推移、寒暑的交替,及至行事的屈伸、处境的穷通、君子小人的相互消长,从本质上说都是阴阳对立、变通的结果。而《韩诗外传》以阴阳观念来解释、贯通自然和人事的思路,与《易》学中阴阳之说的主旨是一致的。不过,《外传》的阴阳说舍弃了《易》学中涉及卦爻象的因素,对某些自然、社会现象的解读也更为细腻。如果再考虑到韩婴对《易》学的熟悉与重视,那么《外传》对《易》学思想的接纳与应用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四、祭祀的意义
《韩诗外传》在削弱神灵的人格主宰之义的同时,解决了善恶报偿的依据问题。但总的来说,《外传》对于神灵还是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外传》一方面在天道赏罚、祭神祀神等问题的讨论中承认人格化的神灵,但另一方面却以天人感应之说削弱了人格主宰的存在。
这一矛盾或许会招致后人对《韩诗外传》的误解,认为其杂引先秦各家,因而缺乏思想的统一性。针对这样的质疑,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对待人格神的矛盾态度并非《外传》所独有。即便在以无神论著称的思想者那里,其对神灵的否定也并不彻底。墨家在对“执无鬼者”的批评中已指出,“执无鬼者”一方面否定鬼神,另一面又强调“必学祭祀”,这其间是存在矛盾的。我们知道,祭祀的本质意义即在于讨好鬼神以求福禳灾。学祭祀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一种人格化的主宰者的承认。所以,墨者批评说,这是“犹无客而学客礼”、“犹无鱼而为鱼罟”。[4](P457)荀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在以阴阳之说消解主宰之天的同时,也还是要对祭祀做出解释和安顿。荀子因此提出了“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的观点。此说区分了君子与百姓的不同:君子并不认为祭祀会取得实际的效果,祭祀的作用和意义仅在于“文之也”;但是,百姓仍然相信神灵的存在,并相信能够通过祭祀讨好神灵。[10](P316)由此看来,无论思想者在论说中如何削弱、消解神灵的人格主宰之义,祭祀仍然是不容否定的,人格神的观念也因此获得保留。在中国古代的大传统中,祭祀可以说是人格神的一个最稳固的载体和庇护所。
由于祭祀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意义,我们最后还是要来看一下《韩诗外传》对祭祀的解释。实际上,《外传》对待人格神的矛盾态度也很清晰地体现在有关祭祀的讨论中。一方面,《外传》很明确地承认祭祀讨好神灵的效用。在卷八“梁山崩晋君召大夫伯宗”一条中,山崩河壅的危机在辇者的建议下是通过祭祀获得解决的,“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6](P288-28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以祭祀讨好神灵就可以获得福报而避免灾祸。在另外一处有关鬼神的讨论中,《外传》就强调了德行的意义:
人事伦,则顺于鬼神;顺于鬼神,则降福孔皆。诗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6](P94)
按照这一论说所呈现的逻辑,人事合于伦理道德是“顺于鬼神”、“降福孔皆”的必要前提。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论说之后所引诗句并没有提及人伦,而只是在强调享神祀神对于获享福报的作用。鉴于《外传》“祠焉河斯流矣”所表现的态度,我们可以知道,诗句享祀以得福禄的表述也是符合《外传》的思想意图的。因此,我们并不应简单地认为,这里引《诗》只是断章而取降福之意。“人事伦”和“以享以祀”的并举或许暗示着,人的德行与祭祀活动同为鬼神降福的必要条件。
《韩诗外传》在承认祭祀的这种功利性作用的同时,也对此表现出了某种怀疑。其引荀子之言:
传曰:雩而雨者,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6](P37)
祭祀作为获取报偿的功利性手段的意义既遭到怀疑,《外传》也就很自然地对祭祀的“文”的方面、亦即其伦理教化的意义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卷三载:
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6](P93)
此言丧祭之礼有助于维系臣下对君主、子女对父母的情感。关于祭祀与人情的联系,荀子已明确指出,“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10](P376)荀子认为,君子将祭祀看作是一种“文”。此所谓“文”即是对情感的文饰。[13](P547)这样一种对情感的引导与文饰具有鲜明的教化意义。《外传》载: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6](P34)
《礼记·祭义》也提到“祀乎明堂”的问题,其言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郑玄注:“祀乎明堂,宗祀文王。”[5](P1339-1340)由此来看,明堂之祀所文饰的是祭祀者对于先祖的思慕、亲爱之情。而这种情感的表达是具有示范、表率意义的。诸侯、民众有鉴于此,则会有孝亲之行。又如:
禘祭不敬,山川失时,则民无畏矣。[6](P179)
姑且搁置礼学上关于禘祭问题的复杂争论,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禘祭表现着天子或诸侯对于神灵的虔敬之心。民众以此为表率,则会有对君上的敬畏与遵从。由此看来,在《韩诗外传》的理解中,祭祀的一项重要意义就是引导、彰显礼乐伦常所需要的某些情感,进而起到表率、教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英]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2]余敦康.宗教·哲学·伦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5]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徐元浩.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9]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2]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13]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