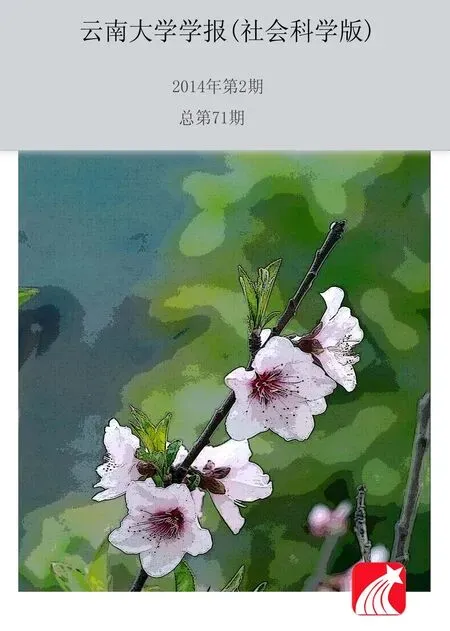从规范理论到诊断实践*
2014-03-06汉斯斯卢加
汉斯·斯卢加 文, 李 华 译
[1.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 CA94720-2390;2.西安邮电大学 西安 710061]
一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马克思(Karl Marx)于1848年在他的《共产党宣言》中如此写道。他接下去还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于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5页。这样富有战斗力的、先知式的话语,表明马克思是他的时代的杰出诊断者。他的这些话迫使我们面对他在诊断方面的洞见的界限。一方面,就现代境况的谱系而言,这一点是成立的。它的流动化事实上是否可以只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状况出发得到澄清呢?为什么同样的流动化日后也在共产主义的俄国和中国表现出来了?另一方面,就马克思的预后能力(prognostische Fähigkeiten)而言,这一点是成立的。现代生活的种种喧嚣,是否实际上迫使人们“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呢?抑或这些喧嚣并没有同时再扬起新的尘埃——这尘埃不断地引起一些新的社会错觉?
马克思作为对现代生活超乎寻常的流变性的观察者,其目光的敏锐性毫不因此而减弱。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本值得一读的、与此相应地以“一切坚固者烟消云散”(这是马克思的那句“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英译)为名的书中,伯曼(Marshall Berman)采用了这个主题。他的书是从现代思想家与企业家的象征性人物,即歌德的浮士德出发的,而浮士德是必朽的,他会这样叙说瞬间(Augenblick):“你如此之美,还是停留片刻吧!”他的书描写了波德莱尔的发现,即现代生活向豪斯曼的(Hausmannschen)巴黎的转变,描写了圣彼得堡如何发展为革命的现代首府(这反映在从普希金[Pushkin]到果戈理[Gogol]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一直到别雷[Andre Biely]和曼德尔斯塔姆[Ossip Mandelstam]的文学作品中),最后还描写了他自己童年时代所在的城市纽约,以及通过城市规划专家摩西(Robert Moses)之手完成的、布鲁克林的变迁与局部毁坏。伯曼意味深长地谈到了这样一个世界,它有“物理科学方面的种种伟大发现,这些发现改变了宇宙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它有工业化生产,这种工业化将科学认识转化成了技术,创造了新的人类生活条件,并摧毁了旧的,它加快了生活的整体速度,也带来了新的群体权利和阶级斗争;它有人口统计上的巨大变革,成百万的人被从本土的住所驱逐出去,他们在全世界都被逼入新的生活条件中去;它有快速而戏剧性的城市发展,有动态性的大众交流系统,这个系统将各种不同的人和团体相互联系与交缠在一起;它有愈益增长而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被按照官僚的方式组织和掌管,不断追求扩展其权力,有人们和诸民族形成的大众运动,来挑动和引诱他们政治与经济上的统治者,以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容易,唾手可得;最后,所有这些人和机构都担负着自身,有个波涛汹涌般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1](P16)
在这些表述中,伯曼效法马克思,同样表明自己是我们当前时代的敏锐诊断者。如今,在这个世界经济危机的寒风凉意阵阵的2011年,他的表述或许能获得比它们在三十年前发表时更强烈的回响。只是伯曼的书在今天要是出新版的话,就必须补充一章,论述亚洲城市(或许是论述香港、上海或北京),论述它们的爆炸性成长对于21世纪人类的生活状况,对于人类的希望与失望,意味着什么。
在某个方面,伯曼当然超越了马克思的表述。在马克思强调现代生活的转变力的地方,伯曼还暗示了,在我们生活的喧嚣之中,等级的、固定的,乃至神圣的事物如何保存下来了,种种传统、习俗和信仰形式如何得以延续,旧的种种结构和机构如何坚守下来——被改建,被改变了功能,有时甚至徒有其表,但总还是可以看到,还是在那儿的。还有,时代的潮流如何在新的产物和形式中的某个地方,积淀下来——变得更宏大,更毫无顾忌,更坚固,更有力,或者至少比一切先前曾在那里的事物都更有力。伯曼阐明,如果我们的世界表明自己只是赫拉克利特之流(Heraklitischer Fluxus),或者在辩证的意义上有条件的前行运动,那它就更容易为人所理解了。
我回想起所有这些,是为了强调,要一瞥便知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整体特征,有多么困难——尤其当我们试图在哲学上思索我们的处境时,更是如此。因为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我们外在的生活状况,而是我们的整个属人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生存状态。如今,面对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人们搬出到现在为止在我们的哲学运思中一直占上风的那种论调——这种论调着重于一些非时间性的规范,一些普遍原理和一些抽象而必然的真理。人们可以这样说,在我们这个电光闪烁的世界,哲学还总是立起一些石制的法板(Gesetzestafeln)来。但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变迁必定会使我们真正重视这一点,即必须要建立另一种哲学运思方式了——这种哲学运思致力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些具体条件,致力于我们所面临的那些实际任务,这些任务无法通过简单诉诸于抽象规范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密切认知我们当前的状况来寻求解决。简而言之,代替惯常的那种规范性理论思考,在从事道德与政治方面的思考时,我们需要的是某种诊断实践。
二
这样一种诊断已经被实践了;问题仅仅在于,要学会并完善它。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指出,康德(Immanuel Kant)是第一位以自己的当下为哲学活动对象的哲学家——确切地说是在他的获奖论文“何谓启蒙?”当中。因此康德堪称哲学中的诊断思想的祖宗了。但凭借其主要的批判著作,他同时又是当今在规范理论领域的几乎所有著作的源头。换句话说,康德站在规范理论和诊断实践最初分道扬镳的那个点上。
黑格尔和马克思更广泛地运用了诊断方法,而马克思是第一个系统地运用它的人。他对于哲学的持久意义就在于此——不管他的种种提纲和理论中其他的内容是否还合乎时宜,都是如此。尼采在诊断方法上达到了真正的突破,因此我在下文中也就更多地讨论他。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影响之下,自那时起,还出现了这套方法论的其他一些实践者。人们想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不是作为《存在与时间》的作者(那本书还是超出时间和历史之外,以非时间的方式在进行思索),而是作为1936年《形而上学导论》和战后时期各种著作的作者——或者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规范理论要求的后期哈贝马斯除外。在政治方面的哲学运思中,施米特(Carl Schmitt)和阿伦特(Hannah Arendt)大概也可以被称作诊断家。最后,福柯的全部著作都占据重要地位。此外,诊断方法还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之外(而且这一点对我自己而言是非常关键的),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治疗”(therapeutischen)思想中,产生了丰富的成果。
三
现在我们先回想一下,我们在规范理论方面的哲学运思是如何对待种种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而那里成问题的又是什么。这样一种哲学运思,一般都将道德-政治问题理解为困境,亦即理解为这样的一些处境:在那里,我们要在两个或者更多个特定的选项之间作出抉择。*抉择可能在于“做A”还是“不做A”,比如“帮助某人”还是“不帮助某人”;它可能在于“做A”还是“做A的反面”,比如“讲真话”还是“撒谎”;它也可能在于一系列的选项,即采取哪种方法来促进出自某个群体的某个人的幸福。无论如何,其基本的假设是,在本质上,处境是透明的(transparent),因此也较少需要人们思索,而且我们在行动上的那些可能的选项都是清楚而可预见的。那么,道德的问题总是在于,我们该如何面对必须作出的抉择。换句话说,这是个决断问题。
我们可以借助康德那里的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来阐明这种处境。一个疯子闯进房子里,高举屠刀,想知道X是否在那里。现在,道德上的困境在于,我该不该讲真话。众所周知,康德借助绝对律令解决了这个决断问题。*在规范理论文献中,对这类模式化情形的描述是很常见的。这些描述应该将抽象的思考具体化,并表明抽象规范可被运用到实际的道德问题上去。但问题在于,对问题情形的这样一种简单化描述是否并未实际地扭曲道德的疑难。罗尔斯(John Rawls),这位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以同样的方式分析了一些道德-政治问题,就像他在1951年的“伦理学决断程序论纲”(Outline of a Decision Procedure for Ethics)一文中所表明的那样。他在那里自问道,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决断方法(至少在某些情形下是如此),以便确定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在相互竞争的一些兴趣之间作出裁决”。他还得出结论说,“行动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作为理论问题,本质上是如何表述一些合理原则的问题”。[2](P1,13)虽然罗尔斯在他后期的那些有名的著作中没有明确重复这些主题,他在根本上还是将道德和政治问题理解为决断问题,这种问题应该通过诉诸于“合理地”被认知的一些原则,而得到解决。
然而,决断问题实际上无法仅仅通过求助于一些原则而得到解决。它们有时是任意解决的,有时是通过具体的即兴决断而解决的,只有在不多的情形下,才通过诉诸于规则或原则来解决。当问题在于面临任一抉择,而这抉择的确切后果对我们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时,或者当我们出于公正方面的考虑,给予每一种可能的抉择以同样的机会时,我们就任意进行决断——比如通过扔硬币或者抽签。比如当我们想确定在一场游戏中谁先出招,或者在一场比赛中谁占据什么位置时,我们就任意进行决断。这样一来,就有了即兴的决断,这些决断在各各不同的程度上,完全可以以一些合理的考虑和盘算为基础,但在它们那里,问题在于具体的人在同样具体的处境下作出的权威决断。我们熟悉这种决断程序,比如在政治体系中,统治者们并不完全靠跟在法律后面亦步亦趋,就可以进行统治。最后,原则方面的决断作为第三种因素加入进来,这些决断的基础是普遍规则的运用;我们和其他出自我们的现代官僚管理体系的人一样,都信赖这些决断。*我在这里要强调,之所以决断能以各各不同的方式被作出,是因为规范理论家们一再暗示我们,在每一种决断后面,都必定有一种普遍的原则在起作用。这种暗示首先在现象学上是错误的,其次在逻辑上也是不连贯的。我们如果假定,在每一个决断那里,都有这样一种原则存在,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为了进行决断,首先必须已经决定运用这一原则了;而这样一来,这种决断就必须以一种原则为基础;但因为我必须决心运用后一原则,事情就陷入某种无穷倒退了。实际上我们有时是在完全无须面临抉择的情形下行动的,而我们在面临某种抉择的时候,则往往并未诉诸于一种决断原则,还有,我们在采用某个原则的时候,则往往并不就此作出决断。
当涉及道德问题时,对于我们——亦即对于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而言很清楚的是,我们不应通过任意决断或即时决断来解决它们。*然而曾经有过一些时代,在那时恰恰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重要的道德和政治问题,显得是正确的(比如借助某个征兆、某个梦或星体)。一些现代的道德哲学家坚信,道德问题只能通过即时决断来解决(而我相信,他们借此便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无论如何,统领性的观点都是,道德困境要通过诉诸于某些普遍的道德规则、原则、诫令或律令来解决,当然那不是随便什么规则、原则等等,而是强制性的或合理的原则,亦即一些能声称具有道德有效性的原则。
但我们要在哪里找到这些原则,我们又该如何证明它们的效用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离我们想将它们运用于其上的那些具体处境特别近。为了找到普遍原则,我们必须对个别情况的具体实在(Realität)进行抽象。道德家必须自己求索出一些超越的、先验的或合理的根据来。先知摩西离开他的民众,进入西奈的旷野,登上和烈山(Berg Horeb),在那里,耶和华本人在火与云的笼罩之下,向他口授其诫令。在柏拉图《理想国》的洞喻中,哲学家为了直接看到善的理念,而离开人的世界。罗尔斯在描述一项思想试验时又借用了《旧约》和柏拉图的隐喻话语,在那项试验中,一群人要磋商如何确定政治正义的原则。“这个处境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没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阶级或他的身份,更不知道随着智力和体力等自然天赋一道而来的他的命运。我甚至还假定,参与者还不知道他们关于善的观念,以及他们的特殊心理倾向。正义的原理是在一张无知之幕后面被确定下来的。这就保证了,没人因为自然或社会状况方面的种种偶然性而具有特权地位,或者受到亏待。因为所有人都处在同样的情境下,没人能设想出基于他的特殊境遇而赋予他特权的原理来,那么正义的诸原理就是一场公正的协定或协商的结果。”[3](S.29)
这样一来,总体而言,对道德问题的本性,就有一种统领性的哲学理解了。这种理解包含三个论点:
1. 道德问题以困境的形式出现:它们是个决断问题。
2. 道德上的决断问题要借助于普遍有效的一些规则来解决。
3. 当人们将这些规则运用到某个道德困境中时,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在X处境下作出Y,在此,X是透明的,而Y是确定的。
在下文中,我会将人们所想到的那些规则(Regeln)作为规范(Normen),将包含了上述三个论点的那些理论作为“规范”理论来谈论。这样,我就在比通常情况下更精确的意义上使用“规范”和“规范的”这两个术语,并以此避免“规范的”与“实践的”这二者之间常见的混淆。
四
然而,并非所有道德-政治的问题都是困境,如我们的规范论者们似乎要假定的那样。一种处境是否透明,这通常取决于它的复杂性。而只有当处境透明时,它才给我们呈现出抉择方面各种明确的可能性。并非所有处境都是像康德关于闯入的疯子的故事那么清楚地被界定了的。人们可以设想,比如说,堕胎或安乐死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首先涉及所有可能的种类的事实(生物学的,医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然后还涉及个人、潜在的个人、家庭、监护人和整个社会的相互重叠的权利与义务。我们的道德哲学家们绝非对这些复杂化的因素毫不知情,但对它们进行抽象化思考的那种做法,妨碍了他们完全看清人类生活的错综复杂和人类心灵的迷误。我们不仅是从哲学著作,也从个人经验和对话,从报章小说、剧本电影、历史与生平叙述中得知这些事的。它们向我们表明,我们的道德家的那些抽象规范其实对我们是多么无益。或者更准确地说,道德规范时而是一种帮助,时而徒增迷误,时而表明自身是无关的,甚至时而令我们更不幸。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有关最好治理形式的问题。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的《历史》中讲述了波斯王子们是如何讨论这个问题,又是如何得到这样的结论的:君主制是最好的治理形式。柏拉图(Platon)后来论证说,哲学王的统治是最好的,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则深信,共和政制是最好的治理形式——或者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话来说,是“最不坏的”。当然,所有这些论断都基于两个假定,这两个假定都是成问题的,亦即:首先,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通盘掌握各种可能的治理形式;其次,我们可以将它们安置到一个线性的级别序列中去。
亚里士多德即使可以说建立起了这样一个等级表,同样也在他的《政治学》第四卷中质疑了它。他在那里叙述道,政治理论必定不能只讨论理想事物,而是也要讨论现实可行的事物。他澄清道,“同一个知识领域的任务首先是考虑,何为最好的政制,一种政制必须具备哪些特征;其次是考虑,哪种政制适合哪种社会秩序”。他继续说道:“最好的政制的实现在很多国家大概是不可能的;而最好的立法者和真正的国务活动家由此也必须不仅关注绝对最好的事物,也关注就目前条件而言最好的事物。”(1288b)*本文使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版本为Aristoteles,Politik,Berlin:Akademie Verlag,1991.再次强调这一点之后,他补充说:“或许王国制度再次广泛流行开来的根据是,过去没有足够多的有素质的人——特别是因为国家都很小……。后来有了一定数量的具有同样高素质的人,不愿深居简出,而是出来寻求造就一个(政治)共同体,因而建成一个共和国……。因为此后国家都变得更大了,现在除民主制之外的任何其他种类的政制或许都很难立足了。”(1268b)*根据边码回查中译本,无此文句,边码或有误。——中译者注
我们将这些话先放一边,暂时把注意力转移到当今的中国。过去在这个世界上,还从未有过一个国家有超过十亿的人口。因此关于如何组织这样一个系统的问题,是无法通过联系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治理形式而得到解决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否要以民主的方式得到有效的治理?而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一般而言又能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政治系统的复杂之处是:巨大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她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她不均匀发展的状况,她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这些都使得人们很难确定,哪种治理形式一般而言对于中国是可行的。以许多小型的民主制或所谓的“西方的民主制”的标尺来衡量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可以运作的某种治理形式,换了个地方或许就不行了。澄清这一点,便是这里直接涉及到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中国人民本身——的任务。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无论如何是不能从外部加以规定的,而“民主制是最好的治理形式”这句老生常谈,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还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规范理论的如下这种直觉性的假定必定是错的:在诸种治理形式之间如何抉择,这听凭我们的做法,这种抉择唯独取决于我们独一的决断,因此就在于我们的责任心了。虽然在每种处境下,人们基本上可以为每一种(认识到的)治理形式找到依据并付诸行动,但它是否以及如何被实现,它会有多稳固和多有效,这些问题都取决于和纯粹道德意愿完全不同的一些因素。就像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的,一种治理形式的可实现性特别受治理对象的复杂性所牵制。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这种复杂性首先取决于隶属于一种治理体系之下的人口数。这种想法当然太过简单了;其他一些使局面复杂化的因素也加入进来,包括对政治的流行理解。因此下面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全是错误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规定了我们的治理形式——虽然这一点就像它所显明的那样,只是诸多决定性因素中的一种。
五
当我们的道德和历史情境并非简单透明,而是复杂且不规则的时候,那么无论如何,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对这情境本身的关注。我们正好必须做出和道德家在登和烈山时所做的事情相反,和哲学家试图离开人们居住的洞穴时所做的事情相反,或者和正义原则的协商者们退回到无知之幕后面时所做的事情相反的事情。我们必须立于最稳固的基础上,仔细检视事物,并且要在白日之光下来看待事物,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身处何方。我们必须直面我们处境的复杂之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如何在现成被给定的情境下行动。换句话说,我们首先必须致力于对我们的情境的一种诊断性研究。
为了更准确地澄清这里所谈的事情,我将批判性地把所需要的道德-政治诊断与医学诊断编列到一起。其他一些比较也是可能的,比如与精神分析的做法比较,后期维特根斯坦带有诊疗的意图,很关注这种做法,又比如与技术上的诊断比较。但我在这里之所以致力于医学上的模式,首先是因为哲学上的诊断者们常常援引这种模式,其次是因为对我而言,这种比较更能使人看到一种哲学诊断的总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看看医学诊断的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拿一种哲学诊断与它们相比较:
1. 辨识症状(现象学);
2. 规定发展进程(发生学);
3. 鉴定进一步的发展(预后);
4. 确定一份疗程报告(规条)。
医学和哲学诊断的起点必定总是对症状的观察。我强调“症候”(Symptome)这个词,是为了澄清诊断的现象学(die diagnostische Phänomenologie)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有着鲜明的区别,后者必得成为本质直观,而不是症候观察。症候首先是指事物、身体或处境的一些直接可见的属性。但它也应该指更深层的、并非直接可见的那些条件(比如身体的某种疾病,一种文化上的衰落,或者一场政治危机)所表现出来的迹象。然而诊断者通常感兴趣的,并不是对其研究对象的一种完备而系统的概观。(他可能会像维特根斯坦一样,驳斥这样一种整体把握的可能性。)他毋宁特别致力于某类“病理”(Pathologien)。*我是从霍耐特(Axel Honneth)那里借用 “病理学”这个术语的,然而我知道,它往往带着医学上的那些联想,很容易被人误解。并非所有最初作为一种病理而出现的事物,都自然会在诊断当中如此这般地表明自身。而且并非所有最初作为某种病理之症候的事物,都会表明自身是症候,或者特别而言,是这种病理的症候。症候现象学作为诊断的起点,必须在进一步诊断的过程中作好进行修正的准备。医学上的诊断者对这一点理解得很好;相反地,我们哲学上的诊断者则经常表明自己在现象学的观察当中更为教条,而他们的诊断结论因此就更频繁地出现缺陷。
医学诊断不仅致力于规定一种可能的疾病的当下症候,也试图查明这些症候的发生,借此也查明症候背后的疾病的发生。医生问,病人已经有多长时间感到不适了,这些症候是如何开始的,它们是如何发展的,如此等等。发生学在哲学诊断中同样必要而不可或缺。一些症候,以及尚待规定的病理,它们的动态形象,是规定它们可能的、进一步的过程,由此也为证明每一种实际的适应症候服务的一个前提条件。
诚然,在医学中,预后往往也是不确定的。它必定取决于一些权衡,而这些权衡并不能被周详地考虑到。慢慢生成的一次前列腺疼痛,经过持续的观察,或许可以暂时不管。
有些病的治疗有时可以或者必须被延迟到靠后的某个日子。一些疾病,比如常规性感冒,随着时间而出现,又自己消失了。一种疾病也许能以不同的方式被治疗,而这些方式各有利弊。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权衡各种选项。也可能发生的是,一种疾病不可治疗,医学还没有治疗它的手段。或许诊断来得太慢,癌症就常常如此。一些治疗只能起减缓的作用,其他一些则至少应当可以延缓疾病的进程。治疗必须总是针对病人,针对疾病的特殊病症。虽然有一些治疗规则,但那始终只是一些暂时性规则。
我就医学诊断所说的话,可以直接转用到哲学诊断上去。在这里,现象学、发生学与预后学也必须齐头并进。在这里,在实际化解被诊断的病理时,也存在着诸种选项、程度和限制;在这里,也存在着一些多少会生效、多少有些强烈与麻烦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多少都有些好的结果预期。存在着一些道德和政治问题,我们对它们束手无策。(我们说它们“悲惨”。)有些时候,我们只能稍稍减缓一下道德或政治上的不利状况,或者阻拦一下道德或政治上的某种衰落。尽管某些处境有规则地一再发生,我们对被诊断病理的治疗总是取决于个别情况。
而由此我们也看到,道德和政治领域内的一种诊断实践,如何尖锐地与规范性的理论空想及其实践上的后果区别开来了。对于规范性的理论空想而言,每一种处境和每一种治疗方式,从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被分配了某种正面的或负面的价值。当我们尝试解决一种道德或政治上的困境时,每种可能的行动,一开始就被标记为善的或恶的,对的或错的,被要求的或被禁止的了。与此相反,诊断性的视角则要求,一定要依据多种维度来判断我们的道德或政治行动。由此,在哲学诊断结束时产生的各各不同的行动方式,就与规范理论的“是-非”判断根本区分开来了。
六
我想尝试联系尼采来仔细阐明这些思考。要穿透尼采多层面的著作而找到问题的出路,绝非易事。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从不中断的诊断性姿态:他致力于道德-政治病理之症候,他详尽的谱系学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预后与规条。在尼采的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尽管在本质上他在专心研究古代,却已经有了对他自己时代的诊断。他将他的时代诊断为一种乐观理性主义的危机与崩溃之点,据他说,这种理性主义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那里就已发端。最后,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作为解毒剂,得到了宣扬。这种诊断在最合乎时宜的那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以对威廉时代德国文化的一种批判性研究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那时居于统领地位的历史主义相反,这里说道:“只在当历史为生命效劳的情况下,我们才愿意为它效劳。”[4](S.97)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的预后诊断是,在此后一些年中,一切最高价值都开始衰落。他在日记中写道:“虚无主义就在门口”,他自问道:“一切客人中最令人害怕的这一位,是从哪里来到我们这儿的?”[5](S.1)在同一批笔记中,他鉴别了这种虚无主义的多种症候:无政府,嗜酒,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对平等的幻想和民族主义。这些症候当然只能通过对其发生过程的一种准确的研究而来理解。因而尼采感到自己必须以一种“道德的谱系”为他那个时代的现象学寻找基础,这种谱系概述了从人类出现之前的阶段到当下社会为止,我们的道德与政治情感的演变,但特别关注两个时刻:古代世界让步于一种新的犹太-基督教道德的瞬间(Augenblick),以及这种犹太-基督教道德体系开始毁坏的时候。就像在马克思那里一样,诊断方面的这种导向,一直是受历史事态的流动化激发的。尼采写道:“瓦解,因而还有不确定性,都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没有任何事物稳稳站立且坚信自身:人们只为明天而活,因为后天不知道会怎样。我们的道路上尽是平滑而危险的东西,此外,承载我们的冰面也变得极薄了:我们全都感受到了冰雪融化的可怕气息——我们还在走的地方,很快就没有任何人能走了。”[5](S. 57)
尼采接着还给我们举出了一个最清晰的例子:一位以医学方式为指向的诊断思想家。他在他的日记里注意到:“病态是如何通过数百年来的共同生活而愈发沉疴难起的:现代的德性,现代的智慧,我们的科学,都是病态的形式。”[5](S. 50)“传承下来的不是疾病(Krankheit),而是病态(Krankhaftigkeit):反抗有害的移民等等时的乏力,打了折扣的反抗力[……]。”[5](S. 47)“但人们当作治疗变质之手段的东西,只是针对变质的某些特定后果的镇痛剂;‘被治疗者’只是某种衰退类型。”[5](S. 42)而在专著《道德的谱系》中谈到禁欲的神父时他说:“他与患者的不适(Unlust)作斗争,而不是与其原因,不是与真正的疾病作斗争——这必定是我们根本反对神父的用药方式之处。”[6](S. 3-17)对于这样一种使用医学概念的方式的意义(以及总问题),尼采通过使用危机概念摆明了。尼采在他的“基督教道德批判”——如他所说,这种批判引出了我们文化中的一种“关键性张力”的问题——中,发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场危机”。
这套关于危机的术语源于医学,准确地说是源于晚期古代盖伦(Galen)那里的医学文献。*关于这个主题,可比较Reinhart Koselleck,Kritik und Krise. Eine Studie zur Pathologie der bürgerlichen Wel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 1973.“危机”在那里指的是一场疾病的进程中某个特殊的时刻(比如体温曲线的高点),而这个时刻则被鉴别为关键点,在这个关键点上,或者疾病消退,或者病人奔向死亡。依据盖伦的理论,疾病进程只有在这个瞬间才是不稳定的,因而医学上的治疗也只有在这个瞬间才有成功的希望。因此诊断者就必须全力以赴,以求精准地确定这个时刻。
从18世纪开始,危机概念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政治事件上,最后来到了尼采这里。在这个迁移过程中,它虽然失去了早先与之相连的一些联想,却保留了其他一些本质性联想。这样,道德和政治危机总是被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的高点和极点,也被理解为被激化了的不稳定性瞬间。危机总是在呼唤实际的干涉,而干涉自然就预设了对所处情境的一种准确诊断。从尼采到施米特的“民主危机”以及阿伦特的“权威危机”,在进行哲学-政治诊断的过程中,这个概念一再被纳入进来,但也以可疑的方式一再导致将当前的情境规定为例外与极端情形,这种情形则在同样的程度上为一些极端对策辩护。[7]
当然并非所有的哲学诊断者都以这些医学概念来表达。福柯虽然那么依赖尼采,虽然自己对医学、精神分析学和心理疗法很感兴趣,却宁愿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医学模式。作为替代,他谈论一种有关权力和权力关系的语言,这种语言在他有关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诊断性研究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七
有两件事情,有利于呈现出一种哲学诊断在方法方面的苗头所存在的问题。因为这种诊断要求实践者致力于经验性事实,而这一点即便对于专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而言也有困难,所以首先要面临的危险是,哲学上的诊断者从哲学运思滑入纯粹的经验性事物中去。只要诊断还是哲学的,就会产生第二个问题,即它能否符合经验科学的标准。我们都知道联系马克思与尼采,也联系海德格尔、阿伦特与福柯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也必须自问,在一种哲学诊断里,应该有什么样的专门哲学。在这里,我可以——同样是与医学诊断相比较——提出两点作为回答:其一是每一类哲学诊断的概念构成方式,其二是它不可避免的、进行怀疑的潜力。
在医学实践中,虽然对症候的观察很关键,但单就其自身来看却是不够的。因为不能只是记下症候,还必须对它们进行描述、分类和解释。因此,医学诊断的进步就取决于创造一套适当的词汇,取决于概念工具的发展——而不仅仅取决于医学器械的可操作性。因此,弗雷克(Ludwik Fleck)在他的《科学事实的产生与发展》一书(1935)中就描述了,人们将梅毒定为由病原体产生的疾病这一做法,是如何彻底地改变了对性病的整个诊断的。这正好与哲学诊断中的处境相符合。从马克思和尼采到福柯,哲学诊断一再涉及的问题是,创造出一套新的词汇,一些新的概念,这样就可以用它们来描述症候和背后的缺陷状况,它们的发生与预后,以及可能的治疗方法了。与传统的那种以先验的方式进行的哲学思考不同,对创造一套新概念的这种关注,有意地以对当前的理解为目标。
我想联系已经提到的关于作为治理形式的民主制的问题来阐明这一点。我们的政治思想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基本概念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借来的,这一点在“政治”(Politik)和“君主制”(Monarchie)、“共和制”(Republik)和“权威”(Autorität)这些术语上,也在“政制”(Verfassung)、“法权”(Recht)和“自由”(Freiheit)这些概念上表现出来了。但随着时代的推进,所有这些术语和概念都经历了一种深刻的意义变迁。以我们所说的“民主制”为例:通过多数人选举出来的代理人——他们作为党派的成员而行动,并长期占据政治职位——所建立起来的某种代表制统治,对于古典时代雅典的希腊人而言,在所有方面都是民主制的反面。他们将代理、多数人选举、政党和占据职位,都视作极其明显地反民主的一些治理环节。那么人们可以争辩说,雅典的体系内在地就是不稳定的,而且肯定与我们当今的种种需求不符合;那我们为何总是动用同样的希腊术语呢?此外,我们自己的所谓“民主”治理形式自身又是处在不断的进展中的,因为它越来越多地被转化成政治中的一个专家体系(Expertensystem)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的一个现代变体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经济人员、律师、学院中人和将军成了我们的王。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里,为了掌握剧烈变动着的政治现实,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全新的概念与概念体系?因此像施米特、阿伦特和福柯这样的思想家在逃脱了旧的概念结构之后,也试图重新理解政治,不管是理解成敌友局面、交往互动,还是理解成诸种权力关系构成的一种战略体系。事情如何发生,这是首先要预见到的。
八
医学诊断的模式使得我们要留意所有诊断程序的认知边界(Erkenntnisgrenzen)。对症候的观察与描述,对某种疾病的辨识以及对它的发生的重建,对它可能的进一步发展的预见,以及最后,对这种或那种治疗方法的选择——在所有个案中,诊断过程都伴随着不确定性。诊断用的资料几乎总是不齐备的、不确定的和多义的。解释都是不确定的,在此用到的概念工具都是不足的。因此,医学上的误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事情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作为病人,当然不喜欢听到这一点。哲学诊断中的情境是类似的。在这里,不确定性还更大一些。首先,诊断的客体不是某个人的身体,而是一种超复杂(hyper-komplexe)的社会结构。*我把这些结构称为超复杂的:它们将对自身的理解作为一个结构要素包含进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一架机器构成的系统就不是超复杂的,甚至当它更复杂的时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一个政治体系则总是在独特的意义上是超复杂的,因为属于这个体系的人总有他们对该体系的某种(或对或错的)理解。通常,人也是超复杂的结构。当然,在医学诊断中,这种超复杂性常常被排除在外了,而它在心理疗法的诊断中,当然具有更大的意义。其次,诊断者与其诊断对象并非外在地相互对立的(就像医生对病人那样),而是他处在他要以诊断的方式加以理解的情境之中。但通过这种处境,哲学诊断者所掌握的资料就被限制在某个框架之内,具有了主观的色彩,也有可能被歪曲了。换句话说,哲学诊断者是在原则上无法见到全貌的条件下工作的——就像维特根斯坦曾针对我们的语法和生活形式申明的那样。因此,哲学诊断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的是不确定的了。
到了这里,我终于接近了哲学诊断真正的薄弱环节——正如它迄今一直被实行的那样。我们的诊断者们在原则上完全认识到了他们的程序在知识上的界限,而一旦涉及他们自己的洞见,他们总是忽视这一认识。因此,哲学诊断常常表明自己极不具有反思性。这一做法始自马克思,尽管他了解人的思想的社会条件,但他的“科学的”理论理解(Theorieverständnis)使得他相信自己的诊断绝对可靠:资本主义必定崩溃;共产革命必定到来。在这一点上,尼采表明自己更为敏感。当他诊断他的时代的颓败时,他了然于胸的一点是,他自己也属于这个颓败的系统,也必须将自己理解为颓败的产物。作为虚无主义的诊断者,他认识到,他自己也是虚无主义者。“从根本上而言,我迄今为止都是虚无主义者,不久前我才向自己承认这一点:我作为虚无主义者无拘无束前行的那股力量,在这个基本事实上欺骗了我。”[5](S.24)但他也没有看清楚,这种处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诊断的可靠性。“我所叙述的”,他在他的日记上写道,“是接下来两百年的历史。我描述了到来的事情,不再另行到来的事情: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5](S. 2)阿伦特在她去世后发表的《政治学导论》中澄清了,我们的政治思想永远无法完全基于有根据的判断之上,“前判断”(Vorurteile)在本质上成了每一种政治理解的组成部分。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我们所有的政治思想的党派性。看得越远,就越好。但当阿伦特,比如在《行动的生活》*即《人的境况》。“行动的生活”是阿伦特自己最初定的名称,后来在编辑的建议之下,更名为“人的境况”。——译者注中,说起现代社会瓦解一切的力量时,她是否也将这些洞见运用到她自己身上了呢?同样地,最后还有福柯,他很好地认识了真理与权力之间网状的相互关联,但却从不自问,他对规驯社会或生物政治学之诞生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陷到这个网络中了。
甚至连我们的那些最果断的诊断思想家,似乎也对他们的实践的可能性与界限,缺少一种足够认真的怀疑态度。与此相反,医学上的诊断从很早开始就一直与怀疑的做法为友了。就像我们今天知道的,哲学的怀疑实际上起源于古希腊医学。而直到今天,医学和怀疑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只需一读本恩(Gottfried Benn)的著作和诗,便可明白。
当哲学诊断最初且首先以诊断的目光审视自身,当它要求诊断者对自己及其在诊断过程中的地位进行诊断时,那么反对规范思想家的人便同样必须服从诊断。对于从如下这一点出发的诊断者而言,规范思想就像他自己的诊断工作一样,也成了诊断性研究的对象:所有思想都出自具体的处境,而且必须从这种处境出发而被理解。诊断者必须问:一般而言,摩西那里的先知,异化了的哲学家,这些形态的情形如何?——这样的哲学家以疏远的姿态就正义的原则进行商谈。还可以更尖锐一点地说:当我们如今的世界已经像马克思和伯曼所描述的那样了(一个不断变革,消解一切固定事物的世界),规范思想家的力量究竟何在?
我必须只限于给出一个简短因而不足的答案。当然,人的全部历史都在运动中,而过去一切时代,都存在着彻底变革。但现代生活的特殊状况与前现代的区别开来了。首先,历史变迁的速度和规模都与以往不同。更为本质的,当然是我们对这种变迁的认识发生了迅速而又极端的变迁。前现代总是可以寻求从非时间性事物出发来理解时间性。我们传统的哲学与宗教思想所具有的那种规范论(Normativismus),就可以在诊断的意义上如此这般来理解。新规范论的情形则有所不同,它是从康德以后,部分地也是从康德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并在最近几十年里在哲学界居于统治地位。人们如何能在我们变动不居的当前时代条件下来理解这样一种思想呢?问题的关键,是否在于向某个看起来稳固的过去时代,乡愁满腹地回望?还是在于忽视我们当前时代的喧嚣特征?或许甚至在于一种有意识而做作的无知(Unwissenheit)?还是种种规范性主张把自己理解成了用来平衡某种动摇性的力量,这种动摇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人所共知的?或者情况是如此这般:那些超复杂的结构和越来越快的变迁过程,只有通过调节与规范化,才能为我们所掌控?那么这就将意味着,规范性事物的力量,是以某种非规范性事物为根据的:以人类幸存下去的实际的必要性和条件为根据。最后,这还将意味着,只有一种全力以赴的诊断实践,才能显明规范性思想的意义,可以说,我们只能将非时间性解释成时间性事物的功能。
九
规范理论和诊断实践表明了一些哲学思考的方式,这些方式之间的冲突在最近的一百年里获得其意义。或许我们今天实际上可以用这些概念来标明整个哲学领域。这将替代“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的那种令人不满的划分,这种划分以一种地理概念来与某种(越来越不确定的)方法概念相对峙。*关于“分析”概念,参见Hans Sluga:“What has history to do with me? Wittgenstein and analytic philosophy”,发表于:Inquiry,42(1988),99-121.
正如已表明的那样,这两种思考方式作为方法程序,被与个别思想者的作品联系起来了。问题在于,这两种思考方式是否无法以体系性的方式被相互关联起来?与此相反,一种逻辑连贯的诊断实践一定会破坏规范思想的无时间性要求。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一再发现,规范理论家们被推向诊断性思索,而诊断者也滑入规范性思考方式。前一种情形清晰地见于罗尔斯的发展,他在其晚期思想中,尝试在对现代人的一种——尽管以图式化的方式发展出来的——诊断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正义原则。从诊断的立场出发就肯定不会对如下这一点感到惊讶:在那些以纯粹规范性方式进行的思索那里,一再闪现出某种诊断实践的因素。实际上,人们可以将任何一个规范性文本化入它那隐而不彰的诊断性背景之中去。因此,人们不仅可以将柏拉图的道德-政治对话解读成对一种纯粹规范性思想的前后一贯的表达,也可以解读为对他那个时代的雅典文化所作的某种诊断的结果。但这些对话同时也表明了,趋向规范思想的追求有多强烈,甚至全力以赴的诊断者也无法避免这一追求。因此,我们总是发现,诊断实践很容易就投入到抽象的-规范性的理论活动的怀抱了。比如,阿伦特从她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诊断,很快就陷入到对于作为自由交往行动的政治事物的一种纯粹抽象的规范性刻画中了。这些过渡如何发生,人们如何能避免它们,这是进一步的诊断性研究的任务。*我得感谢这份文本的一些较早版本的听众们,他们提出了一些极为有益的批评意见。
参考文献:
[1] 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M].New York:Penguin Books Inc.,1982.
[2] J. Rawls.Outline of a Decision Procedure for Ethics[A].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S. Free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3]John Rawls.Eine Theorie der Gerechtigkeit[M].Übers.v.H. Vetter.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9.
[4]Friedrich Nietzsche.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in:Nietzsche, Unzeitgemäβe Bemerkungen,Stuttgart:Alfred Kröner Verlag,1964.
[5]Friedrich Nietzsche.Der Wille zur Macht[M].Stuttgart:Alfred Kröner Verlag,1964.
[6]Friedrich Nietzsche.Zur Genealogie der Moral[M].Stuttgart:Alfred Kröner Verlag,1964.
[7]Hans Sluga.Heidegger’s Cris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