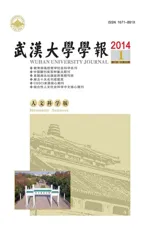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
——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
2014-03-04徐红
徐 红
方壮猷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研究领域涉及古代北方民族史、宋辽金元史、经济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方面。近30余年来,方氏的研究已受到学术界的充分关注,一些成果被重新整理出版*如方壮猷先生在武大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讲义《中国史学概要》被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参见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但其在元史领域的研究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以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20世纪30年代方壮猷所编《元史讲义》为中心,向读者表明,方壮猷先生在元史研究领域的研究因涉及关键学术问题,比其他领域的贡献显得更加重要。
一、 方壮猷《元史讲义》的特点
方壮猷曾于1936年至1950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席,主讲宋辽金元史、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等课程,《元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系他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讲授元史的讲录。该讲义现藏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目前在各类目录及检索系统中均未见此《讲义》的条目,亦未有介绍的文字面世。仔细阅读《讲义》可知,它是重新认识方氏的治史方法及学术视野,了解其在元史研究领域重要成就的难得资料。
《讲义》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照录姚从吾所译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柯劳斯《蒙古史发凡》一文*姚氏译文载《辅仁学志》第1卷第2期,1929年,第1~110页。。第二部分是蒙古人所建察合台汗国、奇卜察克汗国(即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即伊利汗国)世系表,以及柯劭忞《新元史》载各汗国统治者及诸王列传,《新元史》和屠寄《蒙兀儿史记》之帖木儿列传。第三部分是一些蒙元史研究资料及参考书的相关内容摘录,涉及日文参考书目、洪钧《元史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元史》、邵远平《元史类编》、霍渥特(今译作霍渥士)《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等。从选编内容看,方氏认同柯劳斯的观点及姚从吾对柯文的补注,但由于柯文提及中文材料太少,故方氏又将中文相关材料选编于后,以使《讲义》在元史研究材料的介绍方面更趋完善。
以今日之标准,历史教材的写作模式应是以呈现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心,提供给学生关于某断代历史或某一个专题的基本史实描述、历史解释及价值评判,它大致以时间线索为序,易于使读者理解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和演进,这就要求作为教材使用的文本应是尽可能完整、全面的。但是《讲义》并不如此,其重点并非是叙述元朝从建立到发展、繁荣,再到衰落、灭亡的动态历史进程,而是方氏以个人的学识,通过对本土及域外材料的了解和会通,对蒙元历史事实做出独特的观察和解释,进而有选择性地将最能反映蒙元史研究最新成就及蒙元史研究的重要材料选编在一起,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富启发性和指导性的文本。所以《讲义》的编纂,既是满足教学的需要,使学生对材料及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成就有一定的了解,也是方氏基于自身研究旨趣和学术积累的思考。为此,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罗列世界蒙元史研究的各种主要材料,包括中文、日文、西文等多种语言的资料,另一方面,他之所以选择《蒙古史发凡》作为《讲义》的主要内容之一,亦是由于此文关注的四个议题,即“蒙古人之种族”、“蒙古人之近讨远征与国家组织”、“蒙古时代东西间的交通”以及蒙古人与宗教的关系,皆为当时中外学人所热切关注者。
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对于蒙古人与宗教的关系重视不够,较有份量的仅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陈垣发表《元也里可温考》,后经多次修改增订,于1934年改为《元也里可温教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垣史学论著选》将其选入。一文,作者广泛征引《元史》、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汉文资料,论述了也里可温的词源、也里可温教士的东来、也里可温教的影响等问题,其引用材料丰富,见解精辟,迄今为止仍为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显然,方壮猷对国内学术界在此方面的薄弱状况有较为清晰的了解,为此在《讲义》中选编了较多相关内容,如通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出使蒙古的行动,论述蒙古人对宗教的态度。从13至14世纪,陆续有博郎耨喀品(John of Plano Carpino,亦译作柏郎嘉宾)、鲁布卢克(William of Rubruck,亦译作吕柏克)、孟德高维奴(John of Montecorvino,亦译作孟高维纳)、马立哥耨拉(John of Marignolli,亦译作马黎诺里)、鄂多立克(Fra Odorieo da Pordenone,亦译作和德理)等传教士受教皇或法王的派遣,不畏艰险东来,扮演着传教兼外交使节的角色。他们企图说服蒙古人皈依基督教,蒙古统治者对他们待之以礼,甚至还馈赠礼物。这些传教士们所到之处皆为蒙古人领地,且有机会接触拔都、蒙哥、忽必烈等蒙古统治者,因之对蒙古的政治、组织、习俗、宗教等有直接的观察,他们留下的行记、书信、蒙古史等记载,是研究蒙元史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伊斯兰教亦随着波斯和阿拉伯商人营商逐利的足迹,扩大了其在蒙元境内的影响,伊斯兰教学者也留下了诸多关于蒙元的史书、行记、书信集等资料。但遗憾的是,直至今天,这些宗教人士的活动、影响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的重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文字记录除可弥补中国元朝史料的不足外,他们以局外人角度观察的蒙元,与中国自己的记录是不一样的,可能与我们所了解的史实相比,有一些偏差,这又恰可以提醒我们,这些资料亦可作为观察域外人眼中的蒙古和中国的重要资料。方氏当时选编《讲义》时虽未有如此意识,他只是凭依其史识及对域外材料的重视作出的选择,但他深厚的学养和对历史问题的敏锐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二、 方壮猷《元史讲义》所涉及的重要学术问题
关于蒙古人的种族,即蒙古族源问题,是蒙元史研究无法绕过去的关键问题,自13世纪起就有欧亚学者开始进行研究。大致说来,学界主要有六种有价值的观点,即东胡说、突厥说、匈奴说、吐蕃说、蒙汉同源说以及东胡、突厥、吐蕃混合说等*相关内容见樊保良:《蒙古族源诸说述评》,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第19~24页;汤晓芳:《蒙古族族源研究的回顾及其新进展》,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1期,第45~52页。。20世纪初期域外学者及大多数国内学者均普遍认可突厥说或匈奴说*蒙古源自突厥说最早于14世纪由拉施特编撰而成的《史集》首先提出,我国柯劭忞、岑仲勉、冯家升等学者主此说。俄国著名蒙古史学家、东方学奠基人雅琴夫·俾丘林在搜集汉籍史料的基础上,翻译出版了《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辑》,认为蒙古人源自匈奴,中国学者黄文弼、谢再善、佟柱臣等赞同匈奴说。,直至20世纪70年代,这两种观点仍居于学术界的主流地位。方壮猷则发文赞同东胡说。东胡说最早由屠寄《蒙兀儿史记》提出:“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屠寄:《蒙兀儿史记》,中国书店1984年,第1页。但未及展开论证。1927年,王国维作《萌古考》,以新旧《唐书》及《蒙古秘史》为依据,认为蒙兀室韦最早的居地在额尔古纳河下游*王国维:《萌古考》,载《观堂集林》下册卷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689页。,不过并未论及蒙兀室韦之前蒙古的族源问题。方壮猷于1932年发表《鞑靼起源考》一文,广泛征引各类文献,系统论证了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有部分学者由于对方壮猷的相关研究理解有误,导致了对方氏的误读,认为其在蒙古族源问题上主匈奴说。参见樊保良:《蒙古族源诸说述评》,袁飞:《蒙古部若干问题研究》,兰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5页。。文中言,鞑靼之较狭义是蒙古民族之别称,“鞑靼之名,其为突厥民族对其近邻蒙古民族所用之称呼也”,“达靼民族为柔然之苗裔,……柔然为突厥所灭,遗民东附室韦”,“室韦为鲜卑之遗类,自后魏始闻于中国,本名失韦,原不过兴安岭东嫩江流域为限之一小国。……至隋代而失韦国之范围乃骤然扩大及于兴安岭西之额尔古讷河流域,及俱伦泊南北等地”*方壮猷:《鞑靼起源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2号,第194、200、197页。,由此构成鲜卑(属东胡族系)——室韦(柔然附入)——鞑靼(即蒙古)的蒙古族起源路径。遗憾的是,由于蒙古族源问题的复杂性和资料的限制,方氏的这一论断未能引起当时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直至最近20余年以来,随着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材料的逐渐发现和运用,中国学术界再重新讨论蒙古族源问题时,才认识到方氏对于此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目前蒙古源于东胡这一观点已为绝大多数中外学者普遍认同。此前,方壮猷还于1930年作《匈奴语言考》,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论证了匈奴与后世蒙古之关系,认为“就比较语言学上以推测匈奴民族之种属问题,与其认此民族为土耳其种之祖先,实不若认此民族为今蒙古种之远祖之为近真,故白鸟库吉氏遂据此推定匈奴民族之种属,当以蒙古种为骨干,而渗和通古斯种之成分者也”*方壮猷:《匈奴语言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0年第2卷第4号,第739页。,从人种学上说明匈奴属蒙古人种,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蒙古民族共同体的组成成分提供了依据。
方氏另一个独具创见的观点亦与蒙古族源问题密切相关。在《鞑靼起源考》中,方氏广征博引,以两个实例证明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一是“所谓阴山室韦,亦明即《亡辽录》等之所谓阴山达靼”,一是《辽史》所记黑车子室韦,即唐代史料中的黑车子达靼*方壮猷:《鞑靼起源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2号,第195、196页。。关于古代北方民族的称谓,由于音译差异及草原民族频繁迁徙等诸多原因,同一民族甚至同一部族的名称在不同史料中的记载往往不同,后世的学者对此颇感棘手。方氏的这一观点厘清了古代相关文献中对于达靼和室韦记载的纷繁复杂,解决了室韦—达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室韦—达怛研究是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室韦—达怛的活动时间约为北朝至辽金,其大部分部落后来成为蒙古族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室韦—达怛史,对于探索蒙古族族源问题意义重大。相关评述见张久和:《室韦—达怛研究概况》,载《蒙古学信息》1997年第3期,第39~42页。。
学术界对于蒙古南下西进的征服战争,往往与成吉思汗的研究和评价结合在一起进行,很多著名学者如余元盦、韩儒林、周良霄、杨志玖、邱树森、杨讷、余大钧等*余元盦:《成吉思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韩儒林:《论成吉思汗》,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1~10页;周良霄:《关于成吉思汗》,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第1~7页;杨志玖:《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12期,第6~11页;邱树森:《关于评价成吉思汗的几个问题》,载《光明日报·史学》1979年9月11日;杨讷:《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华夏出版社1996年;余大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皆在评价成吉思汗时论及蒙古的征服战争。他们普遍认为,西征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但却极大地破坏了被征服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给当地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于中国而言,则肯定其积极意义较多,如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经济继续发展,出现多元的文化等等。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杨讷即认为,对成吉思汗及其征服战争的评价采用了双重标准,西征否定的多,灭西夏、金朝、南宋则肯定居多。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历史学者必须身临其境理解历史事件,不能只是站在各个被征服国家的立场讨论问题,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评价自然不同。因此,还应该考虑到蒙古人的立场,以征服者的角度看,无论向西、向南,都是屠戮人口、劫掠财物,几乎没有分别。重读方壮猷的《讲义》之后,才发现此种“不同的声音”并非今日之独创,80余年前,前辈学人就已意识到了此类问题。陈寅恪有“了解之同情”一语,其云:“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泛而言之,陈氏所谓“了解之同情”即指站在古人的立场行事,以当事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作为直接受益于陈寅恪的弟子,方氏将“了解之同情”移至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中,非常认同柯劳斯对蒙古人特质的分析*方壮猷:《元史讲义》,武汉大学1936年,第5页。。生存条件的恶劣,人口、物资的匮乏,使蒙古人认为对其他民族的掠夺是一种正常的谋生手段,在他们的观念中,还未及发展出类似基督教“博爱”的情感,亦不可能以儒学的礼义廉耻行事。杀掉于他们毫无用处的俘虏、焚毁城池是天经地义之事,攻城掠地的目的只是抢夺财物、土地。此种景况在各大文明的早期皆曾存在,对于文明发达时期的人们来说已成为过去时,而蒙古人却正当时。历史时段不同,价值观自然不一样,我们不能用文明发达时段的价值观标准衡量仍处于生存竞争状况的蒙古人。
蒙古人对于东西间交通的积极作用,学术界基本已达成共识。就中国而言,蒙元以前,中亚、西亚、欧洲各国对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了解是极其模糊而不准确的,通常皆由于某个东方部族的强大而以其名作为中国的称谓。如7至13、14世纪,域外曾称呼中国为“桃花石”(Taugas),考其语源,尽管有诸多争议,但自伯希和提出其为北魏鲜卑“拓跋”的译名一说后,大多数学者皆认同此一观点,认为拓跋族建立的北魏给漠北及中亚一带的少数民族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当地人以Taugas作为中国北方政权的代称,后逐渐演变为中国的称呼*相关研究评述参见阿地力、孟楠:《百年来关于“桃花石”问题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2期,第10~16页。。辽的强盛使“契丹”(Cathay)一词声名远播,中国在波斯、阿拉伯、欧洲、俄国的历史文献中被称为Cathay*胡阿祥:《认识“中国”》,载《文史知识》2011年第4期,第53页。。实际上,无论哪一种称呼,皆不是中国本土王朝或汉族,显现出西方对中国了解的贫乏。蒙古人的征服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讲义》认为,蒙古人贯通东西的征伐,使中亚、西亚、欧洲不少人来到中国,直接与中国接触,他们或经商逐利,或冒险觅地,或传教布道,以亲身经历记有大量行记,由是西方对中国开始有了逐渐清晰的了解。
但是,与之前唐朝在对外关系中的主动回应不同,蒙古人统治下的汉文化,面对交通发达、中西交流繁盛的机缘,始终处于被动境况,与西人的源源东来探知未知东方世界相比,中国人是相形见绌了,“所可称述者,只一二例外耳”*方壮猷:《元史讲义》,武汉大学1936年,第28页。。生活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在当时的思想、学术脉络下,很容易产生面向世界、西学为用、振奋中学的想法。胡适、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学界精英如此,如方氏一辈后来者亦复如是。他们属意于西北舆地及中西交通之学,考察生活于北地的少数民族的族源,乃至后来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崛起,林林总总,皆蕴涵着中国学人深刻的现实关怀。
三、 方壮猷《元史讲义》所体现的治史方法
20世纪初期,面对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界亦发生重大转变,中外史学开始直接接触,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巨者当为发端于德国的兰克史学。尽管当时兰克史学在西方已备受抨击,但其“如实直书”的核心理念却为中国学者广泛接受,包括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著名学人在内的学界精英,他们的研究方法或多或少有着兰克史学的影子。这一现象与他们的学术渊源密切相关。他们早期接受的治学方法深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而考据学所包含的重视史料、严谨考证等内涵,恰与兰克史学的科学精神不谋而合。所以,在中西学术碰撞之时,很自然地选择了重视史料及其考证方法的兰克史学。
方壮猷因应时代,受到实证主义学风的濡染,以中国古代学术为研究旨趣;又曾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家,颇受他们的启发而正面受益,由此形成自身治史方法上的风格: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非常重视“使用新材料”。《匈奴语言考》是最能反映方氏治史方法的一篇论文。作者认为,匈奴距今久远,所能依据的史料仅中国古代史籍中所存之一部分,非常有限,要解决匈奴之种属问题,只能依赖于考古学的发展,“今考古学犹未大昌,欲从现有之史料以探讨此问题,则舍比较语言学之方法外”,别无他法。为了论证问题,方氏使用了西文史料中对匈奴语言的记载,同时更是广泛参考中国古代史籍,涉及到《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近20种,还引用突厥阙特勒碑铭资料。文中用于比较的语言则有汉语、土耳其语、蒙古语、日语、通古斯语系部分语言、西方语系部分语言等将近20种*方壮猷:《匈奴语言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0年第2卷第4号,第693~740页。。其方法之严格、考证之扎实、学术修养之广博精深尽显于文中。方氏在其他蒙元史研究论文中亦展现出同样的治史特征,往往善于大量征引相关材料,通过比较、分析、联系等方法从材料中发现问题,提出独到的精辟见解。
《讲义》三个部分的选编原则更是显露出方壮猷对材料的重视,特别是西文蒙古史的新材料。西学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必然导致20世纪初期学人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型的变化,就史学材料的处理来说,“五四”以后,学人皆颇受胡适倡导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影响,即以批判的精神和疑古的态度,依据历史的观念,系统整理、研究并重新估定一切材料的价值。这一方法既上承乾嘉,又闪现着西学的影子。方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学术氛围中进行《讲义》的编纂的,因此其基本原则即是汇辑蒙元史研究的各种材料。如果说《讲义》还不足以展示方氏的基本学术功底的话,那么其另一篇长文《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原载《说文月刊》第4卷,1944年,重刊于《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24~50页。即颇能进一步说明其在材料处理上的卓越功力。作历史人物年谱是非常费力费时的工作,时人常常感叹这种“绣花针功夫”难做,因为需翻检大量相关材料,然后条分缕析,将历史人物一生的事迹以时间为经予以串连,找寻其学术轨迹、交游网络、仕宦生涯及思想脉动,其中有考证,有校勘,有描述,有评说。方氏的《二李年谱》就材料之详实、考辨之精审及体例之确当而言,透露出作者笃实的治史追求。
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明显反映出其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国际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在学术界各个领域,且其内涵愈来愈丰富,亦愈来愈体现出中国学者的主动性,即不仅仅是一路向西,更有与西方学者在“共通的语言”平台上的平等学术对话。实际上,这种所谓“对话”在几十年之前即已出现过。20世纪初期中国史家已走出国门,直接接触西方史学。至30年代,如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新学人之翘楚,兼能掌握异域文字,了解西方史学的最新动态,又在骨子里透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兴亡感和民族自尊感。他们采取中西会通的方式,使西方之史学方法、域外之中国研究与中国文史之学达到贯通无阻的境界。方氏曾于1929年赴日留学,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白鸟库吉教授研习东方民族史,白鸟库吉是兰克再传弟子利斯(L.Riess)的学生,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兰克式的史学训练,其研究路径偏重于考证。受中日关系交恶的影响,方氏第二年即愤而回国。1934年赴欧,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东方学大师伯希和,继续东方民族史的学习和研究。这一段留学经历使方氏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国外东方学的学术成果及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对民族语言及起源、西北史地、中西交通等皆有独到之见解。从方壮猷的求学、研究路径看,中国传统学术所倡导之广而博是其基础,惟有如此,才能由博返专,进一步从事专深的学问,这“专深”又是西方学术影响的产物。此种博与专的结合,恰也是一代学人共同之治学特点,如傅斯年、陈寅恪、陈垣等人,皆有深厚而广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凭依所掌握的多种语言文字,利用各种材料,重构中国古代某一段或某一部分历史。正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方氏的研究路数无疑是“预流”于世界蒙元史研究潮流的,惟其如此,才能真正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运用相同的专业语词、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相似议题进行分析、研究、对话,从而发出中国学人自己的声音。
在20世纪初期开始的国际化过程中,蒙元史研究自然首当其冲,若是仍旧只知汉文材料,只观蒙古人在汉地的统治,已不足以完全了解这个对中国影响甚大的民族,甚至不能对元王朝的某些做法知其所以然。于是,当时研究蒙元史的学者皆将其视野由中国及于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将元王朝看作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的一部分。如此的国际视野,使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在20世纪20至40年代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地位,各种文字的蒙元史材料,中国学者也能阅读原文,为己所用;国外学者关注的族源、宗教、蒙古史地等问题,中国学者亦萦绕于心,旁征博引进行分析。方壮猷的《室韦考》、《鞑靼起源考》等蒙元史研究论文,开篇往往皆为评述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现状,尤其重点介绍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就,同时亦指出他们研究的不足和谬误。如关于鞑靼民族之来源问题,英国汉学家巴克依据“鞑靼”一语为乌桓大人“搨顿”之异译,认为鞑靼为乌桓之遗类。方氏对此颇不认同,指出“搨顿为魏武帝所灭,当西历一世纪时,而鞑靼之名之见于记载者则最早亦不过当西历六世纪之时,前后相距凡五六百年之久”,且仅凭依此一孤证,而无其他材料佐证,“是知巴克氏之说未足为定论也”。日本箭内亘《鞑靼考》虽曾驳斥宋代宋白、欧阳修所言鞑靼源于靺鞨之说,但并未详论其民族来源*方壮猷:《鞑靼起源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2号,第186页。。如此学术视野,显现出方氏对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的了解和回应。
方氏以自身的学术视野编撰《讲义》,即是意欲呈现当时中国学术界的这种国际化状况:世界上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关于蒙元史的论著,《讲义》中基本皆有提及,且注明出处,便于查找;一些重要学者的观点,《讲义》中亦有简短介绍,使学生充分掌握相关研究动态。这种对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以及对域外学者研究议题的回应,时至今日,仍是中国学人所应注意的问题。而在中国的声音愈来愈强大的今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摆脱西方话语的主导,形成中国学术界自己的风格,并引领世界学术潮流。
在中国学术界经历了60余年的跌宕起伏之后,如方氏一般前辈学人的治学方法、学术视野及现实关怀,更显得弥足珍贵。尽管时光会不断淡化人们的记忆,当年先贤们念兹在兹的民族存亡、西北舆地问题,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逐渐模糊,不过,蕴藏在他们身上孜孜问道、上下求索的精神,以及无论顺境逆境始终持守理想的境界,却未曾远去,并值得后人琢磨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