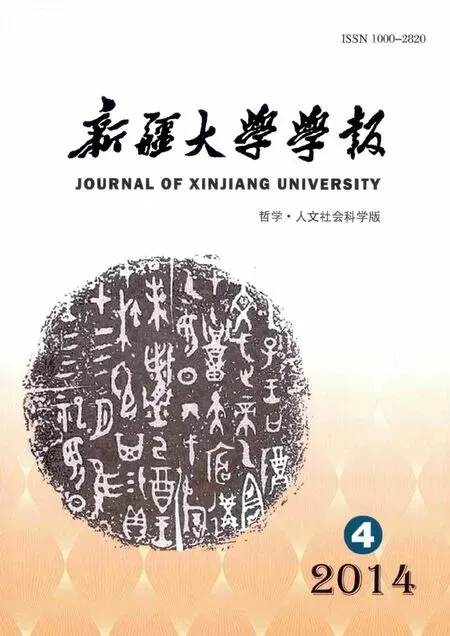论中西喜剧意识的文化发生∗
2014-03-03马小朝
马小朝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笑的发生里隐藏着人类千万年文化实践活动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机制和保持生命和谐韵律、健康节奏的无尽资源。作为人类审美表现的喜剧意识的笑,更是人类社会实践复杂文化心理机制和生命自由资源的审美升华。俄国文论家普罗普说:“人有别于无机界是因为他有精神因素,即理智、意志和情感。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纯逻辑的方法得出这样的假设:滑稽总是同人的精神生活领域有某种联系。”[1]德国美学家里普斯说:“开心就是喜悦,令人喜悦的就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但是我们同样知道:并非每种喜悦都是审美的喜悦,并非每种喜悦感情都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感情。”[2]也就是说,只有具有审美价值的喜悦感情,才能成为审美表现的喜剧意识的笑。反过来说,作为审美表现的喜剧意识的笑,又深化了具有审美价值的喜悦感情。
那么,什么喜悦感情才具有审美价值,从而能够成为审美表现的喜剧意识的笑呢?从通常意义上说,审美是人的心灵自由本质的象征性实现。我们知道,人是通过劳动才真正成为了人,但劳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体的活动,而是集体的活动。所以,劳动资源的占有、劳动方式的采纳、劳动成果的分配等等人与人关系问题,几乎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严酷考验。所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设想原始状态的人类曾经不得不建立起一种社会契约关系。我们从纯逻辑的意义上,可以认同卢梭的假设:人从个体走向集体、从自然走向社会,也就是把自我个体的自由权利以“契约”的形式转让给了集体社会。人们逐步习惯凭借转让“契约”把个体眼下的利害计较遮蔽甚至融化在集体未来的社会目的中。但是,这种为未来长远而牺牲目前短暂的理性驯化毕竟是一个压抑个体生命欲望、枯萎个体生命激情的痛苦过程,所以,每一个人的意识深处一定会潜藏着随时随地逃逸社会“契约”的原始愿望。正如18世纪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说:“但是理智界远不如自然界治理得那样好。因为理智界虽然也有本性上不变的法,却并不始终不渝地遵守这些法,像自然界遵守它的法那样。其理由在于特殊的理智实体受到自己本性的局限,因而会犯错误;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本性又使他们凭自己行动。因此他们并不始终不渝地遵守他们的原始法;甚至他们自己制定的法他们也并不永远遵守。”[3]39我们从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意义上,还不能不指出,卢梭假设的出发点是人在社会建立前就具有先验的合乎理性的本质,所谓社会“契约”就是这个先验的合乎理性本质的对象化。其实,所谓先验的合乎理性的人的本质无非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人类社会关系则是伴随社会劳动实践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性存在。人的先验的合乎理性的本质也就是人类社会劳动实践从低级往高级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因而转让权利的社会“契约”也是人类文明从低级往高级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具体而言,人类最初转让权利的社会“契约”一定不是源自建立和谐社会的文质彬彬的理性协商,而是源自争夺生存繁衍机会的尖锐激烈的欲望交战。所谓社会“契约”也就是各方利益争夺者,既有斗争又有妥协、既有强迫又有退让的艰难博弈的阶段性结果。所有的利益争夺者都不会完全满足社会“契约”的规定。随着人类社会劳动实践从低级往高级的不断变化发展,劳动资源占有、劳动方式采纳、劳动成果分配等等问题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因而也就没有包罗万象、一劳永逸的社会“契约”,只有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契约”。我们由此不难想象,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所谓社会“契约”应该是始终充满错裂罅隙的过程。这就为前面所说“逃逸社会契约的原始愿望”预留了现实的客观空间。同时,社会“契约”还难以保证转让出去的权利不会被误用、滥用情况更可能如孟德斯鸠所说:“但是我们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经验:凡是有权力的人,总要滥用权力,非碰到限度不止”[3]44。因此,社会“契约”也就难以保证权利转让者会心甘情愿地严格遵守。这就为前面所说“逃逸社会契约的原始愿望”预留了现实的主观空间。这样,纯逻辑意义上的“逃逸社会契约的原始愿望”,也就因为社会劳动实践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性过程而获得了现实的主观、客观空间,从而使人的心灵自由本质呈现出复杂微妙的多维性。一方面,人的心灵自由本质不得不服从尽管充满错裂罅隙的社会“契约”,遵循人类文明的必然规律,因为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说:“无疑地,必然作为必然还不是自由;但是自由以必然为前提,包含必然性在自身内,作为被扬弃了的东西”[4]。这就是悲剧发生的历史文化意蕴。另一方面,人的心灵自由本质不能不利用社会“契约”预留的主、客观空间实现逃逸的愿望,获得精神嬉戏的喜悦感情。这种利用社会“契约”预留的主、客观空间实现逃逸愿望,获得精神嬉戏的喜悦感情就具有审美价值,就能够成为审美表现的喜剧意识的笑。所以,人类文化发生学的探讨,倾向于认为文学艺术的起源同人的喜悦感情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比如马克西米利安·戈蒂埃就认为:“笑从本质上说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一种现象,所以可以认为,艺术伊始,就把引人发笑当作它的一种功能。关于这种功能的最早证据之一是一张发现于埃及的莎草纸图画,现保存在都灵博物馆里。这张画所表现的内容是一个神甫和一个舞女之间的爱情生活”[5]。还比如中国喜剧意识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卜筮歌舞、祭祀飨宴。王国维先生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6]58当然,因为各民族历史文化实践活动基础上的文化心理、人文艺术精神、文学艺术实践的不同,喜剧意识的发生发展也会有所不同。反过来说,喜剧意识也可以从一个特殊维度显示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人文艺术精神、文学艺术实践的重要特征。所以,英国作家梅瑞狄斯说:“我认为一国文明的最好考验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喜剧思想和喜剧发达与否;而真正喜剧的考验则在于它能否引起有深意的笑”[7]。
中西方文学有没有共同认可的喜剧呢?喜剧本是一个西方文学的审美概念。中国文学中的喜剧似乎更应当称为“滑稽戏”。西方文学里作为戏剧形式的喜剧,远在古希腊就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中国文学里作为戏剧形式的喜剧直到宋元以后才达到成熟程度。为了避免因为更多牵涉中西戏剧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而冲淡中西文学的喜剧意识研究,我们不妨姑且从更加宽泛、广义的角度,探讨中西文学审美意义上的喜剧意识。那么,中西方文学有没有共同认可的喜剧意识呢?应该说,中西方人在漫长的历史文明实践活动中,都会有前面所说的纯逻辑意义与社会历史变化发展意义上的社会“契约”问题,其心灵自由本质都会呈现出复杂微妙的多维性,即一方面不得不服从尽管充满错裂罅隙的社会“契约”,另一方面不能不利用社会“契约”预留的主、客观空间实现逃逸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方文学都应该有审美意义上的喜剧意识。
中西喜剧意识审美意蕴里最有普遍意义的差异性是什么呢?喜剧意识的审美意蕴既同文学艺术实践活动发生的社会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也同文学艺术实践活动的自身生命机理密切相关。所谓文学艺术实践活动的内在生命机理,主要源自最初发生学时期的历史文化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审美文化心理、人文艺术精神、文学艺术实践。我们关于中西喜剧意识审美意蕴差异性的研究,不得不首先探讨中西方最初发生学时期的历史文化实践活动,如何生成了相应的审美文化心理、培育了相应的人文艺术精神、引动了相应的文学艺术实践活动,孕育了中西方文学喜剧意识审美意蕴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关于中西喜剧意识审美意蕴差异性的研究,更注重中西喜剧意识审美意蕴的历史文化发生学研究。德国启蒙理论家赫尔德最早开创了文化发生学研究的新方法。他说:“树从根处生长,艺术的产生和繁荣也不例外,一开始有艺术,艺术的产生也就有了全部的存在,犹如一种植物的整体或所有组成部分都蕴藏于这植物的一颗种子中了。”[8]深谙历史辨证发展规律的黑格尔也赞同这种文化发生学的研究方法。他说:“萌芽虽然还不是树本身,但在自身中已有着树,并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树完全符合于萌芽的简单形象。”[9]“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0]中西方历史文化的最初发生时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帕森思所说的“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时期,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超越的突破”(Transcendent breakthrough)或者“轴心时代”(Axial age)。大约是指公元前1000年内,分别在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以各不相谋的方式所发生的各不相同的高层次理性认识实现时期。这个高层次理性认识实现时期,分别形成了中西文化或文明的基本雏形。这个文化或文明基本雏形孕育的文学基本雏形,无疑建构起了文学的内在生命机理,从而制约和影响了后来中西喜剧审美意蕴的差异性。
古希腊文明诞生于爱琴海域的诸多海湾、岛屿之上。变幻无常的大海、波谲云诡的商业贸易使古希腊人不能不产生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深不可测的命运感。法国哲学家丹纳说:“希腊人对于命运的观念,不过等于我们现代人对于规律的观念。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这是我们用公式说出来的,而他们是凭猜想预感到的。”[11]258他们关于“命运”的主要理解和说明,就是强调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历史活动,必需变更、调整人与人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将最初的自然关系变更为社会关系,或者说,将原始血缘宗亲关系变更为文明社会劳动协作关系。这种变更、调整的结果就是人与人血缘亲族纽带的被撕裂、毁弃。在此基础上,古希腊人的最初生产实践活动孕育了历史理性主义文化,其核心是肯定历史与人伦的二律背反原则。古希腊人由此而勇敢地迈开了历史文明的沉重步履,哪怕肩负“杀父娶母”的人伦罪孽。但是,古希腊人又终归难以忍受人伦受践踏的情感痛苦、灵魂负疚,他们从审美角度将伴随历史进步的痛苦和负疚升化为悲剧精神。所以,古希腊人特别钟情既表达历史信念,又寄托人伦情感的悲剧精神,而不太看重狂欢放纵的喜剧意识。这就决定了喜剧意识非主流而边缘、非严肃正经而戏谑调侃的审美自由特征。但是,古希腊人的“命运”观在在强调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必然规律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预留了人们自由抉择的空间。因为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必然规律往往是不可见的抽象存在,它还需要依靠具体的超验神灵、经验权威的理解、解释。但是,所谓的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必然规律本是包含许多个别、特殊的偶然碰撞、纠缠,从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正如人类文明历史上的社会“契约”充满错裂罅隙一样,人们如何判定“超验神灵”、“经验权威”是否真正理解、正确解释了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必然规律呢?他们有没有发生无意识的错误、或者别有用心的歪曲呢?既然“超验神灵”、“经验权威”,皆有可能发生无意识的错误、或别有用心的歪曲,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无条件忍受压抑个体生命欲望、枯萎个体生命激情的痛苦呢?人们为什么不能在充满错裂罅隙、蜿蜒曲折的历史活动中寻求一些狂欢放纵或精神嬉戏,从而获得一种特殊的心灵自由本质的象征性实现呢?还如丹纳所说:“他们先用悲剧表现情感的伟大庄严的一面,再用喜剧发泄滑稽突梯和色情的一面。”[11]267所以,在古代希腊文化沐浴着金色阳光的奥林匹克神抵的阴影中,一直有一种更原始、更充满激情的神灵崇拜。“那不是和奥林匹克诸神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与狄奥尼索斯或者说巴库斯相联系的,我们极其自然地把这个神想象成多少是一个不名誉的酗酒与酩酊大醉之神。”[12]古希腊喜剧就直接起源于欢庆狄俄尼索斯酒神死而复生的民间狂欢游行和歌舞。古希腊文“喜剧”一词的意思就是“狂欢游行者之歌”。莫里斯·瓦伦赛说:“喜剧的起源,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像悲剧的起源那样具有很多神秘色彩。亚里士多德将喜剧的起源归于那些最早唱崇拜男性生殖器歌曲的人们。‘喜剧’一词,显然是从狂欢演变而来的。各种推测表明,这一戏剧形式,起始于酒神节里那些身携男性生殖器样东西的狂欢者行列。狂欢者们面对围观的人群,又是唱,又是叫,满嘴尽是下流而又有一定分寸的词语。”[13]显然,欢庆狄俄尼索斯酒神死而复生的民间狂欢游行和歌舞里包含的生殖崇拜内容,可以使人们暂时摘下日常的面具,冲破束缚原始情感的礼仪规范,释放赤裸裸的原始生命激情。古希腊人通过边缘的狄奥尼索斯酒神释放生命激情的同时,还以玩笑嬉戏态度对待主流的奥林匹克诸神,从而拓展了冲决理性规约、蔑视必然规律的喜剧意识。古希腊最优秀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肆无忌惮地表现对待奥林匹克诸神的玩笑嬉戏态度。比如其喜剧《鸟》描写普罗米修斯来鸟国通风报信时,就劝告珀斯特泰洛斯别同宙斯讲和,除非宙斯把巴西勒亚嫁给他。最后,还需要补充的是,古希腊人的海洋作业和商业贸易,还创造了比较早的城市文明,产生了要求分享社会地位的工商业奴隶主和特殊的民主政治、自由民阶层。城市文明、民主政治和自由民阶层,无疑也是古希腊喜剧意识发生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
中国古代文明诞生于大陆农耕文化,因而它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文化。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主要是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宗法伦理等级制度,因而它也不同于古希腊的社会制度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财富占有阶级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最初的生产实践活动孕育了伦理理性主义文化,其核心是无视历史与人伦二律背反原则,坚决维护人伦对历史的绝对优先地位。具体而言,中国人在面对征服自然与人伦和谐命题时,没有认可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矛盾。中国古人坚信“道”就在人伦日常之中。所以,中国人不注重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必然规律的探究,只注重社会等级伦理秩序的建构。中国人虽然也知道大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社会的矛盾可能带给人们灾难、苦难,却始终不愿从科学理性角度直面自然灾难、社会苦难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始终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的坚定信念,始终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乐观精神。所以,“乐”一直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孔子尤其推崇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所以他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等人生哲学和伦理思想的乐观表述。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即使是处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他们也相信终究有一天会‘否极泰来’,‘时来运转’,因为这是符合‘天道’或‘天意’(客观运转规律)的。”[14]这一切无疑奠立了中国喜剧意识发生发展的文化土壤,也决定了中国喜剧意识发生发展的审美意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15]应该说,中国人参透历史人生的虚无感,经过老庄思想形态一直延伸到后来吸收外来的佛教,终于在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发展出同儒家伦理道德互补的佛道超验解脱、同伦理政治哲学互补的人生审美哲学。这样,在儒家的积极入世、乐观进取基础上发生的喜剧意识中无疑也就渗入了佛道的消极出世、悲观退避的虚无因素。
中国喜剧意识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卜筮歌舞、祭祀飨宴。戏剧形式的喜剧表演艺术雏形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专供宫廷贵族调笑娱乐的俳优,西汉时期在民间大量出现的角抵戏,唐代普遍盛行的参军戏等等。中国戏剧形式的喜剧表演艺术显然比戏剧形式的悲剧表演艺术更早诞生。其实,中国的戏剧最初就是喜剧的同义语。王国维先生说:“宋时所谓杂剧,其初殆专指滑稽戏言之。”[6]192后来,甚至已经充分成型的杂剧通常也分艳段、正杂剧、杂扮三部分表演。其中杂扮多为调笑的段子。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喜剧往往比悲剧享有更广阔的发生发展空间,比悲剧更能唤起文学家的创作热情。正如民国李铎著《破涕录》,徐枕亚所作《序》言:“客有问于余者曰:‘李子之《破涕录》中,多闾巷猥琐之谈,村野粗俗之语,比之志怪搜神之作,更觉荒唐。揆之讽世警俗之心,亦无寄托。愚夫稚子读之而神怡,道学缙绅见之而色变也。以李子之才之学,欲从事著述,何书不可为,而乃出之以滑稽游戏,窃东方、淳于之故智,摇唇鼓舌,哓哓不休。既无功于社会,且有损于人心。李子独何取于是乎?’余应之曰:‘唯唯否否,不然。李子之著此书,盖别有深意,所谓哭不得而笑,笑有甚于哭者也。夫志士之所具者,良心;人生之难开者,笑口。吾辈不幸生此五浊世界,莽莽中原,剩一片荆天棘地,茫茫前路,费几回伫苦停辛,一点良心既不能自泯,百年笑口,又胡以自开?追念遗烈,学岘山之涕者;有人顾瞻国步,作新亭之泣者;有人慨念身世,下穷途之泪者;有人忧国忧家,各怀苦趣。斯人斯世,欲唤奈何?不数年而中国之志士且将憔悴以尽,只余一辈软媚人,赓歌扬拜而乐升平矣。李子忧之,爰著是书,以惠吾至亲至爱之同胞,为荡愁涤烦之资料,消磨此可怜日月,延长此垂死光阴。庶几,中华民国共和之真种子,不遽绝于此日;而支离破碎之山河,以一哭送之者,犹不如姑以一笑存之也。然则李子之书,实大有功于社会,大有益于人心,乌得以荒唐二字概之哉?”’[16]喜剧还往往比悲剧更契合文学家的精神气质。还如明代冯梦龙辑《古今笑·自叙》所言:“龙子犹曰:人但知天下事不认真做不得,而不知人心风俗皆以太认真而至于大坏。……后世凡认真者,无非认作一件美事。既有一美,便有一不美者为之对,而况所谓美者又未必真美乎!……一笑而富贵假,而骄吝忮求之路绝;一笑而功名假,而贪妒毁誉之路绝;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标榜倡狂之路绝;推之一笑而子孙眷属亦假,而经营顾虑之路绝;一笑而山河大地皆假,而背叛侵凌之路绝。即挽末世而胥庭之,何不可哉,则又安见夫认真之必是,而取笑之必非乎?非谓认真不如取笑也,古今来原无真可认也。无真可认,吾但有笑而已矣。无真可认而强欲认真,吾益有笑而已矣。野菌有异种,曰‘笑矣乎’,误食者辄笑不止,人以为毒。吾愿人人得笑矣乎而食之,大家笑过日子,岂不太平无事亿万世?”[17]此外,中国农耕生产方式下群体聚居的娱乐需要,皇权专制制度下的民生表达,也给喜剧意识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永恒的社会生活资源。
从最概括意义上说,西方历史理性主义文化中的喜剧意识主要源自历史的微妙。中国伦理主义文化中的喜剧意识主要源自道德的坚决。以此为出发点,中西喜剧意识的审美意蕴终归在审美本质、审美特征、审美风格方面表现出了诸多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