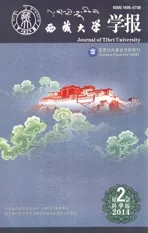说唱艺人: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当代命运
——以阿来《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神授》为例
2014-03-03田频
田频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10)
说唱艺人: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当代命运
——以阿来《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神授》为例
田频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10)
《格萨尔王传》作为藏民族流传了千年的史诗文化,是祖先留给藏族人民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格萨尔史诗传承中,“仲肯”——说唱艺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本身也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然而,他们却均在现代化生活潮流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的《神授》不约而同地书写了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史诗说唱艺人的当代命运,并通过他们形象的塑造,提出了如何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新问题,表达了对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些深入思考与独特见解。
说唱艺人;文化传承;当代命运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进行文化创新的基本工作。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和现代媒体的普及,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本民族优秀的传承文化已现衰微乃至濒临灭绝之势。作为对本民族优秀史诗文化——《格萨尔王传》无限热爱的藏族作家,阿来和次仁罗布分别创作了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与中篇小说《神授》,塑造了晋美和亚尔杰两位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形象,书写了他们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者的当代悲剧命运,同时深刻展示了在现代文明浸染下,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命运走向及作家们对传承史诗文化使命的思索,向世人敲响了保护藏族优秀史诗文化《格萨尔王传》及其传承人的警钟。
一、史诗传承与说唱艺人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在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已流传了千年,是世界上传唱至今唯一的活史诗,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它讲述了藏族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格萨尔王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造福百姓的英雄事迹。在高原严寒的气候及贫乏的文化生活下,这一古老史诗正如黑格尔所说,
“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1]《格萨尔王传》正是这样“一本绝对原始的圣经”,它像空气和水一样滋润着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是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情之源,美之根,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
作为口传文化的代表之作,口口相传是《格萨尔王传》这一古老史诗文化的唯一传播方式。说唱艺人对史诗文化的传唱,在《格萨尔王传》的世代流传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生活在藏族民间的说唱艺人,对藏民族古老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传承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巨大贡献。作为向世人诠释藏族古老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活字典”,他们被誉为藏民族发展历程的“活化石”。正是他们对史诗的演绎和诠释,才使得《格萨尔王传》这部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能够千古流芳。然而,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一直都以史诗的书面文本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史诗的传承者——说唱艺人,却被仅仅当作了解史诗的辅助工具,埋没于史诗宏大的叙事背后。事实上,说唱艺人是史诗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史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说唱艺人的传承活动,特别是以口口相传为传播方式的《格萨尔王传》,完全是依靠说唱艺人的传承活动才得以千古流传。
《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按照获得说唱能力的途径分类,可分为神授艺人、圆光艺人、伏藏艺人、吟诵艺人、传承艺人等五类。其中,神授艺人是《格萨尔王传》所有说唱艺人中最为神秘也最为优秀的史诗传承者。小说中的晋美和亚尔杰,就是这类带有神秘色彩的神授艺人。他们早年家境贫困,只是草原上牧羊的放牧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在机缘巧合中,得到了神灵的眷顾,被剖开胸膛,塞入经书。昏睡几日醒来后,他们脑中清晰地呈现着天界、人界,当他们把头脑中这些影像用语言说唱出来后,就是一个个鲜活的格萨尔王的英雄故事。这些在梦中或疾病中受到神灵的启发或传授,清醒后能进行说唱的艺人被称为“仲肯”,也就是所谓的神授艺人。清醒后的晋美和亚尔杰获得了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能力,能够口若悬河般说唱几十部《格萨尔王传》诗章。
阿来和次仁罗布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本土作家,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格萨尔王传》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感情。他们敏锐地发现了说唱艺人对史诗的传承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小说中,他们以说唱艺人晋美和亚尔杰的传奇一生为主线,把古老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现实处境和说唱艺人的生存状态,生动、形象地展示在了读者面前,用讲故事的方式把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说唱艺人的重要性告诉世人,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格萨尔王》创作于2009年,是阿来旨在“重述神话”的重要作品。不同于苏童、李锐及叶兆言“重述神话”的三部作品,阿来不仅重述了象征藏民族精神文化的史诗神话,而且独创性地把神授艺人晋美纳入小说中,并采用双重线索的叙事方式,把远古格萨尔王的征战历程和现代神授艺人晋美的说唱经历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整个故事的发展。他用自己深情的笔墨,让世人“读懂西藏人的眼神”的同时,把自己对史诗面临的传承困境的担心也呈现在了读者面前。《神授》发表于2011年,小说以神授艺人亚尔杰为主人公,采用多重叙述视角转换的方式,通过亚尔杰说唱技艺得而复失的过程,把亚尔杰从获得说唱能力到失去说唱能力的过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向读者展示了说唱艺人在《格萨尔王传》流传过程中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两部小说虽然创作手法各异,但都通过对《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的描写,揭示了现代文明对传统民间文化的冲击和破坏,传达了作者对本民族口传文化及其说唱艺人将何去何从的隐忧。
千百年来,《格萨尔王传》正是通过无数像晋美、亚尔杰这样不畏艰险,痴迷于说唱的神授艺人才得以广为流传,说唱艺人的世代传唱是《格萨尔王传》最主要也是最本质的存在和传承方式。倘若没有这些说唱艺人的辛勤传播,《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便会被无情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正如冯骥才所断言“中华大地的民间文化就是凭仗着千千万万、无以数计的传承人的传衍。他们像无数雨丝般的线索,闪闪烁烁,延绵不断。如果其中一条线索断了,一种文化随即消失;如果它们大批地中断,就会大片地消亡。”[2]乌丙安教授面对这些现象,也心急如焚地说道:“一旦老艺人自然离去,他身上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消亡,那些绝技、绝艺也就人亡技绝,人亡歌息。”所以,优秀的传承艺人,是口头民间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环节。对于藏民族的优秀文化史诗《格萨尔王传》来说,没有像晋美、亚尔杰这样优秀的说唱艺人,就没有《格萨尔王传》这部宏伟的史诗巨著。
二、现代文明对史诗文化的冲击
小说中,在晋美和亚尔杰最初获得说唱能力之时,西藏社会还处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传统农牧社会时期。贫乏的文化娱乐生活,使得牧民们对聆听《格萨尔王传》相当痴迷,甚至可以不眠不休地听上几天几夜,就连睡梦中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原始的生产劳作方式,也使得牧民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和较为缓慢的生活节奏,可以静下心来慢慢感受古老史诗的文化魅力,他们借助说唱人的表演消耗掉冗长的时间。特别是他们每年去盐湖驮盐的两个月时间里,晚上住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说唱艺人神色俱佳的说唱表演是他们排遣孤独最好的娱乐方式。此时的晋美和亚尔杰,对自己的说唱艺人身份是非常自豪的,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通过说唱《格萨尔王传》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他们像雄鹰一样翱翔在广袤的大草原上,充分释放着自己说唱的激情。在受到牧民们热情欢迎的同时,亚尔杰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读者遗憾地看到,势不可挡的全球化飓风,给藏族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这块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世外桃源悄然发生了巨大变革。人们的经济生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牧民们已由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转为定居或半定居状态,他们再也不需要赶着牦牛驮队运送盐巴,不再需要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一切随着现代化的到来变得简单便利了。生产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导致了史诗传承环境的消失殆尽,同时也使得史诗的听众数量锐减,草原上只有一些上了岁数的人才喜欢听《格萨尔王传》的故事。
特别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现代媒体进入到了草原上的千家万户:电视、收音机、录音录像等现代媒体的发展和普及,草原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化的洪流中。丰富的现代娱乐生活几乎完全替代了相对单调的说唱表演,网络更是吸引了庞大的青少年群体。这一切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覆盖住了民众的审美空间和想象。再加上说唱艺人经济贫乏、生活困顿、居无定所,使得年轻一代对成为传承人失去兴趣,随着老一辈的说唱艺人逐渐老去,而年轻人“每天围着电视转,要不到县城的舞厅、酒吧去玩”,对史诗完全不感兴趣,史诗的传承出现了后继无人的现象,史诗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现代文明和现代媒体的强势冲击下,晋美和亚尔杰在现代社会的说唱命运面临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局面。阿来在《格萨尔王》中说道,神授艺人是“神特别的仆人。为了演唱神授的故事,将四处流浪,无处为家。”[3]由此可以看出,阿来对说唱艺人采取“圈养”保护政策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他为笔下的说唱艺人晋美设计了从电台逃离,寻觅格萨尔王踪迹的说唱命运。然而,晋美的逃离和努力无法扭转史诗文化将面临的衰亡命运,就算他为了更好地吸引听众,不惜学唱流行歌曲,《格萨尔王传》还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关注视野。《神授》中的亚尔杰,选择了和晋美截然不同的说唱命运。他接受了拉萨研究所的“圈养”政策,以为自己为史诗文化的传承找到了合适的传唱途径,通过现代媒体的录制方式,能更好地保证《格萨尔王传》的千古流传。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亚尔杰的行为并没有得到神灵的认可。冰冷的录制机器逐渐熄灭了亚尔杰说唱的激情,现代化林立的高楼阻隔了神灵的降临,最终,神灵收回了赐予亚尔杰的说唱能力。
从阿来和次仁罗布笔下说唱艺人的悲剧命运读者可以清晰看到,现代文明的强势来袭,使得史诗文化传承的民俗基础、传承空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挤压和破坏,从而导致史诗文化的传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对传统民间文化的侵蚀和摧毁不容小觑。尤其是一些民间歌谣、神话史诗等口传文学,在一代代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被遗忘或变得残缺不全。宁夏“坐唱”、土家民歌、黔东南苗族古歌、蒙古族优秀的英雄史诗《英雄格萨尔汗》和《蟒古斯征服记》、阿昌族的长篇诗体创世神话史诗《遮帕麻和遮咪麻》等都陷入了后继乏人,濒临灭绝的局面。小说通过晋美和亚尔杰失语的结局,向世人道破了史诗文化传承的特点:凭借说唱艺人口口相传的史诗文化,不能脱离听众和表演舞台,必须得到反复传唱和表演才能延续下来。只有在说唱艺人神色俱佳的表演中才能显示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和文化魅力。一旦停止了演述,人们便会失去对它的记忆,它的生命力也就随之衰竭。阿来、次仁罗布在小说中以晋美、亚尔杰一波三折的命运走向形象地显示出作家们对这一重大文化问题的深刻思考。
三、文化传承之路的反思
正如小说所揭示,藏族社会正处在一个由农牧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而敏感的年代,藏族的古老史诗《格萨尔王传》没有了相应的传承机制,使得《格萨尔王传》的优秀说唱者陷入了失传和失语的现状中。残酷的现实,给在《格萨尔王传》传统文化精髓浸润下成长起来的阿来和次仁罗布两位作家,带来了无法言说的痛苦与焦虑。说唱传承人的失语、传承环境的丧失及听众的锐减这一切都给藏族的古老民间文化带来了逐渐消亡和毁灭的命运,迫使藏民族原有的古老文明在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下迅速地瓦解、消失、涣散甚至泯灭。正如冯骥才所担忧的一样:“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死去。它们失却得无声无息,好似烟消云散”。[4]人类进程的现代化改变了人类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对于千百年来依赖于口头传承的《格萨尔王传》及其传承人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现代化洪流毫不留情地破坏了其艺术传承的传统机制。显然,《格萨尔王》、《神授》真实、形象地呈现了这一残酷的现实。
读完两部小说,读者发现,尽管晋美和亚尔杰同为神授艺人,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背景,有着相似的获得说唱技艺的经历,作家们却给他们安排了导致失语的不同原因。晋美的失语,是因为他讲述完了格萨尔王的英雄事迹,已经完成了他作为一个说唱艺人的神圣使命。最后,神灵拿走了晋美颈背上的神箭,晋美从此失去了说唱的能力。虽然文中也多次提到或暗示了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毁灭,但是晋美对失去说唱能力却是坦然接受的。而《神授》中亚尔杰的失语,却是他远离了草原和听众,背弃了自己的说唱使命而导致。从这一点来看,虽然晋美和亚尔杰同为神授艺人,他们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然而他们失语的原因却完全不同。相比之下,次仁罗布笔下亚尔杰的失语更具有现实性和警示性。作者通过亚尔杰失语的命运,向读者道破了史诗传承的三大条件:传承人、说唱语境及听众,这三者在史诗的流传过程中缺一不可。小说最后,亚尔杰为了重获说唱能力,离开了拉萨研究所,只身前往若干年前获得神授的色尖草原。在那片熟悉的草原上,他遇到了一名希望成为神授艺人的小孩,两人一起虔诚地磕头、祈祷,等待神灵的降临。最终,亚尔杰和黑影一起消失在了草原的最深处,而这个虔诚的孩子,则成了下一任神授艺人。次仁罗布终是不忍心让代表《格萨尔王传》最高演述水平的神授艺人在他笔下消失,小说最后还是给了读者以希望。
其实,阿来和次仁罗布自身也是一名“仲肯”,他们只是用文字的形式将《格萨尔王传》传播开去。晋美与阿来,亚尔杰与次仁罗布,他们在小说中已融为一体,他们都在为史诗文化的传承做着不懈的努力。同时,面对现代文明的侵袭,他们不得不思考着:作为史诗传承者的神授艺人,他们在现代生活中,应该何去何从?晋美被请去广播电台录制《格萨尔王传》,亚尔杰也被请到拉萨研究所去录制《格萨尔王传》。现代化传播手段让说唱艺人们不再需要流浪四方,只需借助广播、录音机等现代传媒方式,史诗就可以到处传播。从表面上看来,这些“圈养”政策对口传文化的流传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然而,从长远来看,现代媒介改变了《格萨尔王传》口口相传的活态传承方式,盲目的保护只会加剧史诗文化的流失速度。要想从根本上保护和传承史诗文化,可能只有返回到胡塞尔所说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初的、本真的”“日常生活世界”[5]中去。
然而,在西藏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格萨尔王传》传承机制已经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与消解,要想再回到那个“最根本的、原初的、本真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去,无异于一种奢望和幻想。面对残酷的现实,无奈与痛惜震撼了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内心深处。应当怎样做才能更好地保护先人们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这些用生命说唱《格萨尔王》的“活化石”?这是作者和有识之士者们充满痛苦和困惑的地方。鲁迅曾说“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格萨尔王》和《神授》正是将《格萨尔王传》这一藏族古老史诗,借助神授艺人的失传命运撕毁给读者看,以引起人们对史诗文化及说唱艺人衰微命运的关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史诗文化传承之路的担忧,使得《格萨尔王》和《神授》这两部小说不再是简单地叙写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说唱艺人和格萨尔王英雄事迹的故事文本,它们同时还展现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与现实物质生活冲突的复杂内涵,引发读者对藏民族优秀史诗文化及其“活化石”——说唱艺人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关注。这也是阿来和次仁罗布基于民族的、民间立场上的深层文化忧思。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藏族人,阿来和次仁罗布从骨子里就自觉承担着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负。他们用手中的笔,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始终秉承着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信仰:“记述民族心灵,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民族精神,是文学的天职,少数民族作家应具有不可回避的紧迫感和危机感。”[6]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热爱和责任意识,使得他们的写作背景和关注视角从来没有离开过养育他们的藏地,他们的文学宿命已经和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已成为阿来和次仁罗布无法推卸的文学责任,他们用手中的笔书写着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存状态,追寻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基因。晋美和亚尔杰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但是,阿来和次仁罗布不会停止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他们会重新背上晋美的神箭,继续遨游在艺术的广阔天地之中。
[1](德)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8.
[2]冯骥才.活着的遗产——关于民间文化传承人的调查与认定[M]//冯骥才.散花.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307. [3]阿来.格萨尔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110.
[4]冯骥才.抢救与普查: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M]//冯骥才.灵魂不能下跪.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35.
[5]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0.
[6]次仁罗布.来自茅盾文学奖的启示[J].民族文学,2009(4).
Rappers:the Destiny of Cultural Inheritors in the Modern World -Loy’s King Gesar and Tsering Norbu’s The Divine as examples
Tian Pin
(Faculty of Arts,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10)
“King Gesar”,a Tibetan epic with the history of a thousand years,is the most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Tibetan.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epic,“Drom Ken”,namely rapper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y are the living fossil of ethnic culture.However,they received th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in the modern world.“King Gesar”and“The Divine”written by Loy and Tsering Norbu,both describe the destiny of rappers in the modern world.Through shaping the image of rappers,this article displays the new problem of how to protect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and proposed some ideas and insights about the inheritance of ethnic culture.
rappers;cultural inheritance;the destiny in the modern world
I207.9
A
1005-5738(2014)02-141-05
[责任编辑:周晓艳]
2014-03-15
田频,女,汉族,湖南吉首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