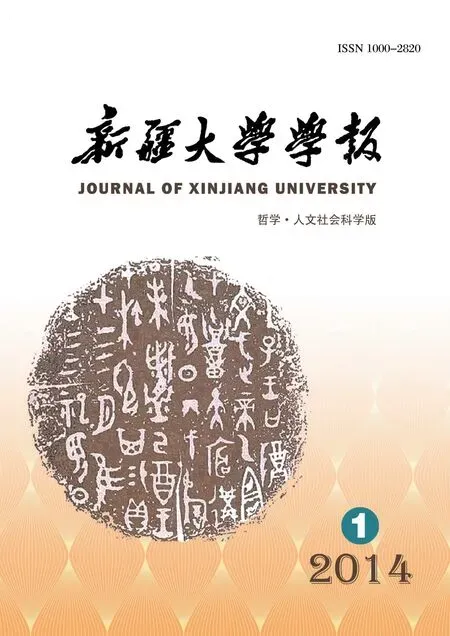回鹘语印度之名änätkäk考
——兼论汉文“印特伽”、蒙文enetkeg、藏文endäkäg∗
2014-03-03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
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西文所记“印度”的名称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集中在Sindh和Hindu及其语音变体India,Indi和Indos。至于两河流域古代典籍所载meluhha的语义、所指涵义,在学术界虽有分歧,但是,大多数研究表明,该名是指古代印度[1]。中国古代汉文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印度的记载,其中有关印度不同的称谓是长期以来众多中外学者努力探讨的焦点。研究者们围绕着汉文史料所记“身毒”、“捐毒”、“天竺”、“天毒”、“印度”、“悬度”、“印特伽”等名称,对其来源以及在梵文、伊朗语和西文中的对应关系、演变过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东西方文献资料中所反映的印度名称在语音结构、词汇来源等方面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古代印度与周边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历史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回鹘语文献记载的印度称谓änätkäk 的来历、演变形式以及与其他语言中的对应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以回鹘人及回鹘语为媒介而发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回鹘文文献中所见印度称谓主要有三种:änätkäk,i/ändäkä(西天)[2]43和Sïndu[3],其中,änätkäk一名的研究在本文中具有特殊意义。
一、änätkäk一名的由来
änätkäk一名首见于《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写本第三幕跋语中,原文撰写:
此外,此名亦见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回鹘语译本卷三[5]、 卷七[6]、 卷八[7]之中,均以änätkäk的形式出现。现存于德国,编号为TIIY37(Mainz 131)的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佛教残片中亦记载了änätkäk一名,意为“印度”[8]。由此观之,änätkäk是古代回鹘人对古代文明国度印度的称谓,并为后世所承袭。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änätkäk一名的来源及其变体的探讨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其含义、来历、演变过程也成为史学家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在此问题上史学家们尚未取得共识,各家对änätkäk一名的来源讨论研究结果如下:
(1)关于änätkäk一名的由来,德国学者史维特尼(Schwentner)在《吐火罗语》一文中写到:史无明证,来源不明,至今无从知晓[9]894。
(2)著名印度学者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在其《中文古籍中的印度古名考》一文中谈及änätkäk,并认为:“龟兹—吐火罗语称印度的形式是‘印特伽’∗in-d1@k-ka>Indäk(a),龟兹—吐火罗语没有h或送气音,这正是龟兹语在辅音方面的特征。突厥语的Indäk(a)完全借自龟兹语,后来出于同一来源的借词亦见于回鹘语,回鹘语印度名称作änätgäk(蒙古语也作änädgäk)。”[10]按照师觉月教授的观点,龟兹吐火罗语中无有以h-起首的词语是将in-d1@k-ka>indäk(a)和änätgäk比拟为吐火罗语词语的唯一根据所在。上述观点,对探讨änätkäk一名的起源及变化形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不可全盘接受,因为在作者的论点中有以下不足之处:首先,作者将änätkäk的来历最终解释为“月氏语”,但至今为止,我们尚不知“月氏语”的任何语言材料,而且,这一语言的命名问题在中外学术界一直留有争论,疑问重重,其语属尚未定论;作者所根据的语言学和历史学依据还很薄弱,缺乏坚实的语言学证据,所以尚不能令人信服。其次,在文中没有指出所谓龟兹吐火罗语in-d1@k-ka的文献出处。据我们所知,龟兹吐火罗语中的印度名称并非in-d1@k-ka,而是yentuke[11]。再次,作者文中没有指出突厥语中印度名称的原形,至今为止,尚未发现突厥语中关于印度名称的明确记载。毋庸置疑,这是根据汉文文献所记“印特伽”而得出的结论,故不可从之。
(3)钱文忠先生在《“印度”的古代汉语译名及其来源》一文中将回鹘语印度名称änätkäk与汉语“印特伽”(印度)联系起来,认为二者皆源自龟兹语(亦作甲种吐火罗语)Yentukem.ne[12]177−181。
(4)徐文堪先生亦主张回鹘语änätkäk源自龟兹语(又称吐火罗语B)Yentukem.ne的观点,并进一步引证更充分的史料指出:考证龟兹语即吐火罗语B中有Yentukem.ne一名,其中kem.的意思是“土地、国土”,-ne是龟兹语单数依格之标志;《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和《宋高僧传》卷三译作“印特伽”,除龟兹语外,粟特语作’yntk’w,回鹘语作’n’tk’k等,亦可比照[13]。
徐文堪和钱文忠两位学者的意见基本一致,即回鹘语änätkäk源自龟兹语(’n’tk’k,又称吐火罗语B)Yentukem.ne,这一结论长期以来为许多学者所遵循,成为了不刊之论。笔者认为,无论从语言方面还是历史方面,都可以对以上所说提出质疑的理由。首先,在语言史料的选用上还是音韵学方面的对应上,在龟兹语Yentukem.ne和回鹘语änätkäk之间很难建立一个对应关系,因此,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其次,以上学者对änätkäk以及与其有关的“印特伽”来历、变体做了详尽的论说,但他们过分地相信前辈学者所提出的吐火罗语说,并未参考粟特文文献所记载的其他例证,亦未涉及该词语音结构及该词所属原语的构词特征,从而偏离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回鹘语印度名称的来历与粟特语有关,并非源自龟兹语Yentukem.ne。粟特人是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贩,在交往中,许多中亚地名、人名、族名以及宗教术语以粟特语的形式传入到其他民族语言当中。1972年,匈牙利学者哈马塔教授撰文对汉文文献所记“突厥”一称,做了颇为详细的考释并提出了他和前人不同的看法。据哈马塔称,汉文“突厥”一名源自其粟特语形式Turkīt或Turkīd[14]。哈马塔教授论证的问题与本文讨论的主题无关,但他关于“突厥”一名的论述和分析,对本文颇有启发。笔者在此想通过粟特语文献中有关记载来剖析änätkäk一名的来源问题。
第一,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中,见有一些粟特语中亚、西域地名, 其中一个作’yntk’w。 ’yntkwt由德国学者赖歇尔特考证为粟特语印度名称的宾格形式[15]14。此外,由恒宁刊布的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Parthian,一称安息语)词汇表中亦有一个地名,称hyndwg’ng,意为“印度的”[16]。其中,帕提亚语印度名称hyndwg’ng在语音结构上与其他伊朗语中的印度名称相一致,均以辅音h-起首,惟有粟特语’yntk’w,’yntkwt在语音和语义上与回鹘语印度名称änätkäk最为接近。据此,笔者初步认定,粟特语’yntk’w,’yntkwt和回鹘语änätkäk同出一源。
第二,我们将粟特语文献所见印度称谓‘yntk’w之宾格形式’yn’tk’k或’yntk’k可分解为’yndu+k+k[indu+k+(i/a)k]三个语言单位,其中,前两个部分由表示“印度”的indu和印度—伊朗语族诸语言中特有的、由名词构成形容词的附加成分-ika,-aka,-iku(亦称性状复合词后缀)组成①–k为印度—伊朗语族诸语言中所常见的、由名词构成形容词或表示领属关系的附加成分。在语言学上,按照梵语的习惯叫法称之为Bahuvrīhi词缀。Bahuvrīhi一词由bah´u(“多、拥有、富有”)+vrīhī(“水稻、大米”)组成,可译为“拥有大米、盛产水稻的”,汉译为性状复合词词缀。,即indu+(?)k>∗induk(’ynd’k),意为“印度语的、印度的、印度人”。与其相当的是:中古波斯语hindūγ;亚美尼亚语作hnduk[9]894;巴克特利亚语(又称大夏语)∗ανδαγo[∗anta+k]①阿富汗出土巴克特里亚语(又称大夏语)文书中见有ανδαγo[antak]一名,《巴克特里亚语词典》(Bactrische WÖrterbuch)将其解释为“地区、区域”。笔者推断,该词应该是巴克特里亚语中的印度称谓,在语音和语义上与粟特语’ynt’k[induk]、中古波斯语hind˜uγ、亚美尼亚语hnduk相当。。据粟特语言学家的研究,粟特语中曾有许多借自其他印度—伊朗语的附加成分,其中,-k最为常见者,常常缀加于人名、地名,具有构形功能[17],这一点我们从粟特语文献中记载的相关地名得到证实。如:kwr’ynk(“楼兰的、楼兰人的”)、Sm’rknδh/sm’rknδk(“撒马尔罕的、撒马尔罕人[的]”)[15]11−14、sγwδy’n’k(“粟特的、粟特人、粟特语[的]”)、’kwcyk=@kučīk(“龟兹的、龟兹人[的]、龟兹语”)[18]。
第三,那么,又如何解释粟特语’yn’tk’k或’yntk’k和回鹘语änätkäk的第二个词缀-k呢?。对此,贝利(Harold Bailey)教授提出的观点是,按照粟特语过时的名词屈折变化形式规律,在构成名词时发生-’k,-’w,-’y相互交替的语音变化,即由宾格形式’ynt’kw变为主格形式’ynt’k’k[9]894。贝利(Harold Bailey)教授对’yn’tk’k的来源和演变形式的判定,笔者大体赞同,唯在其演变过程的具体所指上,与笔者观点略有偏差。需要指出的是,在印度—伊朗语中许多以-k结尾的词语究竟是由性状复合词词缀-k派生而来的形容词还是以-k结尾的本身固有的名词是很难区别开来[19],这主要靠它们在语境所起的作用,即语法功能来区分的。在笔者看来,印度—伊朗语印度名称以’ynt’k[induk]的形式进入粟特语后,又加缀由名词构成形容词的粟特语附加成分-k,从而演变为’yntk’k。这大概是印度名称在粟特语文书中以’ynt’k,’yn’tk’k,’ynt’kw,’ynt’kwt等多种形式出现的原因所在。
第四,在历史上,回鹘人深受粟特文化的熏陶,逐渐接受了大量的伊朗文化因素,这一点在宗教和语言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即便如此,粟特语和回鹘语是两种区别很大的语言,两者构词、语法、词语结构、读音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毋庸讳言,回鹘译经师们对粟特语的词语结构、语法规律不够熟悉,将使粟特语形容词(宾格)形式的名称’yn’tk’k变为名词(即主格形式)并进行语音调整,最终使之成为änätkäk,即“印度”。这种语音变化都是为了调整粟特语借词的音节结构形式,以适应本族固有词音节结构形式的特点。也就是说,回鹘人按照回鹘语元音和谐规律,使粟特语词’yn’tk’k变为änätkäk,以便本族发音习惯,用来指称印度。
二、汉文文献中所见“印特伽”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宋高僧传》所记“印特伽”(即印度)一名的来源与原貌早已为国内外学者们所关注。目前学术界对“印特伽”一名来源的看法基本一致,均认为源自龟兹语(亦称吐火罗语B)Yentukem.ne。但这似乎不能圆满地解决问题。钱文忠先生在《“印度”的古代汉语译名及其来源》一文中引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关“印特伽”的一段资料,认为“印特伽”是’n’tk’k,’ntk’k或’ntk’的音译,但未注明’n’tk’k,’ntk’k或’ntk’所属语言。然而,钱文忠又引证《宋高僧传》“天竺经律传到龟兹,龟兹不解天竺语。呼天竺为印特伽国”一段史料,将“印特伽”比拟为Yentukem.ne之音译[12]179。很显然,钱文忠这一段话与前段看法有相矛盾之处②钱文忠先生在文中提到,“印特伽”即龟兹语(吐火罗语B)Yentukem.ne之音译,似无疑问。揆以当时吐火罗人役属于突厥人,而前者的文化远胜于后者这一史实,则玄奘听说的“印特伽”显然追根寻底是来自龟兹语。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的这一观点都难以成立,不能令人信服。从文化发达或落后的角度来确定词语互借关系的观点是缺乏理论和实践基础的,细究起来,其看法实际上基于1948年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的《中文古籍中的印度古名考》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应该指出,上述研究中,有时太过拘泥于吐火罗语Yentukem.ne的字面意思和语音对应关系,而且,也许限于文献条件,他们没能给出该名吐火罗语形式的文献出处,也没能对除吐火罗语以外的非汉语文献给予充分的重视,在个别问题上还得进一步斟酌推敲。
首先,在语音上“印特伽”和Yentukem.ne的前半部,即“印特”与Yentu在对音上似乎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伽”与Kem.ne的语音明显不符,对应上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其次,“印特伽”与Yentukem.ne(“印度国土”)之间的语义和逻辑关系不够明朗。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汉文文献中的“印特伽”是粟特语印度称谓’yntk’w的对译,与其宾格形式(形容词形式)’yn’tk’k略有不同。“印度”名称的非汉语形式均以辅音h-起首,其波斯语形式为hyndwg;帕提亚语(亦称安息语)作hyndwg’ng;于阗塞语hīdvam.ga;耆那教梵语hindukade´sa;耆那教俗语him.duga-desa;阿维斯陀语hendu,hindu;祆教巴利维语hinduk,hindukān;亚美尼亚安息语hndk,hndakam;龟兹语Yentukem.ne(以半元音y起首),唯粟特语’yntk’w以元音[i],[@],[ε]开头,在语音上与“印特伽”中的“印”(?in)相近或相当[20]。《广韵》作:特,徒得切,入声,其音质为dok/d@k;按王力所拟汉语古音,“特”读作d@k[21]。据此,我们将“印特伽”大概训读为∗ε(@)nt@(o)k(k)a,其读音与粟特语印度称谓’yntk’w(主格形式)相近,似同出一源。
粟特人本是商业民族,他们的足迹遍布古代欧亚大陆的商道上。从魏晋到隋唐,大量粟特人东来兴贩,穿梭往来于粟特本土、西域城邦绿洲诸国、草原游牧汗国和中原王朝之间。正是因为他们代代相传的本领——在各民族之间打交道——粟特人大都通晓多种语言。由于粟特人的这种本领,粟特语也就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上不同民族交往时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唐朝政府早就了解这一点,所以不论在唐朝中央政府所在的两京,还是边镇贸易频繁的州郡,都使用粟特人作译语人[22]。大概玄奘在突厥可汗牙帐那里,从玄奘和突厥可汗之间作译语的粟特人口中听到了’yntk’w这一名称,并将其汉译为“印特伽”。
三、蒙古语文献中的印度名称
在蒙古语文献中,“印度”一名的译写形式十分复杂,又因时代的不同,史料来源的差异而多有变化。蒙古语中指称“印度”的最早形式Hindus(“欣都思”)首见于《蒙古秘史》续集卷二中[23]。由于《蒙古秘史》最初的回鹘体蒙文原著早已失传,现在无从考证其原有的蒙古语读音。然而,德国蒙古学家海涅士(E.Haenisch)将《蒙古秘史》所见“欣都思种”和“直至欣都思种地面”却分别还原为Hindus irgen和Hindus-unγajar-agürtele[24]93−94。《蒙古秘史词汇选释》的作者们同样将“欣都思”训读为Hindus[25]。由于回鹘体蒙古文和以后的蒙文字母,并没有标记词首元音前摩擦音h-的特定符号,因此,我们很难把握“欣都思”的蒙古语原音究竟读作Sindu,indu,Hindu还是Indu,在以上研究中,学者们何所为据,不得其详。
蒙古语“印度”称谓的另一种形式以词首无摩擦音h-的形式始见于年代较迟的蒙古语石刻碑文中。竖立于1335年的《蒙汉双语碑铭》中记载了indu一名,该名亦见于1362年《蒙汉双语碑铭》(《元代西宁王忻都碑》)[24]93。Indu一名是否为汉语对应词“忻都”①至于《元代西宁王忻都碑》中记载的“忻都”,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与其相对应的汉文“印度”称谓亦见于回鹘语《乌古斯汗的传说》中,读作Sïndu。由于时代的差异以及资料来源的不同,我们很难将汉文文献所见印度称谓“身毒”、“信度”、“辛頭”、“辛徒”、“信图”与回鹘语Sïndu联系起来。耿世民先生将回鹘语《乌古斯汗的传说》的撰写年代系于13-14世纪,其年代与汉蒙文献中所记“欣都”、“忻都”相符,据此,回鹘语印度称谓的另一种译写形式Sïndu与“欣都”、“忻都”的对应关系是可成立的。的蒙语译写形式,还是蒙古文译者在此参照其他文献材料所书,目前尚不清楚。
元代以降的蒙古语文献中,“印度”称谓逐渐趋向于以词首无摩擦音h-的形式,与前述形式略有音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代蒙古语文献资料中得到证实。在明代编纂的《华夷译语》的《鞑靼语》(即蒙古语)“人物门”收录了antak(a)/ äntäk(a)一名,汉音译为“昂答克”,意为“西天”,即“印度”。其语音变体亦见于《续增华夷译语》“人物门”,写作altaket/elteket,汉译写为“安惕客惕”②明代火源洁等编纂的《华夷译语》(《鞑靼译语》)中的印度名称与《续增华夷译语》“人物门”中的印度称谓在读音上略有不同,应为其复数形式。在蒙古语族的不同方言中,有的词有两个读音,就是说两个元音间和词尾的边音“l”和鼻音“n”互相对应。,应为蒙古语antak(a)/ äntäk(a)的复数形式。
至于蒙古语印度名称antak(a)/ äntäk(a)的来源,我们暂时拿不出更具说服力的文献资料,但我们却可以引用与其同时代的文献旁证,对其来源、借入途径以及演变过程作进一步的推测。《高昌馆杂字》“人物门”亦收录@nd@k@(“昂答克”),系指“西天”,即印度[2]43。回鹘语@nd@k@(“昂答克”)与蒙古语antak(a)/ äntäk(a)在读音和语音结构上颇为相似或相近,应为同出一源。我们对于二者谁先谁后的问题上,一时无法给予明确的答案,但从其语音结构上,即词首无摩擦音h-以及词末音-k等语音结构特征来判断,二者却均与回鹘语佛教文献所记印度称谓änätkäk当为一词。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学界虽有争议③回鹘语@n@tk@k所载之回鹘文佛教文献《弥勒会见记》译文的成书时间在题记中没有任何表露,故其撰写年代颇具争议。葛玛丽(A.v.Gabain)认为其抄本成书年代应在公元9世纪;耿世民认为,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据德国本可能译成于9-10世纪,而哈密本则抄成于1067年。,但不能因此排除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笔者推断,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及蒙元时代(13—14世纪)译写的回鹘文《玄奘传》所记änätkäk应为蒙古语antak(a)/ äntäk(a)(《华夷译语》)和回鹘语@nd@k@(《高昌馆杂字》)的直接来源。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也曾指出:“回鹘语änätkäk所载之回鹘文文献的撰写年代早于蒙古语文献,据此可以肯定蒙古语antak(a)/ äntäk(a)源于回鹘语änätkäk。”[26]由此观之,借自回鹘语的印度称谓在蒙古语逐渐固定下来,沿袭至今,现代蒙古语中称印度为Enetkeg[27],与《华夷译语·鞑靼语》中之antak(a)/ äntäk(a)和回鹘语änätkäk如出一辙,应为同源词。
四、藏语印度称谓endäkäg
从汉、蒙、藏及回鹘语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在13—14世纪的蒙元时期,是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佛教文化正处于繁荣兴盛之际,这一时期汉、蒙、回、藏等民族之间佛经翻译活动异常频繁,出现了大量的汉藏、汉回、回蒙、藏回以及蒙藏佛教翻译著作;藏语文献中亦出现了从汉、回鹘、蒙古语借来的大量外来词汇[30]403−502,这些例子说明了13—14世纪时期汉、藏、回鹘及蒙古等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语言上的彼此借用情况的一个侧面。
综上所述,鉴于蒙藏民族的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彼此之间的上述文化交流这一事实,笔者有理由推测,藏语endäkäg无疑是以蒙语为媒介而借入的外来词,也就是说,藏语endäkäg的直接来源应是蒙语enetkeg,而其间接来源则是回鹘语änätkäk。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东西方古代文献记载的文明国度印度的种种称谓是一脉相传的,其起源及演变过程均与梵文Sindhu及其伊朗语变体Hindu息息相关。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回鹘文佛教文献所见印度称谓änätkäk系源于粟特语,其原语应为’yn’tk’k,是粟特语印度称谓的宾格(形容词)形式;古代汉文文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宋高僧传》所记“印特伽”乃是粟特语印度称谓’yn’tk’k之主格(名词)形式’yntk’w的对译词。回鹘语印度称谓änätkäk亦见于蒙古和藏语文献中,其在语义和语音上的统一性与13—14世纪时期的回鹘、蒙古和藏族之间共同的宗教文化及相互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