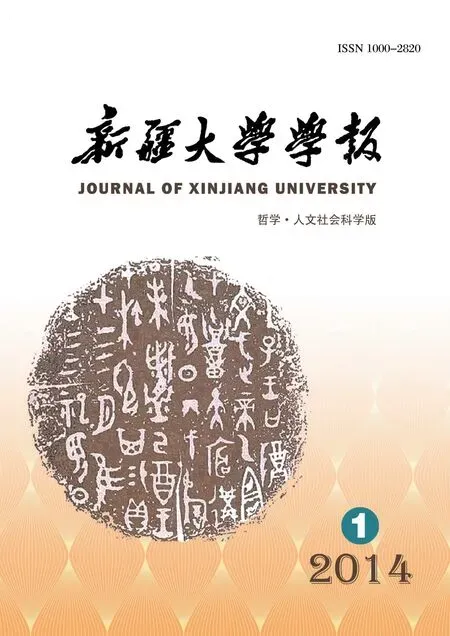吉登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批判的省思∗
2014-03-03孟凯盛卫国
孟凯,盛卫国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000)
吉登斯认为,“不对马克思的著作有深入的理解,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1]他在众多的著作中,特别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集中反思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建构起能够“替代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基本要素”[2]3的理论体系。其中,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社会进化论的错误,需要认真省察。
一、“进化论”批判与“片段变迁”建构
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承认进化论,无论是以伪装的形式还是其他形式。”[2]20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促使人类社会不断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进程,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进化论的观点。对此,吉登斯采取两种方法——方法论的与经验论的对其予以批判。
在方法论上,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进化论,起因于“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对自然控制的日益增强,这体现了某种调适观”[3]360,所谓调适是人对外部自然的适应与掌握,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就是人对外部自然的一种调适观,而“社会没有必要去调适或者是掌握物质环境”[2]21,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经验论上,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是一个“世界成长的故事,并体现了单线压缩和时间歪曲的局限”[3]360。吉登斯从欧洲历史发展的角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先驱,但这并不等于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进化历史的一个普遍阶段。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中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单线性,认为封建社会先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用一种想象的逻辑去取代历史发展的真实,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包含了一种颠倒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把它硬塞到一种特定的发展模式中。”[3]360吉登斯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并不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种关系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其他社会中,阶级并不占据中心地位。阶级分化社会与阶级社会的划分标准是由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在该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所决定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权威性的资源而不是配置性资源是最为主要的媒介。在阶级分化社会,虽然存在着阶级,但是权威性的资源占据主要地位,阶级关系并不是能够提供可以解释该制度化特征的关键性因素。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控制的权力从根本上来自于配置性资源的控制,”[2]210这是惟一适用于马克思的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系的社会,是惟一的阶级社会。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类型划分标准的理论是错误的。
“社会是根据时空伸延的程度予以区分的”[2]90,即根据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变化,引起时空伸延程度的变化作为社会类型划分的标准,并以此把社会划分为三种形式,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与阶级社会。在部落社会中,人们生存时空非常狭小,采取群体和定居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具有高度在场可得性的场所情境的互动,传统与亲缘关系是社会的调节力量。在阶级分化社会中,书写的发明、私有财产的出现、国家的形成导致时空伸延的程度不断扩展,时空具有一定的跨度,城乡之间出现分离,并有着一定的经济交往,但传统和亲属关系在该社会中始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域,由于经济系统具有不断扩张的本性,“一种总体性相互渗透的社会形式——不断增长的全球化系统”[2]166出现了。
吉登斯提出的替代进化论的理论是社会变迁的片段特征化与时空边缘理论。所谓片段,“指具有一定方向与形式的社会变迁进程,并在进程中发生一定的结构性的转变。片段包括从部落社会到阶级分化社会的转变——或者相反的进程”[2]23。由此可见,片段既包括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从一种社会到另一种社会的变迁,也包括结构性变迁的进程,而且变化过程并不具有惟一的方向性,从而否定社会变迁的方向性与历史进化论。
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境遇中的社会体系,不再是一种相互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间的冲突与借鉴的关系,吉登斯借助于时空边缘对此问题給予说明,强调“在片段性变迁过程各种社会类型共时性存在的意义”[2]23。时空边缘是“根据不同原则组织而成的不同社会类型间的连接或者相遇的形态;它们是潜在的或者已实现了的变化边界,是不同社会机体的交叉点”[2]83。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再是一个社会类型取代另一个社会类型的发展过程,而是不同社会形式的共时性存在,吉登斯借此否定单线制的进化论,避免“世界成长的故事”。
二、“进化论”批判的“悖论”
作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4],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根据人们的现实生活、根据人们的实践活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及其发展所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理论观点。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动态结构和发展动力,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结构学和动力学相统一的历史理论体系,是科学的历史观”[5]。
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进化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扭曲,这本身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对象。吉登斯在批判中呈现出思想上的矛盾。
第一,吉登斯正确地认识到“除了个人将其纳入自己行动的目的之外,历史没有目的”[6],但错误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道路、前景的正确描绘与科学阐释等同于历史目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并不是目的论,而是在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历史生成论与发展论。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正是由于实践本身所具有的生成性、开放性,才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历史性。实践活动是二重性的存在。实践首先是一种合规律性的描述性活动,仍然要遵循“是”的原则。人是自然的产物,有其不可摆脱的自然特性和规定性,并只有从事感性的客观活动才能生存。同时,实践又是合目的性的活动,实践主体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其“为我性的”目的对实践活动发挥着规范的功能,不断引导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开展。所以,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一种历史目的论意义上的走向,而是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活动出发,在环境创造人与人创造环境互动中的历史发展论。这也为吉登斯所认肯,“他(注:马克思)指出,‘人们(或让我们直接用人类这个词)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句话说的不错,他们就是这样创造着的”[3]40−41。
第二,吉登斯正确地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但“否认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7]。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并不是矛盾着的存在,历史的规律性本身内含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是历史规律的表征形式。历史规律作为历史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客观的、恒定的联系方式,“本身并不是一个‘奇点’,而是一个‘区间’,亦即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8]。一方面,它是有限度的存在,而此限度就是规律的强制性、约束性、规范性;另一方面,规律的实现形式并不是惟一的,而是多样的存在,具有多种可能,这是为人的主体能动性以及历史的偶然性所致,历史规律实现形式的可能性与多样性又表征主体的能动性与历史的偶然性的存在。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惟一的存在,这体现出历史的统一性与必然性,同时,历史的实现形式是多样的存在,并且能够并存与相互借鉴与发展,这体现出历史的偶然性,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开辟道路,历史偶然性的背后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统一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
第三,反对进化论的吉登斯亦持有进化论的立场,并不能消解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进步论。赖特指出,“吉登斯的时空脱域和片段变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进化理论。······吉登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不是所谓的反进化论与进化论之间的区别,而是不同的社会进化理论的实质性区分。”[9]92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有反思性监控活动的进展,时空不断在伸延与拓展。在部落社会,人们只能在孤立的地点进行着狭隘的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在阶级分化社会,人们的时空虽然有了较大的延伸,但仍然是相对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时空的伸延,社会系统以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为基础,在时空向度上延展开来,从而使得全球化的特征日益显著。社会关系挣脱了互动的时空局限性并不断拓展,这恰恰叙说了吉登斯本人所批判的“世界成长的故事”,表现出社会的“进化论”。而其进化的两种机制——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①象征标志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专家系统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第24页。,从根本上是依赖于科学技术的革新与发展,并表征着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与水平,在此意义上,生产力的发展是时空脱域的前提。时空脱域的不断进行表现出人们对于资源的使用程度在不断扩大,其中蕴涵着配置性资源的不断扩张,这意味着生产力的不断增长,所以,时空脱域的程度表征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因此,吉登斯不仅承认历史进步论,而且在时空脱域的话语下隐藏着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根本原因的思想,从而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动力学的正确性。
吉登斯用时空伸延的水平表征各个社会在长短不一的时空跨度上伸延开去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吉登斯的时空伸延水平仅从“规模”和“数量”的角度反映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没有追问时空伸延不同“规模”和“数量”间的质的差异与区分,“把所有的传统社会和所有的工业社会一视同仁。”[10]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1]人的积极存在是实践的存在,实践是社会物质运动最深刻的本质。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才赋予时空以灵魂与活力,随着实践活动的拓展,时空不断延伸,不同社会时空发展水平的根本差异,是由实践方式的不同所引致的。无论是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世界历史思想,还是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出的“印度没有历史”的论断,以及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无不体现着时空发展的“质”与“量”的辩证统一。
三、“进化论”批判的简要启示
吉登斯把社会时空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并作为解释社会类型划分的标准、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为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批判中可见,吉登斯立足于时代发展和各学科的最新进展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批判的态度和开放的视野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也许有一定的启发。”[12]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也获得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可,赖特(Wright)曾指出这种批判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鉴赏性批判”[9]77。
任何批判都受到批判的对象与批判者自身的制约,批判者对于批判对象的理解构成其批判的逻辑前提。吉登斯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的问题,构成其批判的逻辑前提和批判对象。离开了对马克思原初境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既不能正确理解吉登斯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也不可能对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做出客观的评价。但吉登斯在解读马克思时,肢解马克思,简单化历史唯物主义,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在许多方面正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
吉登斯正确地主张把社会的客观事实与有意识的主体的活动相联系,但他错误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过于强调系统本身的需要,忽视主体的意识作用,“马克思低估了有知识的人类主体”[2]2,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实践“关于反思性的概念太简单了,必须用双向解释才能加以理解”[13]。吉登斯只是把“实践”概念服从于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建构,过于“强调了‘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于是贬低了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7]。吉登斯所主张的“实践”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二者存在根本性的分野,“吉登斯的‘实践’指的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的个人行动,而马克思的实践则指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的活动。”[14]所以,鲍特茂(Bottomore)指出,“这等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概念的拒绝。”[15]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实践主体是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客体是主体活动所指向并发生对象性关系的客观存在,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是一种指向与被指向、作用与被作用的功能耦合关系,历史的发展就是实践主客体之间的对象化进程,是有意识的人的感性活动过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6]。历史主体的自由意志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晚年恩格斯的“社会合力论思想”更是给予充分的说明,单个人的意志是主观的、随机的、不确定的,但各种意志相互作用、冲突、矫正所产生的历史结果,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的存在。正是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解决了吉登斯所力图解决而并没有解决的问题,即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的二元对立问题,真正实现了它们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