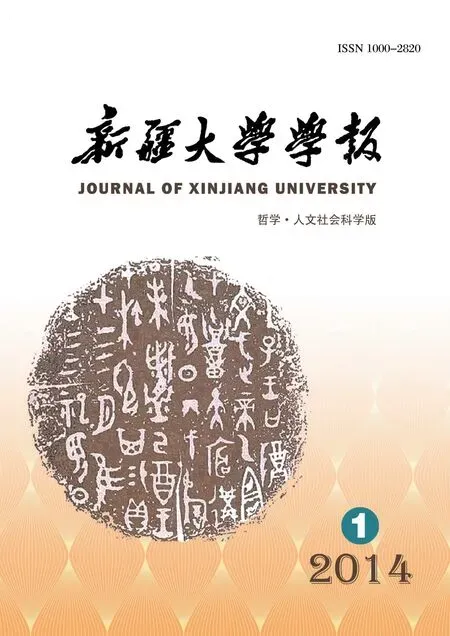晚清民国时期中外旅行家笔下的哈密社会∗
2014-03-03王志佩管守新
王志佩,管守新
(1.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2.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一、居民
在清代史料中,习惯上把新疆天山以南维吾尔族聚居的地方统称为“回部”,称维吾尔人为“回民”。在魏源的《圣武记》中称:“回部者。天山南路也。天山以南为葱岭正干。袤数千里抵哈密。其左右为准回两部。”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谪戍新疆伊犁,在此期间,林则徐曾三次亲临哈密。他看到哈密“城及附近回民约万余户,男戴印花小帽,女穿红衣,土人呼为缠头,其语与华人言大异,然能华人言者亦多”[1]。1906年3月裴景福行至哈密时,见“市贾均汉人,缠民往来其间,凡留发结辫如汉民者,皆应役于官”[2]265。1907年被调赴伊犁创办警政的李德贻在1909年6月途经哈密时,哈密“全市人口约二万馀,缠回居住十之七八,其膏腴之地,皆属回王所有,故回富而汉贫”[3]。清代,由于哈密回王归附清朝较早,对清朝统一新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清朝统一新疆后就给予哈密回王以特殊的待遇,享有特殊的礼遇,在回王统治下的“回”即维吾尔族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优待,故形成了哈密“回富而汉贫”的社会现象。两年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来到哈密,他在《行记》中记载:“哈密是天山南路东端的一个城镇,人家约3000户,土地肥沃,商业、畜牧业都很发达。”[4]1021917年3月谢彬路过哈密,受到第八代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的款待。谢彬看到:“城内回民四百余户,深目隆准,躯干雄伟,圆帽革履,服饰皆殊,文字横行,语言侏俪。乍见疑是西洋人,所异者目睛黑耳。妇女身衣红袍,首蒙巾帨,长及于肩,酷肖印度女子装束。”[5]17谢彬描述的“红袍”正是前文林则徐笔下的“红衣”,而“深目隆准”,“乍见疑是西洋人,所异者目睛黑耳”的体貌特征,则正说明这是民族融合的结果。1919年4月林竞抵达哈密,他在《亲历西北》中写到:“回民男子伟驱浓髯,高鼻深目,状类欧人。”[6]212在提及哈密本地缠回、汉以及汉回等民族时说:“哈密全县人口,缠回约二千户,汉民约一千户,汉回五百户。缠回为土著,言语、风俗、文字均异于汉人,信仰回教,性情淳良。汉人来自内地陕甘一带为多。汉回之语言、状貌、衣冠均与汉人同,风俗、习惯,同者多而异者少,虽奉回教,讼阿拉伯经文,而应用则以汉字为主,追溯源流,虽有一部分血胤源于回纥,唯年代久远。”[6]216另外,“蒙古、西藏、汉人,亦多有信仰其教者,彼此同化,遂未能深别,故其大致反似汉人,而与缠回则迥然不相同。”[6]217
二、建筑
特色鲜明的建筑,往往是一个地区最容易引人瞩目的目标。在上述中外考察家和官员们的笔下几乎都能看到对哈密回王府的描述,而对普通民居等建筑的记述则鲜有提及。这是因为,当时新疆的普通民居大都是以土坯砌墙,原木为樑,芦苇或芦席覆顶,草泥抹墙、抹顶而建成的土坯平顶房,各地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哈密回王府则可以说是当时新疆境内规模最大、最有特色的宫廷式建筑,因此当他们被邀请到王府做客的时候,引起他们的注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人萧雄详细拜谒哈密回王时,回王府“二门内,正宅三层,皆在平地。宅之右,即拾级登台,台上屋舍回环,悬窗下瞰,其内院也。宅左,步长廊,更进一门,则园林焉,亭台数座果树丛杂,名花异草,盆列成行,俨然内地风景”[7]卷2,12。1906年3月裴景福参观王府花园时写到:“广百余亩,土径上覆以砖,有亭馆三四区,结构雅洁,而古木连阴,百花齐放,红白绚烂,为中土园亭所未有。”[2]2681917年谢彬也到此一游,“回王花园,亭榭数处,布置都宜,核桃、杨榆诸树,拔地参天,并有芍药、桃、杏、红莲种种。”[5]21从这些描述中不仅能看出哈密王府对汉族传统古典建筑园林艺术的吸收,而且王府庭院从细节到全貌还体现着中原大宅院的布局风格,同时也体现着新疆维吾尔族民居的特点。王府著名的万寿宫坐落在花园的东北角,是一座“小型的中国古典庙宇建筑形式的独立房屋”,坐北朝南,这里是专门供奉历代清朝皇帝彩色塑像的地方,“每座塑像前都有一个供台,台上有朱色木牌,写着生死年代”[8]217。每年春秋两季,回王和哈密的清朝官员就在这里对历代帝王祭祀。从‘万寿宫’的修建与内部陈设内容的设计,又可以看出哈密回王家族对清朝中央政府的感念与忠诚。
1905年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在哈密时曾受哈密回王之邀进入王府参观。“这个王宫同吐鲁番郡王在鲁克沁的王宫一样,是用方砖建成的,有许多很大的房间,一些房子里装饰得非常美丽。我们看到在所有的墙上,都悬挂着精美的具有中原和和阗风格的壁毯,美丽诉中原和布哈拉风格的丝绸刺绣品,还排列着从和阗运来的玉石、中原的瓷器等。壁炉台上还放着法国的座钟,还有一盏样子非常难看的俄国的煤油灯。”[9]99在我国考察家徐旭生笔下,哈密回王府“客厅颇大,陈设美丽,但光线不明。墙上中堂对联完全汉式”[10]162。哈密王府室内陈设中西合璧、多元文化的特色由此可见一斑。而那个和法国座钟摆放在一起的“俄国煤油灯”正是新疆受俄国文化影响的一种体现。1928年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的斯文·赫定来到哈密提到,“王宫是中国式的”,“室内铺着地毯,摆放着桌子和成行的红漆椅子。墙上悬挂四幅大中堂,上面是福、禄、寿三字”[11]122。汉式的对联、中国式刺绣、“福、禄、寿”等字幅,这些细节又向我们展示了哈密回王受汉文化影响的一面。
除回王府外,回王陵也是当地一座重要的建筑。来访者往往是在参观了回王府后,就“出西门,瞻回王陵”[5]17。回王陵为哈密回王伯锡尔所建,是为表彰和纪念第一代哈密回王额贝都拉对清政府的效忠而修建的一座陵墓,以后各代哈密王均进行维修扩建。在国人笔下,“其顶圆如覆笠,周围皆以琉璃方砖砌成,极为宏丽。”[6]212“高三四丈,下方上圆,墙垣皆花瓷方砖,极其壮丽。通事启门人,左右二碑屹立,上刻可兰经典。逾重门,即五陵所在,皆长方形,上覆彩帛······诸陵之后,有大礼拜堂,规模宏敞,可容千人以上。”[5]17在外国考察家的记录中,“它由坟墓、清真寺和碑石三部分组成。······在门厅中,有两块巨大的花岗岩石碑,石碑为中原风格,其中一块前面刻有波斯文,另一块刻有维吾尔文,其内容是关于清真寺的修建及对王室的祝福······在清真寺附近,我们看到了那座王室坟墓,它是一组木制的建筑物,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混合风格,一半是中原式的。”[9]99哈密回王陵和喀什的阿帕霍加马扎、霍城的吐黑鲁克铁木尔马扎分立于南、北、东疆,对于我们研究新疆陵墓建筑艺术在造型、结构、宗教内涵等方面的内容,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饮食风俗
据文献记载,哈密回王府经常举行宴会,主要宴请中央来新官员、哈密军政官员、著名文士、大商人等,也请本民族的宗教阿訇以及王府亲信官员。每次一般五六桌,多在花园摆设,天冷则在府内客厅。满、汉宾客用满、汉酒席,菜可多至20多道。本民族宾客采用民族饭式,抓饭或肉。每次杀羊20只左右,大米五六斗,清油60斤[8]233。曾在回王府拜访过的勒柯克这样写到:“晚餐也是中原和中亚混合式的,我们吃着中原式的面条,还有包子。这种包子成半圆形,里面装着碎肉、洋葱和大蒜,这些肉菜被糊状的白面包起来后,就放在蒸笼中去蒸。······然后还有煮羊肉、烤羊肉和类似爱尔兰人的马铃薯洋葱煮羊肉,还有肉末的汤,此外,必不可少的还有馕,这里所做的味道比别处更是鲜美。”[9]991928年初斯文·赫定一行也受到哈密王的热情款待,在他们入席后“鱼翅、竹笋和海参以及别种稀奇的美味端上来”[11]122供其享用。谢彬在哈密受邀赴宴时看到:“肴中杨浦鲫鱼,种为左文襄西征时所带来,塞外得食乡味,亦异数也。”[5]18
这一时期途经哈密的考察家和官员几乎都提到了当地的哈密瓜。斯文·赫定说:“早在马可波罗时代,哈密绿洲就以它丰饶的果园和芳香的水果而闻名了。”[11]27“哈密除皮毛岁出八九万斤外,以哈密瓜最有名于世,甘美清香,迥异寻常······以此瓜含糖质最富,切条晒干,味仍香甜,结之如辫,环之成饼,虽历久而不坏也,唯每年出产为数不多”[6]216成为赠送贵客首选的礼物。据谢彬记载,1917年3月4日,“回王送赠鹿茸、和阗毯、哈密瓜干、葡萄干四事。”[5]19徐旭生在此,哈密“李营长来,并送哈密瓜二枚。去后一尝,鲜美绝伦,始知名下无虚”[10]161。1930年,刘文海途经哈密,品尝哈密瓜后认为“哈密瓜甲天下······余曾环游世界两次,又足迹几遍中国,所尝之瓜未有美于此者”[12]69。可谓“玉浆和冷嚼冰凇,崖蜜分甘流齿牙”[13]。德国人勒柯克同样认为“哈密瓜干久负盛名,每年本地的王公们都要将哈密瓜干作为贡品献给北京的中央政府。即使在哈密地区,在山区,日照依然是非常强烈,所吹的风也极干燥,很容易就能把哈密瓜片吹干,这些瓜片的水分吹干后,就可以运往很远的地方。”[9]100
四、教育
晚清民国时期,哈密地区的学校教育主要有为解决官兵子弟接受教育的“义学”和哈密回王开办的经文学堂与世俗学堂。回王沙木胡索特“注意教育,竭力兴学”,并自办义学,吸收维吾尔族学生入学就读。新疆建省初期,沙木胡索特出资兴办伊州书院,教育经费开支,则由“哈密回王于煤窖每车抽银三钱,充经费”[2]273。回王办的义学,原为培养王族、台吉、伯克、大阿訇和毛拉的子弟,课程内容主要有《四书》、《五经》,这对王公子弟了解中原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新疆提出办“新学”。1906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了近代学校教育管理机构——学署,同年根据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将哈密原有义学一律改为初等小学堂,如将伊州书院改设为私立第一初等小学堂和私立第二初等小学堂,后沙木胡索特将这两所学堂改为“‘忠爱汉文小学堂’及简易识字学署”[14]128。
杨增新时期对文化教育的发展采取抑制态度,教育事业停滞不前。据1910年新疆初等学堂分区县统计表记载,哈密厅有学校10所,教员14人,学生人数178人[15]。十所学校中有三所在哈密老城,两所在哈密新城,其他五所分别在哈密城周边村镇。1911年4月28日,被遣戍新疆的温世霖在路过哈密时见“乡村公立小学堂两处,校舍新建,外表颇有可观。”[14]125第二天他“由刘君陪同,参观第一小学。学生三十六人,分甲乙两班。······又阅学生课本,联句略有可观,惟年龄不齐,人数太少。盖城内住户仅二三百家,非学童不愿入学也”[14]125−126。1912年橘瑞超来到哈密时看到“有5所作为教育机关的伊斯兰教经学堂,一个学堂的学生只有十几名;回城又有一所回部王私立的小学堂,以汉族人为老师专门教授汉学,这里的学生也仅二三十名”[4]102。从这一时期考察家、官员们的记录来看,当时哈密的学生人数普遍较少,主要原因是人口数量本身比较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教育的普及程度不高。由哈密的教育情况也可反观整个新疆的教育状况,正如1930年9月刘文海在《西行见闻记》中所写:“以哈密之大,且当东西交通要冲,城内亦仅一小学,汉回儿童合计不过二十,其他偏区落伍情形更可想见矣”。[12]88然而,从哈密回王所办学校实行汉回并重,“以汉族人为老师专门教授汉学”的情况来看,哈密回王对双语教育与文化交流的确是非常重视的,也对当时哈密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从相关史料与上述考察家、官员们的行纪中都有明确的反映。
据《哈密回王》记载:“七世回王伯锡尔能说一口北京官话。”[8]173九世回王沙木胡索特精通汉文、汉语。1911年初温世霖见回王,看到回王沙木胡索特“身材壮伟,颜色和蔼,发辫下垂,粗通汉语。”[14]1271917年谢彬在《新疆游记》中也记载到沙木胡索特“能操汉语,谈新疆情形颇悉”[5]17。1927年徐旭生写到:“回王年七十一,白须苍颜,精神矍铄,身材不高而丰满,衣饰皆汉式,汉话亦极流利,不知者恐难断定为他族也!”[10]161。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沙木胡索特对汉文化始终持积极吸收的态度。另外,沙木胡索特的王府大台吉霍家蔑牙斯“气度自殊,能识汉文并中国算法,曩为军中采粮,曾见在粮台查数,于汉字薄中,且对且算,亦智士也。”[7]卷3,2这里虽然没有关于汉族官员或百姓说维语、写维文的记载,但是哈密回王办学“汉回并重”的双语教育模式,必然会使在此学习的汉族学生能够掌握一定的维吾尔语会话和书写的能力。正是这种相互学习与吸收,不仅在维吾尔语中出现了很多汉语词汇,而且在汉语中也出现了许多的维语词汇,甚至还产生了不少维吾尔语和汉语相杂的民歌,如“衣西克牙甫门关上,其拉克央杜灯点上,克克孜沙棱毡铺上,尧特抗页朋被盖上”[16]。这首民歌每句的前半句是维语,最后三个字是汉语,前后意思相同,充分反映了维汉文化交融的情况。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考察家、官员们的笔下,虽然展现了哈密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但更多反映的则是以哈密回王为代表的当地上层人士的生活场景,对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情况反映的并不多。维吾尔族歌谣中所唱的“王宫高耸在大路旁边,谁也不敢看上它一眼。徭役和差事多如牛毛,谁也不能在家里安眠”[8]180。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哈密底层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这在上述考察家、官员们的记述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如1930年刘文海在《西行见闻记》中写到:“倘遇回汉相争,哈密县长例亦将被告回民交由回王处置;但原告回民亦得向国家法庭起诉汉民。”[12]97哈密当地百姓的赋税沉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维吾尔族歌谣:“王府的捐税重如山,穷人的血汗被榨干······王府的捐税缴不完,穷人的血泪流不断,岁月无情染白了头,日子艰难把背压弯。”[8]182到晚清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国初期,这种“札萨克制”已不能适应当时哈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对此,对新疆问题有相当了解的国内官员、学者在哈密都深有感触。1911年4月温世霖离开哈密市感叹到:“新省之政治军事腐败如是,而强俄接境,一旦苟有边衅,前途不堪设想矣!”[14]1331930年后,受战乱破坏,哈密回城“低矮残破的房屋杂乱的挤在一起,房屋之间是街道,是大车小驴通行的地带,百分之九十五的维吾尔族和百分之五的回族杂住在中间,处处表现着古老的色彩”[8]213。可见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与王府是完全无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