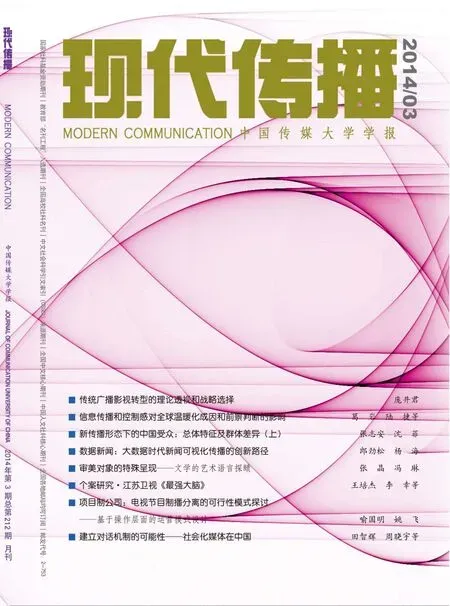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与民族身份/认同
2014-03-03王超
■ 杨 静 王超
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与民族身份/认同
■ 杨 静 王超
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对塑造云南各民族形象、构建民族身份/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至关重要。建国初期的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按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构建了区别于传统民族身份/认同的国家身份/认同,各民族在接受并认同影片中自己民族镜像的同时认同了“镜像”描述的国家主体的身份。新时期以来,各民族以高度的民族自觉性和主体性参与了本民族电影的创作,关注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强调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性意义,强调各民族形象、个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与其民族身份的一致性。按照消费文化逻辑创作的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则构建了一个想尽可能获得更多观众认同的混杂的民族身份却得不到本民族观众认同。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有效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第一,民族身份/认同主体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第二,影片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对白。
少数民族电影;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认同主体;民族语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好莱坞电影迅速崛起,并确立了在全球的霸主地位,欧洲各国提出国家电影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好莱坞以外的各国电影处于边缘弱势地位,各国电影更加强调国家民族气质(风格),以此来抵抗好莱坞电影文化霸权。随即,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相继加入国家电影行列,第三世界国家电影除了相对于好莱坞电影的意义之外,还特别强调塑造国家民族形象和构建民族身分/认同。
此前,在全球传播的好莱坞及欧洲各国的电影中,各民族国家的形象被刻意歪曲,成为被恶意丑化或浪漫化的“他者”形象。1920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中就不断出现丑化中国人的形象:1920年的《红灯笼》《初生》描写了中国妇女缠足、华人街头赌博、吸食鸦片、逛妓院等各种丑恶形象;1930年的《不怕死》则塑造了中国人杀人绑票贩卖鸦片并胆小怕死的卑鄙龌龊形象。因此,我们深刻意识到通过自己的电影塑造真实的国家民族形象,对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稳定社会秩序,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至关重要。
少数民族电影在中国电影格局中有着相似的处境,云南少数民族电影也相应地具有以下意义:(1)边缘弱势地位;(2)表现云南各民族文化;(3)塑造云南各民族形象,构建各民族身份/认同①。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构建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
一些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电影,是新中国成立后制作的第一批少数民族故事片:苗族、哈尼族的《山间铃响马帮来》、拉祜族的《芦笙恋歌》、景颇族的《边寨烽火》《景颇姑娘》、白族的《五朵金花》、傣族的《摩雅傣》、彝族的《阿诗玛》……这是按国家计划生产制作,代表新中国政权的制作者作为各民族文化权威的解释者和改造者,按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主体民族观众的需要,选择表现了各民族文化,塑造各民族形象,构建了区别于传统民族身份/认同的国家身份/认同:强调新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发展的主题,按照阶级压迫、民族歧视、骨肉分离、亲人团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紧密团结、平等互助过上幸福生活的叙事模式来结构情节。人物及其民族性成为民族反抗、阶级反抗二元对立情节模式的象征符号,而传统民族的文化主题几乎被湮没。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彝族故事片《阿诗玛》便是一个典型范例。《阿诗玛》是彝族的一个久远的美丽传说,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叙述中,“抢婚”的传统文化习俗被改造为阶级斗争的情节模式,将抢婚的热布巴拉家与阿诗码一家的矛盾设计为阶级矛盾。阿黑救阿诗玛的情节也演变成了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象征,而阿诗玛的悲剧成了阶级社会被压迫者的悲剧。而事实上,抢婚对彝族人来说是一种有效缔结婚姻的仪式,《阿诗玛》中主流意识形态对民族文化传统习俗进行了有目的的误读,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了政治性、功利性的改造。
但是,美国电影人类学家萨拉·迪基在《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的贡献》一文中指出:“电视(电影)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民族文化力量,它绝不仅仅反映或提出国家利益”。②这些电影同时也为各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表现和表达的空间,使各民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展现。白族故事片《五朵金花》就没有讲述阶级斗争的故事,而是讲述了一个白族青年走遍苍山和洱海寻找一见钟情的金花姑娘的爱情故事。影片中甚至没有脸谱化的阶级敌人形象。大理白族一年一度的三月街的民俗聚会不仅是确证社会成员民族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达成传统文化共识的白族传统节日庆典,更是一种新中国各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的社会景象的体现:捞海草、打鱼、苍山采药……久远历史记忆中在苍山洱海边上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白族人独特的生活场景,传统的摔跤、射箭、赛马运动,传统舞蹈霸王鞭和一路唱来的白族传统民歌,汇入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劳动、炼钢铁、修公路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环境和现实经验中。
影片中阿鹏走遍苍山寻访到的五朵金花,除了体现她们主流社会的身份——副社长、劳动模范、兽医、拖拉机手、炼铁工人以外,作为传统白族家庭的女儿和妻子,她们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也都是典型的白族女子形象,传统的含蓄蕴藉的情感方式,传统的恋爱和婚姻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民族宗教信仰也通过炼铁工人金花“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和管闲事大叔动则向本主起誓的滑稽有趣的言语和行为得以再现。
当然,这仍然存在将各民族文化生活和各民族形象浪漫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并遮蔽了各族人民真实生活和真实生命体验的问题。但是影片却塑造了各民族淳朴善良、能歌善舞的美好形象,这是一个比现实经验更加完美的各民族形象。对于初次在电影中看到与自己如此相似的形象的各民族观众来说,自己民族的形象就应该是这样。于是便不约而同地接受并认同了影片中自己民族的镜像,同时也认同了“镜像”所描述的国家主体身份。
对云南少数民族观众群的调研表明,每个民族都为有一部属于自己民族的电影而自豪,并由衷地认为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自己理想的民族形象。于是,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被其文化源的观众纳入到构建自己身份/认同的民族文化体系之中,通过对影片主人公的认同,各民族观众建构起区别于传统民族身份/认同的国家身份/认同。
二、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构建的现代民族身份/认同
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构建了关注个人命运与个人体验、强调个人主体性的现代身份/认同: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个体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构建的民族身份/认同由此发生相应的变化:(1)本民族成员以高度的民族自觉性和主体性参与了民族现代身份/认同的构建。(2)关注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强调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性意义。(3)强调各民族形象个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与其民族身份的一致性。
哈尼族导演李松霖创作的故事片《俄马之子》就比其他由汉族人创作的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更为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云南传统民族的身份/认同。
《俄玛之子》清晰地表现了基于主人公阿水(即导演李松霖的个人体验)的民族身份/认同。影片中,7岁的主人公哈尼族男孩阿水出生于一个传统哈尼族家庭。耕种之余,父亲靠雕刻制作水烟筒到镇上售卖以换取一家人的盐、肥皂等日用品,母亲生儿育女、操持家务,阿水在稳定、封闭、原始、自然的传统社会中,通过亲长的言传身教习得哈尼族文化并形成其民族身份/认同,阿水在日常生活中(如同生物遗传般被称为文化遗传或种族遗传)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哈尼人传统的礼仪习俗、童谣和歌舞,并在节庆祭祀时跟着村寨长老摩匹学会了唱诵民族起源的神话史诗《萨伊萨》,这也是一首歌颂天神和祖先、祝祷赐福山寨的古歌。
但是,自从阿水上小学那一天起,他的身份便被纳入到更大的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之中。汉族文化及其涵容的主流意识形态对阿水内在固有的③民族身份/认同进行的篡改,将其建构成为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村小学的国旗、来自北京的朱老师,朱老师女儿阿妮书包上的红星,他学习语文、算术、背唐诗,朱老师带着他到镇上的影院看《祖国的花朵》……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阿妮和朱老师在橡皮上写上他的汉文名字“李泉水”,这一具有文化象征性意味的命名,将他安置在汉语言文字表述的秩序中,赋予了他主体的身份。此后,阿水按照学校的汉族文化和现代文化及其承载的主流意识形态来想象并认同自己主体身份。并最终在代表着主流文化的电影演员主考官挑剔的目光中,凭借哈尼族歌舞融入了主流社会,确立了自己在主流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和身份。
影片中阿水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是形成和影响他一生的个性和风格的因素,是构成他生命历程中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民族身份/认同则通过他生活其间的哈尼族古老原始的生存环境和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云雾缭绕的森林中的哈尼山寨;从父母亲长那儿习得的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沿用千年的语言、唱了千年的童谣、讲述了千年的神话和传颂了千年的史诗,传递出一种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生命感和广袤空间中的历史感。他所亲历并体验过的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使阿水个人及其所属民族群体保持着自我(我族)和他者(他族)之间的差别感和界限感,确保了个体身份/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差异性。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使得阿水能够在辨识、认可、接受和欣赏他者(朱老师、《祖国的花朵》《卖花姑娘》《少林寺》等电影塑造的人物代表的他族)的身份、意义、价值和地位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个体性。
同时,阿水现代身份/认同的整合性又使得他具有对新的身份的接纳能力和吸收能力,也就是他在面对现代学校老师,面对媒体(电影和电视)他者(他族)丰富复杂、新奇变幻的身份时,能够在“异”中求“同”;在多种多样、眼花缭乱的新奇的“镜像”中选择认同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有益于自身发展和成长的身份。他学习汉语、学习唐诗、学唱新歌、学练武功、学放电影、演电影,最终拍电影,成为自己拍摄的电影《俄马之子》的原型。
导演李松霖的哈尼族身份使《饿马之子》构建的民族身份能够与本民族观众的现实生活经历和真实生命体验高度一致,从而得到本民族观众的高度认同。
三、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构建的混杂的身份/认同
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消费文化的泛滥,使云南各民族身份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遭受到巨大的冲击,剧烈动荡的流动性和碎裂时空的当下性,极大地模糊甚至掩饰了各民族身份的差异性,消解了各民族认同的历史感,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界限感。云南各传统民族重新塑造着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作为各民族文化构成的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则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化。
《花腰新娘》便是按照消费文化逻辑构建的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的典型范例。进城打工、开办啤酒厂、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欢天喜地看迪斯尼动画片《猫和老鼠》……这正是花腰彝现实社会生活的写照,是花腰彝族社会文化的现实境遇,然而离开了历史积淀于现实的独特民族文化传统,花腰彝山寨将与中国农村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差别。
民俗、服饰和歌舞是维持少数民族故事片新奇感和吸引力、满足大众对这一类型电影消费需求期待的基本的商业元素。
《花腰新娘》中结构影片情节的重要线索“不落夫家”的婚俗,在花腰彝的现实生活中已经无关紧要,年轻人“归家”习俗的观念已经相当淡漠,影片中对这一习俗的反复强调,除了“奇风异俗”的展示外,也是现代女性主义流行话语对传统民族男权社会及其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的想象与批评。对于影片中亲身经历和体验着这一古老传统习俗的凤美来说,这只是一个她并不认同的老规矩,为了加入舞龙队,她反叛并破坏了这一传统,对此她的公婆和父亲颇为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但花腰山寨的权威人物村长却支持和帮助了她。也就是说,影片中强调的花腰彝族这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传承力而不再构成认同主体相对稳定统一的民族身份/认同。
影片中表现的舞龙习俗亦是如此,花腰彝族传统的舞龙源于一年一小祭,十二年一大祭的“祭龙”习俗,花腰彝族传统社会为男性支配,女性被认为是污染的根源,神圣的仪式和圣洁的地方都不准女性介入。花腰彝祭龙的整个过程是不允许女子参加的,祭龙队伍途中遇到妇女都会被认为不吉利,而女子舞龙却彻底颠覆了这一具有宗教性质的祭祀仪式对女人的禁忌。女子舞龙队为啤酒节宣传助兴,使舞龙的传统文化习俗成为顺应现代社会需求的商业表演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片中表现的舞龙已经不再是古老的花腰彝“祭龙”习俗的延续,丧失了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感和广袤空间中的历史感。
对于影片中舞龙队的队员来说,参加全国舞龙大赛似乎是舞龙最重要的意义,这与其他地方其他民族的舞龙队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舞龙不能让凤美及其所属民族群体保持着自我(我族)和他者(他族)之间的差别感和界限感亦即民族身份的差异性。
花腰彝的歌舞及服饰也是影片用以构建民族身份/认同重要的民族文化。歌舞的初衷是取悦神灵祖先,祈请降福人间,庇佑后人。随着人类征服自然力量的增强,这一功能逐渐减弱,而悦人自悦的功能增强,民族歌舞也从民俗仪式中独立出来,成为最具民族独特性的娱乐方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风格独特的歌舞,但《花腰新娘》却将本来是属于石屏彝族的另一支系“三道红”的传统歌舞形式——烟盒舞和海菜腔嫁接到花腰彝族的歌舞中。
影片中的主人公凤美、阿龙及其所属民族群体说汉语(影片为纯汉语对白)、写汉字,他们似乎已经失却了构建民族身份/认同核心特性的民族语言,唱着分不清自我(我族)或别人(他族)的文化元素混杂的歌,跳着混杂的舞。按照需要什么提供什么的消费文化逻辑,穿着耀眼的民族服饰,为满足猎奇的他者目光凝视的需求表演着“归家”的民俗,表演着新“发明的传统”舞龙。一种新的不断趋于同质化无差别的混杂身份/认同正取代着具有清晰的差异性的民族身份/认同。
对于《花腰新娘》构建的混杂文化和身份/认同,作为认同主体的花腰彝普通观众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疑虑,尤其是看着电视长大并有着外出打工经历的年轻人。但是经历了传统社会并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刻体验、深厚感情和自觉意识的少数人却对影片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的他性和混杂性深感担忧和压力,他们无法接受一个花腰女子像凤美一样狼吞虎咽地吃米线,打蚊子时一巴掌打在公公的脸上,在房梁上“倒挂金钩”,上房揭瓦,大嚼黄瓜,他们认为这种粗鲁“野蛮”的行为与花腰女子含蓄温柔的性格及其行为模式不相符合,甚至认为是对自己民族女子形象的丑化。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构建的混杂身份,很难引导本民族观众体验共享的同盟感和归属感。
四、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和基本要素
少数民族故事片构建的民族身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认同感,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分析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可以看出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
1.民族身份/认同主体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
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在中国影视文化格局中的边缘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专业制作人才的匮乏,各民族对电影制作机制的陌生使表现自己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影片需要由汉族或他民族来制作,而由“他者”制作的影片就不可避免地烙印着“他性”,使本民族身份成为满足“他者”消费需求的浪漫化想象。而本民族成员作为主创人员的参与,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电影所表现的民族文化的理解、选择和表达的主体性意愿,同时也能体现本民族观察世界的方式及其形成的独特的形式感和审美趣味,并形成具有民族特质的电影语言风格。
影片《俄玛之子》的导演李松霖就充分体现了哈尼族民族身份/认同主体对民族文化原生性意义和整体风格的把握和掌控,实现了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的传统文化再现体系的创作意图,表现了哈尼族重要的民族文化主题、核心价值取向和真实的生命体验与情感方式,使影片能够唤起民族共享的历史感、生命感,进而引导民族认同主体构建共享的同盟感和归属感。
《诺玛的十七岁》虽然是汉族导演拍摄的哈尼族故事片,但是哈尼族非职业演员魏敏之的参与,保证了其主演的女主人公诺玛的性格和行为模式像一个真正的哈尼少女,同时也避免了像《花腰新娘》中文化理解的差异引发的冲突。
2.民族语言及其话语表达
影片《俄玛之子》和《诺玛的十七岁》中的主要人物对白都用了哈尼族语,而《别姬印象》和《怒江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花腰彝族民族身份/认同的变化的《花腰新娘》的人物对白却都是用汉语。语言不仅只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是社会文化结构的象征系统。与民族历史一样久远的民族语言,是民族身份标志性的特征,对每一个民族成员个体即认同主体来说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母语。《俄玛之子》中阿水的哈尼族孩子身份最根本也是直接的标识正是他一开口就自然而然地说出的哈尼族话语:卖水烟筒的吆喝、与人打招呼、跟父母讲话。《诺玛的十七岁》中诺玛虽然会说汉语乃至学会了简单的英语,影片中她卖玉米的吆喝,与阿明在一起的情节都在说汉语,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她的话语方式,明确辨识她的民族身份/认同。
语言复制和反映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俄玛之子》和《诺玛的十七岁》两部影片正是通过再现哈尼人日常生活中的交谈和对话情景,表现了支配着对话者语言和行为的共同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通过阿水和诺玛在参与一些习惯性的话语过程中自然流露的哈尼族的话语方式、话语情景和情态,表现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而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观众则可以通过他们说汉语时不自然的语音语调以及哈尼族独特的说话方式识别其不同的语言体系、语法规则、文化系统及其民族身份/认同。
《花腰新娘》《怒江魂》中的标准普通话对白和《别姬印象》的汉语方言,都不能准确界定影片人物作为花腰彝族、傈僳族和滇越铁路沿线彝族成员的民族身份/认同,当然也并非只是因为语言本身,话语方式、话语情景和情态以及话语表达呈现的社会文化都与之不符。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一类少数民族故事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并加深了云南各民族的身份/认同危机。
少数民族故事片中的汉语对话,一方面体现着汉族语言体系对各少数民族的想象、描述和规定,这是离开民族语言及其规定的日常话语文化环境的民族成员对民族身份/认同的现实困惑,即便是穿着民族服装,却是在按照汉语对自己民族的描述和想象来思想、行为和言说。另一方面,使用汉语交淡的电影角色作为各民族典范人物形象认同了汉语对自己民族的这一想象、描述和规定,并通过这样一些日常性的话语过程强调了作出这种想象、描述和规定的汉语的社会文化构成。基于语言和话语研究的俗民方法论认为,一个民族习惯性的话语过程就是在维系和强化其共同的文化观念和交谈者所依存的共同的社会结构。④
汉语对白的少数民族故事片弱化了各民族身份/认同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到认同主体对民族身份的理解和体验,使其对民族身份的把握更加困难,民族认同感变得更加淡薄。少数民族故事片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人物对话语言,再加注汉语字幕,既不影响其他民族的观看理解,又能在纪录保存各民族语言的同时,保护了只有通过本民族语言和民族成员的话语表达才能呈现的文化内容及其意义,维护了各民族的身份/认同。同时,也使云南各少数民族通过自己的民族故事片获得一种话语权,能够在大中国民族电影构成体系中发出云南各民族的声音。
注释:
① 英语“identity”在文化人类学中一方面是指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族群区别于其他人或其他民族的个性特征,强调其区别于外在其他人或其他民族的本质上的差异,接近汉语“身份”的表达:“个人身份”或“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内在延续固有的核心同一性或共性:“自我认同”或“民族认同”。人的自我认同是对个体身份的构建和确认,民族认同或文化认同则是确立和维持个体身份中在生物种族和文化传统上与同一族群其他人的同一性。
② [美]萨拉·迪基著:《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载《国际社会科学论丛:人类学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③ [美]乔纳森·弗里德曼在《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一书中认为,民族文化认同“不是实践的结果,而是内在固有的,不是习得的,而是天赋的。”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郭建如译,第48页。
④ [英]奈杰尔·拉波特等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作者杨静系云南艺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影视艺术学博士;王超系云南艺术学院影视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潘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