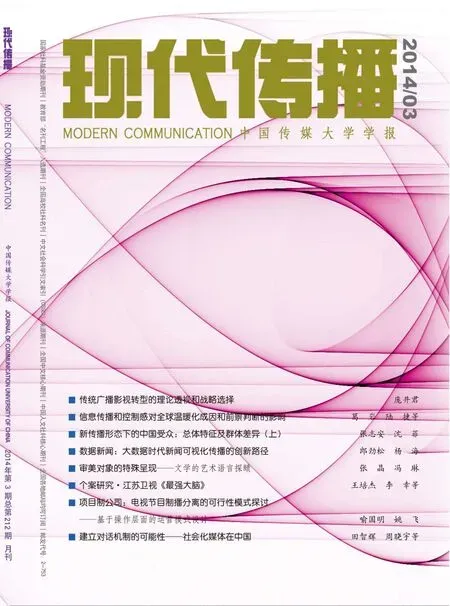2034年的传媒大学(下)
2014-03-03朱光烈
■ 朱光烈
2034年的传媒大学(下)
■ 朱光烈
(续前期)
专业主义教育批判
1.爱因斯坦说,专业主义教育训练出来的是一条很有用的狗
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思想家爱因斯坦在《目标》一文中研究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为我们的志向和价值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目标。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不过是各种事实之间是怎样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是认识客观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但并不能打开通向“应当是什么”的大门,不能导出我们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只是凭着思考我们还领会不到那些终极的和基本的目的。弄清这些基本目的和基本价值,并且使它们在个人感情生活中牢固地建立起来,这正是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必须履行的最重要的职能。“如果人们从它的宗教形式中把这个目标抽了出来,而只看它纯粹属于人性的一面,那么,也许可以把它叙述为:个人的自由而有责任心的发展,使它得以在为全人类的服务中自由地、愉快地贡献他的力量”。“个人的崇高的天命是服务”。“应当帮助青年人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成长,使他感到这些基本原则对他来说就好像他所呼吸的空气一样。”①
在《伦理教育的需要》一文里,爱因斯坦则说:“我确实相信: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只是为着使用和实际的目的,过分强调单纯智育的态度,已经直接导致对伦理价值的损害。我想得比较多的还不是技术进步使人类所直接面临的危险,而是“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人类相互体谅的窒息,这种思想习惯好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在人类的关系之上。”②在《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一文里,爱因斯坦极其反对专业教育,他写道: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许良英、刘明注:这里的价值即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
正是实用的专业主义阻断了人文主义的发展链条,那么人文主义应当如何去培育呢?爱因斯坦继续写道:
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的不是——通过教科书传给年轻的一代的。……当我把“人文科学”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十分枯燥的专门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据的那种精神。③
爱因斯坦这里的论述,恰恰与上述社会建构主义学习范型以及行为教育的主张相一致。其实,这类经验与教育思想并不是源于爱因斯坦的,而是古已有之的,只是工业社会发展起来的专业主义教育把它阻断了而已。而这个时代的爱因斯坦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尖锐地批评专业主义培养出来的只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狗或者好使的机器,他使这些思想更为深刻。但是目前引用出这样的话来,一定会使许多专业主义教育的奉行者感到是发了疯了。
2.专业主义扼杀创造性
所谓专业主义就是指那些眼光只落在专业之内的狭隘经验学习理念。在自然科学经验学习领域中,专业主义就是科学主义,它有一套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严密的逻辑,但是它走不出科学的领域,把科学当成唯一的、排它的真理标准,拒绝与人文主义的整合,也不承认文化素养的意义。爱因斯坦把专业主义教育训练出来的人比做狗,实际上是工业社会对于人的异化结果,这一点也不奇怪。另一方面爱因斯坦也说过,“我想的比较多的还不是技术进步使人类所直接面临的危险,而是‘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人类相互体谅的窒息,这种思想习惯好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在人类的关系之上。”他还曾经表示过,过多的知识传授只能使学习者处于浅薄状态。爱因斯坦并不是一概地反对专业教育,他反对的主要是由于务实的思想所带来的对于文化素养的遗弃。
现行的大量高等教育中的专业教育以在社会上寻找职业为目标,那里不重视基础知识和学科逻辑建设,所看重的只是专业技能的训练、专业直接有用的知识和技术以及狭隘的、可以直接用于操作的联系实际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成为不证自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那些专业主义者看来,当下无法即刻使用的一切学问、知识和理论,都是该死的牢什子,都是瞎胡闹。他们更是不知文化素养为何物。
专业主义教育和学习,特别是狭隘的专业训练和学习,所带来的是封闭的心灵,心被封闭在专业牢笼里,如同黑暗的牢房一样,没有一点活气。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不过,许多人对此习以为常,并不能察觉这种悲哀,死而不知其死,这是悲哀中的悲哀。这里当然不会有创造之花的开放,事事急功近利,很难避免“上手快而后劲不足”的命运。
现代社会的学科越来越多、越来越窄,这种发展趋势使现代人容易忘记且难以把握基本的理论和广博的知识。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一书中写道:远古的学者追求的是道之根本,而后来的诸子百家“各走极端,执迷不悟”,“所以圣人明王的大道,幽暗而不能彰明,闭塞而不能光大,天下人都自以为自己所偏好的见解就是大道。”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一书里曾经说过:“凡事略知一二,胜于全知一事”。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还极其推崇“有教养的人”,这种人“不是数学家,不是传教士,也不是雄辩家,而是有教养的人,我唯一喜欢这种全面性”。生活在20世纪的法国学者路易·多洛说:“20世纪的科学革命与当前的文化联系起来,正提出如下的基本问题:关键不是考虑自己要认识什么,而是不能对什么全然无知,否则就不能自认为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人了”。④对于一件事物来说,“略知一二”难于与“全面性”有缘,但是对于认识整个世界来说,在不同领域的“凡事略知一二”大致说来能够从不同侧面和层次去观察世界,具有相对意义的全面性,以求达到破除“全知一事”的片面性局限。人的能力有限,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
人的精神、人的心灵是极容易被什么东西蒙蔽和禁锢的。这种蒙蔽和禁锢头脑的东西被称为“所知障”,即你所知道的东西对于你进一步认识事物所形成的障碍,你难于跨越这个障碍,创造难于实现。当我们对什么东西比较熟悉、比较习惯的时候,譬如做学问接受某种理论或观点的时候,特别是形成了某种体系的时候,或者业务形成若干经验的时候,不可忘记要随时跳出这些东西给你的心灵设下的“所知障”,跳在圈子外面反观它,怀疑它,批判它。专业主义者充满着专业的所知障,以为除了专业知识其他的都是没有用的劳什子。创造力的绝对要求是必须破除各种所知障。中国有两句话值得我们注意:一句是“隔行如隔山”,我们必须熟悉专业知识和技巧,不然就无法从事专业工作;另一句话是“当局者迷”,所以要进行反观、怀疑、批判,使头脑随时随地处在与外部世界相适应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最佳状态之中,强调把任何事物、任何知识、任何经验都看成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更需要我们不断地完善它,尽量不使它成为“所知障”。只有随时随地破除“所知障”,才能为智慧和创造力的发挥开辟道路,而破除“所知障”的唯一途径是提高文化素养。提高文化素养的第一步就是走向专业的边缘,广泛涉猎不同学科知识以及获取不同领域的经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幅对联充分表现了中国的智慧,它把创造的立足点扩展到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生,强调的正是提高文化素养的决定意义。
我的“乌托邦”?
1.让教育回归本位
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宗教家和教育家约翰·亨利曾经在当时英国的天主教大学发表过演说,在演说里他把大学分成两类,一类是不督察学习的,修满若干课程并考试及格的任何人都授予学位;另一类则既无教授亦无考试,只是把一定数量的年轻人组织起来集体学习。青年人心胸开阔,富于同情心、善于观察,来到一起自由密切交往,即使没有人教育他们,他们也必定互相学习;所有人的谈话,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系列讲座课,讲述他们自己逐日习得新概念和新观点、新的思想以及判断事物和决定行动的各种不同原则。亨利表示,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类大学,它是一种真正的教育。
约翰·亨利的演说发表于近一百六十前,但是,它并不是奇谈怪论,以学生相互学习和自由学习为主本来就是远古时代的学校学习模式,当时的教育模式是教育的本初模式,体现出教育的根本特征——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稍晚一些的教育,譬如中国古代的孔子和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开办的教育,也是以学生相互讨论为主的。工业社会的到来,由于社会实际工作和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越来越多,以及知识总量增多的速度越来越快,教育越来越走向以教师讲课为主和应试教育以及专业主义教育的阶段。世纪之交的先进教育理论和学校教育已经出现了复归古代的教育模式和约翰·亨利理想的趋势。现在看来,我们还不能在所有的专业领域实行这种教育模式,但是,像新闻专业这样的专业,由于它不具有很难习得的操作技巧,而相应的实际工作又需要与社会广泛的接触,采用这种文化主义的教育(学习)改革,我相信是合适的。
据笔者所知,有些西方国家没有师范教育,任何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当教师,但是需要经过相应的一段时间的专门训练。我的设想实际上很像是这种培养教师的路数。这样做的好处之一是利用了其他专业的优势,尤其是基础比较厚实的专业的优势,以克服长期以来用人单位反映的新闻类专业教育后劲不足的痼疾。
笔者也不主张学生靠漫无边际的讨论了事,在现实生活中,我曾经遇到过有的青年人思想极为极端,而且很难改变,因此教师的引导很重要,不过这样的教师一定是高水平的。
笔者并不主张一切专业训练都应当下马,专业性训练依然应当办下去。但是,我建议把教育与专业训练分开来。教育的目标只是培育文化素养,培育人;专业训练的内容只是实际工作所需要的操作技能。未来的学校,特别是未来的大学所从事的只是教育,而不再负责专业训练;专业训练原则上由各个用人机构自己负责,或由社区统一负责。
终身教育的出现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它宣告青少年时代学习然后终生享用学习成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知识爆炸时代的到来,终身教育时代也接踵而至。终身教育实际上是终身学习。我们现在或许还没有意识到终身学习出现的重大意义。在传统教育事业中,学前教育是从小学到大学教育全过程的准备。终身学习的出现将要改写这种格局,重要的不再是学前教育作为教育全过程的准备,而是学校教育(包括从传统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到大学教育)都是终身学习的基础准备。在这个阶段,需要打好知识的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文化素养的培育、人的培育,养成创造性和获得创新能力。学校教育必须以学习为中心。教育必须开倒车,教育至此终结,即以应试和专业技能为上的现代教育的终结。这种终结是对于教育的提纯和回归。这种新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学习,一切外在的教育(外部灌输的教育)都必须服务于内在的学习,学习是永远的。这种转折的根基深深地扎在当前正在兴起的信息社会之中,扎在电脑网络所构成的虚拟世界之中。这个虚拟世界不仅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学习机会,而且其全世界的交流机会、瞬息万变的信息刺激正在冲垮旧的教育模式。
教育的本质是人心的培养,是人的塑造。随着物质主义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到来之后,教育被改造成就业的前期准备,成为为它者服务的工具,被严重物化。在当今大学里,专业设置多如牛毛,在专业主义教育里面,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成为不二的霸主。专业主义教育美其名曰为社会建设服务、为学生就业服务。教育的这种异化如果不能迅速扭转,使其回归教育的本质,人类文明毫无希望。因此必须把教育与职业培训区别开来,一切强加在教育身上的东西都必须要被扔到九霄云外。职业培训当然仍然需要,但是要在教育之外另起炉灶,让教育回归本身。“教育为什么什么服务”这样的信条都是教育异化的堂皇的说辞,教育只为一个目标服务,那就是人心的培养,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达到物我统一的、审美的人生境界。这个目标达到了,整个教育的社会目标也就达到了。
2.思想家摇篮:未来大学的神圣身份
人总是生活在各种压力之下,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而不再是动物,是因为人能够自觉地应对这些压力,在这些压力之下人不断地思考,从而形成了人独有的思想。迄今为止的文明经验告诉我们,面对着这些压力,人类所思考的主要问题除了富裕之外,更为根本的是希望过上自由、平等、公正的生活。来自于自然和社会的压力是永远存在的,因此自由、平等、公正作为一种理念大概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它只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历史进程,是没有尽期的,于是思想探索和发展也就没有了尽期。正是因为这种特质思想赋予了人类真正的生存意义,苏格拉底说过:“没有思考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早在1970年人类社会刚刚进入信息社会的时候,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它的未来学著作《未来的冲击》一书里的《引言》写道,信息社会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为瞬息万变的境遇,来势之猛实已到了足以溃决庙堂、否定价值、毁拔根基的地步。时代发展之巨、之快使人们普遍感到迷茫,风靡一时的后现代主义中的极端相对主义大概就是这种状况的反应,在那里,整个世界都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不可知的矛盾之中。但是急剧而重大的变革又特别需要新的思想及思想家的出现。在我们刚刚进入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机构评出了千年最有影响的十大思想家,包括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牛顿、康德、马克思、麦克斯韦、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被广泛报道。那个时候笔者没有看到别的千年大家的评选的报道,譬如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发明家等,这种把思想家高高地凸显了出来的现象,表明人类目前是多么需要新的思想和新的思想家。
气候变暖以及各种环境的威胁已经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有识之士的广泛忧虑,人类还能不能在地球上持续生存下去早以已经成为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霍金曾一再说过,人类在地球上活不过21世纪末。当前人类最大的危险是物质主义的疯狂肆虐,人类的生存危机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日趋严重。最近一些年来,发达国家的许多研究机构利用各种方法对人类未来进行了许多研究,发现人类文明极大的、根本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世界在“今后20年将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将在2030年遭遇一场‘全面风暴'”,“激进”“巨变”即将来临。“今后40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最近的重大研究成果要算是2012年12月10日美国情报机构委员会组织发表的报告,报告称,在今后18年里将爆发剧烈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关键的节点上,这可能会通往‘截然不同的未来'”。如果这些预测大致是正确的,则文明大革命爆发的时间离我们很近了,早则十七八年,晚则二十七八年。
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应当是文化主义文明。人类以往的文明是以物质力量为主导的,信息社会正在把文明推向以文化力量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一次大革命(这些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在新的文明里,必将涌现出新的发展模式和新的观念,需要很多新的伟大的思想家。
托夫勒曾经说过,信息社会是以大学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大学一没有政府的施政权力,二没有企业的物质力量,那以什么力量来组织社会?没有别的可能性,大学只能通过新的思想探索从而引导社会的发展来组织社会。于是笔者相信,在信息社会以及未来的文明里,思想的探索便成为了大学的真正任务,思想家摇篮便成为大学的真正身份。
3.2034年的我的母校
这里已不再是人山人海的,为数不多的人围坐在一起,或相约散步,讨论着学术和思想问题,争论激烈,这里是2034年的定福庄传媒大学校区;这里是人山人海,数不清的有志之士聚拢在这里,同样讨论着学术和思想问题,争论激烈,这是2034年网上的虚拟的传媒大学。随着整个世界和整个中国一起起舞,从2014年到2034年间,传媒大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从广播学院到传媒大学,长期办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在2034年之前它选择了优势学科并根据时代的巨变对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攻思想家的培养。
文科的专业教育并没有扔掉,但是坚决地把它与思想家培养分离开来,课堂教学为主改变成实习教学为主,目标只是学习专业技能解决就业问题,大多数教师来自于媒介实际工作岗位,自己的教师主要进行组织工作和辅导教学。在20世纪60年代这所学校的新闻系推出过社会知识课和政策讲座课,就是这样实施教学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惜的是后来这些课程都没有继续开下去。这种专业教育大大压缩了时间,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只有少数教室还是老样子,大量的座椅和一个讲台;大多数的教室被隔成了许多小房间,里面有点像今天饭馆里的包间,或者小小的会议室,宿舍大多数也改造成这个样子。在这些小房间里总是有许多人讨论着学术和思想问题。
到这里来的学生是虚拟世界里的传媒大学学生中的佼佼者,酷爱思想的探讨。在虚拟大学里的讨论虽然已经有面对面的感觉,但还总是感到有些隔膜,一些同学久而久之就萌生了到定福庄这个实体的大学里会会老师和同学的想法。
这里的老师很少,他们在社会上都有许多兼职,有些在社会的思想库里兼职,其实学校里也是个思想库,思想库都是自发形成的。教师们的兴趣很广泛,爱好颇多。他们很少登上讲台讲课,而是先给同学提出问题,开列书目,请同学们阅读,然后再与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的结尾一般都是开放性的,没有唯一的结论。
校园里可以经常看到这样两条语录: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卡西尔
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量的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马克思
信息社会是由大学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托夫勒
这些语录在虚拟的传媒大学里也能看到。
在虚拟的校园里,你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曾经的广播学院和传媒大学,那座灰色的五层楼房,那所人流如海的和谁也说不清楚有多少专业和研究机构的五光十色的曾经的传媒大学,2034年的师生们并不难理解那座灰楼,但是他们很难理解曾经的传媒大学。在2034年的建校80周年之际,也许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校园里一边艰难地走着,一边摇着头说:
“连课都不上,都在侃大山,还算是大学吗?”
“我的老学兄,时代变了。”
4.乌托邦?
巨大的规模,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结构是工业社会的典型结构。信息社会正在向着小型化迅速离散。我们正处于急剧的空前的文明大变革的时代,未来的文明将根本不同于以往文明,人们必须而且完全可能从物质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地探讨和创造根本不同于以往的新思想,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精神创造之上将成为每一个人的必需。思想库将在社会里普遍建立,而大学将是最重要的思想库基地。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到2020年中国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次会议展现出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样的可能性:在2030年这个人类文明大革命的“历史关键的节点”到来的时候,使我们这个目前还相对落后的国家以最大的可能接近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任务非常艰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领导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能力,我们不知道他们可能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但是考虑到整个世界即将爆发空前的大革命,此时此刻笔者怀有伟大的希望。
于是我便想象到了2034年的传媒大学的如上,景象2034年是我的母校建校80周年,美国情报机构所指出的“截然不同的未来”的“历史关键的节点”定在2030年,80周年是在这个“历史关键的节点”之后的第4年。如果以上这个预测以及其他类似的预测能够基本实现的话,本文所描述的未来母校发展目标当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的乌托邦,而是一个有理想的有一定根据的乌托邦。未来全球的大变革将成为中国超高速发展的极为有力的推动力。这种乌托邦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积极的乌托邦,按照美国左派学者华勒斯坦的说法,是一种“有托之乡”。我想读者会耻笑我在痴人说梦,这就算是我的“中国梦”吧。
以上的那些关于未来二三十年世界将发生大变局的研究结论大多来自于学界,虽然这些研究是依靠电脑模拟做出的,或许可能仍被认为是乌托邦,但美国情报机构委员会的研究应当是非常讲究实际的。
我们面临的文明空前复杂和瞬息万变,并即将爆发空前的、疾风暴雨式的大变革。我们已有的经验来自于以往社会缓慢运行的阶段,仅凭我们的经验来观察现实和想象未来未必可行,而大型电脑模拟研究被证明可以比较全面地把握这种时代的巨变,对于那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即将到来的预测不可以仅仅当成科幻作品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了之。
刚刚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传媒大学提出了要将自身打造成为世界上知名的传媒大学的发展目标,既如此,就应当超越以往的专业主义追求、操作层面的追求,更必须跳出华而不实“发展”的巢穴,而进入思想探索的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传媒大学长期以来所处的系统环境、专业特点都使得超越自己特别困难,首先是人们的观念很难改变。也许2034年的传媒大学根本就不是这里所说的样子,甚至完全化为乌有。当然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实现这个乌托邦的任务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必然是一重大创新的过程,如同一切重大创新一样,必须拿出大勇气、大智慧来,必然会遭受到种种讽刺、打击和莫名的磨难,但是只有在这样的征途上才会有壮丽的风景可以欣赏。
乌托邦,有托之乡,应然,或然,对于本文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学术写作无论如何不能完全摆脱内心冥冥中的精神指向,谨以此文祝福母校的未来。(2004—2013.11.20)
(续完)
注释:
①②③ 爱因斯坦:《目标》,载许良英、刘明编:《爱因斯坦文录》(中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3;45-46;60页。
④⑤ [法]路易·多洛:《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2页。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张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