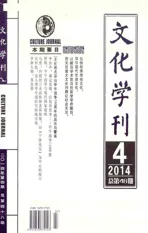读《满蒙古迹考》
2014-02-27纪晓晨
纪晓晨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某些有关中国的民族调查和考古发掘由外国学者开创先河,他们创造的学术财富为日后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素材。回溯人类学的东北研究,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贡献不可磨灭。鸟居龙藏被认为是日本研究东亚民族土俗及历史文化的先驱人物,他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均有建树。《满蒙古迹考》乃是他1927年第八次探查满蒙地区的概要,此书偏重于历史考古学,尤其侧重对渤海、辽、金三国的历史和遗物的研究。鸟居龙藏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翔实的学术资料,更重要的是树立了一种研究的典范。
一、简述鸟居龙藏的学术生涯
相较于书斋中的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学术源泉多来自于密集的海外调查。鸟居龙藏调查地域之广、领域之多、时间之久在当时的学者中无出其右。他田野研究的地域“包括千岛群岛与库页岛 (今俄罗斯)、朝鲜、满蒙 (中国东北、热河)、日本列岛、冲绳群岛、台湾及中国西南,可以说纵横环东亚地带,囊括中国文化圈自东北而西南的边缘地区。”[1]1895年到1900年,他多次来到台湾调查当地原住民的情况,并将研究所得撰写成民族志,这比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出版民族志还提前了十几年。1902年到1903年,他考察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也是他对台湾原住民研究的补充。“调查地区为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调查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等。他考察了诸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各族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事后编写了《苗族调查报告》和《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等著作。”[2]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本土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做过真正的田野调查。1905年后鸟居龙藏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东北地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日本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民族学的主要理论是进化论和传播论等,而日本殖民主义的扩张也是日本民族学发展的背景和条件。鸟居龙藏前往辽东半岛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结束,这个时期还处于军事上的紧张状态,他的田野调查是在日军的协助下进行的,考察地点主要选择在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他热衷于满蒙及朝鲜等地的研究还在于“这两个地区近年来状况改变得非常显著。因为这种理由,从过去继承到的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流失,这也就意味着,鸟居龙藏在这两个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是过去被继承的传统文化的最后时期,资料的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的。”[3]从 1895年首次踏入辽东半岛到1935年,鸟居龙藏先后在中国东北调查了九次,在蒙古调查了五次,在朝鲜调查了六次,这也是他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
二、鸟居龙藏与《满蒙古迹考》
鸟居龙藏撰写的考察报告和著作极多,《满蒙古迹考》充分地反映了他的研究风格,在实地考察中融入了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思考。《满蒙古迹考》一书共三十三章,由于章节偏多且每章篇幅长短不一,暂将内容归纳为四个部分:(一)回溯对于满蒙文化的研究轨迹;(二)满洲历史与现状;(三)记录沿途的考古发现,尤以渤海、辽、金三国的文化和遗物为重;(四)汉族在满洲的遗迹。此次调查鸟居龙藏从大连出发,考察地包括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析木城、普兰店等,其记录之周全、涉猎之广泛令人印象深刻。他在《满蒙古迹考》序言中写道“余之研究满蒙(或朝鲜),殆费半生心血矣”。[4]这位学者以其行为证明了此言不虚。
回顾鸟居龙藏的满蒙考察史要追溯到1895年,由于当时南满铁路没有建成,因此他通过步行加上车马的方式从柳树屯开始先后途径金州、旅顺、熊岳城、析木城、安东等地。这次关于高句丽和辽金等时代的调查令他收获颇丰,例如他在析木城发现了辽代的石棚和砖塔的遗迹,在熊岳城发现了石矛头,在貔子窝发现了石斧,在普兰店发现了汉砖,在金州见识到了古佛像雕刻等,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启发了他对于东北地区石器时代的研究。1905年鸟居龙藏关于普兰店锅底山的调查对满洲石器时代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价值,随后他又至奉天调查清宫殿宝物和萨满祭具,沿途测定满洲人的身体。他在楫安(今吉林集安)考察高句丽时代的陵墓和古碑,还在辽阳考察了砖塔和汉代砖墓,借此联系到汉代的辽东郡治。1905年至1907年,他开始了对东蒙古的探查,他学习蒙古语言文字,测定蒙古人的身体,过赤峰至锦州观辽代砖塔。1910年,鸟居龙藏在旅顺老铁山附近发现汉墓、砖墓、贝塚、土器、石短剑等遗迹,又在辽阳发现了石棺、砖棺、石槨,为满洲汉代的考古学研究建立了基础,随后在抚顺发现了金代的陶器。1911年鸟居龙藏调查了朝鲜咸镜道、满洲的延吉,在图们江发现了石穴,在龙井研究高句丽古坟群,在局子街观铜佛寺古碑考察石器时代遗址,在珲春调查古城和满洲人的土俗。1912年至1913年,鸟居龙藏在铁岭帽子山研究堡塞遗迹,又考察了在开原附近的石棚、辽金时代的石人,在柳河森林发现了女真文石碑。1919年,鸟居龙藏调查了东西伯利亚和北满洲。除了上述七次他又由朝鲜入满洲三四次,调查涉及朝鲜、东西伯利亚及满蒙的基本情况。
回溯满洲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通古斯民族。鸟居龙藏在《满蒙古迹考》中指出在汉族来到满洲之前这片土地的主人是通古斯民族,历史上的肃慎、扶馀、高句丽、靺鞨、渤海、女真等均属于通古斯民族。当通古斯民族居于满洲时,燕国人最先侵入此地并在辽东建立殖民地,以辽阳为中心,东扩至鸭绿江,鸟居龙藏也在当地发现了燕国人所使用的通货。在燕国巩固势力的同时,齐国侵入满洲南端,建立齐国的殖民地。燕国后为秦所灭,再待秦灭亡,汉代在此地设立辽东郡,触角又深入朝鲜西北部,在今黄海等地设乐浪郡。当时汉人也与日本人接触,日本自此开始引入汉族文化。汉在辽东和朝鲜得势之际,北方的高句丽崛起。高句丽是通古斯民族中扶馀的一支,后征服汉在满洲的殖民地。自此,高句丽久踞于朝鲜北部和满洲,其历史遗迹多现于此二地。高句丽后为唐与新罗国夹击所灭,其亡命者多逃于日本。此时,北部满洲同为通古斯民族的渤海王国兴起。渤海国与唐朝交往颇深并吸取了唐的文化,极力模仿唐的制度和文物,上流社会更是弥漫着唐朝文人喜好作诗的文人雅趣,因而渤海国重和平,少战争。除了引入汉族文化,它在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就与日本沟通交流,还与土耳其民族的突厥人有往来,文化程度较高。当渤海国统治满洲时,蒙古的契丹兴起,后灭渤海国建立辽国,控制满洲与东蒙一带。契丹人欣赏渤海文化,抓捕大量渤海人从事锻造、冶炼、造车等工作。辽之文化多受突厥、汉族、朝鲜的影响,军事与文化优势远强于渤海国。辽最终为女真征服,后者建立金国,满洲多见金之遗迹。
历史上满洲人最终灭明朝,进驻北京。由于中国地域辽阔难以统治,因此清廷便任命同族人加以治理,唯恐人数不足又远及松花江和黑龙江等地招致满人进入内地。如此一来满洲人深入内陆,他们原先的居住地遂成为无人劳作之地,而满洲人以此片土地为祖先之地不可侵犯为由禁止汉族人移居于此。山东由于当地人口众多,耕地有限等,因此早已秘密潜入此处采参、狩猎、伐木、造房,开垦者日益增多,待到满洲人发现大势已无可挽回时,不得已解除禁令。此后,越来越来的山东人和山西人移民此地,满洲也逐渐变为汉族的居住地。如鸟居龙藏所言,居住满洲者并非是以前居住在此的民族,而是近代由山东移民至此的汉族人,他探访的满洲实为汉族的满洲。
鸟居龙藏在书中尤为侧重对于渤海、辽、金三国的考古,他通过考察三国之上京来塑造对历史的想象。渤海之上京在宁安的南牡丹江畔,都城选址和形貌与唐的都城颇为相似。渤海古城坐落于巨大的玄武岩石之上,城墙先用土筑再以玄武岩石打造表面,由外部观看宛如石城,然而当时石块多被运往市街,早已看不到满墙的石砖。在城内北门附近的五层楼故址发现不少古瓦、古砖、铁盔等,鸟居龙藏发现此处的瓦片和西伯利亚某古城的瓦片相类似,颇为关注。古城的中心地在北门,南门处有寺院的遗迹,鸟居龙藏对王宫旧址的石礎和寺院旧址的石塔最为看重。他借助城内石礎、池沼、瓦片、寺院、佛像等遗迹来推测渤海国当时的情况。辽上京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城壁由土砖砌成,规模大,城门多。城内多建有宫殿和寺院,可见散落的瓦片、石臼等,城外建有砖塔。锦州、辽阳和铁岭等地的砖塔多为辽代寺院的遗址,可见辽上京昔日的盛大。鸟居龙藏又由上京发现的大日如来像得知辽在当时推行密教信仰。契丹人历来视萨满教为固定信仰,但由于与中国、朝鲜、渤海等国的接触输入了佛教,尤以密教最为重视。鸟居龙藏在辽阳与铁岭等地所见的砖塔皆为辽之遗物,可见当时佛教之盛行、艺术之发达。金上京则分为南北二城,北为古城,南为新城。金上京的城墙砌以土砖,待鸟居龙藏进城发现城内已不见皇宫、石塔、寺院等遗迹,古城内遗物多被运往他处。由发现的一对造车用的箪瓢型石可知当时盛行造车,此城出产的瓦片与渤海古城的瓦片完全不同,这也引起了鸟居龙藏的注意。金上京的城内常发掘出萨满教的铜人、瓦片、陶器破片、古钱等,此地出土甚多的古镜为萨满教巫师祭祀时所使用的腰镜,因此可知萨满教在当时的盛行。另外,此处又发现金属十字架,暗示了基督教传播的痕迹。
以鸟居龙藏看来,金不仅模仿汉族的文化还受到辽文化的影响,沿袭了辽在文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传统。相较于辽上京的盛大,金上京相形见绌,二者的文化高度可见一斑。鸟居龙藏在辽金时代的古城内探查瓦砖、陶器、古钱等物,对两代出产的鬼瓦最感兴趣。鬼瓦分为新旧两种,据此可知它的年代。旧瓦产于辽代具有辽代的特征且样式更佳,新瓦产于金代,但工艺却远不及辽代。此外,他发现辽代多砖塔,辽上京等多处建有大型砖塔,金上京则没有砖塔,此即辽文化更为繁盛的佐证之一。
满洲的历史脱离不开对汉族的书写,汉族在这片土地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鸟居龙藏记录的汉族在南满洲的遗迹大致可分为墓所和住所两类。墓所中留有形状功能各异的石棺、石槨、砖棺、贝壳棺等,由住所中发掘出的器物、钱币等遗物则可窥见当时的生活状态。古墓中的遗物更为丰富,如多种形态的兽镮、壶瓶、器皿、钵、椀、盆、鼎、登、炉、模造品、瓦当等土器和陶器,铜器类则有铜钵、铜镜、金具装饰物、首饰、腕环指环、插垂头、武器等。此外还记有玉制和玻璃制的装饰品、铁器、骨制玩具、朱及纸、古钱、人骨等遗物。鸟居龙藏通过对比不同地区的发掘物发现当时土器和瓦器的使用多于铜器,这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铜器为上流社会和宗教仪式所使用,普通百姓则使用木器土器等。他还认为“满洲之遗迹遗物绝非辽东所独有者,实当时广行于汉族间之一般风俗也。又可知此种遗迹遗物,不仅以上诸地有之,中国各省必皆有之。”[5]进而确定满洲的某些遗迹是汉族留下的。除了《满蒙古迹考》中所记载的考古成果,鸟居龙藏还陆续研究了辽代画像石、林西辽庆陵、医巫闾山东丹王陵等遗迹。
鸟居龙藏在《满蒙古迹考》中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他结合史料分析与实地调查的研究方式,借助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学科间的融合,多角度综合性地考察研究对象。书中对考古描绘的成分居多,内容扎实,注重细节,行文简洁流畅,相较于学术著作而言,本书田野游记的风格更盛。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工作规模较小而且研究主要侧重遗物的寻找和描述,作者并没有将研究内容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他更多的是如实地描述而没有透过对象论述其背后的一套社会组织与关系,其中的民族关系和宗教变迁等内容存在很深的挖掘空间。相较于史禄国注重田野调查和理论建构以及凌纯声侧重历史分析的治学方式,鸟居龙藏在理论提炼中略有欠缺,但本书的学术价值仍是不容忽视的。鸟居龙藏作为中国东北地区近代考古活动和民族志调查的拓荒者,反驳了当时世人皆以为满蒙之地无历史文化的论断。他通过长时间、多地域的实地调查收集到大量的一手资料,他的研究具有着实证主义的风格,这对当时推崇书斋研究的学术传统产生了极大的开创性和示范性,鼓励了更多学者转向田野。他的人类学研究渗入了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内容,虽然理论性较弱,但在彼时实属可贵,树立了独特的研究风格。
三、后记
由鸟居龙藏的考察可知人类学的东北研究开启时间并不迟于西南和东南,却鲜为后人关注,远没有达到后两者所获得的公认性的成果。相较于宗族之于东南、斗鸡之于巴厘岛等充满地方色彩的记录,东北似乎缺少能代表本地社会与文化的典型性描述。与已形成研究范式的地域相比,东北也具有特殊的历史内涵和地方性知识,同样具有研究潜力。东北这个词语本身就经历了多种变迁,最早传说在远古时代,舜帝册封天下十二座名山,位于医巫闾山以北的地方都称作东北,而这只是模糊的地理方向的概念。后远古中国被分为九州,东北划归到幽州境内,肃慎古国是东北地区最早的起源。在辽统一北方后,东北被看作为一个区域,从辽史中可以知晓在辽代东北已被引用为军政建制名称并广为使用。在金代,东北地区则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用东北取代清发祥地“满洲”,现今的东北则指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东部。东北的概念就是在历史中被不断改写,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社会的变迁得以体现,东北的地域独特性也越发彰显。人类学的东北研究离不开对东北历史脉络的梳理,尤其应重视鸟居龙藏、史禄国和凌纯声等中外学者的资料。研究民族志材料的对象需要联系其背后的历史条件,理清它与周遭对象的关系进而明确它在当下又被塑造成怎样的现实。
东北虽处于“边缘”却不是独立隔绝的,历史的沿袭、自身的因素与外界的接触共同塑造了东北的独特性和一般性,这个变动的过程也将持续存在。人类学的东北研究目前还未形式研究范式,而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需要借鉴中外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民族志材料,从中寻找到适合于本地区的研究取向。鸟居龙藏注重田野调查和历史考古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方向,例如他通过仪式器具来推测当时东北地区的宗教情况,从当时的交通状况联系到中日民间的交往等等。以《满蒙古迹考》中展现的东北为例,对比它与其他地域不难发现东北自身的历史轨迹与文化特性,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东北与外界的联系并明确它在整体中处于何等位置。鸟居龙藏作为“他者”具有跨文化的观察视角,为本土学者更深入地认识东北提供了新的角度。人类学的东北研究根植于学术史的回顾,对于民族志的运用须置于历史的脉络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寻找研究地方性知识的灵感。

泥模艺术——陈世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