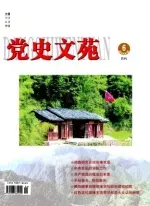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
2014-02-26■卜谷
■卜 谷
泥土会埋葬人与事,淡漠和遗忘也会埋葬人与事,但历史不会埋葬人与事。
——题记
她出生在江西瑞金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为生计所迫,19岁那年当了红军。她曾跟随原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打过游击,还当过原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苏区中央局军委)主席项英的机要员兼保姆;她曾不顾死活,在白军的枪口下为毛泽覃擦洗遗体;她“躲山”被捕枪决时,连遇3颗臭弹,大难不死,虎口余生;她“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出卖毛泽覃的叛徒,被荒唐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当日竟神奇遇赦;她嫁过5个男人,最终还是难逃守寡的命运;她独居深山,为毛泽覃守灵77年,可当墓地打开时,她看到的竟是一座空坟!
她就是中国最老的红军妹——张桂清,至今依然活着,103岁。
在苏区中央局军委工作三年结识了毛泽覃
顺着箬别溪走,溪流越来越大,河面越来越阔,就走到了江宽水阔的绵江,就走到了瑞金县城。
1931年初的绵江清澈见底,那一天上午,19岁的张桂清在绵江边为伤员洗绷带。当时,药品十分紧张,用过的绷带洗干净还要反复使用。岸上传来护士长的叫唤声,说医院的领导叫她立即回去。进到办公室,院长微笑着说的这句话,让她一下子懵了。
“你被选调到苏区中央局军委工作。”
由一个医院领导引领,经过数位哨兵盘问,张桂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进了那片叶茂蔽天的神秘所在。经过报告,他们跟着一位军人由侧门进入一幢灰色的屋宇,从此以后,张桂清就留在叶坪工作,担任时为军委主席的项英的保姆兼做些机要工作,帮助项英的妻子张亮,照顾他们的儿子——小狗。
在苏区中央局军委工作并不孤单,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有十几个女同志,其中有项英的妻子张亮、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毛泽覃的妻子贺怡,随后也认识了这些大姐的丈夫。
贺怡的丈夫毛泽覃也因工作、生活关系,经常出入军委驻地。那天,张桂清一边带着小狗一边支撑竹篙架晒衣服,贺怡与一青年军人路过,二人主动上前帮忙支撑竹篙架晒衣服。贺怡指着那个青年军人介绍,“他就是我的老公——毛泽覃”。
毛泽覃像所有正规军人遇到首长那样双脚“嘭”地一并,身体挺直,行了个很好看的举手礼,然后跨前一步伸出双手与张桂清握手。张桂清张皇失措,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伸出手去。
毛泽覃身材高大英俊,两眼炯炯有神,双手像两团火充满热力,紧紧地握住了张桂清刚才洗过衣物冰凉的双手,有一股电流迅速传遍张桂清全身。她觉得全身热流涌动,脸颊发烧发烫通红通红,许久许久都平静不下来。这一握,给张桂清留下了永远的印象。过去,虽然常见过别人握手,但还没有人与她握过手,而且是用两只手。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张桂清就这样认识了毛泽覃。以后,她每次看到毛泽覃都会想到那次握手,都会面红心跳不好意思,都会联想得很多很多。此后,无论他在哪里出现,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系在他身上。
清晨的樟树林,蒙蒙的,荡漾着浓浓淡淡乳白色雾气,雾气里飘浮着一股清爽的樟香。嘹亮的军号声,日日在雾气中回响,樟树林下是平敞开阔的操场。
张桂清每天在号音中起床,在号音中参加操练。渐渐地,张桂清融入了红军总部的生活之中。
随着越来越紧的枪声,项英夫妻俩决定,儿子小狗先送到群众家寄养。张桂清很茫然,张亮走了,小狗送人了,自己今后怎么办?部队还要不要自己,自己不带人又能干些什么呢?
张桂清清楚记得,“最后一次与贺怡见面也很突然。那天,我正带着小狗在屋檐下玩耍,一个戴着斗笠的人朝我们走过来,到了面前摘下斗笠突然唤我一声,竟是贺怡,更黑更瘦,我都有些不敢认了”。
贺怡是专门来向张桂清告辞的,拉着她的手说了很久的话,嘱咐今后一定会再相见。泪水伴着雨水,张桂清与贺怡相拥而泣,天上的雨越下越大。
贺怡与张桂清的这次告别以及告别时的嘱托,随着时间的久远,越来越清晰地铭刻在青年张桂清心里。张桂清是个实在的人,她记住了这些告别,也记住了与贺怡的友情。
张桂清为毛泽覃擦洗遗体
兵行如水,避高而趋下。红军主力离开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日益紧张。
张桂清没有随中央分局去于都南部的禾丰地区,她与张亮、小狗分手,即编入了毛泽覃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跟着毛泽覃一路向闽赣省突围。
那一段时间,白军占领、进攻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人心惶惶,加上日日奔走行军,吃喝拉撒都困难,更别说洗澡换衣服,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浓浓的味道。上级决定,疏散一些地方干部、老弱病残、妇女,以及不愿意留下的人,好几百人就迅速分散了。
张桂清也属于疏散人员,有点发蒙,不知道怎么办,回到屋里看见别人起身走了,也准备起身就走。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是毛泽覃匆匆过来。
“小张妹子,我抽空来送你一下。”毛泽覃还没站定就急急地说,“你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回去,以后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要把军装脱掉,不要让村里的人知道你当过红军;还要把辫子接长,不能让别人一看你就是苏干;你还要改过一个名字,以后说话要把普通话口音改掉,完全说本地话;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也要完全与本地村民一样;要很快和村民们熟悉,好成一家人,关键时候村民们就会出来保护你……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等红军主力回来时,我们都平平安安活着再见。”
“姐夫,我改一个什么名字好呢?”客家人很讲究取名字的,取得好,好一生,取得不好,不好一生。张桂清原名叫张爱兰,她觉得这个名字少了点什么,很希望毛泽覃为她改一个名字。
“就叫做张桂清吧,桂花的桂,清水的清。”毛泽覃不假思索,顺口就来了一个。
取名字很关键,按客家规矩被取名的人是要请酒的。张桂清请不起酒,她从箱子里掏出早已经准备好的一双布草鞋、一双袜底。那是一双相当结实的袜底,每只袜底上还用红丝线绣了一颗心,心的中间是一颗红五角星。她双手把袜底递给毛泽覃以表感激之情,声音因为激动而有点颤抖,说:“姐夫,你要长命百岁,打仗时要注意保护自己。”
毛泽覃接过草鞋、袜底,抬脚比量了一下,大小正合适。随口应答:“妹子,你放心,我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
开口一句话便说到平日最忌讳、却又不能不时常想到的那个“死”字。她的心颤抖了一下,还想说什么。那边有人在一连声地喊:“秘书长,毛秘书长——”分手在即,张桂清想与毛泽覃紧紧地握个手,可是毛泽覃伸出厚实的大手,拍了拍张桂清的肩膀掉头就走了。边走边大声说:“记住,等红军主力回来时,我们再见啊——”
毛泽覃远去的背影消失在绿树丛中。
“时时可死,步步求生。”张桂清咀嚼着这句话,一个人呆呆地站了许久。
天色突然转暗。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掏出一面小镜子对自己进行了简单的化装。根据毛泽覃讲的自我保护办法,她在剪短了的头发上接了两条长长的辫子。
天漏了一般,梅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寒侵入骨。
1935年4月的春雨是个慢性子,无休无止地下着,阴沉沉的云团遮蔽了日光、月光、星光,像在酝酿一个阴谋。
“砰”地一声屋门大开。几个白军士兵在保长的带领下闯入屋子,这伙白军一身泥泞却兴奋异常,个个大呼小叫,说是剿“匪”立了天大的功劳。要她立即动身去认尸,看打死的人是不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
张桂清心中一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腿脚抖得都迈不动步子。几个士兵特别凶,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推出房门,拽着她的胳膊行走如奔。
张桂清逐渐清醒过来,她不相信白军打得死毛泽覃,一定是白军搞错了。
小道十分泥泞,张桂清越走越快,走得比白军还快。总觉得心里不托底,她急于去看个究竟,一路飞溅的泥浆糊住了她的脚面、裤面。她浑身透湿,冰凉冰凉,一直冰凉到心底。
那一段时间,各路白军在军事上四面出击取得节节胜利,吹牛皮的事情也就层出不穷,有的白军部队胆子更大,为了报功,竟然敢到处宣扬说当场击毙了项英、陈毅,云云。为了搞清楚击毙的人是否真正的毛泽覃,进而邀功请赏,白军特意派人去抓张桂清来黄鳝口的白屋子认尸。
“那个,你仔细看看,是毛泽覃吗?”
尸体搁在白屋子屋场的大禾坪上。这是村民陈德宝、陈忠建的屋背,江声球的家门口。当时,白军的团部就设在村民陈忠建家中。围观的村民有邱达辉、陈德宝、陈忠建、江声球、邱世连等,还有一些妇女、孩子。尸体上缠着碧青的生长着绿叶的藤条,一道一道如绳索一样捆绑得结结实实,两根毛竹在藤条当中一穿,像本地抬野兽一样抬出大山的,一只光脚丫微微翘起来。
白军连长掏出手枪,将子弹上膛,枪口顶住张桂清的脑壳。
当她轻轻揩去那人脸庞上覆盖的厚厚血凝时,只见两眼仍睁着,黑亮的眼珠放着光。张桂清心里一咯噔,以为他还活着,惊叫了一声,过一会儿才确信,他真的死了。真是毛泽覃,还是生前那个高大、青春、潇洒的毛泽覃!她擦拭去他脖颈、手臂、脚裸上的泥污,脱下他脚上的布鞋。果然,鞋里垫着那双她亲手做的袜底,只是这双袜底已经完全被鲜血浸渍成黛红色。
她的心一抖,泪如泉涌,掺和着雨水,“吧嗒吧嗒”打落在毛泽覃苍白的脸庞上。
张桂清忘记了害怕,一下一下,用手轻轻地把毛泽覃微睁的眼睛合上,又使劲地将他脸上一层厚厚的硝烟锈痕揩去,把他嘴里的泥血洗抹掉,把头发上的草屑污泥污血清洗掉。
整理好衣领、衣袖,平静的毛泽覃犹如熟睡。张桂清开始为毛泽覃洗手,那是一双宽大、苍白、长着厚茧的手掌,这双手曾经非常有力,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和久久的温暖。
如今,这双大手就摆在面前,像睡梦中一样失去了力量,张桂清仔仔细细地擦洗着毛泽覃的双手,把每一道皱折、伤痕中的缝隙都擦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她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毛泽覃冰凉冰凉的双手。
一双女性的布满厚茧的小手,一双男性的骨骼嶙峋的大手;一双黝黑有力的小手似刚劲的藤索,一双白皙的大手似一团绵软的棉花。两双手久久地握着、握着,雨水冰凉冰凉,那双小手怎么也无法把热力传输给那双大手。
雨,竟意外地停了。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二次握手,也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握手……
张桂清的心在流血。
确定了年轻的尸体是毛泽覃后,白军连长和士兵们爆发出了一阵阵狂笑,相拽相拥着转身去喝庆功酒了。
白军拍下毛泽覃的遗像,用刺刀把他的头颅割了下来,送到县城去请赏,尔后将毛泽覃的无头尸体抛弃在竹林荒野中。
当天下午,张桂清见到中共地下党员邱达辉,说:“被打死的人,确实是毛主席的亲弟毛泽覃,我认得的……”邱的公开身份是伪保长。
张桂清说,当晚夜里,邱达辉、陈德宝(中共红林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等人悄悄聚合到张屋坪的荒野上,就地挖了一个坑,将毛泽覃的无头尸体秘密掩埋在一片竹林间(另一传说他的尸体埋在县城和尚坟,现已荡然无存)。那是一座平冢,无坟头,无碑石,无标志,大地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靖卫团逼全村人看她生小孩
重重叠叠的山脉,把一座座村庄挤压得很小很扁。白军的挤压如乳白色的浓雾,从山那边弥漫过来,密不透气。风声一日紧似一日。
张桂清第四个老公,是在躲山时乱撞“撞”到的。罗家和原是乡苏维埃团支部书记,才21岁,比张桂清小2岁,生得相当英俊,人也很精明,能跑能打,是游击队的主力成员。新来乍到的张桂清,躲山时常得到罗家和帮助,对他颇有好感。之后,两人结成夫妻,成了游击队中的第七对夫妇。
灭顶之灾祸,在一个清晨降临。
那是一个白雾茫茫的早晨,雾霭在阳光中渐渐消散。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游击队员,罗家和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性。在以往的斗争中,白军常利用清晨进行偷袭,他在游击队里也就养成了清晨早起转移、隐蔽的习惯。
可就在此时,村前突然传来几声犬吠,靖卫团的部队趁着山岚包围了村子,直向罗家和、张桂清的住所扑来。
白军在屋子里外搜索了几遍,开始折磨张桂清。
“你,你是交待还是看着你老婆去死!”白军排长踢了罗家和一脚,喝问道。
那排长并不是在吓唬人,也不多啰唆,转头向一白军发出命令:“立刻先把这个女人枪毙掉!”可连开3枪,竟都是臭弹。
白军排长叫两个士兵把张桂清拖起来,那个执行枪毙的士兵不服,走过去粗鲁地掀开她的衣服看,张桂清的肚子已经很凸,显然是怀着孩子。
“难怪,这是个大肚婆呀,枪杀大肚婆天理不容,难怪枪里面尽是臭弹。”
那两个扶起张桂清的白军说道,你的命真的蛮大,以后会蛮有福气。
白军排长是个职业军人,他很生气,从地上捡起那白军扔掉的步枪。“这枪打不死大肚子,一般人也打不死?!”说着,把枪口一抬胡乱对着张桂清的丈夫罗家和就扣动板机。
“砰”的一声,一股鲜血溅了排长一身一脸。臭弹竟然不臭了,所有的人吓了一跳,白军排长更是惊得半晌开不得声,众白军好似碰到了鬼,一个个面色大变,惊慌失措。
“呸呸,霉时倒运,霉时倒运!”色厉内荏的白军排长抹了一把脸,手上全是热腥热腥的血水,胸襟处湿漉漉一大片血浆。
笃信风水的靖卫团团长欧阳光想到了一个最阴险的计谋。
孕妇不是很凶煞么,那好,他要让全村人来亲眼看张桂清生小孩,让全村人来分解孕婆子的晦气、凶煞气,那么孕婆子的晦气、凶煞气不攻自灭。另外,这棵大檫树不是神树么,就让神树来煞煞张桂清,也让张桂清的晦气、凶煞气来煞煞神树的神气。
几遍锣响,胡竹段村的男女老少都被召集在神树前的大坪上。张桂清被架着经过乌压压的人群,她有点奇怪,难道要开会,要被当众拷打?
正狐疑间,几个士兵上前,当众去扒她的上衣,她紧紧地护住衣服,左挡右遮,衣服一块块撕成片片落在地上,她的上身露了出来。
“大家快看呀,你们知道她是谁吧,她就是你们胡竹段村人,罗家和的老婆,上三乡有名的美女……”
张桂清不停地咒骂着,拽紧裤腰。白军淫笑着又扒她的裤子。她又踢又咬,双手死死地抓住裤腰不松手。不料一个白军绕到她身后,抽出刺刀插入裤内,用力一割,只听得“嘶”的一声,裤带断了,裤子连裆到裤脚割裂;又一刺刀下去,另一只裤腿也被割裂。张桂清拽在手里的只有一块破布,雪白的下身全部裸露无遗。
众目睽睽之下,几个白军开始往张桂清身上一道一道勒绳子,越勒越紧的绳索,把她高高凸起的大肚子勒逼得明显瘪下,这是最野蛮的人工坠胎。
一阵一阵的疼痛从腹部向全身发散。这时,张桂清明白了敌人的用意,是要害自己,害自己的孩子。在大庭广众面前,全裸的张桂清疼痛得厉声尖叫,拼命挣扎,直到晕死过去。
大坪前一条清鳞鳞的小溪,都是冰凉冰凉的山泉,白军拎了一桶溪水,哗地从头到脚泼在她身上,张桂清又从昏迷中冻醒。
白军实施的人工坠胎继续进行,张桂清无力地咒骂着。道道绳索越勒越往下,大肚子越勒越小,腹部绞痛,连呼吸都相当困难,猛然,她感觉巨痛袭来,胯下一热,大小便失禁。她又昏死过去。
突然,一个紫红的胎儿顺着血路掉在了地上。
张桂清第五次嫁人
整不死的人,怎么也整不死,整不死就还要往死里整。
1937年冬,周身伤痕累累的张桂清被抬进县城的大牢。第二天,她便奇迹般地坐了起来,看着身边那个刚出生的孩子,一声不吭,一动不动,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冰凉冰凉没有一丝热气,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也不知道活过没有。
为了惩罚张桂清,靖卫团团长欧阳光叫狱卒给她带上手铐脚镣,拴在牢房的柱子上,一天到晚不能动弹。
不能动弹的张桂清把屎尿都屙在身上地上,一时间,身上地上到处黏糊糊的,臭气薰天。
几天过去,张桂清天天不进食,下身还不停地流血水,可她硬是捱着、撑着、挣扎着,奄奄一息就是不肯死。屋子里生出的苍蝇乌云般地飞来飞去,管牢房的牢头办公桌和厨房灶台上也爬着蛆虫。
狱卒和其他犯人都忍受不住,于是,奄奄一息的张桂清被抬走了,慢慢地,她竟回过阳来。
终于回家了,张桂清回到魂牵梦萦的娘家。不久后她又成亲了,第五任丈夫名叫邱汉华,是一名红军伤残兵,但基本生活还是勉强能够自理。
结婚是一种奇怪的结合,要么捡到一个包袱自己背着,要么自己是个包袱让别人背着。这回,张桂清是捡到了一个大大的包袱。
张桂清并不孤寂。长长的回忆,也是一种生存方式。面对青冢土堆,张桂清偶尔也带上珍藏着的那双袜底——毛泽覃牺牲时穿着的那双袜底。
不知不觉中,张桂清已经生育了一子一女,埋头一心过她的苦日子。
1956年底的一天,邱汉华的咳嗽突然加重,开始发烧,嘴唇都干裂了,晕晕地睁不开眼睛。这不是过去常患的小毛病,邱汉华第二天便撒手人寰。刚刚才过了几年宽松日子,从此张桂清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要养活儿子邱世机,张桂清必须一边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一边帮别人接生挣工分,白天晚上不停地忙碌。可别小看接生这活计,她每次都能带回来几个鸡蛋,关键时刻还能靠这几个鸡蛋换点活命钱。
解放初,张桂清担任过短暂的村干——妇女主任,不久被派到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学习,主要是学习接生。久而久之,这一村子的人和四周许多村子的人都是她接的生。
张桂清是出卖毛泽覃的“叛徒”?
张桂清的命运再次逆转。
“四类分子”邱锤子向大队书记揭发:张桂清是个假老同志,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嫡亲老弟毛泽覃就是她出卖的!
石破天惊,如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整座红林山震动了,整个安治公社乃至整个瑞金县震惊了。过去,人们只风闻毛泽覃牺牲在瑞金,却不知道他具体牺牲在哪里,更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牺牲的。
这句话,像被点燃的山火遇着了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力,迅速越过安治公社,在整个瑞金县蔓延开来。像蚯蚓一样,她被人从地底下掘出来了。
主席的胞弟毛泽覃被叛徒出卖致死,叛徒的踪迹已经暴露,可能是一个女人……
身边一个简单的女人,立即成了一个复杂的谜团。这重大消息如重磅炸弹,炸弹的碎屑、碎片纷纷扬扬,散落处无不高度紧张,无不非常重视。不久,就成立了由省、地、县、公社、大队五级革命委员会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全称为“瑞金县毛泽覃同志牺牲情况专案调查组”,后来,也简称为“县毛泽覃烈士专案组”。细致缜密的调查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都是那时的口号与行动。
瑞金县各级革命组织,纷纷对“四类分子”做出革命的宣判,经常批斗来批斗去真麻烦,他们决定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让这个世界纯洁。
选来选去,决定处以极刑的3人是:张桂清、邱锤子、邱青山。
1968年9月25日上午,是张桂清、邱青山、邱锤子被处以死刑的日子。
在一片惊愕的目光中,吆喝声、狗吠声渐次传来,一群男男女女武装基干民兵成散兵状,将三名死刑犯以及五六名陪斩者五花大绑押赴刑场。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叛徒”,张桂清走在队伍最前面。“时时可死,步步求生。”数十年前毛泽覃的话似乎在耳边响起……
对于死,张桂清一点也不害怕,她知道,无论怎样,反正结果都一样。
在赴死的路上被推搡前行,张桂清想站稳一点,她的双腿膝盖后部遭到猛烈撞击,“扑通”一声,重重地跌跪在地上。
“扑通”“扑通”——
接连两声,另两个死刑犯也先后跪下,三个人一字儿排开跪在地上。张桂清跪在中间,左边跪着邱青山,右边跪着邱锤子。
突然,整座山场寂静了,寂静得没有一丝一毫声音。张桂清的头被按下垂,脸庞几乎贴着地面,她看见,离脸面很近的地面上,几只蚂蚁在匆匆爬行,就像几个士兵在匆匆行走……
“泽覃,保佑我。”张桂清像在对蚂蚁说话,“我来和你们一起做伴了。”
“砰——砰——”两声枪响,滚烫滚烫的鲜溅了张桂清一身。
她突然感到奇怪,自己应该是已经死了,怎么还会有知觉呢?接着,她完全清醒了,知道今天是来陪斩,明天才是自己的死期。
张桂清觉得是毛泽覃在冥冥之中显灵,保佑了自己。
这样,张桂清又多活了一天,一天就是一世。
红林大队的杀人行动,是从张桂清等三人赴刑场开始,也是从张桂清这里被制止。
“就是要 ‘立即执行’我的那天,”幸存者张桂清说,“中央来了 ‘公示’传达到村里,说是不可以杀人了,谁还要杀人就要追究杀人者的责任。”
中央的“公示”下来后,大规模乱杀人的行为暂时被制止了。
陪斩那一夜,张桂清身上沾着许多别人的血污,昏昏沉沉被架回牛棚,第二天被立即释放。
回到家中的张桂清终于透了一口大气,在她看来,冥冥之中,是毛泽覃在关键时刻保佑着自己。
出卖毛泽覃的“叛徒”奇迹般解脱
专案组的足迹遍及湖南三湘四水、城乡村野、工厂街道,调查工作十分辛苦,进展也十分喜人。
结合毛泽覃战友蓝盎子的回忆、红军战士何富庆的叙述以及汤济南一干人的回忆,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黄埂窝纸寮战斗情节链:毛泽覃确实是在黄埂窝纸寮战斗中牺牲,整个战斗就是一个时间短促的遭遇战,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叛徒。
为什么一定要有叛徒呢?这也许原本就是一场没有叛徒的战斗。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逐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张桂清是清白的,毛泽覃的牺牲与她并无干系。
几多波澜,几经曲折,一场围绕着张桂清是叛徒的漫长调查,从起点到终点,转了一个360度的大圈又回到起点。调查的事传播得迅速而又广泛。由于民情风俗的禁忌,尽管周围的人大都知道调查一事,唯独被调查人张桂清,却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知情。风风雨雨,峰回路转,全部屏蔽。
这样最好。
毛泽覃的坟茔竟是一座空坟?
晨星淡淡,张桂清的心有点莫名的忐忑。
张桂清早早地守候在晨风里。听说,要新建毛泽覃的陵墓,动工那天,她有些魂不守舍。其实,不需要来那么早,来那么早也没用,但她睡不着,还是来了。来看究竟的人很多,村民、村领导、乡领导,对所有的人,这都是个谜。
市里有关部门的领导陆续来了,正式的仪式开始了。
众人的眼睛都盯着那片青冢土堆,泥土里,不知道会有什么。
飞舞的锄头在掀开红土,也在掀动历史。
张桂清守望了77年的那堆红土被掘开了,还冒着一丝丝热气!
张桂清情不自禁,双脚一下往前挪动了几步,她要急于看清,那坟墓里到底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可张桂清看见的,却是一片红土!她的心砰砰直跳,再定睛一看,眼前的确是一片实实在在纯净的红土。“挖呀,再往下面挖呀!”挥动的锄头终于停止。她双膝一软跪倒在那掬松软的红土上,不甘心地用双手挖掘起来。可是,红土里面还是红土,红土的深处仍然是红土,除了血一般的红土,什么也没有!
张桂清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十指仍深深地抠在红土地中。泪水汩汩流淌,洒落在这片不知吸吮过自己多少泪水的红土上。莫非,自己忠贞不渝厮守了77年的毛泽覃的墓地,就是一片红土——一座空穴!?
一片红土——一座空穴,意味着什么?
77个春秋,耗在这块土地上。空穴是否是空守,不空穴就是不空守?值得,还是不值得?
三枚未燃尽的檀香,徐徐冒着青烟。张桂清望着红土,泪流满面地喃喃自语:怎么回事,我晓得你一直都在这里躺着,一直都在保佑我。可是,你难道不是躺在这里吗?
“噼噼啪啪——”迁坟的仪式照常进行,纷飞的鞭炮纸屑在天空飞舞,渐渐归于平静。
纷飞的思绪停不下来,一遍一遍,张桂清在梳理对这青冢红土堆的记忆。当初,说的是在这一大片竹林里,这一大片竹林是怎么慢慢地缩小,缩成了这一小掬土堆,又变成的空穴呢……她的心被掏空了。
像被雷击了一般,突然间,张桂清老年痴呆的症状就明显起来,记忆链的断裂使人迷茫异常,她有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有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而另一些记忆链则无比顽固地连接着,她盲目地走着,绕来绕去,又会走到那片坟地。她听不见别人说话,也不与人说话,但她会自言自语:毛泽覃、贺怡……完全沉浸于一个自我的世界。
张桂清深深意识到,他的灵魂已经溶入这片大山、这片红林,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一生一世,她的心不变,情亦不变。
山野之风,热烘烘地拂过她的心田。张桂清镇静不下来,却似窄小幽深的箬溪水般澄澈、坦然、无奈,一个百岁女人的坦然和无奈。
青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度过了战争,度过了“文革”,度过了艰辛,度过了平淡,度过了5次婚姻,度过了102个春秋……她诚实地活着。这个世界,不能只有诚实,除了诚实之外,还得有点防范,否则你就无法也无权诚实。
年届103,张桂清生活圈子原本很小,如今更加缩小,自己的生命除了与活在周边的几个人有关、与死在周边的几个人有关之外,与所有别的人都无关。张桂清已经很苍老而恬淡了,布满了折皱与黑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曾经黑亮黑亮的眸子,掺杂着几重重翳蒙。才几月不见,她的反应也变得更加迟钝,更加深地进入了老年痴呆状态,她的记忆一片模糊,或者说是更加专注。但是,她眼睛里面仍有一种忧郁,一种意外的平静,那是看透了人生才有的忧郁和平静。
山很深,林很密,冷风热风在山林间滑翔,在一个百岁女人的指缝间悄悄地走过,不知来自哪里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