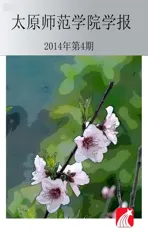张爱玲“红遍上海滩”的原因探析
——从传播的角度
2014-02-12任卉
任 卉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张爱玲“红遍上海滩”的原因探析
——从传播的角度
任 卉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1943年到1945年,张爱玲“红遍上海滩”,她的传奇固然依靠其文学创作,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赢得盛名绝离不开她“生逢其时”和报刊媒体的“推波助澜”。从传播的角度探讨张爱玲“红遍上海滩”的原因,还原当时历史语境,无疑对客观评判其文学史地位有很大裨益。
张爱玲;上海滩;媒体;传播
1943年到1945年,张爱玲“红遍上海滩”。张爱玲的成名,一方面依靠她的文学创作,其作品的独特风格与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赢得如此盛名,决不能忽视文学创作之外的传播环境的造就与大众媒体的宣传辅助作用。正是这些文学内外因素的通力合作使张爱玲的名声越来越大,造就了张爱玲“红遍上海滩”的传奇。
一、时势造英雄
张爱玲的到来可谓是“顺应天时”的,她没有出现在众声喧哗的20世纪30年代文坛,错过了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丁玲、张恨水等作家同台竞争的机会。抗战爆发后,大批作家纷纷离开上海奔赴内地,虽然仍有少数文学前辈滞留上海,但大多隐姓埋名,很少从事写作,于是上海文坛出现了百花凋零的景象。而当时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1942年3月《古今》创刊,1942年8月《杂志》复刊,1943年4月《风雨谈》创刊、《紫罗兰》复刊等一系列文学刊物的创刊和复刊,既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粉饰太平的政治需要,又是在战争和政治的双重高压下,人们到文学领域中寻找精神慰藉的需要。当战争不能给人以希望,政治不能再引起人们的兴趣,只有风雨中的文学与艺术,备受深感人间苦味的人们欢迎。也正是上海的一片死寂,张爱玲应时而出。
而此时与张爱玲“争夺”文学资源的有:以周瘦鹃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以陶亢德为代表的带有汪伪政治背景的“《古今》派”、以柯灵为代表的“《万象》派”作家等。鸳鸯蝴蝶派作家风头早已不在;《古今》派作家延续论语派风格,偏重随笔小品、文史掌故,难现论语派昔日辉煌;柯灵为代表的《万象》派作家继承了新文学的战斗传统,但在日寇的统治之下言论的不自由甚至生命的威胁必然限制了其创作。在与这些作家的竞争中,张爱玲在群雄逐鹿中技压群雄,可谓是“时势造英雄”。
二、迎合市民读者口味
一个作家是否能成名,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读者买不买他的账。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不行,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读者兴趣范围的限制。沦陷时期的上海,惶惑、惊恐困扰着市民阶层,战争一方面催发了他们对英雄的渴望与期待,所以颂扬民族英雄的抗战文学成为时代主流;另一方面,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生存压力和生命威胁使广大市民陷入对世俗生活的留恋和迷恋之中,人们试图在对世俗生活的体验中消解对未来的恐惧和现实的苦闷。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无疑给当时的上海市民读者带来某种排解与安慰。
张爱玲从一开始走向创作就将自己定位于上海市民身份:“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并反复强调“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她常自居为小市民,说“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1]195而张爱玲的散文也让我们看到她对于世俗生活的描绘和喜爱,不厌其烦地描摹那些俗得不能再俗的市井凡人、家常细事,谈吃、谈穿、谈钱、谈女人、谈自己的生活。纵观她的散文,到处是对俗人俗事、俗欲俗趣的描绘。张爱玲不但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带有浓重的世俗化倾向,她甚至将这种世俗化融于学理之中,在谈及京戏、服饰、姓名、绘画、舞蹈、音乐、诗歌、宗教、道德伦理,这些形而下或形而上的话题时,她也无一不用很世俗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把张爱玲当作“传奇”的同时,又觉得她是“懂我们”的。于是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大多都得到了读者的“欢心”,也造成了她作品的畅销,名声的远扬。
三、独具“生意眼”的作品营销
张爱玲的“爆红”离不开她在短时间内迅速“占领”当时上海的多家大型杂志媒体,使得她刚一“出场”就牢牢抓住了大众的眼球,成为镁光灯下的焦点。当然这绝离不开她对自身及其作品独具“生意眼”的“营销”策略。
张爱玲自视甚高,初来乍到便有着比一般人更强烈的成名欲望,也正是这欲望使她在处理自己的作品时倍加谨慎,通常作家发稿都是采用投稿方式,但张爱玲大胆地毛遂自荐,上门推销自己的作品。1943年初春,她经亲戚黄岳渊引荐拜访了鸳鸯蝴蝶派刊物《紫罗兰》主编周瘦鹃。5月,《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复刊号上登载。6月,《沉香屑:第二炉香》在《紫罗兰》月刊上发表。接着,她自己一个人到《万象》杂志社向素不相识的主编柯灵推销小说《心经》。此后的影响力逐步加大,张爱玲的稿件自然不愁发表。由此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张爱玲“上门推销”,使她的作品很快在《紫罗兰》上“露面”,其人其作未必能被更多的编辑所认识。后来她还与《杂志》、《天地》等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使其作品发表得更加快捷顺利。
而张爱玲除了“果敢”的“胆色”,还具有敏锐的“生意眼”。据当时的读者介绍:“张爱玲的《传奇》出版了,每本是亲笔签名、赠送照片。”据说当时有人买来一本《传奇》,研究照片签字后便“金屋藏娇”似的,陈列在书架上,朋友问:你不看为什么买?答:这是刚出版的,我要陈列。[2]7可见张爱玲的照片及签名作品俨然成了一种收藏。在艺术价值之外,商业价值不能小觑。而张爱玲也从不掩饰她对钱的看重,多次与平襟亚谈论“怎样可以有把握风行一时,怎样可以多抽版税”,要求平襟亚“我包销一万册或八千册,版税最好先抽,一次预付”[3]8。总之,在张爱玲对自己作品的自信之外,宣传营销也是其在短时间内取得傲人成绩的原因。
四、媒体“东风”送上位
在张爱玲八面玲珑、四面出击推销其作品时,新闻媒体的强势包装和力捧可以说是其成功上位的“东风”。
在帮助张爱玲成名乃至“红遍上海滩”的众多刊物中,出力最多的就是《杂志》。《杂志》的后台是日本人驻沪领事馆。所以,后台强硬使其能够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其实力远非其他文学杂志可比。纵观张爱玲的创作史,与《杂志》的合作将近持续了三年,其间大量的小说、散文发表于此。此外,《杂志》还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和社会资源,使张爱玲成为焦点新闻人物。比如,1943年8月,朝鲜女舞蹈家崔承禧二次来沪,张爱玲出席欢迎会。1944年3月,《杂志》主持召开女作家座谈会,张爱玲出席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苏青、潘柳黛、关露等。1945年7月,《杂志》召开纳凉晚会,邀请张爱玲与日本电影女明星李香兰、多名日本军人以及汪伪政府文人等出席。
《天地》的主编苏青与张爱玲私交甚好,因此也为她不遗余力地宣传。自1943年11月小说《封锁》在《天地》月刊第2期发表,张爱玲的稿件几乎伴随着《天地》的始终。在《天地》出版的21期中,只有3期没有张爱玲的作品。不仅如此,她还给《天地》绘插图、作封面设计,显示出她对这份刊物极大的兴趣。除了刊发张爱玲的作品,苏青还为张爱玲的作品大做广告,加以推荐,并促成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情,在编辑活动中为其二人“同台”提供机会。在《天地》第10期,张爱玲的《私语》与胡兰成的《随笔六则》同时刊出。第11期,张爱玲的《中国人的宗教》(上)与胡兰成的《乱世文谈》前后刊出。在第21期上,还刊出了胡兰成以“胡览乘”为署名的《张爱玲与左派》。
与《杂志》和《天地》一致地对张爱玲赞美不同,《万象》与张爱玲之间可以说是“爱恨情仇”。一方面《万象》对张爱玲很赏识,在其初登文坛时,给予张爱玲很大的帮助,小说《心经》和《琉璃瓦》都是在《万象》上发表的。另一方面,1944年7月张爱玲因《连环套》的连载中断和小说作品集由《杂志》出版发行,引发《万象》老板平襟亚的不满,“怪罪”张爱玲不“知恩图报”。8月18日、19日,平襟亚署名秋翁在《海报》上发表《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对张爱玲在稿酬上的“生意眼”大肆鞭挞。而张爱玲也于1945年1月在《语林》上发表《不得不说的废话》予以回击。此事件过后,张爱玲与《万象》就再无合作。不过这件纠纷带来不快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引发了大众对张爱玲更多的关注。所以,《万象》对张爱玲初期的力捧和后期的指责在某种程度上帮了她。
五、个人“传奇”的传播
张爱玲曾说,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张爱玲虽熟悉而且警惕,然而却抵挡不住人们对她或她对自己传奇叙事的诱惑。不可否认她个人的传奇经历为其名声远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张爱玲自己也是深谙其道。
一方面,主动“炫耀”贵族出身。1944年6月15日,张爱玲为联系作品集的出版,在写给平襟亚的信中谈到了书的促销方式:“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的祖父和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说的人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气氛的’……”[4]36我们可以感受张爱玲的贵族出身在社会产生的效果——在美化张爱玲的同时,更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刺激读者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关注,更好地“推销”作品。大致和现代社会的“炒作”类似,可见张爱玲独到的生意眼光和敏锐洞察力。
另一方面,演绎“倾城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情直到现在都被人津津乐道,构成了“说不尽的张爱玲”的一部分。张爱玲的文化身份与胡兰成的政治身份都为这段恋情招致了更多的非议和奇观。而在当时,恋情一经发现,就立刻成为众小报争相报道的八卦新闻。“绯闻”的传播,吸引了更多普通受众的眼球。而小报上对于胡、张二人恋情的大肆渲染,胡兰成通过发表文章对张爱玲的热捧,苏青在《天地》为其夫妻二人同台唱戏提供平台,这些信息的传播在演绎二人倾城之恋传奇故事的同时,也在宣扬着张爱玲的名字,使其走下文学神坛,进入平民百姓家。
六、结语
从作家作品的传播过程来看,作家作品作为传播内容只是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传播的效果固然受到传播内容的根本制约,但是传播的接受对象以及传播过程所处的文学场对传播的效果都有着明显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沦陷的上海孤岛使得张爱玲在特定的背景下实现了其作品的价值。如果她错过了上海沦陷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她的作品参与抗战以后的文学活动,作品虽然还是那个作品,但环境变了,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受众群体也必然发生变化,到那时张爱玲要想“红遍上海滩”可谓是遥不可及的痴人说梦,所以,张爱玲在40年代的沦陷区上海红极一时也成为了特定年代背景下实现个人价值的成功案例。这也说明了诸多文学史并没有把张爱玲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的原因,因为走出40年代的上海很难判断其地位,这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缺陷。
[1]张爱玲.张爱玲散文集(六)[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文海犁.《传奇》印象[J].力报,1944(8).
[3]秋翁.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J].海报,1944(8).
[4]谢其章.《光华》中的“张爱玲手札”[G]//创刊号剪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672-2035(2014)04-0095-03
I206.6
A
2014-03-05
任 卉(1990-),女,河北廊坊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责任编辑 冯自变】